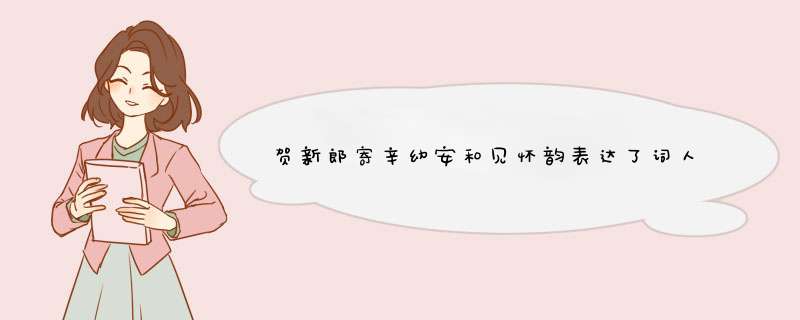
3月初,我在图书馆第一次翻开这本书。图书馆开了空调,热气蒙蒙地,罩住了我的眼睛。
我在昏昏沉沉中翻开第一页,是白先勇先生和友人王国祥的一张肖像,郑重地,煞有介事地摆在面前。我虽看过《一把青》,对白先勇这个名字不算陌生,但却并不知悉他的长相。白先勇是白崇禧将军之子,因此左边那位拘束些、姿态端着些的应该是白先勇吧。百度一看,果然没错。
《树犹如此》是一篇盛赞颇多的散文,点开豆瓣知乎,甚至是微博小红书一类的社交平台,被感动至深的人都不在少数。豆瓣给这本散文集的评分是85,我想,若将《树犹如此》这篇单拎出来,评分95也不为过。我原以为是一篇普通的叙事散文,看到副标题时才察觉不对,“纪念亡友王国祥君”,这竟是一篇悼文。霎时间脑子也清醒了,坐直了身子,开始拜读。
38年相识相伴:缘在人在,缘亡人亡
1954年,白先勇和王国祥在同一所中学读高二,初识并结为好友后,二人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
高中毕业,白先勇梦想去长江三峡筑水坝,便申请保送成大的水利系。王国祥随着他投考成大电机系。
大学读了一年,他们发觉志向均不在本专业,便双双考去台大。白先勇在台大念外文系,王国祥开始研究理论物理。
原本兜兜转转终于安定,王国祥在此时却被诊断出“再生不良性贫血”,这种罕见的贫血症会影响骨髓的造血机能,治愈率也仅有5%。那时白先勇能做的,就是陪伴着王国祥,给予他精神支持。他常常在台大下课后,骑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王国祥。也许是缘分还在,王国祥遇到了救星,江南的一位中医奚复一大夫。西医束手无策之时,确确实实是奚大夫的药方让王国祥一天天好转。药方中有一味“犀牛角”,后白先勇回忆起去加州圣地亚哥动物园参观的经历,对犀牛那种看起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生出无限好感,只因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
缘分未灭,二人出国深造,白先勇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任教,王国祥在宾州州大做博士后。1973年白先勇在“隐谷”(Hidden Valley)买下一处住宅,“三面环山,林木幽深“。这年夏天,王国祥来圣芭芭拉帮忙整顿这处园子花草,他们胼首胝足,一起做园艺、啜杏子酒、啖牛血李、蒸螃蟹,日子过得潇洒快活,人生前途无限光明。隐谷的园子里种满了白先勇钟爱的茶花,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按王国祥的提议,种下了三棵意大利柏树(Italian CyPress)。
十年过去,三棵意大利柏树抽发地傲视群伦,王国祥也数度转换工作,从柏克莱物理系毕业后从事博士后研究,兜兜转转放弃了物理,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
1989年,三棵柏树中间的那一棵无故焦亡,白先勇无奈将其砍掉拖走,后院便出现了一道难以弥补的缺口。而就在这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了。这病来势汹汹,奚大夫的药方也不再管用,白先勇辗转多地访名医,上海、石家庄、杭州……无论是气功还是草药,就像白先勇写的,“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得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8月13日黄昏,缘分尽了。王国祥离世。“霎那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
38年的岁月,白先勇和王国祥相知相伴,王的天性善良,不懂虚伪,二人性格互补,祸福同当。年轻的时候,人们总以为同心协力就能抵御世间万难,可与病魔死神的搏斗中,无论再全力以赴,终将一败涂地。
笔触动人:真实细节,引发共情
关于散文,周立波在其主编的《散文特写选》序言中, 便写下一段颇具权威的话:“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绝对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树犹如此》全文一万一千多字,从隐谷栽树,到挚友爱人离世,再到蓦然回首17岁初识,用词用语再诚挚简单不过,但大量微妙自然的细节却让这篇散文显得如此动人。
他写自己陪王国祥去医院输血,“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在反映着冷冷的青光。” 生过大病的人也许能感同身受。我一直觉得医院是令人非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救病人于水火,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在病痛的折磨下毫无尊严地死去。玻璃门窗泛着的冷冷的青光也代表着客观物质世界对主观生命意识的无动于衷。
他写自己在大陆没有求到药的心境,“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对爱人的愧疚跃然纸上。
他写王国祥送自己离开的场景,“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竞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
这些小细节,经历过生活苦难、亲友分离的人想必是能立马被勾起回忆的。也正是这些真实的小细节,让读者和作者同悲同喜。细想来,和朱自清的”父亲的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真实,所以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影像,勾勒出的影像自然比文字更能引发共情。白先勇曾言,他“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
尽管文中将王国祥称为挚友而非爱人,但阮桃园评《树犹如此》,“那绷在凝敛的声调里的情感几乎是要溢到外头来了…马上猜得到那背后的深情。”
分享我挚爱的一段: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白先勇的生死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出自《世说新语》(上卷言语第二)“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在这篇散文中,白先勇的生死观很明确:人在命运面前是脆弱的,而这一点没有超越《红楼梦》的悲剧哲学。基于这样的生死观,在写作中他将人生与草木相联系。花园的意大利柏树枯亡与王国祥的病逝客观上没什么联系,但白先勇将两者放在一起写,以树喻人,树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当王国祥去世后,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的空白便成了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白先勇写自己“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也许是在安慰自己,命运如此,人的作用有限,但却对自己当初没有尝试气功而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1992年王国祥病逝,1998年白先勇才提笔写作《树犹如此》,字字真切,细节凿凿。大约是真正的伤痛总是无法在第一时间抒发出来的,人总是要愣一愣,缓一缓,从凝固的时间里跳脱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大恸所在。
白先勇退休后曾将王国祥家中两缸桂花搬了回来,移到园中一角。不知道当春秋时节,二人共植的茶花、桂花开放时,他是否会想起1954年的那个夏天。
因为迟到,两个少年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开始了他们命运交织的三十八年。
写在最后:
树犹如此是我看过最好的悼亡文之一,相比冒疆之伪、元白之表演欲、东坡纳兰之文人铺陈,他的字句朴实克制到极端,可是“守望相助三十八年”的深情,即便归有光朱自清也不能及--时光是最强的破坏者,而他们不曾输给时间,只是败给命运。这本基本都是花城红皮白集第六只手指一卷外加一篇树犹如此,擎天笔力的写手抛开一切技巧单用白描,积威所慑下突然有感动的感觉,树犹如此一篇是初读,只觉情真意切,顺带第二次读的第六只手指也颇有几分味道,我们都在老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参考资料
1 知乎专栏,https://zhuanlanzhihucom/p/356143166
2 潘秋枫尘缘如梦——读白先勇散文《树犹如此》[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01):53-55
3 黄自鸿无常、叙述与重复:阅读白先勇《树犹如此》[J]南方文坛,2015(03):137-139
4 陈剑晖中国散文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其跨越[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138-150+208
5 阮桃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解读白先勇《树犹如此》中的同性之情》
前言:上学期在教室上自习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偶然跟同学闲聊,向我推荐了白先勇这位作家。那是我第一次得知白先勇先生的名字,回去搜了一下他的作品,本本书都是豆瓣评分8分以上,加上他竟然是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一下子提起了兴趣。于是便下单购买进行拜读。
正文:辛弃疾在《水龙吟》里写:“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白先勇先生以“树犹如此”来给纪念亡友王国祥的文章命名,一是借用此成语的原本含义,表达一种岁月无情,老病相催的情感。二是表示人的不幸连花草树木都能感应,更别提至交好友了。面对王国祥的死,白先勇就如同他园中疏于照料的花木般,不知萎靡衰败多少日。
1954年,白先勇与王国祥相识于高中补习班,因争抢上楼而相识,他们之间的默契就此开始。白先生从成大水利系重考到台大外文系。王国祥从成大电机系转考到台大物理系。当年转学、转院、转系,都是难如登天的事情,尤其是台大这可是当地顶尖大学,而他们偏偏做到了,想想这里头有多少来自彼此的力量和勇气呢。两人都是有理想的青年,当发现理想偏于真正所喜时,毅然决然,重头再来。两人的性格际遇都是十分相投的,这是多么难得。白先生大学办《现代文学》杂志,王国祥查出“再生不良性贫血”,但他仍然抱病帮白先生拉订户,拿奖学金“经援”快办不下去的杂志。他至始至终支持白先生的理想,堪称灵魂伴侣,白先生也为他没有在物理理论研究这条路走下去而深感遗憾,就像是为自己痛惜一样。当年的病被压下去了,是劫后余生。没想到时隔多年,这体内的妖怪又突然醒来,张牙舞爪,不让人安生。吃药就医后有暂时的人为的安康,他们便去喜爱的饭馆吃一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在东拉西扯的故事里短暂地忘却疾病的痛苦。原以为人生如寄,他将与白先生守望互助,患难与共,却奈何命途多舛,天公作怪,王国祥先一步离开。
一开始读白先生的文章,并不知道先生的性取向,在看《树犹如此》时,却真有看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的感觉。那时对先生并没有像今日那么了解,看似一篇平凡的纪念文,却是字字情深。不知道先生在写时,平平淡淡的文字背后藏着多么汹涌的思念?这淡淡的感觉,像是细水长流,直抵心底。
整篇文章白先生写的只是寻常言语,说的只是平常旧事,感情尽是含蓄,却能在字里行间看到那难以掩饰的伤痛。有的人死了,可能只被怀念一阵子,而有的人死了却能在存者心里活上一辈子。两个人种植的意大利柏树似乎是预知了友人的去世,故而就跟着去了。连树都能有如此深情,何况是先生呢?树归于空,人却在心中。
先生料理完友人的后事,回家照料一院的花草,让死了一回的花草们活得一如当初,尤其是剩下的两棵意大利柏树和王国祥家里的两株桂花,先生似乎也“暂且贪享了人间的瞬息繁华”,只是在抬眼间,却过不去自己心中的那个缺口。正如文章最后写道:“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对白先勇而言,王国祥就是那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吧。
在文章的最后白先勇说他在春日的美好时光中享受着这个世界瞬息的繁华,而美中不足的是那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枯死了一棵,空出了一个大缺口,而这个缺口却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裂痕。读着这样的文字,不难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的感慨,真的很让人心痛,可以想象白先勇先生的心已经被挖去了一大块,那种疼痛该怎么忍受,并在多年后再写下这段故事,缺口是再也无法被修补的,而我猜想白先生也并不想去修补,因为这样他就能时时刻刻念着国祥,他透过这个缺口看到的是曾经在一起的美好画面,又怎么忍心去尘封呢?他们的爱情没有输给世俗的偏见,却还是没有逃过病魔的魔爪,白先生今年82岁,仍然未娶,一个人回忆着他们的那些年,而国祥藏在桂花的清香中、躲在柏树的树荫下、埋在白先勇的心里。
但我觉得他们是幸运的,能在17岁这个最美的年纪遇见彼此,一直相伴了这么多年,这是很多有情人都不曾有过的奢想,世界上的感情并不都是两厢情愿的,所以才会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你喜欢的人刚好喜欢你。”错过了当年的那个他/她,很多时候人到了一定年龄,只要能找到与自己合适的就行了,而与自己年少时的心动渐行渐远,只是很多年后走在路上突然看到路边打闹的小情侣,才又会想起那久远时候爱的人,然后看着遥远的天边笑了笑,继续赶自己的路。其实这样的人又何曾不是心里空了一块,只是他们自己把它缝合了,但伤痕一直在,也许这样爱而不得的人生更痛苦吧,可这恰恰是人生常态,而能与爱人相伴几载已是赚到了。
世人都说他们二人是同性恋人。而“同性恋”一直以来都不被大多人认可。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纠结于真情存在于什么样的人之间,重要的是那种难得的“同怀视之”的情谊的存在。人活一世,只要是能够拥有这样一段感情,无论是友情,亦或爱情,皆是三生有幸的。
又读了一遍《树犹如此》的结尾部分。“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结语: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