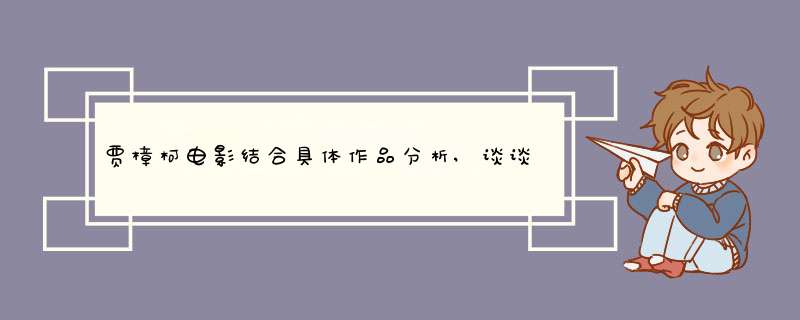
转载过来的,不过挺好,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贾樟柯,所喜欢的**导演贾樟柯。
关于他的童年,有一则流传甚广的秩事。一天上午,县城刮起了大风,上小学的贾樟柯听到一种声音从远方传来,他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火车汽笛声。"到他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时,头一件事就是去看火车。骑上三四十里地,到另一座县城。"我骑了很远很远的路,很累很累了,然后看到了一条铁路。就在那儿等、等,一列拉煤的火车'轰隆隆'地开过,噢,这就是火车!"
多年之后,他拍了一部**,叫做《站台》,火车与汽笛,记忆化作了影像与声音。但当时,这个数学很差的孩子,理想是当个大混混儿,有权有势。他打架,看录像,县城里的青春,在一个狭隘荒芜的空间里左冲右撞,无处可去。他的兄弟们,一拔一拔地辍学上了"社会"。
"跟个朋友去看**,买完票他说上厕所,我就先进去了。我左等右等不见他,出来后发现他被抓走了,他抢了别人的手表。""还有个混混儿朋友,有天骑车去酒厂玩,我们那儿出汾酒,第二天听说他死了,他在酒厂喝了太多的酒,酒精中毒。"
只有一个贾樟柯,成了导演。回头去追忆与表达。他有什么不同呢。他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让他坐在后排随便看书,他遇到了一个好的中学校长,每天下午不上课,可以发呆、写诗。贾樟柯过了几年"文学青年"的生活。还在一个暑假跟着"东北虎摇滚乐团"走穴,走过山西中小城市。他跳霹雳舞。——因为这段生活,后来才有《站台》。
接着就到考大学的时候了。他数学太差,父母把他送到太原去上山西大学的一个美术班,好准备考美术院校。贾樟柯常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公路局**院"看**,有一天,他看到《黄土地》。
"看完之后我就要拍**,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
91到93年,他考了三年,考上北京**学院文学系。同学对他的印象是:"喜欢在天冷的时候穿着他标志性的暗红色羽绒马甲,一个人走来走去,碰到了就来一个温厚的笑容。"这个时候,他的年龄都比同学们大上好几岁了。他的心里有紧迫感。他的表达欲望也强烈得多。
他组织了"青年**实验小组",还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开始拍摄《小山回家》。这个片子得了香港映像节的大奖。得奖并不意味着好片子。这部55分钟的作品,粗糙、模糊、控制力不足,但这其中,有一种敏感直接的气质,意味着真实。它不是一个成功的或成熟的作品,但它为贾樟柯提供了一个机会。一笔30万的钱。让他可以回家,开始他的《小武》。
"那次回家,走在路上,突然一辆卡车开过来,我一个从小很要好的朋友,在卡车上坐着。我在路边站着,他看见我,我看见他,他冲我笑着。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刚到家,稀里糊涂的,那车就开过去了。等他走远之后,问旁边人,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被拉去枪毙的,唉呀!我的感觉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
一切都在废毁之中,而重建不知何日何时。一个叫小武的小偷,以一种手艺人的尊严走在一个中国的县城街道上,他身为朋友、情人、儿子。但所有的关系都分崩离析,让他无从站立。他被铐在光天化日之下,围了一群人,疑惑地看着,指点着。镜头暴露了,它以自己的暴露为代价,撕开惯性的麻木。这是一个好作品,沉痛,温柔。他的思考方式与感情方式,第一次有了完整与深入的表达。
《小武》得了8个奖。进入柏林**节"青年论坛"。贾樟柯成名。
他成了"中国**的希望",所以,《站台》的拍摄不太可能没有压力。但这是一块在他心头压得太久的石头。他必须搬开它。
《小武》是一个切片,而《站台》是一个历程。从80年到90年。再隔了十年回头去看,贾樟柯有了一段让自己平静的距离——他用的,几乎全是中景与全景,没有特写。在这个距离外观照,人物的面目不再有细节的记忆,而悲欢不再如当日般在身心的表面煎熬,它们沉淀到时间的潜流里去,留下的,是一个会意的笑,一个沉默的动容。
这个影片的情绪,化成了一个标志式的影像。三个年轻人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前面的人展开手臂,后面的崔明亮,向着观众坐在后座上,他斜侧着头,有一种茫然而又隐忍的表情。他们在汾阳灰暗的街道上如此飞翔。
越过《站台》,贾樟柯成了新一代**领袖。但他还在"地下",他的**国内看过的人还是不多,至少,象片子里的三明那样的人,没有看到他的影片。
"我常常会突然在一种强烈的绝望之中,对自觉失去信心,对**失去兴趣。那些无法告诉别人的怯懦,那些一次又一次到来的消极时刻,让我自觉意志薄弱。"
**导演是一个将情绪与思想形形式化的职业。贾樟柯是以他的决心与耐心,梦想与行动换来流动的影像。绝望与薄弱或者是不可少的,一个满足的人,不太可能是艺术家。严苛地对待内心,并以实际方式去解决,是一个**工作者的素质。他必须得在长期的琐屑的工作中保持热情。坚持一种完美主义的态度。
《公共场所》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一个30分种的短片,没有剧本与对话,只有表面的展增。贾樟柯一向是强调表面的,他拒斥人为的深度。
而最近看到的他的片子,是一个5分钟短片:《狗的状况》。他自己摄影,狗市,一只只狗被扔进麻袋,一只小狗挣扎出来,从一个破洞中露出头,它出不去,眼睛四下张望。它的眼神温和而困惑。
他说:"我想用**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同是山西人说两句吧,为贾樟柯骄傲,这话不是“老乡见老乡”那种庸俗的套路,而是因为他拍出了给这激荡的时代做注脚的另类**。
其实单论贾樟柯**的技术细节,我觉得是被高估的,因此一看到题主的这个问题,下意识地感觉用两个关键词就能概括——“长镜头、原生态”,这就是贾樟柯**在摄影方面的最大特点,有人要说了,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随便一个学影视摄影的都能成为贾樟柯咯?
当然不是,最大特点只是一部分,贾樟柯之所以是贾樟柯,摄影的特点是基本要素,要知道**除了摄影还有剪辑、对白、表演,贾樟柯**还要加上“思考”——他不通过**明确告诉你什么道理,他只是拍了一部**给你看,其他的事情,交给你自己。
有资格这么做的**导演,至少在我们国家太少了,贾樟柯的出现当然少不了运气,他本身不是导演科班,他是文学系的,又是一个有现实情怀的人,《小山回家》的获奖基本上奠定了他的**风格,这辈子就干这事儿了。
他说过,类似国内大导演拍的商业片,他也能拍,因为在他看来,无非是用华丽的镜头语言去掩饰导演内心的空洞以及叙事的无能(大意如此)。
对此不予置评,等他真的拍出叫好叫座的商业片再做定夺。但是他至少做到了一以贯之的关怀,关怀他的过去以及现在,其实也在关怀这个国家一直避而不谈的那些无人区。
也可以理解,既然是避而不谈,又被冷落到无人提及的角落,描述这些角落的**,又怎么可能是华丽的呢?所以他的**,摄影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平静至无聊乏味的取景框、漫长到令观者略微焦虑的长镜头、随意调度到刻意随意的构图,只有如此,才能用无声动人,当然,动的是有心之人。
至于其他的特点,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哈。
要说的真是太多了。
文/梦里诗书
文艺从来不会是一种作态,山河的情怀更不是以粗估的镜头一味来消费底层的贫穷,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再 难见其早期作品那耐人寻味的真实,反之充斥着做作的的虚伪和自以为是的情感,看到的只是一个导演讨巧博情于西 方的臆想。
这次的贾樟柯将**聚焦一个家庭二十多的情感变迁,以1999年的昨天,2014年的今天,2025年的明天三个节点为展开,但乍看有以山河乡愁底蕴的依托,实则人物塑造缺乏实态,情感倍感空洞,那冗长难耐的叙事,所见只是导演一味的渲染县城底层的贫穷,而于此之中在1999年的昨天女主赵涛徘徊于煤矿主与矿工的三角之恋,最终选择了煤矿主,2014年的今天,昔日的矿工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事,如此情节,无非就是想在**中寄予时代感,在西方彰显出自我敢于呈现古难的**斗士形象,实则其所作只是如同一个怨妇无知的埋怨命运的无常,敷衍了事的剧情缺乏内在深层次的攫取。
2025年的明天,这个导演虚构的未来,煤矿主孩子移民澳大利亚的展开,更充斥着狗血的噱头,一段老人与孩子的不论之恋,令人乍舌,这种未尝有何奠基的情感,大尺度的激情戏,彻底破坏了这部**仅存的那一丝山河故土的乡愁,胡编滥造的天雷滚滚,却又在此时还在妄以寄予探讨何情感的传递,为人所见只是写实的镜头下填充了虚无的情感,如此娇柔的假大空,令人不可思议他是那个昔日能拍出《站台》《三峡好人》这般真正深谙时代的贾樟柯。
《山河故人》诟病的根源在于**仅只是停留在了形式主义的层级上,那悲伤苍凉的基调与写实语境的糅合,虽仍是昔日的贾式风格,但剧情与人物的彻底失败,是其难掩的缺陷,**在磅薄的时代背景下没能形成一个真正以故事为寄予的山河故人,没有人会对一个好故事说不,哪怕它是一个悲剧,敢于揭露国家阴暗《熔炉》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如《山河故人》这般只是如简报般的将几个故事拼凑一体,人物剧情的虚缥缈,力图彰显的一腔情怀也就变的那么不足以为道了。
真情实感的流露还是故作姿态的弄人,这种好与坏在**中是当下立断的,当本自深赋时代充沛的情感化作了虚伪的造作,如此山河何故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