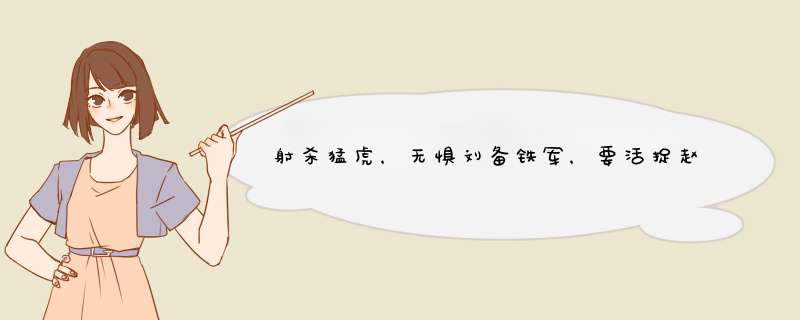
鲍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虚构的一个人物,出场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其真实身份是猎户出身的武将,是东汉末年荆南桂阳太守赵范麾下的管军校尉。在《三国演义》中,鲍隆是荆南五虎之一,曾射杀双虎,威镇江南,与战友陈应合称“桂阳双壁”。
荆南五虎,是《三国演义》中刘备攻取荆南四郡时与刘备军交战的五个武将。荆南五虎,各有各的特点:邢道荣,荆南第一上将,有万夫不当之勇,使一把开山大斧,人称“万人敌”;杨龄,地位力压黄忠、魏延,成为韩玄手下第一勇将。
每逢出战必为先锋,勇不可挡。刘贤,刘度长公子,文武兼修,为荆南著名的雅士,人称“儒将”,擅招贤纳才。陈应,桂阳猛将,善使飞叉,作战冷静,有谋略;鲍隆,射杀过双虎,威镇江南。
鲍隆,跟陈应一样,也只在《三国演义》中出现一回,两小段,有两句单独的台词及与陈应共同对赵范赵云两人各说了一句话,有一次用武与用文的记录。鲍隆,虽曾有射杀过两只老虎的辉煌成绩,就敢说大话,说要活捉赵云,真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桂阳外面,可谓是强者百出,各领风骚。更何况是长板坡上“七进七出”的赵子龙,更是无人能敌的强者、硬汉。因此,像鲍隆这种又鼠目寸光又自不量力还恃勇逞强的人,在赵云面前注定是要受虐的。最后,鲍隆诈降不成,反被赵云斩首示众。
在《三国演义》中,鲍隆自恃有股天生蛮力,自倚有射两虎经历,就在上司和搭档面前口出狂言,肆无忌惮,却处处透着鼠目寸光,自不量力的感觉。一句“我两个诈降在他军中,太守却引兵来搦战,我二人就阵上擒之。”就入木三分刻画出鲍隆的无知。一句“五百骑足矣。”正一语道破勾勒出鲍隆的愚昧。
在小说中,鲍隆之所以会如此自不量力,是因为如下原因。
其一,出身束缚。在门阀政治的社会里,出身至关重要。特别到东汉末期开始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典型的门阀政治局面。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极难有出头之日。鲍隆空有射杀两虎的成绩,可猎户出身成为其最大的短板,在东汉官场很难有发展的空间。为此,鲍隆因出身低贱而束缚其在仕途进步的步伐。
其二,地域限制。鲍隆虽是管军校尉,却不是凭战功靠名气受朝延正封的正牌校尉,而是施恩德获奖励得朝延赏赐的杂号校尉。鲍隆,这个管军校尉,更是杂号校尉中的杂号,只是桂阳郡太守赵范自已私募的校尉,从未纳入朝延的官制系列。
因此,鲍隆要想在仕途有更长足的发展,就是对赵范忠诚不二,想赵范之所想,急赵范之所急,才可以跟着赵范水涨船高,步步高升。要是脱离赵范或离开桂阳郡,鲍隆连打仗吃粮的兵都不是,更何况是管军校尉,只能回到桂阳岭山乡操持老本行
其三,机会制约。桂阳地处南方,与南蛮之地岭南相邻,远离中原中枢,地理位置及重要性不管是在荆州地形上还是在东汉版图上,都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甚至见风使舵的主,谁的实力强就倒向谁。从黄巾军起义到赤壁之战,桂阳郡先是受刘表节制,后曹操南下又归顺曹操。
因而,桂阳郡次次不抵抗而使武将失去建功的机会。因此,鲍隆也错过很多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从而就次次落空飞黄腾达的时机,数十年屈居在管军校尉这一职位上,从未提拔过。
赵云攻取桂阳,对鲍隆而言,是一次机会:打赢,名声官位唾手而得,名利双收;打败,投降认怂,也属正常,司空见惯。所以,鲍隆自不量力,挑战赵云,最根本在于“利”字当头。
鲍隆,本是一个山野猎户,就凭借自己曾射杀过双虎的经历,就敢口出狂言,要跟赵云拼拼力量,活捉赵云。事已愿违,拼不过赵云,还要诈降,最终还是死在赵云之手。正所谓,人要有自知,而不可自大。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刘伯钦,《西游记》中的人物,绰号镇山太保。家住两界山附近,和妻子、母亲,一家三口打猎为生。一日进山打猎,正好遇到老虎要吃西天取经的唐三藏。
刘伯钦救下唐僧,并把他带回家中休息,原来次日就是刘伯钦父亲的忌日,刘伯钦的母亲求唐僧给超度一下,唐僧欣然应允,刘伯钦的父亲夜晚托梦给家人,说经高僧超度,已消了罪业,阎王差人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去了。
刘家对唐僧感激不尽,刘伯钦一直把唐僧送至两界山,方才分手。刘伯钦可谓唐僧最早的守护者。
梁山一百单八将来自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虽然同聚一堂称兄道弟看上去一派祥和的气氛但实际上这些好汉分属于不同的山头和帮派。除了宋江领导的嫡系山头之外至少还有其他山头派系,其中就包括孙立、解珍、解宝、孙新、顾大嫂、乐和、邹渊、邹润等人组成的登州派。
与其他派系相比登州派是一股特殊的力量,这个派系都是由家族成员构成的。比如这个派系的绝对领袖孙立跟孙新是亲兄弟;猎户解珍和解宝同样是亲兄弟,他们俩的表姐是顾大嫂,而顾大嫂又嫁给了孙新,那么孙立、孙新跟解珍解宝就成了亲戚关系;铁叫子乐和的姐姐乐大娘子又嫁给了孙立,那么乐和与孙氏弟兄又成了亲戚。
故而登州派成员沾亲带故的亲情关系是很难靠打压的手段来削弱他们的力量的,对这一点宋江心知肚明。但是宋江又不能任由登州派势力在梁山做大做强影响自己的权威,于是宋江采取了内部分化,人为制造矛盾的方式瓦解登州派成员之间的关系。
宋江刻意重用提拔解珍解宝两兄弟,猛踩孙立。在登州派内部病尉迟孙立是绝对的领袖和大哥,解珍解宝充其量就是孙立的跟班和小弟。但是宋江偏偏把解珍解宝安排进了天罡星序列,解珍排名第三十四位,解宝排名第三十五位;至于孙立则被宋江送到了地煞星里,他的排名是第三十九位。
自己的小弟跟班居然在梁山内部的地位比自己高好几个名次,这分明就是宋江刻意羞辱孙立。孙立会把自己的屈辱导致的愤恨转嫁到解珍解宝两兄弟身上,如此一来登州派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和矛盾,其势力会被压制下去。从对解珍解宝和孙立的安置揭露了宋江诡诈的本性。
在小说《三言二拍之义结生死交》中,猎户因为与书生结为兄弟,在书生遭受困难之时,为书生跳崖自尽,这种行为表达了猎户对友情的执着和忠诚,他选择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忠诚与坚定的信念:在猎户心中,义结生死交的兄弟情义是极其珍贵的。他坚信这种情义的价值,愿意为书生的幸福和安全付出一切,这包括了他的生命。
2 感同身受的共情:猎户深刻地体验到了书生的困难和痛苦,他感同身受,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书生。
3 对后果的预知:猎户可能预知到了书生的危险和可能的牺牲,他选择了主动迎接这种危险,以保护书生。
4 对死亡的直面:对于猎户来说,死亡可能并不是最可怕的,他更害怕看到自己的兄弟陷入困境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总的来说,猎户选择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义结生死交的兄弟情义的执着和对书生的深沉关爱。
发生在清末,东山里有个猎户叫老棒子,这天午后,他带着守山犬“山山”正走着,突然,山山回头冲老棒子轻轻地叫了一声,然后箭一般地蹿了出去。
老棒子精神一振,不远处就是他下的一个套,看来是有猎物落网了,他急忙跟了上去。当他看到套上的猎物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被粗大绳套倒吊在树上的不是动物,而是一个大活人!
那人三十几岁年纪,衣衫刮蹭得破破烂烂,颧骨上有一片青肿,地下扔着一把闪亮的钢刀,显然是被绳套吊起来时失手掉落的。那人挣扎着抬起涨得通红的脸来,叫道:“老哥,我是县城捕头范昌元,快放我下来。”
老棒子扫了一眼钢刀,一眼看出这种刀做工精致,绝非寻常猎户所用之刀,用这种刀的人,非官即匪。老棒子疑惑地问:“捕头?你怎么跑到山里来了?”
“我在一个,下山时迷了路。”范昌元在空中悠荡了半个圈,嚷嚷着,“老哥,有什么话,先放我下来再说好吗?”
就算对方是匪,也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他这种穷猎户,老棒子略一犹豫,上前解开了绳套。范昌元一 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过老棒子递过来的水壶,猛灌了几口。
老棒子问:“盗贼抓到了吗?”
范昌元抹了抹嘴唇,说:“我追了他整整一个时辰,到底还是没留下他活口,掉下山崖,死了。”
范昌元筋疲力尽,随老棒子来到他的小木屋,吃了些剩饭,一头扎在他的热土炕上睡着了。老棒子闲不住,带着山山继续去遛套子。
这次有了收获,有个套子套住了一只傻狍子,老棒子扛着狍子回到木屋旁,就在这时,他发现木屋窗下多了行杂乱的脚印,似乎有人曾经在那儿向屋里窥探。老棒子心里一沉,扔下狍子,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把拉开木屋门冲了进去。
土炕前果然多了个人,此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年纪,同样是一身破烂衣衫,而范昌元原本放在桌上的钢刀,现在已经落在此人手上,刀尖直指坐在土炕上的范昌元。范昌元一脸狂怒之色,却垂着双手不敢动弹。
年轻人听得声响猛地转过身来,他咧开嘴笑了,对老棒子说:“叔,您就是这里的吧?我是县城里的捕头沈七,这家伙是我追捕的逃犯,打扰您了,真不好意思。”
老棒子惊疑不定,这家伙怎么也自称捕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范昌元沉着声说道:“老哥,他是有名的江洋大盗,用蒙汗药迷倒大人一家,犯下了惊天大案,我才是真的捕头,你千万别听他的。”
山山感觉到了几人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它挡在主人面前,毛发直立,摆出一副戒备的姿势,嘴里发出“呜呜”的之声,死死地瞪着年轻人。在老棒子的印象中,官府中人言谈举止都很霸道,可这两人却一个比一个客气,他有些糊涂了,于是缓缓抽出腰间的砍刀,说:“你们都说自己是捕头,可我记得,捕快是有腰牌的吧?”
“当然,您请过目。”沈七掏出一块牌子扔给老棒子,范昌元焦急地叫了起来:“老哥,我俩在悬崖前一场激战,他被我踢下悬崖时扯掉了我的腰牌,现在拿来骗你!”
“言而无信的小人,还敢胡说八道。”沈七回过头来对着老棒子,“,咱们都别废话了,您老帮个忙,把他的双手捆起来,回头报上衙门,县令大人必有赏赐。”
见老棒子似乎意动,范昌元情知不妙,灵机一动,叫道:“且慢,你说你是本县捕快,你知道本县最大的酒楼叫什么名吗?最大的绸缎铺子是哪家吗?”
沈七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皱,范昌元知道自己抓住了他的破绽,正想趁胜追击,沈七却已经出手了,他猛地一转身,钢刀划了个圈从下方挥过,割断了正主人命令的山山的咽喉……
沈七的动作太过突然,等范昌元和老棒子反应过来想出手时,沈七的钢刀已经重新顶在了范昌元的咽喉口,他叹了口气对老棒子说:“大叔,这条狗对我的威胁太大,我只好先下手为强了。你放下刀,不然我就杀了这位真正的捕头。”
这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完成,老棒子和范昌元竟然都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老棒子呆呆地看着血泊里挣扎的爱犬,悲愤地举起刀骂道:“王八蛋,我跟你拼了!”
“老人家别激动,我之所以想冒充捕头,就是不愿意跟你动手,不愿意伤着你。”沈七手上用力,刺破了范昌元咽喉的肌肤,着说:“让他放下刀!”
范昌元知道肉在砧板,不由得他不屈服,只好说:“老哥,别,否则他会杀了我的—”
老棒子投鼠忌器,果然不敢动了,长叹一声,将砍刀丢在地上。沈七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命令老棒子将范昌元绑起来。
老棒子无奈,只好找了根绳子,依言绑好范昌元后,将他挪到墙边的被褥前,说:“靠着点吧,这样舒服一些。”说完,他刚想转身下炕,却见一柄钢刀顶在了他的咽喉上,沈七得意地说:“,我杀了你的狗,是不是恨死我了?”
占尽上风的沈七,脸上再没有一点谦恭之意,眼里尽是杀机。老棒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惊恐地说:“不敢不敢,不过是条狗,死就死了吧。我这一把年纪,只想着多活几天,两年前我采到一支百年老参,藏在那个箱子里,算是买我一条狗命,求求你饶了我吧。”
老棒子指着墙边柜子上的箱子,一脸卑贱之色。沈七饶有兴致地打量他几眼,终于放下心来,说:“原来你是个窝囊废,这倒好办了,只要你把七爷我伺候好了,我不但不杀你,那也当我赏给你了,七爷我有的是价值连城的,没瞧上你那点破玩意儿。”
沈七一把将老棒子扯下炕,自己跳上去,解开范昌元的衣襟,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裹打开。
这时已经日落西山,屋里光线昏暗,可这包裹刚一打开,一股柔和的清光便照亮了整间屋子。
沈七轻轻拈起一颗洁白的珠子,“哈哈”笑道:“夜明珠啊夜明珠,转了几个圈,你终于还是回到我的手上了。”
老棒子虽然没什么见识,却也看得出这珠子绝非凡品,只听范昌元恨声连连地说道:“沈七,这是县令大人为大寿准备的贺礼,如果你识趣的话,立刻放了我投案自首,我可向县令大人求情保你不死,否则就算你藏到洞里,也早晚被抓出来凌迟碎剐,到时候连累了妻儿,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父母妻儿?沈某尚未成家,没有妻儿,至于父母嘛,我倒有兴趣跟你说说他们的 故事 。”沈七命老棒子弄些吃食,然后缓缓说起了他父母的事情。
沈七的沈从儒是一个,家里开了间药铺。沈父为人厚道,医术虽然普通,但心地,贫苦有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他时常有免费看病、赠药之举,素有沈大善人的美誉。在同一条街上另有一家胡家药铺,是县里县丞的亲叔所开,欺行霸市,老百姓都不愿意去他家药铺,无法与沈家相比。
有一天,一个病倒在沈家药铺门前,沈父好心熬药施救,乞丐却因病重不治身亡。胡家药铺借此大做文章,买通了一个地痞冒充乞丐的家人,状告沈父为博善名,胡乱施药致人身亡。沈父被抓进衙门,几番刑讯下来,被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为救沈父,沈家倾家荡产,最后药铺都低价盘给了胡家。好不容易救得沈父出来,可沈父伤势过重,没几日便死了。沈母不堪打击,数日后也一病不起,相随而去。
那一年沈七刚满十七岁,因为自幼好武, 父亲 将他送去千里之外,随一位名师学艺,沈七惊闻噩耗赶乡,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沈七在父母坟前大哭了一场,当晚潜进县衙,杀死了县丞,又一把火烧死了胡家满门,从此远走他乡,专门与为富不仁的达官贵人们作对,成了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
讲完了这段往事,沈七长长地吁了口气,对范昌元说:“我这种活一天赚一天、早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的人,还在乎什么千刀万剐吗?另外,我倒想问一下,你们县令大人俸禄几何?如果他不刮尽民脂民膏,怎么有钱买得起这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范昌元避而不答,换了个话题,说:“如果你不想归案,那么想必是要杀我灭口了?那就给我一个痛快,别婆婆的像个娘们。”
沈七里“哼”了一声,说:“别以为我是狂魔,七爷我从不滥杀无辜,你暂时还不该死,那就好好活着吧,我走的时候自然会放你。”
范昌元似乎松了口气,不再开口,老棒子却忍不住问道:“七爷,听范捕头说,你不是掉下悬崖了吗……”
沈七笑了:“怎么没摔死,对吧?七爷我福大命大,悬崖壁上有棵老树,救了我一命,所以我就爬上来了。”
“可是你当时两手空空,就连这把刀……”老棒子指指桌子上的钢刀,“都是刚刚抢人家范捕头的,你怎么就敢空着手回来找他?”
“你追杀了我一个时辰,我的刀丢掉了,又慌不择路被你逼上了悬崖,侥幸逃得一命后,本该有多远跑多远,估计你也这么想的吧?”沈七看了看同样一脸不解的范昌元,脸上满是嘲弄之色,“其实我本来也这么想的,可我咽不下这口气,你说只要我交出夜明珠,就放我一条生路,所以我把夜明珠给了你,可是你拿到珠子就变脸,又要抓我归案。对你这样言而无信的小人,我就是拼上一死,也得有所回报,所以我顺着雪地里的脚印追了回来,果然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范昌元默然不语,脸上似乎有种说不清的意味。见气氛一下子僵住了,老棒子掀开锅盖放在一旁,一股热气弥漫开来,木屋里尽是诱人的肉香。老棒子扫了一眼范昌元,看着沈七低声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太低了,沈七转过脑袋,探过头去问:“你说什么?”
就在这时,土炕上的范昌元突然跳了起来,手上不知何时多了把匕首,狠狠向沈七刺去。沈七蓦然惊觉,反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顺势向地下一倒,躲开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刀。
范昌元精神大振,一把抓起桌上的钢刀,却不急着追击,而是一个箭步蹿到门口,堵住了沈七的退路,然后才转过身来。与此同时,地上的沈七打了个滚,左手向灶台撑去,试图借势跳起,没想到一只手恰恰撑进了炖肉锅里,他顿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猛地缩回汤水淋漓的手,身子却因此失去平衡,重新坐倒在地。
范昌元把握时机,上前一步用刀指着沈七,“哈哈”大笑着说:“沈七,现在家伙在我手里,还不束手就擒吗?”
沈七死死盯着范昌元另一只手上的匕首,又回头看了一眼土炕上的被褥枕头,露出恍然大悟之色,冲着老棒子骂道:“你个老不死的,在枕头下面藏了匕首?所以你才让他靠在墙边?”
老棒子面无表情,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范昌元狂笑着对沈七说:“你终于明白了?他不过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就明白了,趁你说话时,我一点点割断了绳子,看来你的运气到此为止了,沈七,投降吧,别逼我杀你。”
沈七脸上阴晴不定,片刻之后长叹一声,认命似的反身背起双手,任老棒子取来绳子,像捆范昌元一样将他捆了个结实。
确定沈七再无反抗可能,范昌元终于松了口气,对老棒子说:“这次你配合得很好,要不是你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还没那么容易打他个措手不及。现在咱们开饭,回头你送我下山,我请县令大人重重赏赐于你。”
老棒子勉强一笑,盛上狍子肉,两人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眼见着一锅肉见了底,范昌元终于觉得肚子饱了,可是自从追击沈七开始到现在,他已经近两天一夜没休息,只觉得一阵阵疲惫袭来,忍不住趴在桌上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他听到“扑通”一声,他吃了一惊,竭力抬起头来,这才发现老棒子竟然摔下椅子,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一股寒意自范昌元心里升起,他想站起身,身子却跟噩住一般无法动弹,在昏过去之前,他眼前闪过了沈七那只汤水淋漓的手。
见两人都昏了过去,沈七“哈哈”大笑起来。刚才,范昌元跳起来袭击他,他就知道先机尽失,就算他能够逃出去,可放在桌上的夜明珠就会重新落入范昌元手里。他不甘心这样的结果,所以决心剑走偏锋,作最后一搏,他趁在地上滚动之际,掏出蒙汗药,装作不小心把手撑进锅里,乘机神不知 鬼 不觉地将蒙汗药放进肉锅,然后束手就擒,耐心等待药效发作的这一刻。
沈七反转身子取过匕首,一点点割断绑着的绳子,恢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夜明珠收入怀里,然后再绑住两人,又取了些狍子肉重新下锅炖好,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最后,舀了瓢冷水将两人泼醒。
“你知道县令一家是被我用蒙汗药迷倒的,怎么就不知道防着我点?”沈七显得十分开心,“范昌元,我沈七恩怨分明,杀的都是死有余辜之辈,虽然你是卑鄙小人,但毕竟罪不至死,所以今天我放你一马,如果你有种的话,一会儿你再来抓我,到时候咱们再决个你死我活。”
沈七踢了范昌元一脚,又对老棒子说:“至于你,竟然敢帮着朝廷鹰犬对付我,我也不能就这么放了你,得让你长点记性。”说完,沈七上前一通拳打脚踢,直到老棒子血流满面,他才大笑两声,推开门扬长而去。
沈七只拿走了那把钢刀,却将老棒子的砍刀和匕首扔在了地上。范昌元和老棒子先后割断了绳索。范昌元冲出屋外,虽然已经暮色四合,但白皑皑的雪地上,一行远去的脚印隐约可见,顺着脚印追上去,一定能找到沈七。
范昌元沉重到了极点,沈七临走前的那番话,看似豪气大发不惧死战,但其实占尽了天时地利,如果自己贸然追上去,别说那把破砍刀不趁手,就算趁手,如果中了沈七的埋伏,不丢了性命才怪。
范昌元明知道此次追捕不利于己,可又不甘心就这么看着沈七逃跑,任凭这一天大的功劳白白丢掉,他一犹豫不决。这时,老棒子来到他身边,地说:“范捕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突然,范昌元心里一动:以前,他也听说过一些沈七的事情,沈七专门与达官贵人作对,偷盗得来的大半财物,都花在了百姓身上,大有劫富济贫的侠义古风。刚才,虽然沈七恼怒老棒子自己,但仍然没有杀他,只是打了他几下了事,如果老棒子有危险,沈七会不会回来相救呢?
这些自命侠义的家伙,有时候就是这么笨,只要他肯回来,那自己便是以逸待劳,哪怕是只有一把破砍刀,也有信心与他一拼生死。想到这里,范昌元说:“老棒子,一会儿咱们埋伏在前面他回来的必经之路上,左右夹击,出其不意,一定能制住他。只要夺回夜明珠,抓住沈七,下半辈子你都不用再当猎户了。”
老棒子听得糊涂,眨了眨眼问:“沈七怎么还会回来?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他一定会回来。”范昌元斩钉截铁地说,“他现在还没有逃远,这里火光冲天,他一定看得到,只要他心里有一丁点疑问,只要他心里有一丁点担心你,他就一定会再回来看看。”
老棒子傻傻地问:“什么火光?哪里着火了?”
“老人家,不好意思,为了抓住沈七,我只有烧掉你屋子了。”范昌元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不过你放心,只要抓住沈七,县令大人一定重重有赏,下半辈子你都不用再辛辛苦苦打猎了,更别说一间破屋子了。”
老棒子惊得呆住了,反问道:“可如果沈七不回来,或者你抓不住他呢?”
范昌元不耐烦地说:“我都说了,他一定会回来,你不要再废话。”说完,他奔进屋里,从灶台里拿出燃烧的柴火,就要点燃木屋,老棒子急了,冲上来想阻止他,范昌元勃然大怒,举起砍刀指着老棒子,喝道:“没时间了, 还敢阻拦我,一定要逼着我杀了你吗?”
看着范昌元那张狰狞的脸,老棒子绝望得差点哭出声来,他巴巴地说:“烧了这屋子,老汉我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不敢拦你,你能先让我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吗?”
“你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就是那支百年老参吗?一直惦记着呢。”范昌元冷笑一声,放下砍刀,从柜上取下箱子,一把推开箱盖,见里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长条形的盒子。他眼睛一亮,伸手去拿,可就在他的手刚碰到盒子时,只听得“咔嘣”一声脆响,一个夹子闪电般弹了出来,不但牢牢扣住了他的手,强大的冲击力还将他的腕骨瞬间击碎。
原来,箱子里藏了个专门猎杀猛兽的捕猎夹子,范昌元痛得差点晕了过去,大叫:“老哥,快救我……”
老棒子缓缓走了过去,脸上哪还有一丝怯懦之色?他蹲下身来,看着范昌元一张惨白的脸,叹了口气说:“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参,之所以设这个机关,只是想关键时刻保命而已。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烧了我的家呢?”
为了一支本不存在的老参,恐怕要搭上条命了,范昌元肠子都悔青了,他叫道:“我不是想烧你的家,我只是想抓住沈七,相信我,我没有恶意;再说,县令大人会给你赏赐的。”
“如果没抓住沈七呢?是不是我就活该无家可归、活活冻死?活该被你抢去这支老参?”
“我……我没想抢你老参,我只是想帮你拿出来给你。”范昌元竭力想打动老棒子,“我是官,不是匪。”
“如果你不想抢我的人参,就不该碰它,就像沈七一样。”老棒子嘲讽地说,“实话告诉你吧,在听完沈七的经历后,我就想帮他,想告诉他你正用匕首割绳子,但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不但没能提醒他,而且还分散了他的心神,间接地成了你的帮凶。不过,他从怀里掏出蒙汗药放锅里的时候,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其实我看到了,只是没有提醒你,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你不值得我帮了。”
范昌元绝望地叫道:“可他是我们的敌人啊,他杀了你心爱的狗,还狠狠地揍你,我们应该一起抓他才对啊!”
“他是,所以杀了山山我也不怪他。至于他打我那一顿,其实根本没用什么力气,我知道,包括他先前对我的威胁、辱骂,都是为了给你看的,既然他不愿意杀你,就不能给你迁怒于我的机会。”老棒子愤怒地说,“只是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你居然想烧了我的家,既然如此,我就杀了你这个人,公平吗?”
在范昌元惊骇欲绝的目光里,老棒子高高地举起了砍刀……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