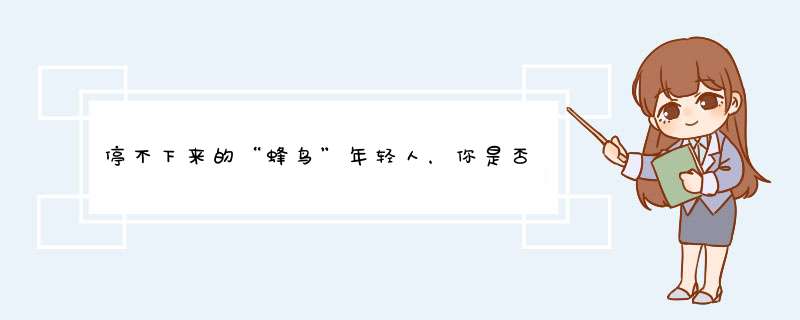
最近,老舒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坛报道,项飙教授对话迈克尔·桑德尔,谈中国社会中的“优绩主义”陷阱。里面提到年轻一代就像无法放松的“蜂鸟”,拼命挥动翅膀,不敢停下。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什么行业什么领域都在疯狂内卷,虽然也有疫情的缘故。学生考研国家线平均比去年高出好多分,考公也难,就业也难。
比如游戏美术领域,从一开始的站着的立绘,发展到华丽的衣物,再到背景有颜色,再到背景比人物还要华丽。b站知识区出现了很多小朋友up主讲解研究生、博士生水平的课程;面试的时候拼学历,拼几十份实习、拼竞品报告……
“不断挥动翅膀”太累了,做人太累了……活着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生前有何经历,最终走向的都是死亡不是么?
100多年前,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下了这样一篇短篇《The Other Side of the Hedge》。这个短篇可以说蕴含着各种对于生与死的思考。
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单调公路上,目光所及之处是飞扬的尘土,和两边棕色的枯枝树篱。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行走,人类社会整体曲折螺旋地向上发展。竞争是我们的动力,科学是我们的手段,拼搏是我们的使命。而在树篱的“另一边”,没有竞争,没有通往哪里的路,人们享受着自己的事情,仿佛一个乌托邦。而这“另一边”,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也是所有人最后的终点。
关于这个作品,老舒希望能有人一起来聊聊,可惜国内网上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并不多。因此今天老舒献上渣渣的机翻+意译。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原文看看。老舒的翻译……⬇️
《树篱的另一边》
翻译:老舒牌机翻+意译
我的 计步器 告诉我,我已经 25 (无单位)了。尽管现在停止行走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但我是在太累了,就坐在旁边的一块 里程碑 上休息。人们不断超过我,边走边嘲笑我,但是我实在没兴趣生气。甚至伟大的教育家Miss Eliza Dimbleby从我旁边匆匆走过,不忘勉励我继续前行,我也只是笑着挥了挥帽子。
起初,我以为我会像我 兄弟 一样。他把呼吸浪费在唱歌上,把力量浪费在帮助别人上。因此我不得不在一两年前就把他丢在了街角路边。不过我选择了一条更加 明智 的旅程。现在只有单调的公路让我感到压抑——脚下的尘土,两边的褐色树篱。从我有记忆开始,只有这些东西一直与我相伴。
而且我已经不断 掉 了好几件东西了。实际上,我们身后都是大家掉的东西,七零八落散成一片,蒙上了一层白灰,看上去和石头没什么两样。我的肌肉十分疲惫,甚至无法承受现在身上仍背负的所有东西的重量。我从里程碑上滑落下来,一蹶不振地倒在路中央。望着那大片干枯的树篱,我祈祷着我能够就此 放弃 。
一阵微风让我逐渐恢复了活力,它似乎来自树篱那头。当我睁开眼睛,我能看到一缕微光从杂乱的枯枝落叶的缝隙中透过来。树篱似乎不再像往常一样厚实。我从没有像此刻——拖着虚弱的病态的身躯,那么渴望穿过 树篱的另一侧 ,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目光所及之处没有别人,不然我可能也没有勇气想去试试。因为我们这条路上的人在交谈时, 从不承认 树篱另一半的存在。
我屈服于这种 诱惑 ,并告诉自己只是去去就回。荆棘刮伤了我的脸,我不得不将手臂当作盾牌,单单靠双脚驱动着前行。走到一半我就想回去了,因为忽然想起刚才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刮走了,现在甚至衣服都破了。但我已经越陷越深,返回已经不可能了,只好盲目地向前蠕动。我无时无刻不期待着力量衰竭,就此葬身于这片灌木丛中。
突然间,我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似乎要永远地沉了下去——原来是从树篱丛掉落到一个深水池里。好不容易浮出了水面,我大声向周围呼救。这时,我听到对岸有人笑着说:“ 又一个! ”然后我就被猛拽上去,气喘吁吁地躺在干地上。
即使我的眼睛里不再有水,眼前的景色仍让我感到迷茫——我从未到过这么大的空间,也没见过这样的绿草和阳光,蓝天不再是带状的。蓝天之下,山丘从大地中高高隆起,形成光秃秃的山脊。山脊上有山毛榉树,脚下有草地和清澈的池塘。但这里的小山并不高,而且给我一种 人造山景 的感觉。我想人们可以叫它公园或者小花园——如果这些词语不意味着某种琐碎或和约束的话。
当我的呼吸一缓过来,我就马上问救我的人:
“这个地方通向哪里?”
“ 无处可去 ,感谢上帝!”他这样说着,又笑了起来。眼前的男人大概五六十岁——正是我们在路上不会相信的那种年纪。但他的态度中看不出任何不安与焦虑,而且他的声音是 18岁男孩的声音 。
“但它总会通向某个地方吧!”我不禁大声辩驳。他的回答太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甚至没来得及想起,要感谢他救了我的命。
“他想知道它通向哪里!”男人对着山坡上的人们大喊。从山坡上传来阵阵笑声,那些人挥舞帽子,回应着他。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刚才掉进去的水池,实际上是一条护城河。它向蜿蜒曲折地左右延伸,而树篱也跟着它一路延伸下去。这一边的树篱是绿色的,从清澈的水中隐约可见它的树根。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树篱上面长满了犬蔷薇和铁线莲花。这一边茂密的树篱已成为了我回去的 阻碍 。一瞬间,我对这里的一切——不管是草地蓝天,还是树木和欢笑的男男女女,都失去了兴趣。无论它有多美多么广阔,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就是个 监狱 。
我们离开了边界。然后沿着一条几乎平行于边界的路,穿过了草地。我承认我走起路来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一直试图远离我的同伴,而由于这个地方不知道通往何处,我这么做并无好处。自从抛下兄弟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任何人保持步调一致过。
我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取笑他:
我突然停下脚步,沮丧地说:“这太 可怕 了。一个人无法前进、无法进步。现在我们的道路——”
“是的,我知道。”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断进步 。”
“我知道。”
“我们一直在学习、探索、发展。为什么?即使在我短暂的一生,我也见识过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德兰士瓦战役、财政问题、基督教科学派、镭的发现。比方说——”
我拿出了我的计步器,它依旧标记着25,没有再上调一度。
“啊,它怎么 停 了!我本想给你看看。它本该记录我和你行走的这一路时光,但是它仍然停留在25。”
“很多东西在这里都不起作用,”男人说道,“有一天有人带来了一杆MLM步枪,结果那玩意在这儿根本用不了。”
“科学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一定是护城河的水把它的装置弄坏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切都能工作。 科学与竞争 的精神——这是我们成为‘ 我们是谁 ’的力量。”
经过的人们不断和我们进行愉快地打招呼,我不得不停下来一一回应。他们中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交谈,还有的人从事园艺、干草制作或是其他基础行业。他们看上去都很快乐,我本可以和他们一样快乐,如果我能够忘记这是个不知道能通往哪里的地方。
突然一个年轻人向我们冲刺而来,吓了我一跳。他穿过我们行走的小径,帅气地跨过栅栏,将耕地翻腾个底朝天,直到跳进湖泊中游起泳来。这才是真正的活力,我惊叹道。“一场精彩的越野赛!其他人在哪里?”
“ 没有其他人 。”我的同伴回答我。后来,当我们经过一片茂盛的草丛时,里面传来女孩独自一人精致的歌声。我的同伴又强调了一遍:“ 没有其他人 。”我有点搞糊涂了,这里的人为什么都在做无谓的生产工作。我不禁喃喃自语:“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男人告诉我说:“ 除了它本身,它没有任何意义 。”
然后,他又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好像我是个孩子。
“我明白,”我轻轻地说,“但我并不赞同。每一项成就都是 毫无意义 的,除非它是 发展链 上的某一环节。我不能再冒犯你的好意了。我要修好我的计步器,找个办法回到路上。”
“那首先你必须看到大门,”男人回答说,“因为我们有大门,尽管从未用过。”
我礼貌让步。没过多久我们又到了护城河,那里有一座桥横跨两岸。桥上有一扇大门,它像 象牙 一样白,卡在边界树篱的缺口中。大门向外打开,我不由得惊呼——门外有一条路,就和我离开时的路一样——脚下尘土飞扬,两边是棕色的枯枝树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目光所及之处,一直是这些东西。
“那就是我的路!”我大叫道。
男人关上了大门,并说道:“但不是你 那部分的路 。无数年前,人类就是从 这扇门 走出去的,被一股极度渴望步行的力量所摄了魂,走了出去。
我否认了这一点,指出我离开的那条路离这儿不过两英里远。但他以多年养成的固执态度重复道:“这是 同一条路 。这里是 起点 ,它似乎沿着直线逐渐离我们远去,但它来回折返得很频繁,因此它从未远离过我们的边界,有时还能直接接触到它。”他在护城河边弯下腰,沾水在地上描画出一幅荒谬的迷宫图案。当我们穿过草地走回去时,我试图说服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就当这条路有时会来回折返,但这也符合我们规律的一部分。说不准这条路总体的趋势就是向前的呢?尽管现在路的尽头是什么还不明确,它可能是某座我们能触碰到天空的高山,又或是越过悬崖进入大海。但它总是前进的——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追求卓越。而这也给了我们你们所缺乏的动力。就比如那个经过我们的男性,他是跑得很快,跳得很高,游得也很好,但我们有人可以比他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游得更好。
专业化产生的结果能让你大吃一惊。同样,那个唱歌的女孩——”
突然我打断了自己,感叹道:“天哪!我可以发誓,在那儿的不是Miss Eliza Dimbleby吗!(文章第一段出现过的教育家)她怎么还踏入了这里的喷泉嬉戏!”
男人表示相信我说的话。
“这不可能!我把她留在了路上,而且今晚她有坦布里奇韦尔斯(位于伦敦东南部)的讲课安排。为什么?她从伦敦的加农街出发的火车应该在今天的——好吧我的手表像其他东西一样不转了。总之她是最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
“人们总是对彼此的相遇感到惊奇。各种各样的人都会穿过树篱,不断涌入进来——不管他们是在比赛中遥遥领先的人,还是落后的人,还是被抛弃等死的人。我经常站在边界附近,听着路的声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并想知道有没有人从那条路上离开。我很高兴能帮助掉进护城河里的人,就像我之前帮了你一样。因为我们的家园还在慢慢填满中,尽管它是 为全人类准备的 。”
“人类有其他的目标,”我温和地说,因为我相信他是好心的。“我必须加入他们。”我向他道了晚安,因为太阳正慢慢落下,而我希望能在天黑前上路。令我震惊的是,他猛地抓住我的手,大叫道:“ 你还不能走! ”我试图甩开他,因为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了,他的礼貌也让我感到厌烦起来。但是无论我如何挣扎,这个令人厌烦的老头都不愿放手。而且,由于摔跤也不是我的专场,我被迫继续跟着他走。
确实我也无法自己一个人找到进来的地方。我希望当我看过他要我看的他所担心的其他地方后,就能带我回去。不过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过夜,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地方,我也不相信这里的人,尽管他们很友善。虽然我很饿,但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吃牛奶和水果组成的晚餐。当他们送我鲜花时,我立马偷偷扔掉。夜色下,他们像牛一样卧下休息了:有的人躺在光秃秃的山坡上,有的人成群结队地睡在山毛榉树下。在橘**的夕阳下,我跟着我不受欢迎的向导匆匆赶路。我累的不行了,因为缺乏食物而显得昏昏沉沉的。但我仍不愿就此屈服,喃喃自语道:“ 给我以生命 ,伴随着它的奋斗与胜利,伴随着它的失败与仇恨,伴随着它深刻的道德意义和未知的目的!”
终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环绕着的护城河被另一座桥横跨,这里有另一扇门拦在树篱的边界线中央。它和我前面看到的第一扇门不同,它像 牛角 一样泛着半透明的光,而且是向 内 打开的。尽管如此,在微弱的光线下,我再次看到了我离开时的那条路——单调的,尘土飞扬的,两边是棕色的嘎吱作响的枯枝树篱,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如此。
我对这幅光景感到 奇怪的不安 ,这种不安让我失控。此时,一个男人从我们身边经过,他晚上要回山里去。他肩上扛着一把镰刀,手里拿着装有某种液体的罐子。我忽然忘记了我们种族/竞争(race)的使命,忘记了眼前的路。我不受控制地冲向这个男人,把罐子从他手中夺过来一饮而尽。
它的味道并没有比酒烈多少,但在我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它一下子就征服了我。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我看到老人关上了大门,听见他说:“这里就是你的路的 终点 ,通过这扇门,人类——所有剩下的人, 将成为我们 。”
虽然我的意识正逐渐湮没,但好像在彻底消失之前散开至无边无际。我能感知到夜莺婉转的歌声、看不见的干草的气味,还有刺破逐渐暗淡的天际的星星。那个被我偷了酒的男人轻轻地把我放下,让我睡去。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到他是 我的兄弟。
施工完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