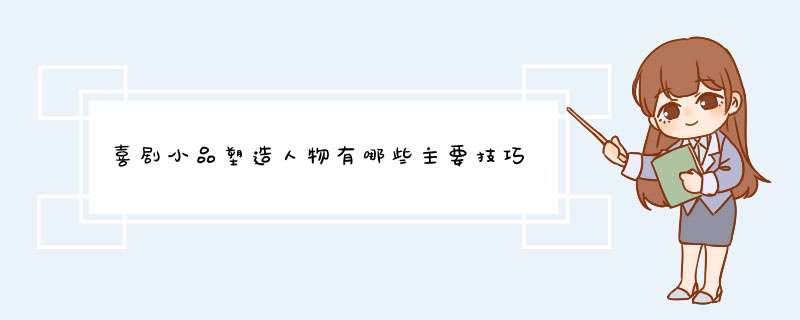
喜剧小品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它要写出表现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只有这样,作品才有了意义。
喜剧小品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样式,它的特点决定了布景、道具等舞台表演手段的简化和情节结构的淡化,但是人物塑造却是不可简化、淡化的。为了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喜剧小品的创作要恰当运用各种艺术技巧,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
第一,对比。
喜剧小品的人物与其他剧类相比要少得多,就近十年在舞台上出现的作品而言,少可一人,多则数人,而大多为二三人;剧中的人物之间大多不存在各种复杂的关系,大量存在的也不是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性格上的某种差别、对立。写好这种差别和对立,就可以在对比中突出人物的鲜明性格,如恩格斯所说的:“ 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在生活中,人们的性格区别是丰富多彩的,而当我们把生活中的人物塑造为典型后,这种区别就形成各自鲜明的性格,这样,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间就有了鲜明的对比。
小品《相亲》就是用对比的手法,使我们看到了两位老人的性格差异。剧本塑造的老蔫和马丫,一个是鳏夫,一个是寡妇,有着同病相怜的处境,然而对于可以唾手而得的幸福,前者敢于大胆追求,后者则顾虑重重,不敢越雷池一步,两人的性格就是在对待黄昏恋的不同态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试想,如果把马丫也写成直爽痛快地表态接受求婚,这个小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简单化,人物就不典型,就写了两个性格相同的人物,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在一些针砭时弊的小品中,对比是塑造人物不可缺少的技巧。比如小品《送礼》就用了对比的手法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昭然若揭。剧本的主旨是批评送礼行贿的不正之风,如何表达这一主题思想呢?作品为我们设计了两种人物,一为送礼者,一为送礼的对象,一反一正,那个为一己私利行贿的送礼者三次碰壁, 终于在浩然正气的李局长面前显出了他卑劣渺小的原形。而送礼的对象这一组人物的思想性格也有着差别。第一个(丈母娘)见礼颜开,贪得无厌,她与后三个送礼的对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个(保姆)心地善良,对自己曾受骗上当于送礼者后悔不迭,对送礼者的无耻行径气愤不已;第三个(离休干部)善于识破送礼者的诡计,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第四个(女局长)为官清廉,对不正之风决不手软。通过对比,不仅使正反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对几个正面人物性格特征的差异也作了区别。
郭达、蔡明、句号表演的喜剧小品《送礼》。
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年龄、环境等因素的变化都足以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所变化。小品运用对比的手法去表现人物的这种复杂性,有利于性格的丰富化。《又是秋叶飘落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悲剧小品,但其中也不乏喜剧性因素。这个小品就是用对比手法来表现铁柱与玉凤自身的这种变化的。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玉凤自作主张把孙女的婚事包办了,孙女与铁柱的哑巴孙儿定了亲,对此,铁柱不仅不反对 而且深表谢意。剧本如果只写了这一事实,就谈不上主题的深刻性与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剧本以倒叙手法表现了五十年前铁柱和玉凤曾经是一对企图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而如今他俩自己又成了封建礼教的推行者,两相对比,便形成了人物性格上的强烈反差,丰富了性格的内涵。
第二,陪衬与烘托。
陪衬是借助人物相互关系的映衬来突出性格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往往在人物较多、性格相近的喜剧小品中得到运用。剧中作为陪衬的人物,虽然属于次要角色,但却是剧情发展中可能存在或必然存在的人物,决不是简单的生拼硬凑。
在喜剧小品《打麻将》中,丈夫与小姨子是两个性格相近、遭遇相同的人物,后者的丈夫嗜砌“长城”,赌输了就向妻子要钱,不给就打,为了免遭拳脚之痛,小姨子只有求援于姐夫,决无反抗丈夫之勇气;前者的妻子是麻将迷,输了钱回家,丈夫不仅要卑躬屈膝地为其按摩酸痛的手臂,还会享受妻子赐予的“金光灿烂”的耳光,并要答应外出筹措赌资,丈夫对此的反应是忍辱负痛,求援于小姨子。尽管剧本的结局戏剧性地以丈夫取得胜利、制服妻子告终,但丈夫的命运仍是悲剧性的,以小姨子的软弱陪衬其姐夫,使男主人公性格的悲剧色彩得以加重,这正是作者所着意刻画的,即所谓“以软弱陪衬次软弱”吧。
烘云托月是塑造人物常用的方法,烘托就是用环境气氛加深人物性格。当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感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矛盾时,人物的形象就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
巩汉林、岳红表演的喜剧小品《打麻将》
小品《又是秋叶飘落时》成功地运用烘托方法来加深人物性格及其社会意义。 剧中人铁柱与玉凤五十年前曾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五十年后他俩又亲手促成了自己孙儿女的包办婚姻,使又一代人的青春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之中。为了加强这种性格的悲剧性,剧本设计了满天黄叶飘然落下的场景,青春似同秋天的落叶飘然逝去。与此同时,当铁柱为感谢玉凤而跪倒在玉凤脚下时,玉凤却乐极生悲,“两眼突然一黑栽倒在铁柱怀里”,形喜实悲,这是他俩性格之使然。剧本又在此时设计了《迎亲曲》顿起的音乐,一面是喜庆的乐曲,一面是对五十年来悲剧人生的咀嚼,在喜与悲的对比中,性格的悲剧色彩浓化了,喜庆的氛围烘托了人物的悲剧性格。
在喜剧小品中,烘托往往落笔于高潮中,这是深化性格的最佳时机。小品《二娘开店》塑造了一个亲切善良的酒店女主人形象,她伺候酒客周到殷勤,却使酒客借酒发泄邪念,对她动手动脚,为了使两个司机不致醉后开车闯祸,女主人与之痛饮,包揽了整瓶酒。剧情的高潮是女主人与两个司机对饮的场面,她借酒劲踩凳子上桌,左右开弓与酒客猜拳,两个司机怎么也不是她的对手,场面好不热闹,而剧本正是借这种兴奋热烈以及孕含着酒后开车的教训的酒令来烘托她心中的凄楚与悲愤,以致当她划出“一个寡妇,独守空房,男人玩命,女人······断肠······” 的最后一拳后,“音乐起哀怨的乐声,二娘泣不成声”,二娘的善良与高尚人格至此也可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第三,迂回。
迂回是指小品在刻画人物时不正面强攻,而是或旁敲侧击,或层层剖析,使人物最终才显示其庐山真面目。
喜剧小品《照相》要表现的是某处长的一种思想境界,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呢?剧本从照相师设法逗其笑着手,玩具不行,光荣称号也不行,一个个试了过去,逐层剥落,逼近内心深处,最后在照相馆经理的一句“你明天就要升局长了”的诱发下,处长终于笑了。于是摄影机响了,摄下了包藏在笑容中的内心世界:一个升官的愿望。这是多么生动而深刻的瞬间啊!观众与照相师的思路同步,一个个猜测被否定了,直到撩开最后的面纱,这个处长的庸俗人生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四,铺垫。
铺垫是指在主要人物上场之前,由其他人先作介绍,让观众对即将上场的主要人物有所准备。从结构上说,铺垫的内容就是小品中无法再现的情节;就人物而言,铺垫的内容就是戏剧冲突的因素。
小品《求求你》就是借助铺垫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的。此剧是对农民科技致富之路的反映。全剧人物为兄弟二人,身为记者的兄先上场,在城里工作的这个哥哥总是担心弟弟来访,害怕经济拮据的农民弟弟向自己有所索取。哥哥的这种自白是对尚未上场的弟弟家境贫困的铺垫,也预示着弟弟一旦到来将会引发的矛盾冲突。弟弟终于来了,在一场戏剧性的误会后,弟弟从那个背在身上的旅行包中取出了五千元现金,摆在哥哥那张旧式的办公桌上。“求求你!”现在到底谁该求谁? 求求你!不该是弟弟说的了,他靠科学养狐狸致富,有了钱,来回报哥哥,弟弟只要求为兄的说一句“求求你!”这是致富后典型的农民喜悦心理。
铺垫,在情节上设了悬念,使人物的塑造处在动势之中,没有这一铺垫,情节的展开就会缺乏依据,弟弟上场后的行为也会使观众无法理解。从索取到回报,弟弟的变化如此之大,一个靠科技致富的农民典型就形象地呈现在观众的视界中了。若不采用铺垫法,剧本势必将要增加弟弟向哥哥屡屡求索的情节,这样,情节量就会加大, 小品就变成短剧了。
潘长江、巩汉林表演的喜剧小品《求求你》。
第五,反复。
反复就是以不断地重现人物相似或相同的语言或动作为手段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有时是对人物情绪、思想的强调,有时是细腻地刻画着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人物的性格就是在那一系列的举手投足中被深化的。转自手机胖蛋小品mpangdancom小品《八月的离别》对于反复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整个剧本就是立足于以反复手法刻画女主人公瑞瑞的情意的,在憨厚纯朴的男主人公成喜眼中,瑞瑞不过是个天真的“丫头片子”,谁知这个情窦初开的农村少女已有心于他,于是在成喜准备坐火车启程上大学的路上,瑞瑞借机拦住了他,拦住他,并非为了表白几句甜言蜜语,这不是山沟里姑娘的本色。话是要讲的,但不仅是话,还有实实在在的事,那才是对心上人真正的关切。而这种关切并不容易启齿,聪明的瑞瑞是以等火车要看时间为契机来表白她的情意的。剧中这样写道:
瑞瑞:俺有个表。
成喜:你?!
瑞瑞:反正俺也用不上,要不,你戴上吧?
成喜:我?······
瑞瑞:(突然不好意思)就是大了点······(一把掀开背篓上的青草,摸出一只硕大的马蹄闹钟,挂在那人儿的脖子上)
但篓中取物这一动作并未到此为止,瑞瑞借着对季节、旅途、学校生活的议论,像变戏法一样把这一动作反复了七次:第二次“掏出了一个土陶烫壶”,为的是让成喜不必有钻凉被窝之忧;第三次“摸出一个麦秆笼子”,好让成喜在火车上解闷;第四次从背篓中取出一捆包谷秆,专为火车上解渴用;第五次“取出一条又长又宽的红布腰带”,可以装钱防偷;第六次“摸出一个特号大老碗”,是把她哥的碗偷出来,让成喜在食堂买饭方便点;第七次则倾篓而出,“将背篓朝地上一扣,倒出一只口袋”,里面装着一堆蒜,要成喜一天吃一,想着家乡······
剧本把瑞瑞从背篓中取物的动作反复了七次,同样一种动作,内容却不一样, 它刻画了少女对心上人体贴入微的细腻感情。这反复的动作的结果,使动作的对象也表现出感情的变化。第一次动作的结果,成喜表现为懵懵懂懂,对此不可理解;第二次惊得“张口结舌”;第三次是“目瞪口呆”;第四次则使这个老实的青年冲动地喊出:“······瑞瑞”; 第五次动作后,他“瞅瞅腰上的红腰带,望望瑞瑞,突然结巴起来”,终于这样说:“瑞瑞,我,我一直还把你当成个小、小丫头片儿,谁知道,这个,那什么,我(想拉瑞瑞的手······)”这个憨厚纯朴的人已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第六次,当他接着碗后,就发出了“我忘不了你,不管我到了啥地方,我都忘不了你”的誓言;最后一次,他连瑞瑞请他吃什么都还没有弄清,就连声允诺:“我吃,我一定吃!”他已被少女的一片真情熨帖了冲动的心,变得百依百顺,与开头那种听了瑞瑞的话后只是“漫不经心”,只是“搔头”相比,判若二人。试想,如果把这七次动作一次性地完成了,人物的性格就变成了图解,也就无戏可言。可见,反复手法的巧妙运用,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种有效方法。
第六,夸张。
夸张是喜剧小品刻画人物必不可少的一种技巧。夸张是通过人物的变形而产生戏剧效应,亦庄亦谐,富于幽默感。
夸张有两种表现形式:动作夸张和语言夸张。动作夸张是一种直观夸张,它通过观众的视觉,直接调动联想,形成扩散性思维,并进行再创造,使人领悟其蕴藉的意味。在哑剧小品中夸张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如王景愚表演的《吃鸡》,其中有一个想咬断鸡骨头的动作:演员绕着假想的桌子走了一圈,鸡仍未被咬断,吃鸡者的这种韧性就是在这种高度的动作夸张中被刻画出来的。在喜剧小品中,动作的夸张可以和巧设的情境同步。比如小品《手术之前》开场, 丈夫胸前吊了大彩电,身后背的是排烟机,彩电上端还堆着电饭煲,左手挽着录音机,右手捻着电熨斗,由于面部被遮,观众几乎可以把它看作为电器柜台,但这“柜台”在移动着,这位丈夫在晃晃悠悠地朝前挪步,观众从他那句“我的老婆哎,礼品办齐!”的台词中,才明白了真相:为了使住院的丈母娘能顺利地手术,他要给医务人员送礼。这一夸张动作刻画了丈夫的变形,这种无奈的变形讽刺了不正之风的畸形世态,而归根结底还是表现出人物的可笑性和可鄙性。
动作的夸张应讲究得体和适度,夸张的失体和过度往往使人物的刻画效果适得其反。有一出小品用这样的夸张动作来表现一个信息公司经理的公务繁忙:桌上四部电话铃声此伏彼起,经理左右开弓忙着接电话,最后他摔掉电话听筒在地下打滚。就接受美学而言,这种“打滚”显然是一种丑陋的失态,是无边的夸张, 没有把握住夸张的度,使这一小品变成了闹剧。如果把主人公的打滚改成趴在桌上气促、翻白眼,效果也许要好得多。
动作夸张是通过观众的视觉来接受的,而语言夸张是通过观众的听觉产生效应的。小品《手术之前》中就有这种由扩大与缩小组成的对比式语言夸张:在讨论怎样向医务人员送礼时,妻子认为送礼要按“劳”取“酬”,丈夫就说:“‘劳’大‘酬’ 高的当然是主刀医师,彩电非他莫属。他得了彩电,手下留情,刀口开得小,开得浅,丈母娘少受皮肉之苦;否则一刀切下去,10公分见方,老太太可要遭大罪!”但妻子却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彩电应送给麻醉师,因为万一麻醉程度不到位,岂不痛死老太太!而丈夫又据理反驳:“不行!麻醉师彩电一到手,太兴奋,药量过大,麻醉过深,丈母娘岂不一命呜呼!”两人对比式的语言夸张,合乎情理地刻画出夫妻俩的矛盾心态,成为这一喜剧小品塑造人物性格的巧妙手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