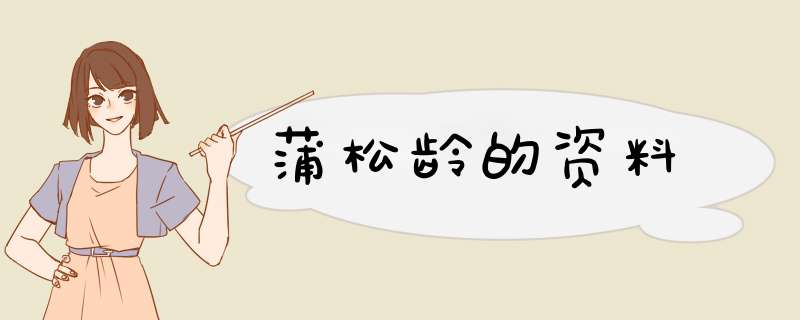
蒲松龄(1640-1715,明崇祯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世称“聊斋先生”�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是“写人写鬼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是“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聊斋志异》书成后,蒲松龄因家贫无力印行,直至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著名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为内容编写的戏剧、**、电视剧达160多出(部)。�
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1卷,100余阕;戏本3出(考词
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蜚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
《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
《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 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 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
《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 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 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
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 (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 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 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 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 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 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
《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
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更多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
二、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 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 ,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
《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 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三、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化、强化,而男性则被痴化、弱化,这造成了男女性角色的错位。女性形象也是丰富多采的,而男性形象则相对单一化、类型化,表面看来是作者重视女性,从中也透露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那么蒲松龄 的女性观实质是什么?
“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和化身,人物作为叙述主体,其自我言说也 就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它们是作者之自我与个性的张扬。”④《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书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作者自身角度来说,蒲松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描写本阶层的生活自然有得心应手之便,一部《聊斋志异》读下来,人们的记忆当中往往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寥寥几个,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x生”。《酒友》中的酒鬼叫“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叫“冷生”,《青梅》中的那位痴郎则称作“程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叶生》开篇一句说道:“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惚、 奇妙。作者曾明确的宣称《聊斋》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史,乃“异史”。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男性人物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因为作者把自身寄托在这些书生身上了。原因何在?首先,这与蒲松龄自己的个性、气质及思维方式有关。他是个才子,曾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乡里,思维活跃,积极追求创新也富有创新能力,对现有的思想,能用自己的头脑加以分析思考。其次,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有关,他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社会也因而产生了反叛的思想。蒲松龄通过其笔下较多的人物,批判社会、科举制度、官吏的腐败等。再次,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的蒲松龄是以功名作为追求目标的,自然而然也接受了封建的女性观,正面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佐君子以成”的淑女、贤妻、良母,在一些优秀的、反映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英雄美人”。虽然他对此作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其改变还是为男性所用的。
从男性本质角度来说,书生类男人是古代受约束最甚的男性,男性与生俱来的攻击性的冲动,在书生类男人身上明显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将军士兵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战场的厮杀强劫当中,官宦贵族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争权夺利和鱼肉人民之上。像蒲松龄这样的书生类男人只能把这种冲动发泄的文学作品当中,因此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两方面的蕴涵,一是她们往往持有一种反叛姿态,其行为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反世俗的色彩,超越规范而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某种理想的化身。二是在狐女鬼女身上实际寄托了作家的某种理想与情感,反映男性作家某种潜意识。
蒲松龄为其笔下的男主人公“配备”得到美化和强化的女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他自己对女性的渴慕。所以说蒲松龄是本性里有着大男子的“喜新厌旧”意识和“一夫多妻”的愿望。
蒲松龄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能力的增强以及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些女性是有点翻身解放!看起来这些女性绚丽多姿了,打破了“花瓶”模式!蒲好像赋予这些女性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像给鹦鹉一样带上了脚环,困在房子里,供那些困顿中的书生赏玩。有了翅膀不能飞,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啊!
古代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弃妇、怨妇、思妇、烈女等女性形象,很少有花木兰、穆桂英的形象,而在《聊斋志异》中觉醒的女性随处可见。西方文学常把婚姻比做坟墓,而《聊斋志异》让我们相信只有婚姻才能建立完满的男女关系。这样一来,男人就能幸福的拥有娇妻和美妾,而两个共事一男的女人也会亲如姐妹,轮换地侍寝,欢乐地忙于生育、持家,帮助男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类想得太好,编得太美的故事常常肤浅到成人童话的程度,我们看起来觉得有点乏味和可笑。但是,蒲松龄笔下的女性是觉醒了,地位提高了,男女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透出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光芒,尽管在男性视角的笼罩下其光芒毕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具有这样一个空想也是一种进步。</CA>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蜚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一、《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二、《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三、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化、强化,而男性则被痴化、弱化,这造成了男女性角色的错位。女性形象也是丰富多采的,而男性形象则相对单一化、类型化,表面看来是作者重视女性,从中也透露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那么蒲松龄的女性观实质是什么?“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和化身,人物作为叙述主体,其自我言说也就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它们是作者之自我与个性的张扬。”④《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书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作者自身角度来说,蒲松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描写本阶层的生活自然有得心应手之便,一部《聊斋志异》读下来,人们的记忆当中往往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寥寥几个,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x生”。《酒友》中的酒鬼叫“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叫“冷生”,《青梅》中的那位痴郎则称作“程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叶生》开篇一句说道:“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惚、奇妙。作者曾明确的宣称《聊斋》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史,乃“异史”。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男性人物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因为作者把自身寄托在这些书生身上了。原因何在?首先,这与蒲松龄自己的个性、气质及思维方式有关。他是个才子,曾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乡里,思维活跃,积极追求创新也富有创新能力,对现有的思想,能用自己的头脑加以分析思考。其次,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有关,他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社会也因而产生了反叛的思想。蒲松龄通过其笔下较多的人物,批判社会、科举制度、官吏的腐败等。再次,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的蒲松龄是以功名作为追求目标的,自然而然也接受了封建的女性观,正面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佐君子以成”的淑女、贤妻、良母,在一些优秀的、反映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英雄美人”。虽然他对此作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其改变还是为男性所用的。从男性本质角度来说,书生类男人是古代受约束最甚的男性,男性与生俱来的攻击性的冲动,在书生类男人身上明显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将军士兵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战场的厮杀强劫当中,官宦贵族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争权夺利和鱼肉人民之上。像蒲松龄这样的书生类男人只能把这种冲动发泄的文学作品当中,因此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两方面的蕴涵,一是她们往往持有一种反叛姿态,其行为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反世俗的色彩,超越规范而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某种理想的化身。二是在狐女鬼女身上实际寄托了作家的某种理想与情感,反映男性作家某种潜意识。蒲松龄为其笔下的男主人公“配备”得到美化和强化的女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他自己对女性的渴慕。狐鬼花妖和书生的恋爱模式有人将它归纳为“女鬼三步曲”:一是异类女性自荐枕席;二是男人欣然接受,遂同寝处;三是幽明殊途,在片刻的欢乐后分离。⑤那么蒲松龄如此安排有什么目的呢?穷书生不但花不起钱纳妾、嫖妓,而且缺失行动的能力,没有勇气承担偷情的罪责。他们希望一切私情都发生在绝对密闭的情况下。因此,与他们幽会的女性全都保持着诡秘的行踪,半夜来,天明去,完全不受常识的时空限制。仿佛她们随时都在准备接受男人的需要,常常是在对方感到寂寞的时候,她们就及时送来了一片温情。在消受艳福的事情上,最使男人感到麻烦的就是事后的责任,蒲松龄始终把一切都编得很美,他告诉我们,雨收云散之后,侍寝的女性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她们不用生计拖累男人,也不要求这样那样的承诺,她们只充当临时的性伙伴,很少在白天的世界里给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带来干扰。确切的说,她们在故事中主要扮演了一种为他人弥补人生的缺憾的角色。蒲松龄在《青梅》的结尾感慨道:“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从某种程度上说,蒲松龄正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显示他深信“造物所必争”的事情,在想象中把世俗颠倒了的价值再颠倒过来。鬼妖美女的主动献身及其一反流俗是深情厚意便是他自我肯定的形式,是他唯一能自慰和慰人的美梦。在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意识主使下,异类的女性于是多少闪现出神性的灵光,向需要帮助的凡人布施色相和情爱,成了在男女关系的范围内实行利他主义的善人。正如蒲松龄在向上天呼吁时所说:“吾愿恒河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哭众生矣。”(《凤仙》)《聊斋志异》中美化了、强化了的女性是母性与妻性的合体。人类学家认为恋母是寻求庇护,恋妻是为寻求性爱。母性庇护不同于男(父)性庇护,它不仅能帮助弱者战胜对手,克服困难,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使弱者(或不幸者)达到自身的安逸,取得生活的温存。当一位穷困潦倒,精神委靡的书生陷入某种困境或绝境之时,一位美丽的狐女出现在眼前,不仅给予他性爱的满足,而且还给予他慷慨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安全感。母亲和妻妾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救助是无条件的,主动和自发的。但是妻妾的角色表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她不仅自己为桑生生子,而且为桑生找了妾。《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这些狐女,以其母性料理家政,以其妻性哺儿事夫,完全是妇德的化身,是性爱与道德完美的结合。那么作者出于何种目的让女主人公在完成了给其以性爱,助其以富贵,延其以子嗣后总是离开人间呢?是因为犯了某种禁忌,还是出于作者的个人潜意识里的某种愿望呢?按禁忌主题来划分的话,这种人和动物结合是属于天鹅处女型禁忌主题。⑤这类禁忌表现在人与异类结合后,当被异类发现是非人类之后就马上消失。如在《绿衣女》中绿衣女在被发现异类后,在桌上爬出一个“谢”就消失了。这类在《聊斋志异》中是属于少数的,的则是尽管发现对方为异类,男主人公宁愿折寿也要和之结合。然而在女性完成了这“任务”之后,她们的命运就难以脱离传统女性的轨迹,她们尽管才能出众。要么离开男性,要么留下来继续为男子服务。在《幸十四娘》中的幸十四娘自己逐步变丑,并为找好“替身”后离开。而《颜氏》中才女颜氏嫁给“文与卿似是两人”的顺天某生,她先是“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当夫“再试再黜”“嗷嗷悲泣”时,负气女扮男妆,代夫应考,求得了功名富贵,不但丈夫坐享侍丽,翁姑也受封于新妇。颜氏确实对男权传统所规定的妇道进行了冲击,但这只是男权藩篱里面的小动作。她因“怒其不争”,在男装的掩饰下开始她的平步青云的活动,等待她的是作为妻子的角色,最终以“二女共事一夫”为结局。所以说蒲松龄是本性里有着大男子的“喜新厌旧”意识和“一夫多妻”的愿望。蒲松龄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能力的增强以及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些女性是有点翻身解放!看起来这些女性绚丽多姿了,打破了“花瓶”模式!蒲好像赋予这些女性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像给鹦鹉一样带上了脚环,困在房子里,供那些困顿中的书生赏玩。有了翅膀不能飞,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啊!古代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弃妇、怨妇、思妇、烈女等女性形象,很少有花木兰、穆桂英的形象,而在《聊斋志异》中觉醒的女性随处可见。西方文学常把婚姻比做坟墓,而《聊斋志异》让我们相信只有婚姻才能建立完满的男女关系。这样一来,男人就能幸福的拥有娇妻和美妾,而两个共事一男的女人也会亲如姐妹,轮换地侍寝,欢乐地忙于生育、持家,帮助男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类想得太好,编得太美的故事常常肤浅到成人童话的程度,我们看起来觉得有点乏味和可笑。但是,蒲松龄笔下的女性是觉醒了,地位提高了,男女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透出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光芒,尽管在男性视角的笼罩下其光芒毕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具有这样一个空想也是一种进步。
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
《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
《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 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 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
《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 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 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
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 (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 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 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 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 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 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
《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
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更多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
二、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 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 ,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
《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 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