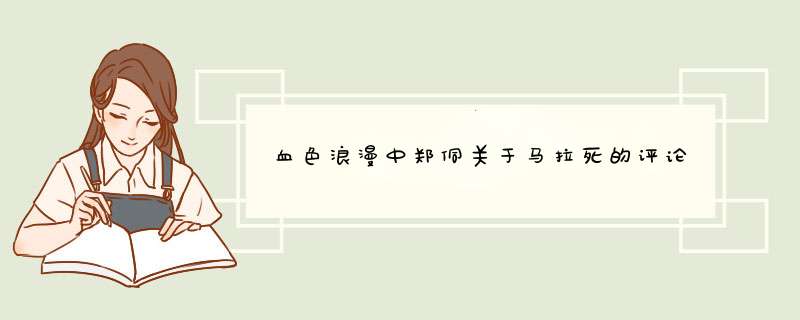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 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剌杀马拉的人,夏 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 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 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 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 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 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 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 ,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 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 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的气质、谈吐、衣着及 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 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 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 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 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 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 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 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 ,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 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
们的 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 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 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 ,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 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 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 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 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 《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 只能是您的一孔之见。"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文革初期时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请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 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 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
《血色浪漫》:钟跃民的爱情
钟跃民是《血色浪漫》剧中一号主人公,他在爱情方面的经历,非同一般,可圈可点。
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脱俗”,即周晓白对他的理解:他是个干大事的人,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女人不要奢望用婚姻套住他。而钟跃民自己对此也有相同的解释,他曾给高玥说过下面意思的话:听到一个女人对相爱的男人说“我把我这一生可都交给你了”,他觉得这话说的太重了,也太累人了,若是他钟跃民听了这话,就承当不起。
但这能够确定为是钟跃民的爱情观吗?
回答似乎应是无法确定。原因是钟跃民并非是一个女人也不钟爱的人。他爱秦岭,而且爱的十分真诚。真诚的见证是:他参军入伍以后,一直给秦岭写信,秦岭不回信,他转给郑桐写信,要郑桐一次次去追问秦岭为何不回信。这实际上将自己退缩到与周晓白交往中周所处的位置,即秦岭代替了钟跃民成为交往关系中主动的一方,钟跃民代替了周晓白尝到了被动是何滋味。这种被动一直延续到又一次见到秦岭。在这之前,他从未忘记寻找秦岭。此外,他与周晓白、高玥相爱过,与何眉有暧昧关系,但这些人都没有听到过由他开口说出要结婚的话。惟有秦岭,得到了他的求婚,希望秦岭能够“名正言顺地做他的妻子”。
可为什么秦岭会得到钟跃民的青睐呢?引钟跃民的一句话是:“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在钟跃民的心底深处,蕴藏着对音乐的独到理解。在他看来,他所接触的女人中,也惟有秦岭身上储存着可观的艺术细胞。他因此而沉醉于其中,不可自拔。
那么,如何解释周晓白“女人套不住”钟跃民的这一理解呢?只能说这里面有自嘲的意思,她实际上并未“看透”钟跃民。
又如何看待高玥所说的是她把钟跃民“套住了”的话呢?只能说这是一厢情愿的认识,她即使追到青海,也无法将钟跃民“套住”。
钟跃民还要等待,等待下一个秦岭的出现。
秦岭,这个女人成为钟跃民心目中一个标准,为难着钟跃民的婚姻。
1、1968年,北京的钟跃民和好友袁军、郑桐等整日游荡在大街上,为单调的生活寻求着刺激。在一场钟跃民看来似乎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恶作剧中,高雅、纯情、浪漫的周晓白无意中闯进了钟跃民的生活,二人的生活悄无声息的改变着。
2、晓白的高雅、浪漫唤醒了潜藏在跃民内心深处的一种久违了的渴望。在袁军、郑桐等童年伙伴的戏弄下,钟跃民向晓白展开了执著的追求。这种突如其来的追求,对于周晓白这等靓丽的焦点女孩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晓白游刃有余,跃民无所适从。在时间面前跃民潜在的艺术气质得到点点挥发,点点挥发的艺术气质俘获着晓白,高傲的晓白被彻彻底底的征服了,她情愫发展,一天比一天强烈。
3、晓白沉浸在恋爱的快乐中,当跃民被郑重地带到晓白父母面前时,这个原以为被自己牢牢掌握的爱情出现了危机,跃民告诉晓白父母他对这段爱情不能给予任何承诺,晓白如坠万丈冰窟。在跃民羡慕的眼神中,晓白带着惶恐和好友罗芸、袁军一同参军入伍,跃民和好友郑桐也来到农村。
4、信笺维系着晓白和跃民的恋情。晓白的担忧终于成了现实,青春、质朴的秦岭让跃民真正懂得了羞涩、懂得了含蓄,秦岭的悦耳的歌声、秦岭的一切都让跃民沉醉,晓白失恋了。在极度的绝望中,晓白走到了对她倾慕已久的张海洋的身边,此时满腹心机的好友罗芸却对袁军展开了狂热的追求。参军入伍的喜讯突然而至,跃民的心愿即将实现,可此时的跃民却备感惆怅,因为平生真正的恋爱刚刚开始。在村边的茅草丛中,跃民真正拥有了秦岭,在不舍中跃民走了,当了一名出色的侦察兵。
5、改革开放后,童年伙伴们结婚了,张海洋、晓白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钟跃民转业回到北京,他们又相聚了并且他又遇到一个可以为钟跃民做任何事的一个女人:高玥,在钟跃民的嬉皮笑脸的调戏下他们成为了合伙人。转业后的跃民生活窘迫,在黎援朝的帮助下跃民到他的公司任职。长久的寂寞让跃民接受了爱慕虚荣的秘书何眉,直到一日在音乐厅邂逅了思念中的秦岭。秦岭、跃民的爱情火速复燃,而此时的秦岭非彼时的秦岭,秦岭隐瞒着已嫁富豪的婚姻事实。冷落让何眉恼羞成怒,她举报跃民挪用巨额公款。
6、跃民、晓白和他们童年的伙伴走在烽火台上,一抹血色的夕阳映照在他们身上,映照着他们的浪漫人生。
小说:《血色浪漫》是都梁编著的小说。
讲述1968年,北京的钟跃民和好友袁军、郑桐等整日游荡在大街上,为单调的生活寻求着刺激。在一场钟跃民看来似乎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恶作剧中,高雅、纯情、浪漫的周晓白无意中闯进了钟跃民的生活。
鉴赏:
血色浪漫之友谊论
《血色浪漫》中钟跃民和袁军成了朋友,周晓白和罗芸也建立了友谊。当生命受到威胁,前者依然会选择朋友,虽然这看起来有点流里流气;当面对爱情和前途,罗芸却选择后者,更是不惜以谎言为代价用周晓白的前途换取自己的前途。
同样是友谊,为什么有的亘久弥香,有的却如一壶浊水。这种情况下把朋友做一个区分是有必要的,那些是绝对朋友,那些是相对朋友。爱因斯坦说,物理定律与参考系的选择无关,那么绝对朋友与参考系的选择也无关。人们平常所交的朋友大多是相对朋友,在甲需要时乙能给甲以帮助,在乙需要时甲能给乙以帮助,当然前提是你的需要不要触动他的利益,对一个相对朋友来说,这就够了。
下面谈谈绝对朋友:
朋友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有些相处了几年的朋友有时却不如交了几个月的,这里面应该主要是个人特色的原因。向后推,可以得出交友必慎。向前推,甲和乙为什么能成为绝对朋友。我想大抵有以下三个原因:
共同的信仰。人是应当有信仰的,而且不能低俗,最好有点理想化。因为如果信仰低俗的话,比如说甲和乙因共同信仰高官厚禄成为朋友,突然有一天,甲和乙面对着同一个职位,这个时候对甲来说,乙和职位就产生了矛盾,甲只能不择手段选择职位,否则就不叫信仰了。但如果甲和乙因都信仰广义相对论而成为朋友,对甲来说,乙和广义相对论会产生矛盾吗?不会,就是因为信仰的理想性。这样的话,即使面对同一个职位,甲也不会不择手段的去陷害乙,因为职位不是他的信仰,他们都不在乎职位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一起生活的经历。这的确能够建立友谊,但这种友谊会随着时间而渐渐消逝,只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甲和乙从出生就一块玩,这并不是说邻居就行,这需要机缘;二是共患过难,这需要机会。除了这两种情况外建立的友谊,时间一长,必会消融。即使甲特别仗义、不吝财富,十年如一日,乙也早已不是当年甲所认为的乙,因为这种友谊的基础并不牢固。好像需要给绝对朋友下个清晰的定义了,举个例子,甲和乙一年不联系了,突然甲去乙家免费吃住了半年,甲没有任何不好意思,乙待甲始终如从前,那么他们应该就是绝对朋友了。
相互利用。这是当下普遍的一种交友观念,我结识你,因为你对我可能有用,这个既实在又实惠。这种交友观念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之所以不反对,是因为成为绝对朋友的前两个条件太过苛刻,只可一遇,不可强求;之所以不赞同,是因为这种利用往往只反映在利益方面,这就低俗了。如果相互利用的是对方的学识、人格等闪光的东西,我是极欣赏的,因为这有点像信仰,有点理想化。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