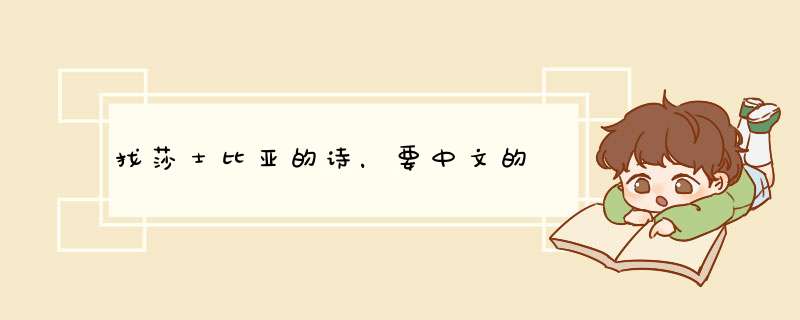
阁下犬马仆 威廉·莎士比亚
太阳刚刚东升,圆圆的脸又大又红,
泣露的清晓也刚刚别去,犹留遗踪,
双颊绯红的阿都尼,就已驰逐匆匆。
他爱好的是追猎,他嗤笑的是谈情。
维纳斯偏把单思害,急急忙忙,紧紧随定,
拚却女儿羞容,凭厚颜,要演一出凰求凤。
她先夸他美,说,“你比我还美好几倍。
地上百卉你为魁,芬芳清逸绝无对。
仙子比你失颜色,壮男比你空雄伟。
你洁白胜过白鸽子,娇红胜过红玫瑰。
造化生你,自斗智慧,使你一身,俊秀荟萃。
她说,‘你若一旦休,便天地同尽,万物共毁。’
“你这奇异的英华,请你屈尊先下骏马。
且把昂然的马首鞍头络,缰绳鞍头搭。
你若赏脸肯贬身价,那我的温存浃洽,
有万般未经人知的甜蜜,作你的酬答。
咱们到这永无嘶嘶蛇鸣的地方先坐下,
坐定后,要紧紧相偎倚,我好把你来吻杀。
“我这吻,决不会因过多而腻得你恶心,
它若越多,它就越会惹得你饥渴难忍。
它叫你的嘴唇时红时白,变化无穷尽。
十吻犹似一吻新,一吻就甜过二十吻。
如果在这样消遣光阴的娱乐中共厮混,
那么,炎夏迟迟的长日,都要去得像一瞬。”
她这样讲,并捉住他汗津津的手不放。
(汗津津的,表示他精力充沛、血气盛旺)
风情激得她颤声叫这汗是玉液琼浆,
世上给女神治相思的灵药,数它最强。
爱焰给了她一股力量,弄得她如痴如狂,
叫她勇气勃勃地,把他从马上揪到地上。
她一只手挽住了缰绳,把骏马轻拢,
另一只胳膊把那嫩孩子紧紧挟定。
只见他又红脸,又噘嘴,老那么心硬,
似木石无灵,不懂什么叫男女风情。
她脸又红,心又热,似一团炭火,熊熊融融,
他脸也红,心却冷,只羞似霞烘,严如霜凝。
她轻快敏捷地——使她这样的是爱力——
把镂饰的缰绳在皴裂的树枝上拴起。
马已经这样系牢,她就连忙打主意,
想把骑马那个人的心也牢牢紧系。
她像愿意人家对她那样,推他仰卧在地。
爱既无法使他就范,她就用力把他控制。
他一倒在尘埃,她也卧下和他并排。
他们用胳膊和胯骨支身,侧卧相挨。
他直皱眉头,她就直抚摸他的两腮。
他开口骂,她就用吻把他的嘴堵塞。
她一边吻,一边把情话续续断断讲起来。
“你要是骂,我就堵住了你,叫你有口难开。”
他又烦躁、又害臊,闹得两腮似火烧。
她就用泪往他处女一般热的脸上浇。
接着又叹息像轻风袅,金发像日色耀,
把汗在他脸上的泪痕,给他吹干拂掉。
他骂她轻佻,说她不知自好,净卖弄风骚。
他还要絮叨,她就用嘴堵得他语咽声销。
空腹的苍鹰,饿得眼疾心急,馋涎欲滴,
抓住小鸟,用利喙把毛、肉、骨头一齐撕。
鼓翼助威势,贪婪猛吞噬,忙忙又急急,
饥胃填不满,食物咽不尽,就无停止时。
她就像这样,把他的额、腮、下颏吻个不已,
因为她吻完了一遍,又从头儿开始吻起。
他无奈只好不抵抗,要他情愿却难想。
他躺在那儿直喘息,气都扑到她脸上。
她把这气吸,像强者吃弱者的肉那样。
她说这就是天降的云液,神赐的玉浆;
她恨不得她的双颊就是花园,花发草长,
好来承受这样甘霖的灌溉,琼露的滋养。
你曾见过小鸟落了网罗,无法能逃脱?
阿都尼在她怀里,就像小鸟落了网罗。
他懊恼,半因羞涩,半因不敢强挣硬夺。
他的两眼越含嗔,他的美貌越增颜色。
本来就满了槽的河水,再加上大雨滂沱,
势必溢出河槽,往两岸氾滥,把四处淹没。
她一直地苦诉衷怀,迷人地苦诉衷怀,
因为她要对迷人的两耳,把心事表白。
但是他却老闹脾气,老皱头,老不耐,
有时羞得脸通红,又有时气得脸灰白。
脸红时她最爱,脸白时她就爱上更加爱,
那比起她所最爱的来,更叫她笑逐颜开。
不管他羞答答,怒冲冲,她看着都动情。
她指着她那永远纤柔、白嫩的手作证,
说她决不离开他那柔软温暖的酥胸,
除非他被她的眼泪所驯服,言听计从;
因为她早就已经泪如雨倾,满脸上纵横。
甜甜一吻,就能把本来没有完的债还清。
他听她作了这样誓词,便把下颏仰起。
但他正要把她所求的东西勉强赐给,
却像鸊鹈在水里那样,稍一探头窥伺,
看见有人了望,就又一下钻回了水底。
因此她虽把双唇噘起,准备他对她还礼,
他却把嘴转到另一边,同时把眼睛一闭。
夏日炎炎中路上的人,即便渴得要晕,
也从来没有像她那样,急于一润渴吻。
她只闻香却难到口,这心痒叫人怎忍。
她泪水如浴似淋,却救不得心火如焚。
“哎呀,”她喊道,“你这孩子心如铁石真好狠,
我不过只求你一吻,又何必这样苦悭吝。
“我也曾有一度被追求得忙,像你这样。
追我的非别个,是战神,威凛冽,貌昂藏。
他在战场上,从未低过头,出名的强项。
他到处战无不胜,从来就没打过败仗。
然而他却是我的俘虏,甘心作我的厮养。
他向我求过现在你能不求而获的欢畅。
“他那伤痕斑斑的盾,百战犹完的甲,
还有长矛,都曾在我的祭坛上闲挂,
他为我,学会了蹁跹舞步,诸般戏耍,
他为我,学会了打情骂俏,斗口磨牙,
耳里厌闻战鼓喧闹,眼里厌看旌旗飘飒;
在我的绣榻上安营,在我的玉臂间厮杀。
“这样,以威势服人的还得服我的威势。
一根红玫瑰链子,就拴得他匍匐在地。
多么硬的钢铁,在他手里都成了烂泥。
然而我对他鄙夷,他却只有奴颜婢膝。
你现在能使制伏了战神的我低声下气,
请不必骄傲夸耀,回答我的爱才是正理。
“你只把你的香唇触到我的嘴唇上,
(我的嘴唇也很红,虽然没有你的香),
那这个吻的甜蜜,咱们就能同受共享。
抬起头来!地上有什么吸引你的眼光?
往我瞳人里望,那儿有你的倩影深深藏。
眼和眼既然成对,唇和唇为何不能成双?
“你接吻不惯?那你就闭上眼,不要看。
我也闭上眼。这样,白天就仿佛夜晚。
只要有一女一男,‘爱’就能取乐追欢。
你要放胆,咱们尽管畅玩,没人看见。
咱们身下这紫络的二月蓝,决不会多言,
它们也不懂得,咱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
“你迷人的嘴上黄毛嫩,说你还是童孩。
但你却早就有秀色可餐,有英华堪采。
行乐须及时,莫疑猜,机会错过不复来。
丽质应该传代,及身而止,只暴殄美材。
好花盛开,就该尽先摘,慎莫待美景难再,
否则一瞬间,它就要雕零萎谢,落在尘埃。
“我若头秃脸麻,形容老丑,鸡皮鹤发;
我若性情粗暴,行动乖戾,举止欠雅;
患风湿,长癣疥,枯瘦干瘪,嗓音粗哑;
千人厌,万人弃,先天不育,两眼昏花:
那你退缩原也不差;因我和你本难配搭。
但这既都不在话下,到底什么叫你惊怕?
“你在我额上,决不会找出来半条皱纹。
我的眼水汪汪碧波欲流,转盼多风韵。
我的美丽像春日,年年不老,岁岁更新。
我的肌肤丰润,连骨髓里都春情欲焚。
我这腻滑的手,你若肯握一握表示亲近,
它就要在你手里,如酥欲融,化去不复存。
“我也会闲谈答话,作悦耳的解语花;
我也会学精灵,在绿莎上细步轻踏;
我也会学水中仙子,飘飘披着长发,
用平沙作舞茵,却不见有脚踪留下。
爱之为物,本是火的精华,空灵、倏忽、飘洒,
并非重浊而下沉,却是轻清上浮而欲化。
“你看我身下坡陀上的樱草,虽然荏弱,
却能像粗壮的大树,把我的身子轻托。
拉着我的辇周天游遍的,是两只鹁鸽:
它们弱小,却能叫我整天价到处行乐。
爱既这样轻盈柔和,那么,你这个小哥哥,
却为什么,把它看作是沉重得难以负荷?
“难道你会无端爱上了自己的面孔?
难道你的右手会抓住了左手谈情?
那样,你只好自爱自,自弃自,一场空,
自陷自设的情网,自怨解脱不可能。
那耳喀索斯就这样自己作了自己的爱宠,
后来还为吻泉水中自己的影子送了命。
“蜡炬点起光明来,珠翠盛饰增仪态,
珍馐美味为适口,绮年玉貌宜欢爱,
欲嗅芳芬芳馨折,欲采果实果树栽。
生而只为己,辜负天地好生的本怀。
种因种生,种复生种,天生丽质也无例外;
父母生了你,你再生子女,本你份内应该。
“如果你不繁殖,供给大地生息之资,
那大地为什么就该繁殖,供你生息?
按照自然的大道理,你必须留后嗣:
这样,一旦你死去,你仍旧可以不死;
这样,你虽然死去,却实在仍旧永存于世:
因为有和你一样的生命,永远延续不止。”
说这里,害单思的爱神津津汗湿,
因为他们躺的地方,阴影已经渐移。
日神在中午正热的时候,也有倦意,
眼里冒火,看着下方这对男顽女痴。
他恨不得阿都尼能替他把车马来驾驶,
自己却像阿都尼,在爱神的香怀里偎倚。
这时候,阿都尼心烦意厌,身懒体慵;
满眼都是不快活,一脸全是不高兴;
紧锁眉头,眯得一双秀目朦朦胧胧;
象云雾满空,遮断了蓝蔚,迷迷蒙蒙。
他阴郁地喊,“别再什么情不情!我不爱听。
太阳晒到了我脸上来了,我得活动活动。”
“哎呀,”维纳斯喊道,“你年纪轻,心可真狠,
居然用这样毫无道理的借口图脱身!
我要吹出像天风的气,叫它习习成阵,
把要西去的红日,搧得清冷冷、凉森森。
我要用头发把你遮住,叫它沉沉生幽阴。
如果头发也晒着了,我就用眼泪把它淋。
“天上照耀的太阳虽然正是最热之时,
但是我却也给你把它完全都遮住。
太阳的火对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
使我如燃欲焚的火本从你眼里射出。
我若不是长生不死,那我这副柔肠媚骨,
早就要在天上人间二火之间,遭到焚如。
“难道你的心真正比石还顽,比铁还硬?
石经雨滴也会磨损,铁经火炼也能熔。
莫非你不是妇人生,竟连爱情都不懂?
也不知道爱不见答,能给人多大苦痛?
哎哟,如果你妈也会像你这样冥顽无情,
那她到死都要孤零,你就没有机会下生。
“我是不是神,竟会叫你这样鄙视厌恨?
我对你求爱,里面会含什么危险成分?
不过区区一吻,难道会于你双唇有损?
说呀,好人,说好听的,否则不敢有劳您。
我只求你一吻,我回敬你,也决不过一吻。
你若愿我接个双吻,那另一吻就算利润。
“呸!不喘气的画中人物,冰冷冷的顽石,
装满涂饰的偶象,冥顽不灵的死形体,
精妙工致的雕刻,却原来中看不中吃。
样子虽然像人,却不像妇人所生所育。
你并不是个男子,虽然面貌也像个男子;
因为男子对于接吻,求之不得,哪会畏避?”
这话说完,烦躁把她娓娓的语声咽断,
越来越强烈的爱,激动得她有口难言。
她脸发烧、眼冒火,一齐喷出满腹幽怨。
风情月债本归她管,自家公案却难办。
她一会嗫嚅欲开口,一会又涕泗流满面,
另一会就哽噎得要说的话打断难接连。
她有时摇自己的头,又有时拉他的手,
有时往他脸上瞧,又有时就往地上瞅,
另有时就像箍住了一般,用力把他搂。
她愿把他老这样搂,他却要她放他走。
他在她怀里硬挣强夺想要脱身的时候,
她就把百合般的纤指一个一个紧紧扣。
“心肝,”她说,“我既筑起这一道象牙围篱,
把你这样在里面团团围定,紧紧圈起,
那我就是你的苑囿,你就是我的幼麑。
那里有山有溪,可供你随意食宿游息。
先到双唇咀嚼吮吸,如果那儿水枯山瘠,
再往下面游去,那儿有清泉涓涓草萋萋。
“这座囿里水草又丰美,游息又可意,
低谷有绿茵芊绵,平坡有密树阴翳,
丛灌蒙茸交叶暗,丘阜圆圆微坟起,
给你又遮断了狂风,又挡住了暴雨。
苑囿既然这样美,那你为什么不作幼麑?
纵有千条犬吠声狂,都决不能惊扰了你。”
他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好像表示鄙夷,
于是他腮上,两个迷人的小酒窝现出;
那两个小圆坑儿,本是“爱”的精心绝艺,
为的自己遭不幸,能有个简单的坟墓。
但实在说来,他既然是“爱”,那他所在之处,
就不会有死亡:这种情况他早预见先知。
这两个迷人的小圆窝,迷人的小圆坑,
象张着小嘴,使迷恋的爱后坠入其中。
她早就神智失常了,现在更神智不清;
她头一下就打闷了,又何用两下才成?
可怜你,爱神,作法自毙,掉进自掘的陷阱,
一死地迷上了对你只表示鄙夷的面孔。
她现在该怎么办?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话都说完了,她的苦恼却越来越难堪。
时光过去了,她爱的那人却归心似箭,
从紧缠着他的玉臂中,用力挣脱羁绊。
“求你,”她喊道,“把情面稍一顾,把心稍一软。”
他却不管,一跃而起,奔向骏马,想跨雕鞍。
但是你看,在邻近一丛矮树林子里,
有匹捷尼骡马,口嫩神骏,精壮少比,
瞥见阿都尼的骏骑,正用蹄子刨地,
就连忙跑出来,气喘吁吁,振鬣长嘶。
那匹马首昂然的骏骑,本来在树上软系,
一见了这样,忙扯断缰绳,一直向她跑去。
他威武地又蹦又踢,又腾跃,又长嘶。
密织的马肚带,他一迸就两下分离。
他那硬铁蹄,划伤了生万物的大地,
使地心发出回声,只有天上雷声可比。
他嘴里的马嚼子,他一咬就都碎得像泥,
一下就完全制伏了用来制伏他的东西。
他两耳耸起;编结的长鬣本下垂拂披,
现在却在昂然拱起的长颈上直竖立;
他的鼻子吸进去的,本是清新的空气,
现在却像呼呼的闷炉,喷出一片水汽;
他的眼睛发出像火一般的光,闪烁斜视,
表示他的春心已经大动,情欲已经盛炽。
他有时细步急蹴,好像要把脚步数;
威仪中有温柔含,骄傲中有谦虚露;
忽然又半身直举,往前猛跳又猛扑,
仿佛说,你瞧瞧,我有多么大的气力!
我这是对站在我一旁的骒马显威武,
好教她眼花缭乱,心生爱慕,作我的俘虏。
他主人惊讶、忙乱、气愤,他一概不理论。
他主人用“喂喂,别动!”哄他,他也耳朵沉。
他哪里还管马刺刺得痛,马勒勒得紧?
他哪里还管马衣是否美,马具是否新?
他只见所爱,别的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因为在他那闪烁的眼光里,什么能够可心?
画家若想画一匹骨肉匀停的骏马,
使它比起真的活马来还要增身价,
那他的手笔,得比天工还精巧伟大,
使笔下的死马,远超过自然的活马。
现在这匹马,论起骨胳、色泽、气质、步伐,
胜过普通马,像画家的马,胜过天生的马。
蹄子圆,骹骨短,距毛蒙茸、丛杂而翩跹,
胸脯阔,眼睛圆,头颅小,鼻孔宽,呼吸便,
两耳小而尖,头颈昂而弯,四足直而健,
鬣毛稀,尾毛密,皮肤光润,臀部肥又圆;
看!马所应有的,他没有一样不具备完全,
只少个骑马的人,高踞他阔背上的华鞍。
他有时往远处狂蹿,又站住脚回头看,
于是一根羽毛一战颤,他又往前猛颠。
这一颠,都简直想和风争先后,赛快慢。
但是他还是飞,还是跑,没有人敢断言;
因为劲风正掠着他的尾和鬣,鸣啸呼喊,
把他的毛吹得像长翎的翅膀一般翩跹。
他朝着他的所爱斜视,冲着她长嘶。
她也长嘶回报,好像懂得他的心意;
又像一般女性,见他求爱,把脸绷起,
故意作嫌恶的神气,假装狠心不理;
对他的爱情厌弃,把他炽盛的春情鄙夷。
他从她后面拥抱她,她就用蹄子使劲踢。
于是他就像个失意的人,抑郁又愁闷,
把尾巴像倒垂的羽缨那样,下拂后臀,
给欲火烧得如化的那一部分作覆阴。
他又刨地,又愤怒地把苍蝇乱咬一阵。
他的所爱,看见了他春情这样如狂似焚,
稍露怜心;他也由暴怒渐渐地变为斯文。
他那容易动怒的小主人家想去捉他,
谁知那未经人骑的骒马,一见害了怕,
就连忙把他来撇下,惟恐自己被人抓。
她前奔,他也后随,把阿都尼单独剩下。
疯了一般蹿进树林子里面的是他们俩;
叫他们撂在后面的是想追他们的老鸦。
阿都尼气得肚子发胀,一下坐在地上;
一面大骂这匹不受拘管的畜生混账。
现在又来了一次于爱后有利的时光,
可以用甜言蜜语给她的单思帮帮忙。
因为恋爱的人总说,若不让“爱”借重舌簧,
就是叫它受比平常三倍多的委屈冤枉。
一条河流完全壅障,水就流得更猖狂;
一个闷炉丝毫不通气,火就着得更旺;
密不告人的愁烦,也正是同样的情况;
自由畅谈,可以使“爱”的烈焰稍稍低降。
但是如果一旦“爱”的辩护士都一声不响,
那案中人除了伤心而亡,还有什么希望?
他看见她来到,脸上另一阵又红又烧,
就像要灭的炭火,让微风一下又吹着。
他用帽子把他蹙着的额连忙遮盖牢,
眼睛瞅着无情的地,心里不知怎么好,
也不管她还是并未近前,还是已经挨靠。
因为他眼里的她,只值得从眼角那儿瞧。
留心细看她那样匆匆忙忙,悄悄冥冥,
去就那顽梗任性的孩童,真是一奇景。
你看她脸上忽白忽红,红掩白、白减红,
满心的冲突,都表现在脸色的斗争中。
这一瞬间,她脸上还是灰白的;稍待片顷,
它就要射出红火来,和天上的闪电相同。
她现在已经来到了他坐的那个地点,
就像卑躬屈节的男爱人,跪在他面前,
用纤手把他的帽子,轻轻地撩在一边,
另一只柔嫩的手,就摸他更柔嫩的脸。
他这脸经她一摸,就有她的纤指印出现,
像初雪松又软,一触就留下了斑深痕浅。
哦,他们眼光交锋,多生动的一场战争!
她老满眼含情,望着他的眼哀求恳请。
他就满眼含嗔,好像没看见她的眼睛。
她老用眼传情,他就老用眼鄙视这情。
这一出哑剧,一幕一幕地演得分分明明;
她泪如雨倾,作剧中陪衬,更使剧情生动。
她现在极尽温柔地握住了他的手,
就好像白雪筑起围墙,把百合拘囚;
又好像石膏圆箍,把象牙密裹紧扣。
这样白的朋友,碰到这样白的对头!
这场“美”与“美”的斗争,一面猛攻,一面严守,
就好像两只银色的鸽子,喙交喙,口接口。
她的思想传达器官——喉舌又开始动作:
“哦,滚滚尘寰中,你这最秀美的过客,
我恨不得我能变成你,你能变成我;
我心完好似你心,你心伤如我心多;
那样,你只报我以和颜,我便助你得解脱,
即使我得因此舍上命,我也一定无吝色。”
“还我的手,”他说,“你摸我的手什么道理?”
“还我的心,”她说,“那我就把你的手还你。
不然,你的心就要使我的心变成铁石,
变成铁石,它就要不理会动人的叹息,
这样,情人的呻吟,我也要听来绝不在意,
因为阿都尼的心已使我的心变得狠戾。”
“你要点脸,”他喊道,“快放开手,别再纠缠。
我这一天的乐事,算是全完。马也不见。
都是你,闹得我和马,两下里都不照面;
我说,你走开,单留下我在这儿想一番。
因为我一心一意、满头满脑、急忙地盘算,
想要叫我那匹骏马从骒马那儿回转。”
“你的马,”她答道,“该走的路就是这一条,
因为他这是对柔情的强烈攻势回报。
‘爱’和炭相同,烧起来,得设法叫它冷却。
让它任意着,那它就要把一颗心烧焦。
大海有崖岸,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范牢。
所以你的马跑掉,并非奇事,不值得惊扰。
“他系在树上时,看着多么像驽骀下驷,
仿佛一根皮带,就能治得他老老实实。
但他一见他的所爱——青春应有的美侣,
他并没把那不足道的束缚放在眼里。
他从他那拱起的颈上把缰绳一下甩去,
使他的头、口、颈、胸,都脱去羁绊,获得舒适。
“一个人看到他的所爱,裸体榻上横陈,
雪白的床单,都比不上她肤色的玉润,
那他岂肯只用饕餮的眼睛饱餐一顿,
而别的感官却能不同样地情不自禁?
冰雪凛冽,天气严寒,哪会有人过于小心,
见了热火,却远远躲着,不敢靠前去亲近?
“因此我的小哥哥,你不该骂骏马顽劣。
我反倒恳切地要求你跟他好好地学,
不要对送到门上来的快乐随便轻蔑。
他的行动就是你的模范,毋须我喋喋。
哦,你要学着恋爱;这个玩意简单又明确,
它还是一下学会了,就永远不会再忘却。”
“我不懂恋爱是什么,我也不想学,”
他说,“只有野猪我才爱,因为它能供我猎获。
我不要跟你强借,也不要你强借给我。
我对于‘爱’也爱,但只爱暴露它的龌龊。
因为我听人说,它只能跟‘死亡’讨点生活,
它也哭也笑,但只一呼吸间,便一生度过。
“衣服还未裁好作完,有谁能就去穿?
半个瓣还没长出来的花,谁肯赏玩?
生长发育的东西如受伤,虽只半点,
都要盛年萎谢,不会长得璀璨绚烂。
马驹年幼时,就叫他驮人负物,引重致远,
那他就要精力耗减,永远不能长得壮健。
“我的手叫你攥得痛起来,咱们得分开。
不要再瞎谈什么叫情,胡说什么叫爱。
你顶好撤围;我的心不能投降任屠宰;
它不会给向它猛攻的‘爱’,把城门开开。
请收起誓言、谀词和装出来的热泪满腮,
因为它们在坚定的心里,不能当作炮台。”
“怎么,你还会出声?”她说,“舌头还会活动?
其实顶好你没有舌头,或者我两耳聋。
你像美人鱼这样一说,叫我加倍伤情。
我本来就心里沉重,听你这话更沉重。
和谐中有龃龉,一派仙乐却奏得极难听。
耳边极美的乐声,却引起心里深创巨痛。
“假设说,我只有两只耳朵,却没有眼睛,
那你内在的美,我目虽不见,耳却能听。
若我两耳聋,那你外表的美,如能看清,
也照样能把我一切感受的器官打动。
如果我也无耳、也无目,只有触觉还余剩,
那我只凭触觉,也要对你产生热烈的爱情。
“再假设,我连触觉也全都失去了功能,
听也听不见,摸也摸不着,看也看不清,
单单剩下嗅觉一种,孤独地把职务行,
那我对你,仍旧一样要有强烈的爱情。
因你的脸发秀挺英,霞蔚云蒸,华升精腾,
有芬芳气息喷涌,叫人嗅着,爱情油然生。
“但你对这四种感官,既这样抚养滋息,
那你对于味觉,该是怎样的华筵盛席?
它们难道不想要客无散日,杯无空时?
难道不想要‘疑虑’,用双簧锁把门锁起,
好叫‘嫉妒’,那不受欢迎、爱闹脾气的东西,
别偷偷地溜了进来,搅扰了它们的宴集?”
他那两扇鲜红的门——嘴唇——又一次敞开,
叫他要说的话,甜蜜地畅通不受阻碍;
那就像清晓刚刚来,就出现了红云彩,
预示那海上船要沉没,陆上雨要成灾;
预示那鸟儿要受苦难,牧羊人要受损害;
牧牛人和牛群要遭疾飘和狂飇的破坏。
这种不吉的预兆,她留心注意早看到。
那就像暴雨之前,狂风一时停止怒号;
又像狼把牙一露,就知道他要开口嗥;
又像浆果一裂,就知道有黑水往外冒。
枪子出了膛,还不是有人遭殃,要被打倒?
所以,他还没开口,他的心思她就已猜着。
她一看他这样的神色,便往地上跌倒。
神色能使“爱”活人间,也能使“爱”赴阴曹,
眉头一皱创伤生,嫣然一笑就创伤好。
伤心人得到“爱”这样治疗,得说福气高。
那个傻孩子,一见她这样,认为她真不妙,
就用手拍她灰白的脸,直拍到脸生红潮。
他满腹惊讶,刚打好的主意也变了卦,
因为,他本来想对她来一番切责痛骂。
但是狡黠的“爱”,却极巧妙地制人先发。
我给“机警”祝福,因为它这样维护了她!
她躺在草地上,呼吸停止,好像一下羞杀。
他给她渡气、接唇,到了她苏醒过来才罢。
他轻轻弯她的手指,使劲按她的脉息,
他微微拍她的两腮,慢慢搓她的鼻子,
轻轻揉她的嘴唇:总之想尽千方百计,
要把他的狠心给她的创伤医疗救治。
他吻她。她呢,一见大喜,就乐得将计就计,
老老实实地躺在那儿,好叫他吻个不止。
原先的愁苦阴沉似夜,现已变为白日。
她那碧波欲流的眼,似碧牖轻轻开启。
那就像辉煌的朝日,穿着耀眼的新衣,
使晨光欢畅,使大地呈现出一片喜气:
就这样,如同丽日映辉得太空明朗美丽,
她那一双美目,映辉得她的脸明艳美丽。
她的眼光,射到他那白净无须的脸上,
好像她的眼光,都从他那儿来的一样。
若非他两眼因不悦而紧蹙,稍显微茫,
从来没有过这样四只眼睛,交辉争光。
她的眼,由于隔着晶莹的泪而放出光芒,
所以就好像夜晚月映清塘看来的景象。
“哦!”她说,“我身在何方?在人间还是天上?
我在海里遭淹没?还是在火里受烧伤?
现是何时光?清晨明朗?还是昏夜漫长?
我还是一心想要活?还是一意愿死亡?
我刚才还活着,但却活得比死了还凄惶;
后来又死了,但在死中却得了生的欢畅。
“你曾叫我死掉,我求你再叫我死一遭。
你的眼受了恶师——你的狠心——的指教,
只会把鄙夷的样子现,不屑的神色表,
因此我这颗可怜的心,你早已杀害了。
我这一双眼,本来是女后我忠实的向导,
如无你的嘴唇,也早就离开了我的躯壳。
“为你双唇救了我,我祝它们长相接!
我祝它们鲜红永不褪,新装永不卸!
我祝它们存在时,青春永保无残缺!
把疫疠从应降大灾的年月中祓除绝。
这样,星象家尽管已把人们的生死判决,
你喘的气,却回天旋地,把人命留,瘟疫灭。
“你的香唇,曾在我的柔唇上留下甜印,
要叫这甜印永存,我订任何契约都肯,
即使我得为此而卖身,我也完全甘心,
只要你肯出价购买,交易公平信用准。
成交以后,如果你还怕会有伪币生纠纷,
那你就把印打上我这火漆般红的嘴唇。
“你只付吻一千,我的心就永远归你管。
你还毋须忙,可以一个一个从容清算。
在我嘴上触一千下就成,有什么麻烦?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