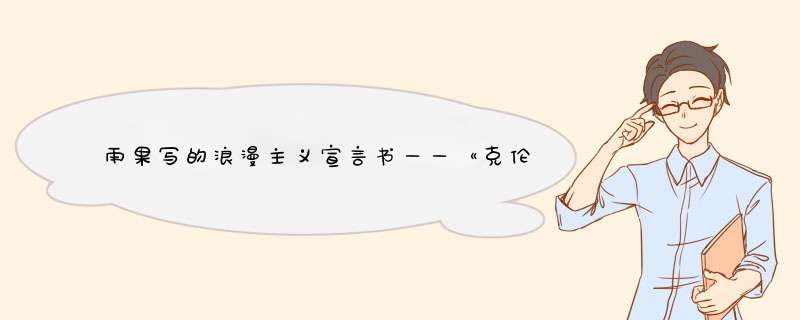
《克伦威尔》序言
[法]雨果 著 柳鸣九 译
我们从一个事实出发:世界不总是由同一性质的文明,也就是说老是由同一个社会形式(这样说更为确切,虽然涵义较广阔了一些)所支配和统治。整个人类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经历过生长、发展和成熟的阶段。他通过了孩提时代、成人时期;而现在到达了老迈之年。在近代社会名之曰“古代”的历史时期之前,还有另一个世纪,古人称之为“神话时代”,而其正确的名称可能是“原始时代”。这就是文明从它最初的源泉发展到今天所经过的三大连续的程序。而由于诗总是建筑在社会之上,那末,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诗在原始时期、古代和近代这三大人类发展阶段中的特点究竟是怎样的。
在原始时期,当人在一个刚刚形成的世界中觉醒过来的时候,诗也随之觉醒了。面对着使他眼花缭乱、使他陶醉的大自然的奇迹,他最先的话语只是一种赞美歌。那时,他离上帝还很近,因此,所有的沉思都出神入化,一切遐想都成为神的启示。他抒发内心之情,他歌唱有如呼吸,他的竖琴只有三根弦,上帝、心灵和创造;但是这三种奥妙包括一切,这三位一体的思想孕含万象。土地差不多还是荒芜不毛的。已经有了家庭,但还没有民族;有了父老,但还没有国王。每个种族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没有私人财产,没有法律,没有冲突,也没有战争。一切东西都属于每个人,也属于集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共体。没有任何东西束缚人。人过着田园的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是一切文明的起点,而且多么有利于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他任情地工作,任情地行动。他的思想如同他的生活一样,象天空的云彩,随着风向而变幻、而飘荡。这就是最初的人,这就是最初的诗人。他年青,富有诗情。祈求是他全部的宗教,歌谣是他所有的诗章。
这种诗,原始时期的这种歌谣,就是《创世纪》。
但是,这种青年时期渐渐过去。一切的范围都扩大了;宗教变成部族,部族变成民族。……这些民族在地球上开始过于拥挤。他们彼此妨碍,彼此摩擦;由此便产生各国的冲突,产生战争①。他们互相侵犯;由此便产生民族的迁徙,产生流浪②。诗反映这些巨大的事件;它由抒发思想过渡到描写事物。它歌唱这些世纪、人民和国家。它成为史诗性的,它产生了荷马。
我们要重复指出,表现出这一种文化的,只有史诗。史诗具有好几种形式,但又永不失其特征。品达与其说是属于抒情诗的,不如说是属于史诗。如果编年史家这些在人类发展第二时期必不可少的人,去从事收集各种传说,并且开始以世纪纪年,那末,他们是白费力气了,纪年学不能把诗排斥掉;历史仍旧还是史诗。希罗多德就是一个荷马。
史诗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同样,它所代表的社会也面临末日,这种诗也因自我循环时日已久而陈旧过时,罗马模仿希腊,维吉尔摹临荷马;似乎为了体体面面地告终,史诗是在这最后的分娩中消亡的。
时候到了。世界和诗的另一个纪元即将开始。
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物质的,表面的偶像崇拜并潜入古代社会的中心,将它除灭,而在这一种衰老的文化的尸体上,播下近代文化的种子。这种宗教是完整的,因为他是真实的;它在教义和教仪之间,用道德深深地加以维系。并且首先把最重要的真理指示给人说,生命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如同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总之,他就象双线的交切点,象包罗世界的两条实体的锁链间的连接环,这两条锁链,一条是物质实体的系统,一条是无形存在的系统,前者由石头一直数到人,后者由人开始而到上帝。
没有什么比古代的神谱更实际的了。它完全不象基督教那样把精神和肉体分开,而是赋予一切以形体和外貌,甚至对精神和灵智也都如此。在这里,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具有感性。那些神都需要云雾来掩饰自己。他们也吃、喝、睡觉。把他们伤害了,他们也要流血;把他们伤成了残废,他们就永世成为跛子。这种宗教有一些神,也有一些半神。它的霹雷是在铁砧上锤炼出来的,在其他的成分之中,还有三道弯曲的雨线③,它的天神邱比特把世界悬吊在一根金链上;它的太阳驾上四匹马拉的大车;它的地狱是一个深渊,地理上还标志了它的出口;它的神界是在一座山上。
这样,多神教用同一种粘土来塑造种种创造物,因而就缩小了神明而扩大了人类。荷马的英雄差不多和神同样高大,阿雅克斯④冒犯朱比特,阿喀琉斯比得上玛斯⑤。我们刚才说过,基督教却相反,它把灵气和物质彻底分开。它划了一道深渊在灵魂与肉体之间,一道深渊在人与神之间。
基督教把诗引到真理。近代的诗艺也会如同基督教一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来看事物。它会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它会要探求艺术家狭隘而相对的理性是否应该胜过造物主的无穷而绝对的灵智;是否要人来矫正上帝;自然一经矫揉造作是否反而更美;艺术是否有权把人、生命与创作割裂成为两个方面,每一件东西如果去掉了筋脉和弹力是否会走得更好;还有,是否“凡要成为和谐的那种方法”都是不完整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诗着眼于既可笑又可怕的事件上,并且在我们刚才考察过的基督教的忧郁精神和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下,它将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这一步好象是地震的震撼一样,将改变整个精神世界的面貌。它将开始象自然一样行动,在它的创作中,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因为宗教的出发点总是诗的出发点。两者互相关联。
这是古代未曾有过的原则,是进入到诗中来的新类型,由于作为一个条件,它使整个事物都有所改变,于是在艺术中发展出一种新形式。这种新类型就是“滑稽”,这种新形式就是喜剧。
请允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详加考究;因为我们刚才指出了那一种不同的特征,根本的差别。在我们看来,这一种差别把近代艺术和古代艺术,把现存形式和死亡形式区分开,或者用比较含糊但却流行的话来说,把“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古典主义的”文学区分开来。
相反,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却具有广泛的作用。它到处都存在;一方面,它创造了畸形和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它把千种古怪的迷信聚集在宗教的周围,把万般奇美的想象附丽于诗歌之上。是它,在空气、水、火和泥土里满把地播种下我们至今还觉得是活生生的、中世纪人民传说中的无数的中介物;是它,使得魔法师在漆黑的午夜里跳着可怕的圆舞;也是它,给予撒旦以两只头角,一双山羊蹄,一对蝙蝠翅膀。是它,总之都是它,它有时在基督教的地狱里投进以后被但丁和弥尔顿严峻的天才所召唤来的那些奇丑的形象⑥,有时则扔入加洛⑦这个滑稽的米开朗琪罗在其中自娱的形象。从理想世界到真实世界,是要经过无数的人类的滑稽变形。斯嘉哈莫奚⑧式,克利斯⑨式和阿尔勒甘⑩式的人物都是它的奇想的创造,这都是人的怪象的侧影,是严肃的古代完全陌生的、而从意大利古典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典型。最后,还是它把南北两方的想象的色彩轮换地涂在同一个戏剧上,使斯加纳海勒在唐·璜⑾的周围蹦跳,靡非斯特在浮士德左右周旋。
而它的举止是多么自由而明朗!它多么大胆地使前一个时代如此羞涩地用襁褓包扎起来的那些奇怪的形象都跳了出来。古代的诗不得不给跛子伏尔甘安排一些同伴,但却极力用扩大他们伟岸身躯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畸形。近代精神保存了那些非凡的铁匠的传说,但却一下子给它加上一个截然相反并使它更加突出的特性;它把巨人变成了侏儒,把独眼巨人变成了地下的小神。正是以这同样的独创性,它把并不怎么奇怪的七头蛇代之以我们传说中土产的怪物,鲁昂的加尔古叶,麦茨的克拉—乌易,特洛依的夏尔—沙内,蒙德勒利的特赫,塔哈斯贡的塔哈斯克,这些怪物的外形如此多变,而它们这些古怪的名子又更增加了一种奇特。这些创造物从它们自己的本性里就能得到一种深沉而有力的音调,在这音调前,古代有时似乎也要却步。的确,希腊的妖怪远不及《麦克佩斯》中的魔女可怕,因而也更缺少真实,希腊神话中蒲鲁东⑿也并不是魔鬼。
照我们看来,在艺术中如何运用滑稽丑怪这个问题,足可写出一本新颖的书来。人们可以举出,近代人从这个丰富的典型里汲取了多么强烈的效果,而今天却还有一种狭隘的批评在激烈地反对它。我们的主题可能马上就要引导我们来顺便指出这一幅广阔图画中的某些特点。但在这里,我们只想说,根据我们的意见,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毫无疑问,鲁本斯⒀是了解这点的,因为他得意地在皇家仪典的进行中,在加冕典礼里,在荣耀的仪式里也掺杂进去几个宫廷小丑的丑陋形象。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老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并且,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和滑稽丑怪的接触已经给予近代的崇高以一些比古代的美更纯净、更伟大,更高尚的东西;而且,也应该是这样。当艺术本身合理的时候,就更有把握使各种事物都达到最后的目标。如果荷马式的仙境与这种天国的情趣,与弥尔顿的天堂中仙使的美丽相距很远,那是因为在伊甸园的下面,有一个和多神教的地狱之底各有千秋的可怕的地狱。如果法朗塞斯伽·达·里米尼⒁和贝亚特丽不是在但丁这个把读者关进饥饿之塔迫使读者分享于哥利诺⒂可厌的餐食的诗人的笔下写来,会有这样吸引人吗?但丁如果不写得这样有力,就不可能这样动人。肌体丰腴的河神,强壮的人鱼,放荡的风神,他们有没有我们的水仙和天神那种透明的流动性?难道不是因为现代人能够想象出在我们的陵墓里有吸血鬼,食人怪,妖精,役蛇怪,大蝙蝠,僵尸和骷髅荡来荡去,这种想象才能够赋予它的妖精以那种虚幻的形状,那种为多神教的仙女所很少达到的精灵的纯度?古代的维纳斯姿容美艳,无疑地招人喜爱;但是,是什么在让·古容⒃所有的画面上散布那种精美、那种奇妙而空灵的风韵呢?是什么赋予它们以那种为生活和伟大所没有认识的特点?如果不是对中世纪雄劲遒健的雕刻术的接近,又是什么呢?
如果在这些还可以说得更为透彻一点的必要的议论之中,我们思想的线索还没有在读者的思想里面中断的话,他就一定会了解到,滑稽丑怪这一个被近代诗神所承继的喜剧的萌芽,一旦移植到比偶像教和史诗更为有利的土壤上,就会以多么旺盛的生命力生长和发展起来。实际上,在新的诗歌中,崇高优美将表现灵魂经过基督教道德净化后的真实状态,而滑稽丑怪则表现人类的兽性。第一种典型将从不纯的混合质中解脱出来而拥有一切魅力、风韵和美丽;总有一天它应能创造出朱丽叶,苔丝特蒙娜,莪菲丽亚⒄。第二种典型收揽了一切可笑,畸形的丑恶。在人类和事物的这个分野中,一切情欲,缺点和罪恶,都将归之于它;它将是奢侈、卑贱、贪婪、吝啬、背信、混乱、伪善;它将轮流扮演牙戈、答丢夫、巴西尔⒅;波罗纽斯、阿巴贡,巴尔特罗⒆;福尔斯塔夫、史嘉本、费加乐⒇。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因为,从情理上来说,美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表现在它最简单的关系中,在它最严整的对称中,在与我们的结构最为亲近的和谐中的一种形式。因此,它总是呈献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但却和我们一样拘谨的整体。而我们称之为丑的那个东西则相反,它是一个不为我们所了解的庞然整体的细部,它与整个万物协调和谐,而不是与人协调和谐。这就是它为什么经常不断呈现出崭新的、然而不完整的面貌。
研究滑稽丑怪在近代的运用和发展,这是一件有趣的事。首先,它侵入,涨溢,泛滥,象一道激流冲破堤防。它诞生之时,贯穿在垂死的拉丁文学之中,……然后,它就散布在那些改造欧洲的新兴民族的想象里。它充满在那些故事作者、历史家和小说家的想象里。它由南到北蔓延开来。它游戏在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中,并且同时以它的灵气唤活那些可赞美的西班牙《诗歌集》,这真正骑士时代的《依利亚特》。举个例子来说,它在《蔷薇传奇》(21)中这样描写一个庄严的仪式,一个国王的选举:
于是他们选出了一位大个子的平民
这是他们中间的头号大块头
……
要更加突出说明滑稽丑怪在第三文明期的影响,那是多余的。在所谓浪漫主义时代里,一切都表现出它与“美”之间的紧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以最为纯朴的民间传说而言,也无一不以一种可爱的本性表现了近代艺术的这种神秘。古代就不可能创造出《美人和野兽》。
的确,在我们刚才考察的时代里,滑稽丑怪在文学中比崇高优美更占优势,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是一种反应的狂热,一种一瞬即逝的对新颖的热情;这是一个要渐渐平伏下去的最初的浪潮。美的典型不久又要恢复它的地位和权利,它并不排斥另一种原则,而是要胜过它。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让滑稽丑怪在牟利罗(22)巨大的壁画上,在维罗尼斯(23)神圣的篇幅中只占有画幅的一角;让滑稽丑怪只渗入到艺术将引以自豪的两幅《最后的审判》中去,只渗入到米开朗琪罗将用来装饰梵蒂冈的悦目而又可怕的图景中去(24),只渗入到鲁本斯将描绘在昂魏尔斯大教堂的穹窿屋顶上的人类堕落的骇人的图案中去。在两种原则之间建立平衡的时候现在已经来到了。不久就会有一个人,一个诗王(如象但丁称呼荷马一样),来确定它。这两种敌对的天才汇合起双方的光辉,而在这种光辉之中诞生了莎士比亚。
这样我们便到达了近代的诗的顶点。莎士比亚,这就是戏剧;而戏剧,它以同一种气息溶合了滑稽丑怪和崇高优美,溶合了可怕和可笑,悲剧和喜剧,戏剧是诗的第三阶段的,也就是当前文学的固有的特性。
我们把上面所讨论的这些事实加以简要的概括,可见诗有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相应地和一个社会时期有联系,这三个时期就是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抒情短歌歌唱永恒,史诗传颂历史,戏剧描绘人生。第一种诗的特征是纯朴,第二种是单纯,第三种是真实。行吟诗人是抒情诗人向史诗诗人的过渡,就好象小说家是史诗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过渡。历史家与第二个时期一道来临,编年史家、批评家则和第三个时期同时产生。抒情短歌的人物是伟人:亚当、该隐,挪亚(25);史诗的人物是巨人:阿喀琉斯、阿特鲁斯、奥里斯特斯(26);戏剧的人物则是凡人: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赛罗。抒情短歌靠理想而生活,史诗借雄伟而存在,戏剧以真实来维持。总之,这三种诗是来自三个伟大的泉源即《圣经》、荷马和莎士比亚。
为了证明新的思想(指浪漫主义者的文艺思想——译者)远非要毁坏艺术而仅仅是要把艺术改造得更坚固、更稳实,我们姑且来试着根据我们的意见指出:区分从艺术出发的真实和从自然出发的真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象一些不长进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把这两者混淆起来,那真有些冒失。艺术中的真实根本不能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真实。艺术不能提供原物。我们且试想,一个主张不加考虑地模仿绝对自然、模仿艺术视野之外的自然的人,当他看到一出浪漫主义戏剧(譬如《熙德》吧)的演出时,会作何表现。他首先一定会说,“怎么?《熙德》的人物说话也用诗!用诗说话是不自然的。”“那你要人物怎样说话呢?”“要用散文。”“好,就用散文。”如果他坚持自己的原则的话,过一会他又要说了:“怎么,《熙德》的人物讲的是法国话!”“那么应该怎样呢?”“自然要求剧中人讲本国语言,他只能讲西班牙语。”“那我们就会一点也听不懂了;不过还是依你的。”你以为挑剔就完了?不;西班牙话还没有讲上十句,他又该站起来了,并且质问这位说话的熙德是不是真正的原原本本的熙德?这位名叫彼得或雅克的演员有什么权利顶用熙德的名字?这都是虚伪。这样下去没有任何理由使他不坚持要求用太阳代替台灯,用“真正的”树木和房屋来代替那些虚假的舞台布景。因为这样一开了头,逻辑就把我们逼下去,再也停煞不住。
因此,人们应该承认艺术的领域和自然的领域是很不相同的,否则就要流于荒谬。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事,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艺术除了其理想部分以外,还有尘世的和实在的部分。不论它创作什么,它总是框在语法学和韵律学之间,在吴日拉(27)和黎希莱(28)之间。对于最为自由的创作,它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各种创作方法和要塑造的一大堆的材料。对天才来说,这些都是精巧的手段,对于庸人来说则是笨重的工具。
我们好象觉得已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戏剧是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不过,如果这面镜子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一个刻板的平面镜,那么它只能够映照出事物暗淡、平面、忠实但却毫无光彩的形象;大家都知道,经过这样简单的映照,事物的颜色和光彩会失去了多少。戏剧应该是一面集中的镜子,它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因此,只有戏剧才为艺术所承认。
舞台是一个视觉的集中点。世界上,历史上,生活中和人类中的一切都应该而且能够在其中得到反映,但是必须是在艺术魔棍的作用下才成。艺术历观各世纪和自然界,穷究历史,尽力再现事物的真实,特别是再现比事物更确凿,更少矛盾的风俗和性格的真实,它起用编年史家所节略的材料,调和他们剥除了的东西,发现他们所遗漏的并加以修理,用富有时代色彩的想象来充实他们的漏洞,把他们任其散乱的东西收集起来,把人类傀儡下面的神为的提线再接起来,给一切都穿上既有诗意而又自然的外装,并且赋予它们以产生幻想的、真实和活力的生命,也就是那种现实的魔力,它能激起观众的热情,而且首先是激起诗人自己的热情,因为诗人是具有良知的。由此,艺术的目的差不多是神圣的,如果它写作历史,就是起死回生,如果它写作诗歌,就是创作。
如果我们看到戏剧这样广泛的发展,那真是伟大而壮丽的事情:在这种戏剧中,艺术强有力地发展了自然,情节坚定而又轻快地逐步朝向结局发展,既不繁杂又不小气,诗人全面地完成了艺术的复杂的目的,那就是向观众展示出两个意境,同时照亮了人物的外部和内心,通过言行表现他们的外部形貌,通过旁白和独白刻划内在的心理,总之一句话,就是把生活的戏和内心的戏交织在同一幅图景中。
我们认为,要写这类作品,如果说诗人应该在这些东西中有所选择的话,那他选的不是美,而是特征。这也并不意味着象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去渲染一些地方色彩,也就是说,在完成了一部归根到底是虚伪和一般化的作品之后,然后在这作品上加上一些触目的颜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地方色彩不该在戏剧的表面,而该在作品的内部,甚至在作品的中心,地方色彩生动地从那里自然而均匀地流到外面来,也可以说流布到戏剧的各个部分,好象树液从根茎一直输送到最尖端的树叶。戏剧应该完全浸透着这种时代的色彩;戏剧在这种色彩中就好象在空气中一样,使人在进出于其间的时候,只感到变换了世纪和气氛。要达到这种境地就需要一些钻研和努力;这样更好。艺术的大道被荆棘所阻塞,在它面前,除了意志坚强的人以外,一切都见而却步,这也是件好事。正是这种为热烈的灵感所支持的钻研会使戏剧免于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一般化。一般化是短视的和缺乏才能的诗人的毛病。在舞台的视野上,一切形象都应该表现得特色鲜明,富有个性,精确恰当。甚至庸俗和平凡的东西也应有各自的特点。什么都不应放弃。真正的诗人象上帝一样同时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每一个地方。天才好象制币机一样,既能够在金币上也能够在铜钱上铸刻国王的头像。
我们并不犹疑,而这正向有诚意的人证明,我们是多么不想使艺术走样,我们毫不犹疑把诗看作是最适于防止艺术遭受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种灾难的一种方法,看作是防止“一般化”泛滥的最坚固的堤防,这种“一般化”与“民主”一样在精神领域里到处流泛。在这里,请拥有这样多作家和作品的年青的文学容许我们向它指出一个我们觉得它已经陷入了的错误,这个错误和旧派那些不可置信的谬误相比,就太值得辩护了。新的世纪正处在成长茁壮的时期,在这时,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错误纠正过来。
要是我们有权凭自己的高兴来说戏剧的风格应该怎样,那末我们希望一种自由、明晓而诚实的韵文,它敢于毫不矫揉地说出一切,毫不考究地表现一切;它以自然的步调由喜剧而到悲剧、由崇高而到滑稽;它有时实际、有的富有诗意,它的整体既是艺术的也是灵感的,既是深刻的也是突然的,既是宽广的也是真实的;它善于适当地断句和转移停顿,以掩饰亚历山大体的单调;它爱用延长句子的跨行句甚于混淆意义的倒装句;它忠于韵律这一位受制约的王后,我们的诗歌的最高雅的风韵,我们的格律的母亲;这种韵文的表现方法是无穷尽的,它美妙和结构的秘密是无从掌握的;它好象普洛透斯(29)一样在形式上千变万化,但又不改其典型和特征,它避免长篇大论的台词,而在对话中悠然自得;它总隐藏在人物的后面;它首先注意的是要得体,并且当它成为“美”的时候,好象只不过是偶然的事,不是由它自己作主,而且它自己也不自觉意识到这点;它成为抒情的,还是成为史诗性的或者戏剧性的,这得看需要而言;它能掠过诗的各个音阶,从高音到低音,从最高尚的思想到最平庸的思想,从最滑稽的到最庄重的,从最表面的到最抽象的,从来也不超出道白场面的界限;总之,这种韵文如此美好,就好似一个从仙女那里既得到了高乃依的心灵、又得到莫里哀的头脑的人所写出来的一样。我们觉得这种韵文会“象散文一样地优美”。
我们特别要重述,舞台上的诗应该排除一切自怜自爱的东西,一切过分的要求和一切取媚的卖弄。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应该承受一切事物的形式,它没有什么要强加在戏剧之上的东西,相反,它应该接受戏剧的一切:法文、拉丁文、法律条文、王公贵族的辱骂、民间的俗话、喜剧、悲剧、笑、眼泪、散文和诗,把这一切都传达给观众。如果诗人的诗句故作傲然,那真是不幸!不过,这种的形式是青铜的形式,它把思想嵌在它的格律中,在这种形式之下,戏剧是不可毁灭的,这种诗把戏深深印刻在演员的精神里,向他指点它所增减的东西,禁止他篡改它的角色,禁止他僭替作者的原意,使每一个字神圣化,并且使诗人所说过的东西在很久以后还屹立在听众记忆里。思想,在诗句中得到冶炼,立刻就具有了某种更深刻、更光辉的东西。
中国人,看李白,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浪漫主义的主题思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热衷用世,追求功名;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复杂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大唐帝国表面的强大昌盛,鼓舞着李白向往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强烈愿望。他常在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谢安自许。他还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钦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他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凭借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李白甚至幻想过一种相互礼让、尊敬平等的君臣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之二)表达了渴望明君的美好愿望。但当这种愿望落空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如《古风》第十首中: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诗中对鲁仲连却秦的功绩深表仰慕,对鲁仲连轻千金、顾笑平原的风度则更倾心折服。
天宝元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怀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供奉翰林,实际上只把他当作用以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翰林既非实际的官职,更没有政治实权。他那“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又不肯投靠权贵和奸相李林甫,桀傲不驯,整日纵酒狂歌,遭到当权的官宦外戚对他的暗中诋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写了不少诗篇表达自己的愤懑和痛苦。如著名的《行路难》之一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
虽然茫然,虽然徘徊,但李白并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自信。第二首着重揭露黑暗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第三首列举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的遭遇,表示要及早引退:“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又是多么消沉、颓唐。
在《梁甫吟》中,他以愤怒控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悲愤声中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诗的结尾,他以宏大的气势,表明了自己胜利的信心。“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当安之!”
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理想,时而悲叹个人的不幸;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诗歌,他的感情就是这样激荡着、矛盾着……
二、蔑视权贵、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
李白的浪漫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反对权贵、轻视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对腐朽的上层贵族势力的蔑视、抨击和反抗,是他的诗歌民主性精华的集中体现。
李白常说自己是“野人”、“布衣”,象屈原那样痛恨那些“党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录施满高门。”(《古风》第五十一)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
李白意识到自己与那班皇亲国戚豪门势族是具有不同身份的两类人。他“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送烟子元演隐仙城王序》)李白在诗里对于权贵及他们的荣华富贵投以强烈的蔑视,表现出一种傲岸不屈的性格,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里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这种粪土权门、轻视富贵的傲岸性格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与李白相比呢?
李白的反权贵精神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在这首长诗里,他对以斗鸡媚上的幸臣,以屠杀邀功的武将,投以憎恶轻蔑的嘲笑,说他们“万言不直一杯水”。接下来对自己和王十二光明磊落却遭受小人诽谤、谗言中伤,被逐出朝,表示了满腹的愤恨: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 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扬》、《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风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用曲高和寡来比喻自己不被重用,用“晋君”、“和氏璧”的故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借前秦宰相王堕骂董龙的话,斥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鸡狗不如,接着抒发了自己的心情及志向。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政治的腐败,为惨死在奸相李林甫之手的李邕、裴敦复鸣冤叫屈,称赞被暗杀的“李邕”“英风豪气”,对封建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颠倒黑白,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面目,作了尽情的揭露,表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结尾表示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丑恶的政治篱笆。
李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一方面蔑视权贵,另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于“王公大臣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表现出对荣华富贵的留恋和羡慕:“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候七贵同杯酒。”他不断地干谒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希望得到他们的汲引: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赠崔谘议》)这是何等低颜下气!可见李白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既是清高的,又是庸俗的。李白的反抗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去向整个统治阶级斗争,是脱离人民的,是没有出路的。他的孤傲虽然具有对抗权贵的意义,但也正表现了他的局限性。
三、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不仅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蔑视世间的一切;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于是他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急切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脱。
他在《赠新平少年》中写道:“摧残槛中虎,羁绁 上鹰,何时腾风云,博击申所能!”感到自己象“槛中虎”、“ 上鹰”,渴望自己能摆脱羁绊腾风凌云,得到个人自由。
他屡次自比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在《大鹏赋》中,描写大鹏鸟“上摩苍苍、下覆漫漫”“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博,雄无所争。”向往大鹏的境界,自由翱翔于宇宙之间,颇有道家庄子的气势。
因崇尚庄子,所以在诗中不自然地流露出轻视儒家的意思,如《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论。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以精炼生动的笔墨,刻画了鲁儒迂腐可笑的面目,体现了诗人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子都不放在眼里,是何等的狂傲。
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策士、酒徒等方面的气质。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稿》)传说他曾经为抱打不平而“手刃数人”,以后又受到那些无名游侠的感染,写了不少歌颂游侠的诗,如著名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 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侠义行动如“十步杀一人”“救赵挥金槌”,还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慷慨无私的精神,都与李白不愿屈己干人的性格,拯物救世的政治理想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品德有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李白能成功地把儒家、道家、游侠三者结合在一起,依赖于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功成身退。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个性在山水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如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送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这一泻千里,咆哮愤怒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都曲折地代表了李白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和决心。
李白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优美的,而是雄伟的;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顶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狂放不羁的叛逆性格,他好像要登涉山川和天地星辰同呼吸,和神灵相往来。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其中对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从娴静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幻入仙境,更完全是色彩缤纷的神话世界,诗人尽情驰骋于浪漫想像的空间,展示了一幅现实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朦胧离奇的奇山异景图。令人留恋忘返。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放,难怪他梦醒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李白虽被人号称“诗仙”“谪仙”,但他目睹和经历了唐帝国的繁荣、危机、战乱,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本质决定着他还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
李白非常关心国家的强大统一,象盛唐边塞诗人一样,热情讴歌保卫祖国边疆的戍边卫士。《塞下曲》其一写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眼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显示了边防将士不畏艰苦,勇敢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他们忠勇为国的高尚品质,实际上也是诗人渴望以身许国政治豪情的反映。《塞下曲》第六写道:“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诗中描写了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终能得到重新任用的机会,为国家消除边患,最后两句不但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
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虽远在江南,却写了一系列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他在《永王东巡歌》里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深感焦急忧虑。后来他因从 的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的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他在《赠张相稿》中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在《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首长诗中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的爱国之心至老不衰。
李白还有少数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处处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如《丁督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当时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营造宫室甲第和点缀园林,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盛夏酷热,天旱水涸时拖运巨石的艰辛与劳苦,对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再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致。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 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食。”第三、四句的“苦”和“寒”二字,凝结着农民无限的辛酸,诉说了他们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贫苦,虽然女主人盛情待客,但用来款待客人的只有 胡饭,此情此景,使空有满腔热情、远大抱负的李白产生了对荀媪的感激惭愧之情。
五、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作,不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在《江上吟》中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诗圣杜甫也高度称赞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化的形象,强烈的主观色彩
李白的生活经历很广,思想很复杂,他那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时不可磨灭地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色彩。
2.大胆的夸张、惊人的幻想、瞬息万变的感情
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又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恢宏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自己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3.语言质朴、清新、豪放,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字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是李白对自己诗歌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首诗的普通的景物普通的比喻显示了李白与朋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厚友情,语意极其真挚自然。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性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诗人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李白的诗中,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高度成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