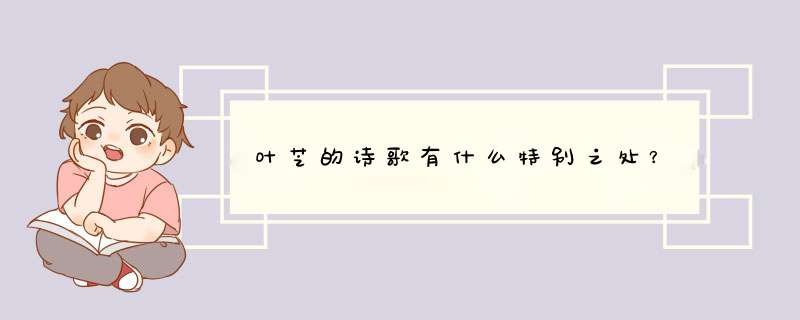
威廉·巴特勒·叶芝,也可以翻译成“叶慈”、“耶茨”。叶芝是爱尔兰伟大的诗人、散文家、神秘主义者。威廉·巴特勒·叶芝还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领袖,艾比剧院的创始人之一。叶芝的诗歌受到很多文艺思想的影响,最终演变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生在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不远的一个叫做山迪蒙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童年时期,他分别在都柏林和伦敦度过。叶芝早期学习过绘画,而且还是伦敦艺术家中年轻的一员,经常关注当地期刊《黄皮书》。叶芝和一些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当时除了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之外,他们还对古代的传奇故事、诗歌、民歌等进行翻译和挖掘,这些工作对运动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场运动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艾比剧院的建立。成立的前两年并没有获得成功,之后在他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有了起色。等到著名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参与进来之后,他们的团体还赚到不少钱,并且还修建了艾比剧院。叶芝通过朋友庞德认识许多现代主义者,这个使得他的作品跟早期的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等到晚年期间,他不再像中年一样关注政治相关的题材,而是开始了自己独有特色的风格写作。叶芝开始为自己的家人进行写作,有时候还描写时间的流逝,表达自己的无奈和感伤。
叶芝是21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他是象征主义诗歌在英国的早期代表人物,对21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叶芝的历史就是世纪之交爱尔兰的历史,而他的诗歌则将他个人的历史与那一时期的爱尔兰历史融为一体。
年轻时代的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之一,其早期诗歌多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传奇与民谣。叶芝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诗中的一大主题;而与叶芝的民族主义激情紧密相连的是他对献身于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杰出女演员莫德·冈的爱情,因而爱情对于叶芝也是个终生的主题。他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对爱尔兰戏剧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叶芝的这一连串人生经历同其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凭着他那能创造神话的想象力,叶芝将生活中许多平凡事件化为美妙的诗句,再在他的诗中创造出具有叶芝风格的象征主义。而且,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叶芝的许多诗中亦得到了表现。在创造他的艺术、他的象征主义的同时,叶芝似乎也急欲为历史画像。也许是受到了神秘主义(包括布莱克的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一幅神秘的历史画像颇具悲剧色彩。人的命运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历史的轮盘不停地旋转,已现的必将重现。《丽达与天鹅》与《基督重临》描述的正是这一主题。多样性的人生,多样性的主题,多样性的风格与技巧,时隐时现的历史影子,构成了叶芝诗歌的伟大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后世的评论家一般将叶芝的诗歌分为三个时期。
叶芝的早期诗歌创作包括他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芦苇中的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为止。初入诗道,叶芝接受的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对他深具影响的是前拉斐尔派诗人及其后继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说是叶芝的最主要的影响者。莫里斯是叶芝的朋友,他对叶芝的影响在《莪相的漫游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为明显。布莱克和雪莱也对叶芝早期的诗歌产生过影响,因为叶芝曾编选过布莱克的诗集(1893)。这些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信念及情感使叶芝深有感触。
然而,尽管叶芝的早期诗歌属于自十九世纪发展而来的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其爱尔兰背景,他的早期诗歌以其独特的爱尔兰题材而有别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叶芝独特的早期风格: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诗中所述人物则多为爱尔兰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智者、诗人以及魔术师等。同时,这些诗表现出一种忧郁抒情的氛围,笔触颇似雪莱。对于年轻敏感的叶芝而言,诗就是梦,梦能保护俗世中的诗人,而他从孩童时就沉浸于其中的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故事则是他寻梦的遥远去处。这一时期的主题大多为回忆和梦想,其顶峰之作也许就是“茵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诗可谓叶芝白日梦的杰作,实际上反映的是诗人对故乡爱尔兰的一种思恋情绪。其广为传诵的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其彻底的浪漫主义主题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叶芝中期创作的诗歌主要包括《在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1904)《绿色头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责任》 ,(Responsibilities,1914)《库尔的野天鹅》 ,(The Wild Swan at Coole,1917,1919)以及《迈克尔·罗巴茨与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Dancer,1921),其时间跨度约为1899年《芦苇中的风》出版之后至1926年《幻象》 (A Vision,1925)出版之前。关于叶芝诗歌时期的划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主要以其诗歌主题、风格变换为参照。正当叶芝感到早期风格已到顶点,而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时,艾兹拉·庞德进入了叶芝的生活圈子,并对其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叶芝中期诗歌中有一种新的精微的具体性,这一特点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共通之处。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措词上,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质朴无华的、具体的风格。它更关注精神的意象和细节,所表现的情感也更为明确。
这一时期,叶芝开始用贵族的理想观点来衡量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革命者及爱尔兰大众,其结果只能是失望。在叶芝看来,暴力、内战并非爱国的表现,而是“黄鼠狼洞里打架”。他觉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缺乏在约翰·奥利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尔兰传说中的高贵和古老的英雄主义气质。对爱尔兰政治的失望使得叶芝改变了他的诗风。早期寓言般的梦想被抛弃了,他的诗更加现实、复杂、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岛”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征主义柔弱无力,必须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为此,叶芝发展了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集中表现在《幻象》(1926)一书中。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周而复始,当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许多诗歌就是这种历史理论的直接说明。
叶芝后期诗歌的风格更为朴实、精确,口语色彩较浓厚,多取材于诗人个人生活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且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思索。后期诗歌包括诗集《钟楼》(The Tower,1928)《盘旋的楼梯》 ,(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圆月》 ,(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后的诗歌及两个剧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钟楼》收集了叶芝的一些内涵最丰富的诗,如:“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钟楼”、“内战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丽达与天鹅”以及“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对于叶芝来说,生活与艺术是一种冲突。随着年纪不断增大,年龄与欲望又成为一对矛盾。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诗人构造了日渐衰老的肉体的渴望与灵魂对自由的向往。诗中,一位老人拒绝了年轻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摆脱肉体束缚而追求永恒的艺术世界的愿望。在“在学童们中间”一诗中,他也谈到了时间与人生的问题。而“丽达与天鹅”则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历史循环这一主题上。
《弯弯的楼梯》(1933)包括了一些很优秀的哲理诗,如“自我与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ofSelf and Soul),但也有一些是回忆过去的诗歌,包括对朋友的怀念。其中“库尔庄园与巴利里”(Coole Park and Ballylee,1931)一诗谈到诗人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友谊与他们的文学功绩。诗云: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选择了
传统的神圣与美好为主题。
这“最后”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叶芝在文学史中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圆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组称为“超自然的歌”的文学诗。这些诗浓缩了叶芝的思想,语言简朴。其中“人的四个年龄阶段”一诗体现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叶芝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诗的象征》一文中,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幻象》中的思想也并非什么完整的理论,而是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一种价值观念。叶芝是个诗人,他的成就在于那多样性的诗歌,丰富的题材与想象。此外,娴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华兹华斯统治了上一个世纪的英语诗歌,那么叶芝则统治了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英国与爱尔兰诗歌。
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我谈不出什么可以帮助青年作者们的内容,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像我那样开始。在学校的时候我用于预备第二天功课的时间要比大多数学生多,然而却什么都学不会。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垫底,只有一两门功课我根本不用学。我父亲会对我说:“你对你没兴趣的事总是不能集中精神,可我送你去上学就是为了让你学习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不曾受过什么“诗歌气质”的折磨,我写作是出于某种心理缺陷。当不了大学者就当更大的诗人。即使在今天,当我置身常人之中,我依然要和缺乏自信做斗争,这种缺乏自信来自日常的羞辱,因为别人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可以费劲地读一点法语诗歌,但我曾努力学习过的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却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关于我的学生时代,只有一个回忆能带给我快乐;尽管我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学校读书时,我在班上总是叨陪末座,但我的朋友们却名列前茅,因为那时,一如现在,我讨厌傻瓜。当我想知道某人是否值得信任,我就要看他是否品学兼优。在爱尔兰的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查尔斯·约翰逊,他的父亲是奥兰治的***。在中考中他成了整个爱尔兰的状元。数年后我在美国碰到他时,他说:“我什么都一学就会,可什么都不想学。”某种本能使我们两人走近,我只对他才朗诵我的诗作。那都是些诗剧——除了有一首以斯宾塞诗节写成的长诗,长诗写到一位今已淡忘的女人,她是否漂亮,是否从哪儿抄来的,是否在购物时走丢了,这一切我都记不清楚。我记得那三个剧本,没有任何价值,其中之一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伊丽莎白时代的风格,场景是日耳曼森林;另一个剧本是对雪莱的模仿,场景是月亮上的一个火山口;再一个剧本源自某人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其场景为一座印度寺庙。查尔斯·约翰逊太喜欢这些诗的某些段落了,我怀疑他是否想过我已将这些剧本写到了家。那出印度剧的一个片段,或整个剧本,被我放在了我的《诗合集》的开头部分,我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查尔斯还活着,而如今这剧本还在书中是因为我忘了将它撤出来。有时我怀疑我写诗是不是为了医治我的精神不安,就像猫在便秘时吃缬草一样。但这样也不行,因为在我变得深深的谦卑以前,我已经对骄傲、自信的人感兴趣了。有人说我举止矫揉造作,如果真是这样,或许的确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十一二岁时父亲带我去看过厄文的著名的《哈姆雷特》。多年以后我漫步在都柏林街头,无人看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摆出一副高视阔步的样子,被戈登·克莱格比作舞蹈中的动作,我让我塑造的人物用厄文那种沉思的沮丧的野蛮腔调说话。两个月前,在描述基督重临时我写下这样两行诗:
是什么将蚊蝇一下子哄起?
是厄文和他那骄傲的香气。
不应认为一个青年诗人必定忧郁而孱弱,或他必有过孤独的挣扎。我想某些功成名就的老人会认为他们在学生时代就获得了令人愉快的声望;我那时当然也有一小帮人欣赏我那些一钱不值的作品,他们的欣赏给了我巨大自信的理由。
我在十八九岁时写了一出田园剧,这出剧受到济慈和雪莱的影响,也受到约翰逊《悲哀的牧羊人》的左右。我的一个朋友把它拿给三一学院的某些大学生看,当时他们正出版着《都柏林大学评论》这样一份雄心勃勃的政治和文学期刊,这份期刊办了几个月。我不记得是谁拿给他们看的,肯定不是查尔斯·约翰斯顿,他那时已通过印度民事机构的考试去了印度,并且在那儿一直待到他厌倦了那里的生活为止。那时我进了美术学校,因为美术是我的家庭专长,而且因为我认为我无法通过三一学院的入学考试。那些大学生们喜欢我的诗,并且邀请我把诗读给一个比我们都大四五岁的人。这人是巴里,后来成为古代史的专家和吉本著作的编者。我很兴奋,不只是因为他将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我的剧本,而且因为他是一位中学校长。我以前从未在我的私人生活中遇到过一位校长。上中学时有一次被校长爱德华·多登喊去,我太紧张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多登只好把我带入另一个房间。也许我可以让巴里对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我无法集中精神关注的东西。
我想一个人应该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深信不疑。有一次我对一位摆弄着马蹄铁形铁块,让我把头摆正位置的摄影师说:“由于你只用黑白相纸而不能拥有光和影,所以你不能再现自然。一个艺术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使用某种象征。”令我吃惊的是他并未因为我对他的攻击而愤怒,他回答说:“照相是技术工作。”即使今天我依然有如此思考的习惯,但只是针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几天前,我读到有关某大学会议的报道。当有人说“今天没有人再相信个人的魔鬼”时,阿克顿勋爵说:“我相信。”而我知道由于在他所计划出版的《牛津宇宙史》中并未包括个人魔鬼对于具体事件影响的内容,所以阿克顿勋爵是一个活生生的说谎者。由于我记不清的某种原因,后来我单独和巴里在一起时,我曾花大力气克服了我的羞涩,对巴里说:“我知道你会维护普通的教育制度,说它强化了意志力,但我相信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它弱化了冲击力。”他笑了,看上去有些尴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田园剧《塑像之岛》在《评论》上发表了,有好多年我没再看过它,但那时我所做的一切都未取得成功。我的《诗合集》收入了田园剧中两首抒情诗,不是因为我喜欢它们,而是因为在我收入它们的时候,与它们有关的朋友都还活着。这本书一出版,或还在出版之前,有两位将要对爱尔兰知识分子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影响了我,他们是老约翰·奥莱里和斯坦底什·奥格雷第。奥莱里是芬尼亚运动***,在他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青年爱尔兰”的诗人们的作品,而奥格雷第则用茁壮的浪漫的英语重写了某些古代爱尔兰的英雄传说。由于和这两个人交谈,由于其中一个借给我的书和另一个所写的书,我不再津津乐道于异国题材,我意识到种族比个人更重要,并开始写作《奥依幸的漫游》。这首诗和其他许多短诗一起以订购的方式出版,由约翰·奥莱里找来几乎所有的订购者。因此我成了崛起的诗人之一。我待在伦敦,有许多朋友,如果我每周挣不到一个男人或一个男孩食宿所需的20先令,我就去和我的家人或亲戚住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比伊莎多拉·邓肯幸运得多。邓肯在描述她早期的伦敦生活时说:“我拥有名望和王子们的热爱,但没有足够的食物。”作为一名职业作家我既笨拙又拘谨又懒散。当我写一篇书评时我不得不写出我自己的激烈想法,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从主题引发出思想;当我写一首只有6行的诗时我要花差不多6天的时间,因为我决心在自然语序中使用自然平易的词汇。在我的想象领域依然充满了诗学辞令,这还是我在学校读书时的老问题,唯一的不同是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1938年
(西川 译)
注释:
爱德华·戈登·克莱格(1872—?): 英国演员和舞台美术设计者。
约翰·巴格诺·巴里(1861—1927): 曾任都柏林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教授,著有《晚期罗马帝国史》和《希腊史》等。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录》。
巴伦·阿克顿勋爵(1843—1902): 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
斯坦底什·奥格雷第(1843—1928): 爱尔兰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其著作《爱尔兰史——英雄时代》对爱尔兰文学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 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
赏析
叶芝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成就居于欧美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很长,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是什么使他成为著名的诗人?又是什么让他具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呢?从这篇写于晚年的随笔《我变成了作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创作动因和创作历程。他自言:“我不曾受过什么‘诗歌气质’的折磨,我写作是出于某种心理缺陷。当不了大学者就当更大的诗人。”正是这种自信,成就了他的诗名。纵观其创作历程,从青涩到成熟,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三次转变。
叶芝的创作始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他早年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雪莱为榜样,同时也接受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是民间传说和历史英雄故事,幻想色彩浓重,忧郁、悲观、自我放纵的感情充斥其中,自然的想象,梦幻般的氛围以及音乐般的美构成他早期诗歌的主要特征。《茵尼斯弗利湖心岛》、《梦见仙境的人》等诗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然而,正当叶芝对象征主义深信不疑时,一位摄影家提醒他“照相是技术工作”,诚如诗歌的象征只是技术一样,它永远也不能“再现自然”。而古代史专家巴里则教会他懂得了诗歌的深层意蕴,促使他对诗歌创作进一步思考。
叶芝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风格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此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加上情场失意带来的痛苦,叶芝从传统诗人开始向现代诗人转变。除了进一步接受法国的象征主义和英国玄学派的影响,他还吸取了庞德和艾略特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转变后的叶芝开始由虚幻走向现实,用诗歌形式揭示深奥复杂的人类问题,如对生命的思索、对爱情的追问以及对政治和宗教的理解。早期诗中的忧郁、梦幻情绪被现实理想破灭后的愤慨、痛苦所代替。然而他的诗歌仍然是简洁而丰富的,既带有玄学派诗人的智慧、象征主义的意象,又具有现代诗歌的气息。《1913年九月》、《丽达与天鹅》等便创作于这一时期,诗中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辛辣讽刺,也表达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深沉思考。
叶芝进入半百之年后,迎来了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三次转变,中期创作中的冷嘲热讽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对青春流逝、生命荒废的感慨。他开始向往、呼唤永恒世界,试图从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中摆脱出来,进入到超越时空的艺术和智慧的世界中去。青春与衰老、爱情与战争、肉体与灵魂、生命与艺术的对立是他的后期诗歌经久不衰的主题,借以揭示出人类尴尬的生存处境。《幻象——生命的阐释》是他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就包含了他晚年对生命的意义、宇宙的永恒、历史的发展等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多重思考。这些思考让他的作品带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叶芝的一生是对诗歌创作不断探索的一生。在这篇回忆录性质的散文中,他谈到了他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与转变,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诗人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不倦怠、充满活力的灵魂。正是对诗歌难以割舍的终生热爱,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最终使叶芝成为一位获得世界认可的知名诗人。这也佐证了诗人的坚定信念:“一个人应该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深信不疑。”
(王媛媛)
叶芝,我最喜欢的外国诗人。
第一次读叶芝,还是这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
而诗人写这首诗时,他所爱恋的对象正值青春年少,有着靓丽的容颜和迷人的风韵。
若把话说在前面,这首诗我是完全喜欢不起来的。
是的,我们还不够年龄,不够成熟,我们叹服却难以共情。读起来颇有种《锦瑟》般的追忆与伤感
我们有时会崇尚真情,却难以真正理解。
直到后来,无意间得到一本《叶芝诗选》,我认识到这样一位诗人:
他在爱而不得中诉说着、践行着真情,
并顺手,将19世纪英文世界最美、最梦幻的诗句创造了出来。
韵脚解读:英文诗不同于中文古诗,主要以ABAB式、ABBA式(如前四句的dream、pride、betide、gleam)等的交替押韵
也许多人更喜欢轻柔淡写的文字而非华丽地堆砌辞藻,但叶芝,却在极致的浪漫主义中用诗词砌出了一个个梦境。
是的,叶芝的诗,绝不仅仅是像《当你老了》这样缠绵地吐露着深沉的真情。
我想,在这里,只为大家带来叶芝众多”主义“与元素中,最打动我的二者:唯美与永恒。
正如上诗《尘世玫瑰》,叶芝通过赋予玫瑰以永恒,并无刻意地塑造意境,却流于诗句将爱与唯美洋溢得淋漓尽致。
同时,他也会借助各种意象、诗句重复、对称:
韵脚解读:前四句ABAB与后四句BAAB 中间的B共用
叶芝对于她的终身恋人茅德·冈一见钟情,而且一往情深,叶芝这样描写过他第一次见到茅德·冈的情形:“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深深的爱恋着她。
下面这首诗多赋予了一种轮回与永恒的味道
“去恨,去爱,没什么抱怨。”
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求不得”——失意引发诗意从1889年遇到她的第一次起,茉德•冈昂就如影随形,不断出现在叶慈的梦里,心里,诗里;即便如今她已去世多年,却在叶慈的诗歌中永生。此后,叶慈又陆续向她求婚四次,一次一次地被惨拒。1917年,叶芝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向茉德•冈昂求婚,失败。好友格雷戈里夫人鼓励他继续努力,而他只回答了一句话,“不,我已经累了,不想再折腾了。”这时,离他在苹果花下对茉德•冈昂一见钟情,已经过去28年了。这一年,叶慈已经52岁了。
娓娓读来,诗人似乎宁愿愿意失去这世界,而仅仅是沉醉在纯粹的美中。
纯粹,这亦是我所推崇的,抛去”接受美学“,不去过多理解诗人或背景,而从纯粹的诗句中获得纯粹的美感。
你是否能想象,所有的诗,都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女人所写,以至于人们感谢这位名为茅德·冈的女子的拒绝,让诺贝尔文学奖上再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的艺术代表着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叶芝早年的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风格,善于营造梦幻般的氛围。后期转向了神秘主义与自我想象的象征主义。
本文重点仍在欣赏前者。
不妨看一眼除了”唯美“以外的主题。
——我最喜欢的诗之一
天鹅是叶芝的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通常,叶芝以天鹅象征人类的灵魂层面。
即使灵魂失去了某些激情之时,少些刻意地追寻美,而是去发现美。
试着如同天鹅般变得平静、优雅,也许,我们仍能收获远飞。
他淡淡写下墓志铭:
cast a cold eye , on life , on death , horseman , pass by
冷眼一瞥,生与死,骑者且前行。
就这样,遗憾永远留在那个美丽而战乱的时代,一个传统而追逐美丽的诗歌时代。
而,诗以美本身必将永恒。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