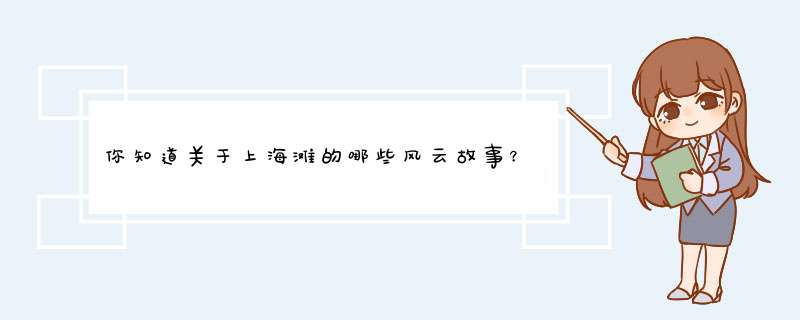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一恶少阎瑞生嗜赌成性,后来“花界红人”王莲英在她的朋友家中邂逅阎瑞生,阎瑞生见王莲英穿金戴银,因而萌生抢劫杀人的念头。为此,阎瑞生先向朱老五借了一辆汽车,然后假意邀请王莲英去兜风,借以行凶作案,并弃尸麦田。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我国著名音乐家何占豪、陈钢先生在1959年创作完成的,并在同年5月27日在上海首演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正统历史的记载里是由来没有什么根据,可是它在中国民间至少已流传了六七百年以上,无南无北,都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传说,甚至还有各种遗迹。
“梁祝”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杭州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
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会稽(今绍兴)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
不一日,二人来到杭州城的万松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
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贸阝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又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
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贸阝城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
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在朝廷做宰相的上虞名人谢安听说这一奇事,就奏请皇帝,敕封为"义妇冢"。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正统历史的记载里是由来没有什么根据,可是它在中国民间至少已流传了一千六百年以上,无南无北,都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传说,甚至还有各种遗迹。它可以说是民间故事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迫使统治阶级官书性质的"地方志",也不得不郑而重之地把它收集下来,作成一种"准历史的记载"。这就是《宁波府志》里面何以会有梁祝故事的来历。
《宁波府志》不但肯定了梁祝是东晋时代的人物,连梁山伯的生年和死年,也说得清清楚楚(按其所记,山伯是生于352年,死于373年)。至于所记的梁祝籍贯,家世以及情死的经过,大体上也是和一般传说相似,显然它是从民间传说的轮廓上构画来的。唯一需要解释的是,它根据了什么材料能够把年代肯定得这样结实。
清朝人有好几种笔记本,说到梁祝,似乎都是取材于《宁波府志》,也许有一、二种是写在府志之前而为它所取材的,反正这也没有多大出入,来历总不外乎是民间传说。
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流传在民间至少已有六七百年呢?因为南宋时代早就有了"祝英台近"或"祝英台"的词牌名称(后来曲牌也有),元曲的大作家王实甫,也曾在他的"王彩云丝竹芙蓉亭"里,借王彩云的口,唱出了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人物的名字,表演她求爱的苦闷心情,里面就有两句:哎!你个梁山伯不采(睬)我祝英台,羞的我怏怏而来。"梁祝的名字和宋玉、巫娥、周瑗姬、卓文君等摆在一起,说明了他们俩的名字在当时是怎样的被人熟习。
不过,这个故事在元朝、明朝时期,都是被当做虚幻的故事看待,不作为历史故事来处理。这也有一个旁证:明人杨守阝止 有一首《碧鲜坛》诗,是依据其封建礼法观点大骂祝英台的。诗中列举了历史上几个女扮男装的事例,如堤萦、木兰等,恭维她们是"事缘不得已,乃留千古名",接着就质问"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照这个封建小丑的见解,女孩子要念书尽可以在家里念,象班昭那样,没有"男儿朋"也一样的成就了学问。底下他就说:"悠悠稗官语,有无不可征",这意思就是否认它的真实性。
从上引的两条,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流传的年代是很久的,六七百年不过是最低的估计。
问题在:梁祝故事流传得如此久,势力如此大,而除去官书,笔记外,我们却看不到以它为题材的古典文学作品,甚至于在中国的俗文学史上,简直找不到关于它的一些痕迹。
我们现在要研究白蛇、赵五娘、孟姜女、李三娘,可以从明朝以及明朝前的小说戏曲作品中,去寻得若干材料,从而检认这些故事的演化过程,可是对于梁祝故事却没有多大的办法。我翻了一下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毫无所获。
明朝的小说戏曲作者,是最善于从民间传说的角落里找材料的,他们不会放过这样的好题目;而且在杨守阝止 的《碧鲜坛》诗里,不是明明在说"悠悠稗官语,有无不可征"吗?可见至少在明朝是有一种"稗官"取材于梁祝故事的,但是几百年来文献散失,现在我们已找不到那样的东西了。过去我翻阅郑振铎介绍《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在《拍案惊奇二刻》的目录里,发现"同窗友将假作真"一条,很像是指梁祝,后来拿《今古奇观》一对证,才知道就是写闻俊卿女扮男装读书择婿的故事,和梁祝是不相干的。
我们知道,各地都有梁祝故事的唱本,石印小字本的梁祝小说,也曾有过,尽管这都是很晚出的东西,现在搜寻起来却也不大便利。
梁祝故事的流传区域,几乎遍及全国,故事地点的说法也各不同,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是浙江说(认为地点是在杭州、宁波、上虞一带),一是江苏说(虽承认梁祝的浙江籍贯,但是指梁祝读书的地点。在江苏宜兴善权寺后还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大字石刻,并且指附近的祝陵就是祝英台的葬地)。总之,这个传说在江苏浙民间是最有力的,而检查江南最流行的弹词本,却也不见它的踪迹。
抗日战争以前,郑振铎从苏州、扬州、杭州、南京各地搜集了弹词本一百多种,编成书目,比较最重要而最普遍的本子,可以说是相当地收轹完全了;阿英在这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他收到《真本玉堂春全传》可以说是一个收获,可是他们都没有得到梁祝故事的弹词本。
事实上,较远期的梁祝唱本、话本和小说本,是不会没有的,甚至在宋人话本中也可能早已有过。(王实甫引了它的情节入曲,几乎不是得于口传,元曲获取宋人话本材料,是有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的研究和探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为程砚秋深爱国家
程砚秋悲切地说,“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做外国奴,他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亡国奴的屈辱,急切地盼望中国人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程砚秋万分高兴,逢人便说:“看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真高兴呀!我早就相信中国亡不了!艺术亡不了!”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做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寇在华的种种罪行。同时,他宣布,改“三闭主义”为“三开主义”,即开口、开眼、开心,开始重新登台演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在军政委莫文骅率领下进入北平城,接管北平的防务。2月1日,41军军部和直属队进驻报子胡同。由于41军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41军军部也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部的通讯科就住在18号程砚秋家。为了表示对程先生的谢意,莫文骅和41军军长吴克华、军政治部主任欧阳文来到程先生家。程先生见到他们,激动地说:“贵军为民赴汤蹈火,理应盛情款待,只是家人甚多,寒舍狭小,实在抱歉。”几位军首长赶忙说:“这已经给您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请程先生海涵。”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重新开始在京剧舞台上活跃起来。1950年,程砚秋在西安表演后写成《西北戏曲调查小记》,掀起了西北之行演出的序幕。在此期间,程砚秋曾与贺龙元帅邂逅,贺龙元帅赠宝刀一柄,并说,“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1951年,程砚秋赴西南考察返回路过武汉时,得知当地同志们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还差几个“螺丝钉”,立即不顾劳顿辛苦,在汉口连唱五天义务戏。
程砚秋入党 周总理点赞
1957年春天,程砚秋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对于程砚秋在抗战期间的爱国壮举,周恩来总理曾赞扬道:程砚秋坚持民族气节,反对日伪统治,毅然息影剧坛,避居山村,荷锄务农的爱国主义壮举,不仅在当时成为鼓舞人们抗日救国的巨大精神力量,而且将永远在中华民族抗敌御侮、争取解放的斗争史册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经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讨论通过,程砚秋成为中国***预备党员。
1958年程砚秋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正式党员。
如果大而化之地研究京剧,那就可以通过透视一个人(梅兰芳)进行。如果范围稍微扩大,就可以
通过透视一个集团(如四大名旦)进行。四大名旦在1927年由报社组织戏迷自发选举产生(顺序依次是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其作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它内部也发生了微调,其顺序
变成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一出,立刻产生出诸多的“派生物”,比如“四大
须生”、“四小名旦”、“四大坤旦”、“上海(南方)四大名旦”等。但没有哪一个能和四大名旦齐
眉比肩。在近现代京剧史上,从没有哪个集团可以贯穿如此长久的时间,也没有哪个集团可以把影响波
及到所有行当、流派中去。如今,四大名旦都变成了“古人”,但他们的艺术流派、魅力和方法,他们
分别在文化上的建树,不但流传至今,还必将延续下去。昔日,他们合灌过《四五花洞》的唱片,其实
只有每人一句,但它风靡了几十年,甚至使得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海派新戏《盘丝洞》,主人公蜘蛛精还
要在一个唱段中学唱四大名旦的唱腔。四大名旦曾合影过几次,每一张合影都让戏迷珍藏,如果久久凝
视,其中的文化背景便能告诉你许多“上不了纸面”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三大名旦的合影,也能产生相
似的功能。这“三”与“四”之间的空隙,恰恰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无须讳言,所谓“问题”者,不
外就是一些矛盾以及它解决的过程。
梨园是个很讲门派的地方。遇到公众都有的剧目,内行都问你跟从的是哪一派。梅、程有区别,梅
、尚也有区别,三位青衣和一位花旦的区别就更大。既提倡“艺术平均分要高”,事实上又实行“一招
先,吃遍天”。四大名旦都是从“一招”起家的,他们一旦成名,很快就注意各个艺术单项平均发展,
最突出者就是梅兰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中国京剧院,就注意运用比较文化的观点,去品味这四位大师的艺术风范
,既寻找其共同点,也努力发现其不同点。我采访了这四个家族,认识了他们的夫人、子女和主要传人
,先后写过四个家门的访问记。我是单个写又单个发表的,在当时自然只能“都说好(的一面)”。事
实上每个人并不是“都好”,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从而
完善和丰富了观众的艺术视野和审美情趣。
梨园人是“警惕”的,他们从一开始向后辈传授技艺时,就防范后人将来会“欺师灭祖”。一旦发
现有这个倾向,抛弃之,毁灭之,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近十年间,我集中力量研究了梅兰芳文
化现象,为此我挨过些“小骂”,但从大处讲,我的收益就实在太大了。搞艺术研究,就一定是要有比
较的。我说梅兰芳,实际就是对比其他三位(以及其他行当、流派的许多位)。我的《梅兰芳三部曲》
,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今,北京图书馆分馆提供了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提倡积极探讨的场
合,我也退出了梨园的第一线,同时岁数和身体也要求我抓紧时间说真话,于是三思之后,就确定下这
个题目。我一共讲了四讲,准备进一步收集材料,最后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根据图书馆的要求,先把
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编进这本合集当中。
我在讲课时就说:它貌似“老问题”,因为关心这个题目的人,似乎都得超过50岁;但我真的谈完
了,听众中赞同的人又有几许?我心里没底。其实呢,它是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为京剧要前进
,就绕不过这个“早成定局”的四大名旦,而且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新认识。不这样做,似乎就无法
开创新局面。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急迫了。对京剧知之较深的人,一是数量少了,二是岁数偏大,而对于
其新理念的“运做”,偏偏又须通过50岁以下的人去实践。我早过了50岁,但又与50岁以下的人有密切
的联系。历史需要认真去做这个课题。从时机讲已经晚了,但不能再晚。
先说几句正面肯定的话,这不是套话,而是铁的事实。四大名旦是什么?是梨园的旗帜,是历史的
骄傲,是时代进一步的缩影,同时也是今天梨园继续前进的“阻力”或“包袱”。他们空前绝后,京剧
行程中只有过他们的“这一次”。历史不会倒流,所以他们既不会被复制,更不会被超越。京戏如今遇
到了麻烦,这麻烦要求我们认真“补课”,力求做好这个课题。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豁”出来
一“试”的。既然是“试”,或许就会失败。一但我失败了,依然会有再后来的人去“试”的。
他们分别出生在:(梅)1894、(尚)1900、(荀)1900、(程)1904。各自的艺术特征:他们
共同的老师王瑶卿这样归纳: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
”。这是王瑶卿非常有名的“一字评”。王瑶卿只用一个字去概括,比用“梅兰芳的富丽雍容、程的沉
郁深刻……”这样的泛泛之词,都更入木三分。他们同唱旦行,但又各有侧重。20世纪30年代,广大观
众曾给他们四位一个评分表。其中有单项分数,也综合总分。梅兰芳在单项上不是都第一,但总分他最
高,年轻时如此,晚年亦如此。这或许是梅兰芳一直在整个序列中一直领先并领衔的道理所在。但千万
不要绝对化,因为京剧在重视综合的同时,也是重视单项的。程砚秋的“唱腔”独特,不是风靡了几代
人?总之,登高在文化的云霄俯瞰,近现代京剧的行程,被四大名旦的光辉笼罩了半个世纪以远。在此
之前之后,似乎还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次下决心展开比较,办法有三:一、“主谈一人,对比另外三位”;二、“对比着谈两人”;
三、从“层面”上对比这两位与那两位
“恰如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到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说的是那难以捉摸的缘。缘是奇异的,有灵气,却无定迹。不知道何时会来,也不知道何时会去。来得无声无息,如天外飞仙,去也无踪无迹,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仿佛有缘了,你觉得“千里来相会”;忽而却又销声匿迹,“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只好望洋兴叹,大呼“无缘对面不相逢”。然而相信缘分的,总是心里存了希冀,觉得此时无缘,未必彼时也无缘。或许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或许也会邂逅于某一天某个想不到的所在,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呢。
如果大而化之地研究京剧,那就可以通过透视一个人(梅兰芳)进行。如果范围稍微扩大,就可以
通过透视一个集团(如四大名旦)进行。四大名旦在1927年由报社组织戏迷自发选举产生(顺序依次是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其作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它内部也发生了微调,其顺序
变成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一出,立刻产生出诸多的“派生物”,比如“四大
须生”、“四小名旦”、“四大坤旦”、“上海(南方)四大名旦”等。但没有哪一个能和四大名旦齐
眉比肩。在近现代京剧史上,从没有哪个集团可以贯穿如此长久的时间,也没有哪个集团可以把影响波
及到所有行当、流派中去。如今,四大名旦都变成了“古人”,但他们的艺术流派、魅力和方法,他们
分别在文化上的建树,不但流传至今,还必将延续下去。昔日,他们合灌过《四五花洞》的唱片,其实
只有每人一句,但它风靡了几十年,甚至使得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海派新戏《盘丝洞》,主人公蜘蛛精还
要在一个唱段中学唱四大名旦的唱腔。四大名旦曾合影过几次,每一张合影都让戏迷珍藏,如果久久凝
视,其中的文化背景便能告诉你许多“上不了纸面”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三大名旦的合影,也能产生相
似的功能。这“三”与“四”之间的空隙,恰恰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无须讳言,所谓“问题”者,不
外就是一些矛盾以及它解决的过程。
梨园是个很讲门派的地方。遇到公众都有的剧目,内行都问你跟从的是哪一派。梅、程有区别,梅
、尚也有区别,三位青衣和一位花旦的区别就更大。既提倡“艺术平均分要高”,事实上又实行“一招
先,吃遍天”。四大名旦都是从“一招”起家的,他们一旦成名,很快就注意各个艺术单项平均发展,
最突出者就是梅兰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中国京剧院,就注意运用比较文化的观点,去品味这四位大师的艺术风范
,既寻找其共同点,也努力发现其不同点。我采访了这四个家族,认识了他们的夫人、子女和主要传人
,先后写过四个家门的访问记。我是单个写又单个发表的,在当时自然只能“都说好(的一面)”。事
实上每个人并不是“都好”,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从而
完善和丰富了观众的艺术视野和审美情趣。
梨园人是“警惕”的,他们从一开始向后辈传授技艺时,就防范后人将来会“欺师灭祖”。一旦发
现有这个倾向,抛弃之,毁灭之,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近十年间,我集中力量研究了梅兰芳文
化现象,为此我挨过些“小骂”,但从大处讲,我的收益就实在太大了。搞艺术研究,就一定是要有比
较的。我说梅兰芳,实际就是对比其他三位(以及其他行当、流派的许多位)。我的《梅兰芳三部曲》
,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今,北京图书馆分馆提供了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提倡积极探讨的场
合,我也退出了梨园的第一线,同时岁数和身体也要求我抓紧时间说真话,于是三思之后,就确定下这
个题目。我一共讲了四讲,准备进一步收集材料,最后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根据图书馆的要求,先把
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编进这本合集当中。
我在讲课时就说:它貌似“老问题”,因为关心这个题目的人,似乎都得超过50岁;但我真的谈完
了,听众中赞同的人又有几许?我心里没底。其实呢,它是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为京剧要前进
,就绕不过这个“早成定局”的四大名旦,而且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新认识。不这样做,似乎就无法
开创新局面。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急迫了。对京剧知之较深的人,一是数量少了,二是岁数偏大,而对于
其新理念的“运做”,偏偏又须通过50岁以下的人去实践。我早过了50岁,但又与50岁以下的人有密切
的联系。历史需要认真去做这个课题。从时机讲已经晚了,但不能再晚。
先说几句正面肯定的话,这不是套话,而是铁的事实。四大名旦是什么?是梨园的旗帜,是历史的
骄傲,是时代进一步的缩影,同时也是今天梨园继续前进的“阻力”或“包袱”。他们空前绝后,京剧
行程中只有过他们的“这一次”。历史不会倒流,所以他们既不会被复制,更不会被超越。京戏如今遇
到了麻烦,这麻烦要求我们认真“补课”,力求做好这个课题。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豁”出来
一“试”的。既然是“试”,或许就会失败。一但我失败了,依然会有再后来的人去“试”的。
他们分别出生在:(梅)1894、(尚)1900、(荀)1900、(程)1904。各自的艺术特征:他们
共同的老师王瑶卿这样归纳: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
”。这是王瑶卿非常有名的“一字评”。王瑶卿只用一个字去概括,比用“梅兰芳的富丽雍容、程的沉
郁深刻……”这样的泛泛之词,都更入木三分。他们同唱旦行,但又各有侧重。20世纪30年代,广大观
众曾给他们四位一个评分表。其中有单项分数,也综合总分。梅兰芳在单项上不是都第一,但总分他最
高,年轻时如此,晚年亦如此。这或许是梅兰芳一直在整个序列中一直领先并领衔的道理所在。但千万
不要绝对化,因为京剧在重视综合的同时,也是重视单项的。程砚秋的“唱腔”独特,不是风靡了几代
人?总之,登高在文化的云霄俯瞰,近现代京剧的行程,被四大名旦的光辉笼罩了半个世纪以远。在此
之前之后,似乎还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次下决心展开比较,办法有三:一、“主谈一人,对比另外三位”;二、“对比着谈两人”;
三、从“层面”上对比这两位与那两位
“恰如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到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说的是那难以捉摸的缘。缘是奇异的,有灵气,却无定迹。不知道何时会来,也不知道何时会去。来得无声无息,如天外飞仙,去也无踪无迹,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仿佛有缘了,你觉得“千里来相会”;忽而却又销声匿迹,“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只好望洋兴叹,大呼“无缘对面不相逢”。然而相信缘分的,总是心里存了希冀,觉得此时无缘,未必彼时也无缘。或许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或许也会邂逅于某一天某个想不到的所在,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呢。
如果大而化之地研究京剧,那就可以通过透视一个人(梅兰芳)进行。如果范围稍微扩大,就可以
通过透视一个集团(如四大名旦)进行。四大名旦在1927年由报社组织戏迷自发选举产生(顺序依次是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其作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它内部也发生了微调,其顺序
变成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一出,立刻产生出诸多的“派生物”,比如“四大
须生”、“四小名旦”、“四大坤旦”、“上海(南方)四大名旦”等。但没有哪一个能和四大名旦齐
眉比肩。在近现代京剧史上,从没有哪个集团可以贯穿如此长久的时间,也没有哪个集团可以把影响波
及到所有行当、流派中去。如今,四大名旦都变成了“古人”,但他们的艺术流派、魅力和方法,他们
分别在文化上的建树,不但流传至今,还必将延续下去。昔日,他们合灌过《四五花洞》的唱片,其实
只有每人一句,但它风靡了几十年,甚至使得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海派新戏《盘丝洞》,主人公蜘蛛精还
要在一个唱段中学唱四大名旦的唱腔。四大名旦曾合影过几次,每一张合影都让戏迷珍藏,如果久久凝
视,其中的文化背景便能告诉你许多“上不了纸面”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三大名旦的合影,也能产生相
似的功能。这“三”与“四”之间的空隙,恰恰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无须讳言,所谓“问题”者,不
外就是一些矛盾以及它解决的过程。
梨园是个很讲门派的地方。遇到公众都有的剧目,内行都问你跟从的是哪一派。梅、程有区别,梅
、尚也有区别,三位青衣和一位花旦的区别就更大。既提倡“艺术平均分要高”,事实上又实行“一招
先,吃遍天”。四大名旦都是从“一招”起家的,他们一旦成名,很快就注意各个艺术单项平均发展,
最突出者就是梅兰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中国京剧院,就注意运用比较文化的观点,去品味这四位大师的艺术风范
,既寻找其共同点,也努力发现其不同点。我采访了这四个家族,认识了他们的夫人、子女和主要传人
,先后写过四个家门的访问记。我是单个写又单个发表的,在当时自然只能“都说好(的一面)”。事
实上每个人并不是“都好”,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从而
完善和丰富了观众的艺术视野和审美情趣。
梨园人是“警惕”的,他们从一开始向后辈传授技艺时,就防范后人将来会“欺师灭祖”。一旦发
现有这个倾向,抛弃之,毁灭之,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近十年间,我集中力量研究了梅兰芳文
化现象,为此我挨过些“小骂”,但从大处讲,我的收益就实在太大了。搞艺术研究,就一定是要有比
较的。我说梅兰芳,实际就是对比其他三位(以及其他行当、流派的许多位)。我的《梅兰芳三部曲》
,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今,北京图书馆分馆提供了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提倡积极探讨的场
合,我也退出了梨园的第一线,同时岁数和身体也要求我抓紧时间说真话,于是三思之后,就确定下这
个题目。我一共讲了四讲,准备进一步收集材料,最后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根据图书馆的要求,先把
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编进这本合集当中。
我在讲课时就说:它貌似“老问题”,因为关心这个题目的人,似乎都得超过50岁;但我真的谈完
了,听众中赞同的人又有几许?我心里没底。其实呢,它是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为京剧要前进
,就绕不过这个“早成定局”的四大名旦,而且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新认识。不这样做,似乎就无法
开创新局面。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急迫了。对京剧知之较深的人,一是数量少了,二是岁数偏大,而对于
其新理念的“运做”,偏偏又须通过50岁以下的人去实践。我早过了50岁,但又与50岁以下的人有密切
的联系。历史需要认真去做这个课题。从时机讲已经晚了,但不能再晚。
先说几句正面肯定的话,这不是套话,而是铁的事实。四大名旦是什么?是梨园的旗帜,是历史的
骄傲,是时代进一步的缩影,同时也是今天梨园继续前进的“阻力”或“包袱”。他们空前绝后,京剧
行程中只有过他们的“这一次”。历史不会倒流,所以他们既不会被复制,更不会被超越。京戏如今遇
到了麻烦,这麻烦要求我们认真“补课”,力求做好这个课题。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豁”出来
一“试”的。既然是“试”,或许就会失败。一但我失败了,依然会有再后来的人去“试”的。
他们分别出生在:(梅)1894、(尚)1900、(荀)1900、(程)1904。各自的艺术特征:他们
共同的老师王瑶卿这样归纳: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
”。这是王瑶卿非常有名的“一字评”。王瑶卿只用一个字去概括,比用“梅兰芳的富丽雍容、程的沉
郁深刻……”这样的泛泛之词,都更入木三分。他们同唱旦行,但又各有侧重。20世纪30年代,广大观
众曾给他们四位一个评分表。其中有单项分数,也综合总分。梅兰芳在单项上不是都第一,但总分他最
高,年轻时如此,晚年亦如此。这或许是梅兰芳一直在整个序列中一直领先并领衔的道理所在。但千万
不要绝对化,因为京剧在重视综合的同时,也是重视单项的。程砚秋的“唱腔”独特,不是风靡了几代
人?总之,登高在文化的云霄俯瞰,近现代京剧的行程,被四大名旦的光辉笼罩了半个世纪以远。在此
之前之后,似乎还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次下决心展开比较,办法有三:一、“主谈一人,对比另外三位”;二、“对比着谈两人”;
三、从“层面”上对比这两位与那两位
“恰如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到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说的是那难以捉摸的缘。缘是奇异的,有灵气,却无定迹。不知道何时会来,也不知道何时会去。来得无声无息,如天外飞仙,去也无踪无迹,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仿佛有缘了,你觉得“千里来相会”;忽而却又销声匿迹,“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只好望洋兴叹,大呼“无缘对面不相逢”。然而相信缘分的,总是心里存了希冀,觉得此时无缘,未必彼时也无缘。或许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或许也会邂逅于某一天某个想不到的所在,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呢。
如果大而化之地研究京剧,那就可以通过透视一个人(梅兰芳)进行。如果范围稍微扩大,就可以
通过透视一个集团(如四大名旦)进行。四大名旦在1927年由报社组织戏迷自发选举产生(顺序依次是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其作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它内部也发生了微调,其顺序
变成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一出,立刻产生出诸多的“派生物”,比如“四大
须生”、“四小名旦”、“四大坤旦”、“上海(南方)四大名旦”等。但没有哪一个能和四大名旦齐
眉比肩。在近现代京剧史上,从没有哪个集团可以贯穿如此长久的时间,也没有哪个集团可以把影响波
及到所有行当、流派中去。如今,四大名旦都变成了“古人”,但他们的艺术流派、魅力和方法,他们
分别在文化上的建树,不但流传至今,还必将延续下去。昔日,他们合灌过《四五花洞》的唱片,其实
只有每人一句,但它风靡了几十年,甚至使得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海派新戏《盘丝洞》,主人公蜘蛛精还
要在一个唱段中学唱四大名旦的唱腔。四大名旦曾合影过几次,每一张合影都让戏迷珍藏,如果久久凝
视,其中的文化背景便能告诉你许多“上不了纸面”的东西。甚至有许多三大名旦的合影,也能产生相
似的功能。这“三”与“四”之间的空隙,恰恰能够说明很多的问题。无须讳言,所谓“问题”者,不
外就是一些矛盾以及它解决的过程。
梨园是个很讲门派的地方。遇到公众都有的剧目,内行都问你跟从的是哪一派。梅、程有区别,梅
、尚也有区别,三位青衣和一位花旦的区别就更大。既提倡“艺术平均分要高”,事实上又实行“一招
先,吃遍天”。四大名旦都是从“一招”起家的,他们一旦成名,很快就注意各个艺术单项平均发展,
最突出者就是梅兰芳。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人中国京剧院,就注意运用比较文化的观点,去品味这四位大师的艺术风范
,既寻找其共同点,也努力发现其不同点。我采访了这四个家族,认识了他们的夫人、子女和主要传人
,先后写过四个家门的访问记。我是单个写又单个发表的,在当时自然只能“都说好(的一面)”。事
实上每个人并不是“都好”,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从而
完善和丰富了观众的艺术视野和审美情趣。
梨园人是“警惕”的,他们从一开始向后辈传授技艺时,就防范后人将来会“欺师灭祖”。一旦发
现有这个倾向,抛弃之,毁灭之,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近十年间,我集中力量研究了梅兰芳文
化现象,为此我挨过些“小骂”,但从大处讲,我的收益就实在太大了。搞艺术研究,就一定是要有比
较的。我说梅兰芳,实际就是对比其他三位(以及其他行当、流派的许多位)。我的《梅兰芳三部曲》
,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今,北京图书馆分馆提供了这样一个富于文化氛围、提倡积极探讨的场
合,我也退出了梨园的第一线,同时岁数和身体也要求我抓紧时间说真话,于是三思之后,就确定下这
个题目。我一共讲了四讲,准备进一步收集材料,最后是要写一本书的。现在根据图书馆的要求,先把
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编进这本合集当中。
我在讲课时就说:它貌似“老问题”,因为关心这个题目的人,似乎都得超过50岁;但我真的谈完
了,听众中赞同的人又有几许?我心里没底。其实呢,它是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为京剧要前进
,就绕不过这个“早成定局”的四大名旦,而且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新认识。不这样做,似乎就无法
开创新局面。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急迫了。对京剧知之较深的人,一是数量少了,二是岁数偏大,而对于
其新理念的“运做”,偏偏又须通过50岁以下的人去实践。我早过了50岁,但又与50岁以下的人有密切
的联系。历史需要认真去做这个课题。从时机讲已经晚了,但不能再晚。
先说几句正面肯定的话,这不是套话,而是铁的事实。四大名旦是什么?是梨园的旗帜,是历史的
骄傲,是时代进一步的缩影,同时也是今天梨园继续前进的“阻力”或“包袱”。他们空前绝后,京剧
行程中只有过他们的“这一次”。历史不会倒流,所以他们既不会被复制,更不会被超越。京戏如今遇
到了麻烦,这麻烦要求我们认真“补课”,力求做好这个课题。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豁”出来
一“试”的。既然是“试”,或许就会失败。一但我失败了,依然会有再后来的人去“试”的。
他们分别出生在:(梅)1894、(尚)1900、(荀)1900、(程)1904。各自的艺术特征:他们
共同的老师王瑶卿这样归纳: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
”。这是王瑶卿非常有名的“一字评”。王瑶卿只用一个字去概括,比用“梅兰芳的富丽雍容、程的沉
郁深刻……”这样的泛泛之词,都更入木三分。他们同唱旦行,但又各有侧重。20世纪30年代,广大观
众曾给他们四位一个评分表。其中有单项分数,也综合总分。梅兰芳在单项上不是都第一,但总分他最
高,年轻时如此,晚年亦如此。这或许是梅兰芳一直在整个序列中一直领先并领衔的道理所在。但千万
不要绝对化,因为京剧在重视综合的同时,也是重视单项的。程砚秋的“唱腔”独特,不是风靡了几代
人?总之,登高在文化的云霄俯瞰,近现代京剧的行程,被四大名旦的光辉笼罩了半个世纪以远。在此
之前之后,似乎还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次下决心展开比较,办法有三:一、“主谈一人,对比另外三位”;二、“对比着谈两人”;
三、从“层面”上对比这两位与那两位
“恰如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到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说的是那难以捉摸的缘。缘是奇异的,有灵气,却无定迹。不知道何时会来,也不知道何时会去。来得无声无息,如天外飞仙,去也无踪无迹,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仿佛有缘了,你觉得“千里来相会”;忽而却又销声匿迹,“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只好望洋兴叹,大呼“无缘对面不相逢”。然而相信缘分的,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落敌手。敌伪当局要求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义务表演,为日军唱捐飞机。在敌人的威逼下,很多人不敢不唱,唯有一人坚定地说:“我不能为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牵连。献机义务戏的事,我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此人,正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程派创始人程砚秋。
■人物小传
程砚秋:(1904~1958,满族正黄旗人)
原名承麟,著名京剧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程派创始人,中共党员。代表剧目有《锁麟囊》《窦娥冤》《荒山泪》《春闺梦》等。
对外称病 名旦退隐
程砚秋,著名京剧艺术家,1904年生于北京,6岁卖身学艺,11岁登台演出,17岁独立成班。1927年,他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被评选为“四大名旦”,那一年他才23岁。
1937年拒绝为日军唱戏后,程砚秋的日子过得很不平静。1941年,他乘102次列车从上海演出归来,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以伪警察徐大麻子为首的几个便衣,在罩棚下围住程砚秋,不容分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程砚秋从小学习武旦,师从多位名家,具有很好的武功根底,只见他挥拳左迎右击,徐大麻子等人挨了不少拳头。徐大麻子恼羞成怒,抡起刀鞘向程砚秋脸上打去。眼看程砚秋要吃亏,路经此处的铁路工人小沈机智地用日语喊道:“八嘎牙路(混蛋),不要打了!”别看徐大麻子对中国人耀武扬威,可对日本主子却百依百顺。一听这句日本话,徐大麻子等人马上住手。程砚秋乘机向出站口跑去,脱离了险境。回到家,程砚秋对夫人说:“我程某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重重的压力和敌人的机关算计极大地影响了程砚秋的日常生活,他不得不时刻处于防备状态中,这样的生活使他身心俱疲。在此情形下,程砚秋决定谢绝舞台、息演退隐。一方面,他对外宣称身体患病,不能登台演出,并托人请德国大夫亲笔开具了一个患病证明。另一方面,他告别了城里报子胡同的家人,到了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开始了务农生活。
村居务农 难避日伪
搬到青龙桥时适逢春节,程先生自书自撰一副春联:“蓄发事耕耘,杜门谢来往;殷勤语行人,早作退步想。”春联贴在门上,程砚秋便开始了村居的漫长生活。
一代名伶程砚秋真的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购置了60多亩地,添置牲畜、马车、农具,请了几位农民做帮工。烈日之下,只见他带着孩子跟随帮工来到黑山扈山坡锄地,身披青布衣褂,脚穿黑布鞋,俨然一位壮实的庄稼汉。在玉米地里,年轻的农家帮伙正在教程家父子“一步三锄”地耪玉米,他们共同练习前跨一大步,连耪三锄,将田间杂草除掉,还要注意不能伤了秧苗。还没干上一上午,大伙已经大汗淋漓。
此间,程砚秋宣称要实行“三闭主义”,即闭口、闭眼、闭心,意在避开日伪的骚扰。同时,他带来很多的历史古籍,专心攻读《汉书》《大宋宣和遗事》《明史》等书籍,由历史事件联系到中国当时的命运,又想到自己的处境,不胜感慨。他说:“前日已读完《汉书》《宣和遗事》,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令人不忍睹。现在该轮到我们来做亡国奴了,别无选择似的非要你逆来顺受。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他们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国破家亡,个人安危又算得什么?让他们来吧!”
虽然已经停止了登台演出,但此时的程砚秋仍然无时无刻不心系京剧。他一方面不断对自己以往的剧目精雕细琢,反复修改以日臻完美。甚至经常邀请友人同行切磋技艺。另一方面,结合自己攻读的历史古籍和心中所思,开始酝酿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凝合了他自己的心绪和感受,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比如经典剧目《通灵笔》。
世外桃源的生活并非始终平静。虽然程砚秋已经不登台演出,并且移居郊外。但日伪特务仍然经常上门骚扰。1944年2月的一个深夜,日本宪兵和伪警突然闯入程砚秋的家中,准备抓人。幸亏当日程砚秋未在家中,事后程夫人通过挚友申请保释,才免除了冤狱之灾。程砚秋悲切地说,“士可杀不可辱,”他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亡国奴的屈辱,急切地盼望中国人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闻获捷报 重登戏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程砚秋万分高兴,逢人便说:“看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真高兴呀!我早就相信中国亡不了!艺术亡不了!”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做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寇在华的种种罪行。同时,他宣布,改“三闭主义”为“三开主义”,即开口、开眼、开心,开始重新登台演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在军政委莫文骅率领下进入北平城,接管北平的防务。2月1日,41军军部和直属队进驻报子胡同。由于41军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41军军部也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部的通讯科就住在18号程砚秋家。为了表示对程先生的谢意,莫文骅和41军军长吴克华、军政治部主任欧阳文来到程先生家。程先生见到他们,激动地说:“贵军为民赴汤蹈火,理应盛情款待,只是家人甚多,寒舍狭小,实在抱歉。”几位军首长赶忙说:“这已经给您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请程先生海涵。”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重新开始在京剧舞台上活跃起来。1950年,程砚秋在西安表演后写成《西北戏曲调查小记》,掀起了西北之行演出的序幕。在此期间,程砚秋曾与贺龙元帅邂逅,贺龙元帅赠宝刀一柄,并说,“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1951年,程砚秋赴西南考察返回路过武汉时,得知当地同志们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还差几个“螺丝钉”,立即不顾劳顿辛苦,在汉口连唱五天义务戏。
补白
程砚秋入党 周总理点赞
1957年春天,程砚秋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经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对于程砚秋在抗战期间的爱国壮举,周恩来总理曾赞扬道:程砚秋坚持民族气节,反对日伪统治,毅然息影剧坛,避居山村,荷锄务农的爱国主义壮举,不仅在当时成为鼓舞人们抗日救国的巨大精神力量,而且将永远在中华民族抗敌御侮、争取解放的斗争史册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经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讨论通过,程砚秋成为中国***预备党员。
1958年程砚秋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正式党员。
史实寻踪
西四北三条39条(原报子胡同18号)是程砚秋的故居。
这是一所三进的四合院,如意门开在东南角的巽位,进门是一个影壁。前院北房是程砚秋的书斋和客厅;中院有梨树、青竹、花坛,非常美丽;连接中院和后院的是一个建筑精美的垂花门,后院正房是三间北房、两间耳房的格局,程砚秋的卧室在东耳房。
故居现如今还保持着原建的格局,他生前用过的戏装、剧本、图书和学习生活等用品均保存完好。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