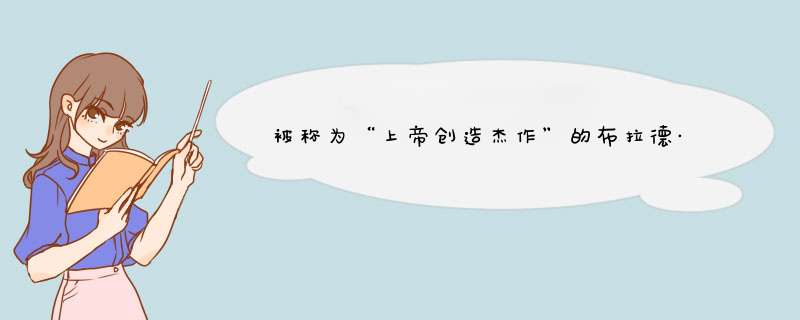
布拉德皮特年轻的时候,颜值时刻在线,可以说是无数个少女的梦中情人了。虽然他最火的时候还没有颜值这个词语,但是他英俊的脸庞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布拉德皮特出演的第一部**《无主地》,只那么一瞬间的镜头,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印象深刻。即使到了现在,他也没有因为岁月而变得油腻。
01、美男子这个词语,怎么能够用来形容一见倾心呢
布拉德皮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他看向镜头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这双眼睛里盛满了忧郁、有时候却又是一些狠厉,这个人饰演的角色可以说是非常多变,但是我的三观取决于他的五官。这样说很肤浅,但是这种男孩子简直是所有女孩子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不仅帅气,甚至有一点点的痞气。
02、他风流潇洒的气质,导致无数美女趋之若鹜
布拉德皮特用咱们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浪子,因为他其实有过好几任女朋友,可以说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除此之外,他的那些女朋友不仅长得非常好看,而且基本上也都是明星。但是他没有和其中的任何一位步入婚姻的殿堂。这种风流潇洒,不是应该出现在武侠小说里吗?他简直是典型的西方美男子。
03、演技同样出众的布拉德皮特,才能撑起票房
除了颜值,布拉德皮特的演技简直甩一些小鲜肉几条街,这才是真正的演员好吗?他出演的角色其实有之间没有什么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深入人心,每部**都十分出彩,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好莱坞演员,成为好莱坞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第三季的第十二集。
1、爱情公寓第三季的第十二集剧情介绍:曾小贤约了一位美女喝咖啡,他故意找来体育组的主持人做陪衬,因为那名主持皮特朱见到美女就会结巴,曾小贤美滋滋的准备用皮特朱的缺点衬托自己,可是没想到皮特朱和诺兰一见如故说起了体育新闻。
2、《爱情公寓3》由汪远编剧、韦正导演,高格影视制作出品,由王传君、邓家佳、陈赫、娄艺潇、孙艺洲、李金铭、金世佳、赵霁主演。
《迷失z城》(the lost city of z)
2012 《柯根的交易》cogan's trade
2012 《important artifacts》
2011 《钱与球》或译《点球成金》 (moneyball
2011 《快乐的大脚2》(voice)
2010 《超级大坏蛋》(megamind)
2010 《生命之树》(tree of life)
2010 《chad schmidt》
2009 《无耻混蛋》(inglorious bastards)
2008 《肮脏伎俩》(dirty tricks)
2008
2008 《阅后即焚》(burn after reading)
2007 《十三罗汉》(ocean's thirteen)
2007 《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2006 《通天塔》(babel)
2005 《史密斯夫妇》(mrand mrs smith)2004 《十二罗汉》(ocean's twelve)
2004 《特洛伊》(troy)
2003 《辛巴达七海传奇》(sinbad legend of the seven seas
2001 《墨西哥人》( the mexican)
2001 《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
2001 《间谍游戏》(spy game)
2000 《偷拐抢骗》(snatch)
1999 《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1998 《第六感生死恋》\meet joe black
1997 《再见艳阳天》(the dark side of the sun)
1997 《沉睡者》(sleepers)
1997 与魔鬼共行\the devil's own
1995 《七宗罪》(seven)
1995 《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4 《初恋情人》(the favor)
1994 《燃情岁月》(或译《秋日传奇》)(legends of the fall)
1994 《夜访吸血鬼》(或译《吸血迷情》)(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1993 《加州杀手》(kalifornia)
1993 《绝命大煞星》(true romance)
1992 《梦幻强尼》(johnny suede)
1992 《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
1992 《美女闯天关》(cool world)
1991 《田径双雄》(across the tracks)
1991 《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
1990 《辉煌岁月》(glory days)
1990 《早逝》(too young to die)
1988 《下课后》(cutting class)
1987 《无主地》(no man's land
由于背景和前史的铺陈少得可怜,品特戏剧中的人物通常显得令人费解。往深里想,这些身份暧昧、行为乖张的人物可能是某种符号,某种哲学概念;往近了想,他们又可能是你,是我,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评论家们对品特及其作品的定位也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有人认为品特是继贝克特之后的又一位陷于存在主义的荒诞派剧作家,而另外一些人则把他看作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作家。实际的情况是,想用一两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来定义品特是极其困难的。品特本人也十分讨厌被贴标签或是归类,经常跳出来指责那些所谓的“品特专家”胡说八道。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品特戏剧人物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状态。或许“存在主义”与“现实主义”正是品特戏剧的两个不同面相:“存在”确实是品特关注的问题,但这种“存在”并非形而上的玄想,而是对“现实”的直喻。
品特的代表作《生日晚会》1957年首演于英国剑桥。剧情虽不复杂,却有些“无厘头”(没来由)。主人公斯坦利在海滨的一户普通家庭寄宿,和房东夫妇梅格、皮特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两个陌生男人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这两个来路不明的男人到达后便开始了对斯坦利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莫名其妙地宣称斯坦利是组织的叛徒。最后,这两个不速之客带着斯坦利离开了,而后者从一个健全人变得口齿不清,只能够咿咿呀呀地瞎比划。
一位女观众在观看完演出后,就自己的几点疑惑给品特写信了一封信,问了下面几个问题:“1 那两个敲门的人是谁? 2 斯坦利来自何方?3 这些人神智正常吗?”这位观众在信中说,如果无法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她就根本无法理解这部作品。品特很快就对这封观众来信做出了回复:“亲爱的女士,下面几点是我无法理解的:1 你是谁?2 你来自何方?3 你神智正常吗?你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我恐怕无法理解你的信。”
幸亏品特和这位女士之间的通讯后来在媒体上传开了,要不然,恐怕会有成千上万的观众给他寄来内容一模一样的信。舞台上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些对于一般戏剧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品特的戏里却成了无从解答的谜题。其实,品特的回信并不是一个恶作剧,这些问题正是他对世界的荒谬性发出的真诚拷问。
品特一生中写了20部舞台剧,其中出现的人物足有百个之多。这些人物的背景大部分都是空白的,观众只能够简单地从他们的语言和行动,配合上下文的内容来大致推断出部分人物的“身份”。实际上,用“身份”二字来分析讨论品特作品中的人物并不合适,甚至有些牵强,因为在品特作品中没有任何“绝对”之说。“身份”总是随着当事人的处境变化而变化,个人的意愿总是随着一股未知却又是必然的更大力量的渗入继而被瓦解或扭曲。用来代表“身份”的人名在品特作品中经常都在变化。到底哪一个名字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观众也不知道。真实与虚假是无从下定论的。也许这就是品特的初衷所在,这些人物叫什么都可以,品特希望看到的是观众只关注最重要的本质,那便是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无论他的名字叫什么,来自何方。品特有一句话被引用过无数次,他说:“真实与虚假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事情并不是非真即假,也可以是既真又假。”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深究所谓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而仅仅想借用在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人物身份作为切入口去深入了解和探讨其中的内涵。在很多的作品中,人物更像是在随意的时间和空间里偶然做出一些特定行为的路人而已,观众和读者只能从最浅白的层面上去做一个宽泛的归类。例如,在《生日晚会》中的追踪者、《升降梯》中的杀手、《归家》中出现的教授,司机和皮条客、《看护人》中的流浪汉、《背叛》中的出版商和作家、《山语》中的监狱看守、《夜校》中出现的xx女郎、《微痛》中卖火柴的男人等。在缺少上下文的情况下,这些人物的一举一动在很多时候都显得极其突兀,荒诞,甚至可笑。英国戏剧评论家艾文・沃尔多把品特的戏剧称为“威胁喜剧”是不无道理的,其中“喜剧”的这一提法给观众和读者提供了另一种看待和了解品特的作品的方向。
分析人物的喜剧性是从喜剧角度来看待品特戏剧的一种很好的手段。以《生日晚会》为例,不速之客麦肯和哥德堡从出场到退场都板着脸孔,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是肩负着某种沉重的使命,尤其是麦肯。的确,这两个人物在剧中确实是拥有着“掌控命运”的权力,他们一出场便能凝固周围的空气,使场上其他人物惴惴不安。有趣的是,舞台上紧张,压抑,一触即发,危机四伏的人物关系并没有使观众如同剧中人物一样惶恐,相反,观众在观剧过程中,紧张之余常常发出阵阵笑声。这种奇特的现象,很多时候完全在导演和编剧的意料之外。
许多评论家对这种现象也感到很好奇。品特在1968年接受美国文学评论家劳伦斯・本斯基的采访谈到:“我很少刻意去幽默。但是,我发现在某一时刻,写到某一点上时,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情不自禁笑了出来的并不只是品特一人。同样地,品特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很少刻意去玩弄幽默,相反,他们大部分时候都非常认真严肃。也许便是这种认真到了极致,误让观众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
笑的原因是自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分析主要从笑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来进行的。在品特作品中客体的原因不外乎舞台上人物的动作和语言。在《生日晚会》第二场开始的时候,麦肯坐在桌子旁边,像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一样摆弄着一张报纸。他将报纸撕成长短一致的细条,然后以五条为一组,整整齐齐地将其摆放在桌面上。他表情认真严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一丝不苟的科学工作者那样。一本正经的神情和机械的举动构成了一个可笑和滑稽的场面。而从主体的角度上来看,第一场结束的时候,观众脑子里充满了悬念,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两位不速之客与斯坦利的第一次交锋,期待着斯坦利命运的未知变化。所以当第二场开场时,观众屏着呼吸,焦急等来的却是这一幅充满孩子气的画面。“笑”在这个时候便自然发生了,既是笑舞台上人物举动的怪诞,也是笑自己莫须有的“严阵以待”。
把麦肯看为纯粹的喜剧人物丝毫不过分,可以说他就是《生日晚会》里最主要的笑点。这位西装革履的强权人物的很多举动却显得非常笨拙与僵化。同样是第二场,在“坐下!”一幕中,麦肯和哥德堡正准备“拷问”斯坦利。麦肯和哥德堡分别站在桌子的两边,斯坦利在中间。这时候哥德堡命令斯坦利坐下,斯坦利拒绝,对话围绕着“坐下!”,“不,你才坐下!”展开。两个人于是你来我往,不厌其烦地重复‘鸡生蛋,蛋生鸡’的对话模式。而麦肯这时好像成了一个满头雾水的小孩一样不知所措。他一会儿充当哥德堡的应声虫,不断帮腔。一会儿又像成了解说员,向哥德堡汇报斯坦利的动作,譬如当斯坦利拒绝坐下的时候,他便说:他(斯坦利)不肯坐!在麦肯的搅和下,他自己和哥德堡倒是被斯坦利连哄带蒙地诱导而在桌子的两端坐下了,而斯坦利依然还是‘站立’着。最后麦肯意识到自己的‘失策’,连忙站起来说:That"s a dirty trick, I"ll kick the shite out of him!(我们中了他臭把戏了,我要狠狠把他揍一顿) 。然后哥德堡也站了起来说:No! I have stood up(算了,我已经站起来了。) 麦肯接着说:Sit down again!(那就再坐下!) 哥德堡义正词严地说:Once I"m up I"m up (我一旦站起来就不会再坐下!) 斯坦利把话接过去说了一句:我也是!这时观众笑了。在这一幕的较量中,麦肯和哥德堡明显处于下风。麦肯所代表的‘权威’身份和他愣头愣脑的行为同样构成了一个可笑的情景。
在《生日晚会》中,品特还设置了另外一位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那便是房东太太梅格。《生日晚会》开始的时候,梅格在与她的丈夫皮特的对话中便显露出愚钝,无知却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性格特点。她的举动和言谈都明显缺乏与她的年龄应该有的成熟和世故。她从一出场便一直喋喋不休,与看报纸的丈夫没话找话地攀谈。
梅格:你在看什么?
皮特:有人刚生了个小孩儿。
梅格:哦,不是吧!谁?”
皮特:一个女的。
梅格:是谁啊?皮特,是谁?
皮特:你肯定不认识的。
梅格:那她叫什么名字?
对于这件与她毫无关系的琐事,梅格穷追不舍地问,这种像小孩子般的执拗让人觉得十分可笑。这个场景一方面将小市民生活的琐碎和无聊描绘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与后面梅格对斯坦利受虐的漠视和健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与斯坦利的交往中,梅格的举动也是令人忍俊不禁。第一场中有一幕是梅格叫斯坦利起床,梅格的表现完全不像是对待一位房客,却像是在对待情人般的亲昵。“斯坦尼,斯坦!你再不下来我就上来了啊!我这就上来了!我数三声!一!二!三! 我来了!(她走上楼梯。斯坦利喊了一声“等会儿!”,这时梅格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皮特把盘子端到灶台上。楼上传来喊叫声。大笑。皮特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吭。梅格上。)他这就下来了。(她一边喘着气,一边整理着头发。)”1968年,在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的时候,导演威廉・富莱德金把后台的这一幕展现了出来。梅格推门进了斯坦利的房间,掀起了斯坦利的被子,不断“咯咯咯”地狂笑。
剧中点题的生日晚会一幕也是由梅格一手策划的。在两位陌生人来临的当天,梅格通知大家当天是斯坦利的生日,并且要在晚上为他举行惊喜生日晚会。而她一直神秘兮兮为斯坦利,这个奔四的男人,准备的生日礼物却是一个小孩子玩耍时候用的棒槌和鼓。而观众后来从斯坦利的口中获知其实当天也并非他的生日。然而就这么一位对斯坦利关爱有加的人在最后斯坛利被带走的时候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但是这种落差却是带有强烈的讽刺和喜剧色彩。在剧终的时候,梅格从楼上走了下来,对之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一无所知,一切又回到戏开场时候的样子。
梅格:那两个人的车已经开走了。他们走了吗?他们会在这里吃午饭吗?
皮特:是的,走了。
梅格:真是遗憾。外面太热了。你在干什么?
皮特:看报纸……
梅格:斯坦呢?他下来了没有?
皮特:没有……他……
梅格:他还在睡觉吧?
皮特:是,他…… 还在睡觉。
梅格:他总是这样,早餐迟到。……昨晚的晚会真是开心。我都好多年没有笑得这么厉害了。我们又唱又跳,还玩游戏。……我是晚会上的美女。他们都这么说。哦,真的。我知道我是美女。
梅格这个人物其实是意味深长的。她关注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情,报纸上的八卦和江湖传言,她执着追问的是报纸上报道的某个名人又生儿育女了,而真正应该在乎的事情却是懵懵懂懂,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事实与真相之外。观众笑了,这种笑是笑她的无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同情。
1996年在接受巴塞罗那大学访问的时候品特被问道:“在贝克特剧院演出《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观众时不时地爆发出笑声。你怎么看待观众的这种反应?”品特的回答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品特剧作中引人发笑的更多原因:“那要看情况。如果他们在尼古拉斯和吉拉对话的那一幕里笑,我会很惊讶。当然,在其他部分肯定会有观众发笑。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或是我们自己的丑陋时,我们会发笑。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意识到存在于自身的丑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品特舞台上的滑稽人物更像是一面巨型的镜子。而人物在舞台上的种种滑稽之态使观众发笑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自我省视的过程。
品特喜欢将人物置身于狭窄封闭的空间里,在这里,人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大部分时候的对话是牛头不对马嘴。在这样一个“无处可逃”的空间里,人物彼此总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直到一方完全瓦解。在这里,没有所谓“人性的光辉”最终胜出的乐观主义精神,大部分时候,结局是恰好相反的。力量的较量在品特的舞台上无处不在,而弱者总在最后时刻被彻底地摧毁。语言是人物在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的最直接的手段,语言的交锋所迸发出的火花和幽默更是充满智慧,
要完全弄懂品特作品中的人物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虽然观众连蒙带猜最后在戏结束的时候终于有点头绪,但往往是带着更多的疑惑离开剧院的。因为猜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是有待商榷的,猜测过程更是一种很主观,很私人的事情。可以说,品特是一位能够充分调动观众情商,将观演的互动关系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剧作家。毫不夸张地说,品特的舞台演出效果有一大半是通过观众的情感参与来获得的。也许,这便是品特作品引人入胜的地方。观看,阅读过程就像侦察案件一样,人物的言语,服装,行为,道具就是剧作家留下来的种种证据,而观看过程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通过长时间细心摆布这些零星的小碎片才能使一个画面最终成形。当然,也许花上时间和精力后,最后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又得从零开始,但这也许便是品特从195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在剧场里一直长久不衰的秘诀所在。
蔡芳钿:中央戏剧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许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