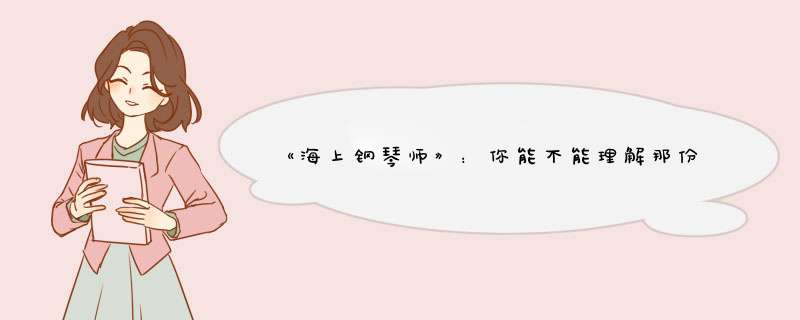
宁愿在自己的世界里死去,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异类。这是也许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只是有人让自己属于所有的世界,而有的人则忠于一种环境罢了,这没有心胸的宽广与狭隘之分,更不存在那种人更优于另一种人的论断。思维的路线是不是一种和实践的反比,这我说不准,但是1900所身处的那一点,散发出的无数的想象力和诠释艺术的活力,是没有谁可以做到的,《海上钢琴师》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部悲剧**,它所要展现的仅仅是一个特殊的人的一生而已,悲剧本身有很多种,我并不认为英年早逝比丧失活力更充满悲剧性。心灵的禁锢到底代表什么,我们都很难说清,普世的价值能否去定义一个人是否拥有心理上的疾病,也是同上帝一样是未知的。如果人的终极意义是美学价值的话,那么像1900这样一个禁锢在狭隘的心灵中的人,似乎是最高价值的模板。
音乐,他用音乐去感受世界,还是用世界来感受音乐?**在表现1900出神入化的音乐技能的同时,伴随的是船上所有客人的翩翩起舞和无止境的陶醉,不知**在这种表现之下到底有没有意义,然而给予我们的感受却是一种在1900的上帝视角下,我们这般狼狈与无能。这种无能到底是源于那种自认为无所不能的感觉同自知之明之间的落差,**通过1900与爵士乐手的斗琴体现的淋漓尽致,爵士乐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些正常人,我们这些自认为无所不知、适应力超强的社会物种。1900利用他的超凡的天赋击败了所有游轮上的人们,然而他的一生却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面前既不是神,也不是怪胎,而是和我们一样平等、自由的生物。对外界的环境疯狂的适应,会造就一个毫无美学价值的废物,可是站立在一个空间点上却拥有终极意义的人,迎接他的就只有生命的过早终结。这两种状态到底哪一种是人们应该有的,早已不是争论的焦点,心理学煞费苦心的去研究如何治愈一个被心灵禁锢的人,不论是否成功,它得到的也只是另一种平等的心理状态而已。 "You asked for it, asshole"这是1900在斗琴的最后一曲之前,对那个看似不可一世的爵士乐手说的话,**表现最后一曲的震撼力,是用画面的重复叠加以及在他与观众之间镜头的频繁切换来完成的。这种俯看全场的感觉,无论如何都显得十分无情,**并不是想表现在1900的眼中,其他人一切的音乐都是垃圾,而是想要表现在情感之外,一切的美学都是空谈。人们可以模仿,更可以机械的复制,但是对于一个靠情感来诠释生命的人,这就如同是在玷污他的生命。**在唱片录制的那一幕,似乎是解释了前后所有的情节的缘由,他既不愿让自己的音乐脱离自己的手指,更不愿意让他的音乐成为无情的复制品。音乐如同爱情一样不容侵犯,而爱情和艺术却都等同于他的生命,当生命进入另一个世界,那么他的艺术和情感也将面临这抉择,这种对环境的恐惧我们都存在过,可是却没有谁能真正去思考过适应力背后的代价,那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欠缺。 美学是人们最能轻易放弃的东西,所以在生命和也没学面前,我们大多数人宁可选择生命,因为我们认为生命的延续就是美学的延续。可是美学本身是笼统的学科,没有人会在生命过程中去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存在着美学意义,制造终极意义的人或许不会懂得什么是意义,可是并非刻意制造又懂得自身的奥秘的人,似乎只有在**中才能寻得到。1900明白什么是他应该带走的,也明白他能留下什么,就**本身的情节来说,他的知名度远远够不上的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可是他却可以明白,知名度本身是对他的玷污与糟蹋。他宁愿随着爆炸声远离人世,也不愿意在那种位置的恐怖阴影下苟且偷生,在名利的沉浸下失去原始的自我,依照尼采的哲学,他是一个能拥有和发挥原始本能的人,却不是一个强壮的超人,超人改变世界亦能保持自我,而他却只能保持自己不变。可是就这一境界,世上又有几人能够达得到?我有时就会思索,假若给我一个能够诠释美学的力量,我是否也宁愿死在这里?
登船梯,下到一半便不再下去。**制造了艺术片上惯用的煽情,但足够让整个情节趋于思维上的明朗,这是我们的世界而不是他的。也有另一种他们的世界就不是我们的,在面对适应力成形后的变革空间或时间,在面对新时代的迅速更替和变化的时候,我们又当怎样选择,是逃避还是植入他们?“励志”本身只是生活态度的一种而已,价值是均等的,代表人类的智慧和生命的完美的元素可以是不同的,但意义是平等的,而所谓的生活轨迹或生死态度,仅仅是我们选择意义的方式罢了。
《失踪的女人》,1938年出品的,在1979年翻拍过的
剧情:1938年8月的一天,赶往伦敦结婚的美国人凯莉**;生活杂志社的摄影记者康德先生;给一名德国将军做过保姆,现今辞职回老家的芙瑞夫人;前往伦敦看国际板球比赛的查特兹和考特先生;以及一副学者派头的哈里兹医生在巴伐利亚一个叫多萨的小站上,登上了开往巴塞尔的列车。
上车后,凯莉**和芙瑞夫人有幸和自称是德国男爵夫人的一行坐在同一个包厢。列车开出不久,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当凯莉小憩一会儿后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坐在对面的芙瑞夫人竟然不见了。在问遍包括男爵夫人在内的、列车上所有的人并得到根本就没有见过芙瑞这样一个人的结果后,凯莉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
列车经过一个小站时,哈里兹医生下车将一个面部紧缠纱带的病人抬上了自己的包厢。就在凯莉为找不到芙瑞显得有些急躁而让其他人误认为凯莉是酒后神情恍惚时,车窗外一张从前面飘过来的商标图案让康德意识到凯莉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和康德一起继续寻找芙瑞的过程中,负责给哈里兹医生看护病人的修女脚上穿的一双高跟鞋引起了凯莉对哈里兹和被纱带蒙面的病人的疑虑。而此时,当凯莉和康德喝下哈里兹下过迷药的红酒后,哈里兹承认了病人就是芙瑞的事实。
原来,哈里兹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而芙瑞此行回伦敦带着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秘密。经过一场生死攸关、惊心动魄的较量后,凯莉和康德救下了芙瑞,并将德国纳粹包围的列车成功地开到了中立国瑞士的领土。等共坠爱河的凯莉和康德赶到伦敦政府转达芙瑞临下车前交代的秘密口信时,让她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伦敦政府的办公大楼里又见到了在列车上曾神秘失踪的芙瑞夫人。
今年已经70多岁的赵方幸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了一辈子的视唱练耳。也不过在圈内“小有名气”。谁想到退休以后,由于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中做了一回评委。竟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步步高老太太”(编者注:第九届青歌赛冠名单位为“步步高”)。前不久,当人们还沉浸在申奥成功的喜悦当中时,《音乐周报》社收到了一份名为《新北京,新奥运》的歌曲投稿。说这首歌并不是因为它的作者正是这位“步步高老太太”,而是因为这首歌特殊的创作手法。它通篇只有一种节奏——切分音。如果不是事先注明,谁也想不到这首充满了动感活力的歌曲是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之手。这件事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电话里同赵老师约好了时间面谈,一探究竟。
我如约拜访赵老师时,她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那里,她为当地的音乐教师们举办了一个视唱练耳的大师班,继续为推广她的视唱练耳的教学理念而奔波。我们的话题当然是从那首《新北京,新奥运》的歌说起。7月13日,中国串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国欢庆。赵老师更是激动不已。当晚的电视转播看完之后,兴奋得2点多才睡着觉。第二天,喜悦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一股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一直在心中激荡,于是拿起笔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激情澎湃的“奥运之歌”。一谈起体育,赵老师的眼中总会放出异样的光芒。因为,她对体育有着特殊的情感。
说话间,赵老师拿出了她珍藏多年的影集,里面全是一些有着五六十年历史的发黄的老厢片。她指着其中一张骄傲地对记者说:“这是我们当年参加广东省的田径运动会得了冠军,并破了全省记录以后的留影。”随后,她又自豪地问我:“怎么样?能看出来哪个是我吗?……”原来,赵方幸教授从小就是一名体育健将,小学时短跑成绩就已达到50米6秒9,100米t3秒9。她的教练是一名曾经代表中国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在30年代能得到这样的名师指点实在是十分难得。据赵老师介绍,她跑得快主要是因为起跑快,由于她的节奏感好,能够恰当地把握起跑时的韵律。所以,往往是发令枪一响,别人刚起步她已经率先跑出去了。望着照片中自己当年飒爽的英姿,赵老师感慨地说:“要不是中学业时正赶上1937年日军侵华,自己也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浪潮中,说不定在体育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呢!”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断了在体育方面的发展,但是,这段经历却赋予了赵老师乐观开朗、坚韧不拔的性格。她谈起话来,底气十足,说到激动之处还会有力地挥动起手臂,用她自己的话说“经常忘了自己几岁”。走上音乐道路之后,这种性格也帮了她不少的忙。中学毕业后,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经受过洗礼的她考入了当时全国仅存的几家音乐学校之一的福建音专。当时很多著名的音乐教师,如江定仙、缪天瑞、陆华柏等,都因躲避战乱撒到了福建音专,使得赵方幸有幸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初到音专的赵方幸如鱼得水,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由于自己的钢琴底子薄,就总是想方设法地赶上去。说到这里,赵老师为我讲了一个很“脏”的故事。当时的福建音专建在山区,条件十分艰苦,琴少人多。想要多练琴,就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但女生宿舍的管理特别严格,定点熄灯,专人看管,晚上想要从正门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几个胆子大的女同学开始琢磨“邪门歪道”了。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赵老师。工夫不负有心人,同学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通道——通过女厕所里为掏粪工人准备的一条窄逋爬出去。此后,每天晚上都会上演惊碱的一幕——儿个小姑娘为了能练琴,冒着掉进粪池的危险从女厕所往外爬。练完琴后再原路返回。今天回想起来,就连赵老师自己都想不出当时怎么能忍受那么脏的环境。可能,与练琴比起来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也许是赵老师的名字中有一个“幸”字,她的一生真的很幸运。走到哪里都能遇上好的老师。她说这使她一生都受用不尽。正因为如此,从小学教她体育的司徒薇老师和她的丈夫(她的那位田径教练)到音专教她钢琴的李嘉禄老师,凡是教过她的老师她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有些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联系。她把从又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她从不打骂学生,但是有股特殊的威严,学生们既尊敬她又怕她。由于她总是不放过学生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学生们就背地里送了她一个雅号“符点音符”。再比如在那次电视歌手大奖赛上,她对参赛歌手的任何一点不准确的地方都要指出来,有人说她“太不讲情面”。但老人家有自己的道理,她说:“中央台的节目要向全国、全世界转播。我往里一坐,代表的可是中国的音乐学院的教授,我可不能让人说‘中国的专家连这点错儿都听不出来。’”这位“步步高老太太”实在是倔强得可爱。 (张萌 于2001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