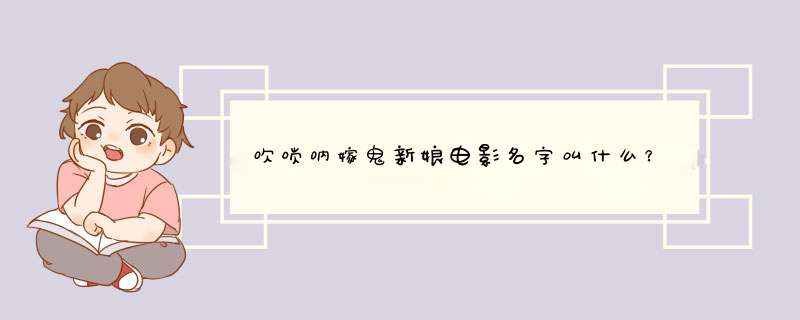
《新僵尸先生》是香港1992年拍摄的一部恐怖喜剧**,由《僵尸先生》的原班人马拍摄,包括导演刘观伟和主演林正英、钱小豪和许冠英三师徒,是林正英僵尸系列的作品。 该片的故事讲述了道长带领他的弟子与僵尸孽婴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部片搞笑场面甚多,吴君如和楼南光的加入,大大减低**的阴沉感觉,连严肃的林正英亦变得十分诙谐。《新僵尸先生》于1992年8月8日公映。
昨晚,很晚,整个小镇都睡下了,我不困,在听小提琴版本的《我爱你,中国》,悠扬的旋律,柔和的音色,细腻的抚弦,听腻了字正腔圆的美声唱法,这种无歌词的纯音乐仿佛空谷足音,余音袅袅……
一大清早,爬起来,阳光已经洒满了窗台。回想过去听了诸多歌声,如天上繁星,如恒河沙数,脑海中有些挥之不去,沉淀在生命的河流中。
我接触到的第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是豫剧了。我的家乡,阜南县段郢小乡,每年三月三,春光明媚,暖风习习,蝌蚪甩着尾巴,我们一路小跑去看戏,最期待的是看后背插满旗帜的将军对阵,而最着迷的却是美丽的青衣**姐,一袭裙裾,千转百折,碎步款款,盈盈水间,“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种艺术感染力直观告诉我,只有七岁的我什么是古典美,我在人群中,她在舞台上,我是一个小屁孩,鼻涕常常抹在袖子上,她是典雅不失激越,宁静不失婉约的才艺大姑娘…………如今,她已到中年了吧,愿流逝的时光善待她,她们~~~
2019年初秋,举国欢庆。蒲庄村,段郢乡下辖一个行政村,请来了豫剧团,我和妹妹季怡洁,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搬了板凳,在人群中踏着夜色仰脸看戏。唱段,在夜风里飘,这里有二胡的抒情哀怨,有唢呐的激情慷慨,有梆子的忽远忽近,有牛皮鼓的急如雨点,也有芦笙的清脆悠扬………我不喜欢插科打诨,低俗粗鲁,没羞没躁,从剧情来看,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思想性,艺术性,是需要工匠精神的,不能苛刻。
豫剧史上,一个新的高峰不得不说《朝阳沟》,那经典的唱段,那朴实的追求,那凝炼的语言,那紧跟时代的脉搏,那听从号召的历史自觉,这一切都无可挑剔。
“漫山的野花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把山腰缠,青凌凌的一股水,春夏不断~~~”
魏云的唱音在山谷里回荡,女声伴唱也随之而起,一场三咏,重重叠叠,身临其境,不知归路……
虽是黑白**,却分外明朗,有杏子压弯了枝头,有麦田绿,有油菜黄,有蝴蝶飞~~~
阜南县城以北,有个地方叫冷庙,那里也曾有豫剧演出,我的一个学校同事,甘泰贤,年逾古稀,也赶来听戏。没想到张娇娇也喜欢听戏,那一年,她还是刘宇的女朋友,如今,她是刘宇的娇妻。偌大的舞台下,年轻人似乎只有我们三个,张娇娇请我们吃棉花糖,白白的棉花糖,大大的,像天上的云朵……
那一年,2012年,也是春天,我在绍兴,有幸邂逅越剧,江南杏花烟雨里的越剧。那天傍晚,天要黑了,华灯初上,我从姐姐家,董蔓丽的姐姐董瑞,抱起椅子冲到楼下小河边,是《楼台会》,越剧经典剧目,渔后村每逢春暖花开都会请剧团,这便是鲁迅笔下《社戏》的原型,越剧大多女子,甚至某个剧目清一色女子担任任何角色,她们翩翩起舞的衣袂,太美不忍直视,太仙仿若隔世,然后,唱词却听不懂,完全听不懂这类似外语的吴侬软语,念白也听不懂,但这种南国方言却甚是动听,听一句,骨头都酥了,出嫁的姑娘要回头,铁打的汉子两泪流………
第二天的黄昏,是《飞鱼》,真牡丹冷酷无情,假牡丹温柔多情,人若无情不如妖。剧团里有个**姐,时年十五六岁,居然不读书了,跟随家人走江湖,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学戏,我只能谢绝,俺是个粗人,学不会的。很感激她,她是我唯一一个戏剧演员的朋友,QQ密码忘记后,从此失去了联系……
这些都是流动的剧团,绍兴的小百花越剧团是有固定的大剧院,那天,明媚,花草也微笑,我兴冲冲跑过去,却扑了空,适逢她们休假,没有演出安排,我只好一步步走长廊,看她们的海报,海报里她们,好美,魂牵梦绕……
小百花,疫情以后的某一年,我一定坐在大剧院的第一排,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喜欢雨巷旖旎的风光,却不是因为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有一年在长沙老城的江边,踏着台阶孑孓而下,左畔是一座破旧的仓库,右畔是一座荒芜的小山,时有群鸟喧哗,细雨如丝,巷子里的青苔斑斑驳驳,在石径上肆意地攀爬。
北方有来客,遗世而独立。那个情景,真的要铭记一辈子。乱树杂花,云涌风起,偶尔觑见扎着围裙的老婆婆在同样斑驳的木门内向外探一探身子。已经能够听见江涛了,呼喇喇,呼喇喇地慵懒撞击。一辈子有多长呢,不晓得哎,但再听到类似的江涛,恍惚便过了十年,那已是站在重庆朝天门的码头上,胸怀激荡,顾盼神飞。
漂泊难以治愈,能够被轻松治愈的,一定也意味着可以轻松忘却。间或蓦然回首,雨巷就像是一道美丽的疤痕, 可以触摸,可以感念。还记得那一日回程的公车上,邂逅一位花臂(刺青)的少女,大概与谭维维的类似——恰好是谭获得超女亚军的第二年,又恰好是长沙。花臂少女高大健壮,前卫的衣着除外,更引人瞩目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鼻环,设若戴(望舒)诗人正在现场,在朋克风的冲撞之下,不知道要写出何等“瑰丽”的篇章。
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诗人们倒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提炼的翘楚。譬如余光中《芝加哥》一诗中就有相当潮流的句子,“爵士乐拂来时,街灯簇簇地开了。/色斯风打着滚,疯狂的世纪构发了——/罪恶在成熟,夜总会里有蛇和夏娃,/而黑人猫叫着,将上帝溺死在杯里。”却又另一首《五陵少年》风骚古朴,“千金裘在拍黄行的橱窗 挂著/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再没有周末在西门町等我/於是枕头下孵一窝武侠小说/来一瓶高梁哪 店小二”。这得让多少当下所谓的“名”诗人自惭形秽,诚然,这得要他们还有一丢丢起码的良知。
推及洛夫、痖弦、周梦蝶们亦然。在台北武昌街,自一九五六年始,退役归来的周梦蝶摆摊卖书营生,至一九八零年因胃病书摊歇业,计二十一载。他礼佛习禅,终日静坐繁华街头,先后出版诗集五部,分别是《孤独国》《还魂草》《十三朵白菊花》《约会》和《有一种鸟或人》。周梦蝶少年丧母,青军从军,台岛飘零,复又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一生清贫而孤独。晚年的周梦蝶一个人居住在一爿逼仄的陋室里,食素面,居小床。赤祼沐浴,赤祼着衣。慢慢早餐,慢慢拄杖。出门买报读报,坐车,裁纸,磨墨,写字,听经。慢慢讲话,慢慢思量。这是凤凰网前些年制作的一个纪录片中,真实拍摄的日常场景。
周梦蝶曾在诗中感叹,“不敢回头,不敢哭、也不敢笑,生怕自己成为江河。”生怕自己成为江河——这句诗与余光中的“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深契洛夫的那阙“你的信像一尾鱼游来/读水的温暖/读你额上动人的鳞片/读江河如读一面镜/读镜中你的笑/如读泡沫”。许多评论家将这些诗作归之为“伤痕文学”,实不敢苟同,悲欢离合,家国情怀,不过是时代的颠沛罢了,当哭则哭,当笑而笑,既然发自内心,出乎真情实感,何来的恁些标签乱给它。
长沙的江涛稍平缓,重庆的江涛则稍奔放。形似谭维维大花臂的公车少女并无不雅,戴(望舒)诗人的纸伞姑娘未必就是良家。“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幸存者偏差理论下的结论,从来带着些些侥幸的因子。所以在史铁生先生笔下“内容”丰富的地坛,到了别人眼里,恐怕乏味得很。脱离开浪漫的成分,长沙雨巷下旧仓库的锤凿之声才是真谛,至于朝天门码头,头顶烈日,睡眼惺忪,恍惚占据了大部分情绪。
江南江北的N年中,每至一地,每至一城,如果有闲暇,又有情致,并不愿刻意去寻什么山水形胜,古迹遗址,反而热衷于轻装简行,泡一泡人家的老城区。风土人情,乡言俚语。咥面的老汉,淘米的婆姨,假寐的黄犬,疯跑的小孩子。走累了,就坐到街下的一个小馆子里,与主人家寒暄几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没有傲娇,没有凡尔赛,实打实的心猿意马,走马而观花。
早上被楼下高亢的唢呐惊醒。又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最后的仪式感显得又热闹,又冷清。海子把这种场景写成“我生下来时哭几声/我死去时别人又哭”,在那首诗名为《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中,他还写道,“或者我干脆就是树枝/我以前睡在黑暗的壳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边疆/就是一颗梨/在我成型之前/我是知冷知热的白花”,因为查不到作品的创作时间,也就无法知晓彼时的海子是梦幻,还是清醒。
不疯魔不成活么。在**《霸王别姬》中,段小楼如此来形容程蝶衣的飞蛾扑火。都说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想一想忽然觉得说不出的惊悚。
再后来,唢呐没了动静,蝉声、鸟声则铺张开来。
嘶哑啁啾,如至无人之境。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