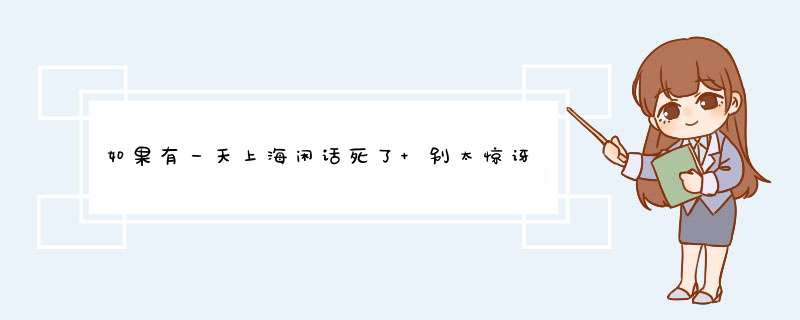
“现在上海的孩子都不会说上海闲话了,我妹妹的孩子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只说普通话。说上海闲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上海闲话距离消失估计也不远了。”我的同事彬哥怀着浓烈的告别口吻说完了这句话。看着他的眼神,我以为他在参加某人的遗体告别会。
彬哥的话我只同意一半——上海闲话迟早会成为博物馆语音展厅里的陈品,或是语言爱好者研究的活标本。但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归咎于使用人数的锐减,而是造词能力的严重退化。
01 造词能力是一门语言的活力源泉
语言和人的身体一样,需要新鲜细胞的支持,也就是所谓的新陈代谢。新词汇代替旧词汇,仿佛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一般,为语言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帮助延续生命力,实现进化。
中文本身就是一门造词能力极强的语言。曹操在打败袁绍后,写了篇《观沧海》,写到兴高采烈时,用“幸甚至哉”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千年后,到了民国,抗战胜利时,人们高呼的是“万岁”;再到现代,人们只用一个字就能表达以上心情——“爽”。这就是造词的过程,曹操想不到现代人会用爽字,现代人也不会再刻意像曹操那样用繁复文字表达心情。语言就这样经过新陈代谢,实现了进步,并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英文也一样。韦氏词典里每年都会收录大量新生单词。staycation / 宅度假,sock puppet / 上网用的马甲小号,vlog / 影像网络日志,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新词汇崭露头角。
可见,中文会造词,英文会造词,法文会造词,德文也会造词。可是,上海闲话呢?告诉我,你上一次听说完全由上海语创造出的新鲜词汇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2 上海闲话的黄金岁月
上海闲话并非天生缺乏生命力。回顾过往,它曾有过如此辉煌的时代,它也曾像少男少女一般,迷人富有想法。
清末,伴随着上海开埠,北方人,南方人,外国人纷纷涌入这种年轻的城市。他们操各自的语言,过着各自的生活。时间久了,生活开始融合,语言也跟着融合。上海的移民们对此无比热衷,甚至主动创造。上海闲话迎来了黄金时代。其中,最有味道的莫过于结合了英文的词汇。
斯别林 ——弹簧。来自于英语Spring。
老克勒 ——有派头,有档次的人。关于“克勒”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英语Color的音译。也就是衣服领子的意思。另一种是“clerk”也就是职员的音译。
汇山 ——路边。1845年,英国人在黄浦江畔建造了一个浮动码头,由于觉得该码头极其简易,就随便给它起了个名字“Way side”意指路边小码头。结果上海人再次化腐朽为神奇,将way side翻译成了颇具诗意的汇山。
昂三 ——差劲,令人恶心。来自于英语on sale,暗示说你这人人品差到只能搁在路边卖了。
瘪三 ——无业游民。有人认为该词来自洋泾浜英语中的beg say,也有认为来自洋泾浜语的empty cents(或penniless)
至于“阿三”这样的词汇,我不说,大家一定也都耳熟能详了。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闲话迎来又一波造词高潮。
打桩模子 ——黑市上做倒卖生意的人。这些人长时间站在某一处,浑身上下抖动不停,像个打桩机。因此得名。
淘浆糊 ——形容一个人做事好马虎,爱糊弄。
可是,在此之后,直到现在,上海闲话再没有迎来造词高峰。超过20年,没有一个像样的新词汇。
03 排外是杀死造词力的罪魁
如果放宽搜索范围,上海闲话还是造出了一个新词的——硬盘。一个用来侮辱外地来沪人士的词语。伴随着上海的开放,某些上海人的内心却变得闭塞。一部分上海人开始坚持一种看法:上海闲话是上海人发明的。因此,他们拒绝在上海闲话里体现移民特色。你难道指望某句上海闲话里出现一个东北词?或者安徽词?
可令他们尴尬的事实却是,上海闲话本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宁波话为主要基础的。甚至连我们最引以为豪的自我介绍词——阿拉,以及最拿手的脏话——XXXXX,都是土生土长的宁波词汇。
为什么当年的上海先辈们能够坦然地使用宁波话作为上海语的基础。现在的我们,反而更保守了?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先辈们本来就大多来自宁波以及江浙地区。
上海闲话是移民们带来的语言。移民创造出的语言是离不开宽容与包容精神的。当现在的我们为了“上海本土精神”放弃老移民精神时,我们已经亲手掐断了上海闲话的大动脉。
“外地人,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不会在上海闲话里加入外地词;外国语,我们喜欢,但我们直接用最标准的英语发音就好了,干嘛要费劲创造洋泾浜式词汇。”
这个不愿意,那个又不肯。不愿接受其他语言词汇,又不愿开创制定符合时代特色的新语言准则。当同为方言的粤语不断自我更新时,当我们的普通话以每年数十个新词汇与时俱进时,上海闲话却与其他不思进取闭关自守的方言一样,逐渐枯萎,失去创造力。
04 音调无法适应诞生的新词
更糟糕的是,由于发音的天生缺陷,上海闲话无法表达大部分的普通话新词。“神马都是浮云”。“不明觉厉”“十然动拒”“喜大普奔”等网络新词很难用上海闲话发音。这也难怪为什么新一代的上海人总喜欢在用上海闲话聊天时,不自觉地加入普通话。没办法,上海闲话的发音太难与新词汇接轨了。而从目前来看,似乎也不会有哪位人士愿意站出来,为适应文字的进步而编制新发音表。
没有创造力,没有造词系统又有严重局限性的语言有什么理由继续被使用呢?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呢?毕竟,语言的流通程度首先在于其实用性,其次才是底蕴与乡土情怀。
如果有一天,上海闲话真的死了。所有狭隘自守又无所作为的上海人都是共犯。
本集完。
上字幕
是这真的,999是千足金的标志,意思为含金量为999%现在国家统一标准,所有黄金饰品统一行业标准都为足金产品,并没有千足金足金的区别,但是大一点的品牌对黄金的品质还是有要求的,要达到千足的标准,比如周大生和怡朵珠宝。还有一种纯度的说法叫万纯金,但其实那是商家杜撰的说法,是用来吸引消费者的噱头。梦金园就有过万纯金产品,但其实是不存在的。
阅读札记
《上海的风花雪月》 (ISBN 978-7-5321-5747-1 )
上海的市民常常有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生活,每个人都收拾得体体面面,纹丝不乱,丰衣足食的样子,看上去生活的真是得意而幸福。商店也是这样,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笑脸相迎,样样东西都亮闪闪的,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儿背着大街的弄堂后门,堆着没有拆包的货物,走过来上班的店员,窄小的过道上墙都是黑的,被人的衣服擦得发亮。**还没有梳妆好,吃到一半的菜馒头上留着擦上去的口红印子。而人呢,第二种生活是在弄堂里的,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头上做了花花绿绿的发卷,利落地把家里的小块地毯挂到梧桐树上打灰,到底觉得吸尘器弄不清爽。男人们围着花围裙洗碗,他们有一点好,手不那么怕洗洁精的损伤,所以家里的碗总是他们洗的。
上海市民真正的生活是在大玻璃墙和黄铜的美国钟摆后面的,不过,他们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是他们隐私的空间,也是他们的自尊。
—— 《时代咖啡馆》(P3 ~6 )
说明:时代咖啡馆属于时代公司,在淮海中路(原名霞飞路)。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年少时光的眷念和一个市民对自己城市过去的怀想,是富有意味的,并饱含着价值判断的感情。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感情如同历史真实和丰富的细节一样。探索这种感情,不光可以因此而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是探索自己的途径。它因此而吸引了我。这种感情还很容易被误会,这是后来我才懂得的。十年前,我以为鲁迅骂施蛰存“洋场恶少”,黄宗江称赞姚克“洋场良少”的时代都已经过去。现在我知道,也许并不是这样,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而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价值判断中的文化意义会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一切都因为标上了价钱而庸俗。
——《1997-2007 ,咖啡馆十年记》P37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腌的咸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哔哔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的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弄堂里的春光》P205
这风花雪月,因为遍布沧桑与蹉跎,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点缀生活的情调,所以才要称他为上海的风花雪月,它沉浮于大时代的疾风骤雨里,竭力护卫着自己的风格。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懂这个街区和这个街区的人,看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要享受自己内心的惆怅。
——《1997 —2007 ,街道十年记》P218
这移民的城市有时就像是一个大中转站,总是在流动着,总是在到来与离开的匆忙之中。那里的地上全是脚印子,那里的窗台上常常被人放下喝光的可乐瓶子,那里的垃圾被人随手乱扔,就是这样。这是都市的冷漠和自由带来的,也有人就是爱这样的自由气息,像小孩子常常因为穿新衣服有太多的约束而宁可穿旧衣服,他们看到一只用过的塑料袋在街心随风飞舞,会突然觉得身心俱醒,将自己从循规蹈矩的轨道里脱离出来。
——《纽约与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P275
上海是个文化多元并善于包容并蓄的丰饶都会吗?上海在精神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强烈个性与内在冲突吗?这是在我看来,它是否能最终成为国际大都市的精神指标。它从未月白风清过,总是泥沙俱下却奔腾万里。但无论是怎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始终萦绕在城市上空的惆怅都有力地镇定了它的躁动,辽阔了它的心胸。
——《城市》P305
一个时代过去了,方才显示出它的气息,像吃光了鱼肉以后,才显出它的白色骨头。
——《上海美容院》P338
当一种生活方式被终于认同,如小资情调,那在边缘时的清秀苍茫之气,立刻成为热气喧哗的世故与市井。
——跋二(2007 )P515
上海的1970年代,悄悄诞生了这样一群人,所谓老克勒。他们为人客气文雅,从不轻易伤害别人,但人们却会轻易就看不起他们对浪漫生活的追求,看不起他们誓言做旧时代寄生虫的心愿。人们觉得他们免不了虚荣和软弱,更像破落户。他们喜欢所有洋务物,但却大多没有好英文,当然也没有好法文和德文。他们读一本司汤达,一本奥斯汀,然后谈论一种叫英国乡村四步舞的社交舞,所以他们喜欢的并非是西方西方文明,而是西方情调。他们苦苦追求个性自由,这种自由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与政治倾向关系不大,他们不去想这么严肃的事,相对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他们只是追求可以体面地吃上一顿像样西餐的自由,能自由选择一支流行乐曲,无所顾忌地穿上与众不同的衣裙,找到一处好像西方太平世界的背景,摆好战后那些好莱坞**里的明星姿势,好好照一组照片,假装在外国的自由。他们大多数人并非没有阅历,但都缺少在严酷环境下出人头地的勇气和耐力,他们总是步步后退,直到脱离单位,回到家庭,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获得自己憧憬的生活的能力,尤其不会挣钱,不懂竞争,却敏感脆弱。因此,上海老克勒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不过十几年,正是禁锢时代与物质时代的空隙。当物质时代真的到来,国门真的开放,他们却越活越窝囊,渐渐不合时宜。这时,他们是真正落魄了。
这是我所认识的上海老克勒。
——《2008 ~2015 ,人群再八年记》P382-383
灯下她们的笑容。不是演唱者的笑容,而是陶醉者的笑容,是那种忍也忍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笑。那样的笑,穿越了不顺心的人际关系,工作中的惨败,孩子成长给出的无穷难题,感情上的漫长的孤独,身体上的不适,对渐渐变老的恐惧,失去年迈父母的痛苦,漏水的卫生间,手脚不干净的保姆,难缠的办公室政治,这种种生活中的不如意,这种种生活中渐渐被揭开的真相,这种种孤独和恐惧……才最终在脸上绽放开来。那孩子般全心沉醉的笑容,终于穿越了所有经历过的伤害,布满了她们不再年轻的脸,那笑容终于照亮了他们脸上的每个角落,就像明亮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连阴影都变得柔和而愉快。
——《1997 ~2007 ,人群十年记》P378
阅毕辑录于新安小家
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 夜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