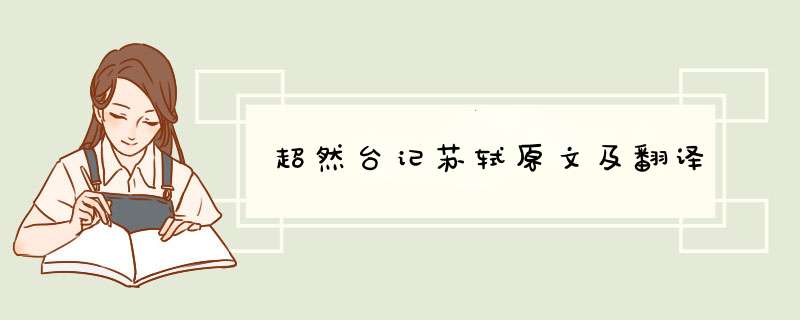
超然台记苏轼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翻译:
春天还没有过去,微风细细,柳枝斜斜随之起舞。试着登上超然台远远眺望,护城河内半满的春水微微闪动,满城处处春花明艳,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千家万户皆看不真切。
寒食节过后,酒醒反而因思乡而叹息不已。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姑且点上新火来烹煮一杯刚采的新茶,作诗醉酒都要趁年华尚在啊。
赏析:
这首词为双调,比原来的单调的《望江南》增加了一叠。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景象,包括三个层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登上超然台远眺,春色尚未褪尽,和风习习,吹起柳丝千条细。首先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意暮而未老。“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这一湾护城河水绕了半座城,满城内皆是春花灿烂。
其次,三、四句直说,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烟雨暗千家。”五句是说,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文章鉴赏
〔注〕 游:游心,涉想。 安丘、高密:皆密州属县。 马耳、常山皆山名。马耳在山东诸城县南五里,常山在诸城县南二十里。 卢山在诸城县南三十里,因卢敖而得名。苏轼《卢山五咏·卢敖洞》自注:“《图经》云:‘敖,秦博士,避难此山,遂得道。’” 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 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云:“姓姜名牙,后文王得之渭滨,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盖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号为师尚父也。”武王克商后,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为开国之君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成王遣使者至齐军中质问:两国一北一南,风马牛不相及,何故竟兵临我楚地?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所践履之界,指得行征伐之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谓此“穆陵”疑即今湖北麻城县北一百里与河南光山县、新县接界之穆陵关,春秋时属楚,故管仲说齐先君太公实受命得专征伐,有权至楚国之境;或以今山东临朐县南一百里大岘山之穆陵关当之,恐不合《传》意云云。今按苏轼登超然台所望之穆陵关自在山东,而文章连及于“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当是因《左传“南至于穆陵”的同名楚地而触发遐想。 潍水:《水经·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郦道元注:“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馀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不终:指韩信先以功封王,后贬淮阴侯,终被吕后所杀。 “余弟”三句:苏轼弟辙(字子由)于熙宁六年至九年任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有《超然台赋》,《序》云:“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
超然台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旧党争中自请外调,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1075),修葺超然台。文章即写于此时。虽属景物记,然超然台上说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写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夹缝中,隐约能体味到蕴蓄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丝苦闷,尽管它是被掩盖在一片超然之乐的下面。
文章起笔峥嵘,以“凡物”两字领起,陡然发挥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观”因而“皆有可乐”的议论。作者认为,不必定是奇异瑰丽的东西才能使人快乐,即便是食酒糟、饮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饱。由此,他推论出“吾安往而不乐”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思想认识。虽无一字涉及台上,然而这段议论却正是点出了台名“超然”的题旨,起到了正面阐发超然则乐的道理的作用;并且“乐”字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便从“乐”字拓开,说明不超然则哀的道理。作者先从议论祸福与悲喜的关系入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祸,是因为“福可喜而祸可悲”。然而却又有求福反而祸至的情况,这显然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祸而辞福”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其客观原因便是人的欲望无穷,而能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又有限,于是有些人为了满足其奢望,便总是在心里、眼前权衡、抉择,以至“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经常陷入烦恼之中。然后,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观原因,则是“物有以盖之矣”———外物蒙蔽住了他们的视野,亦即他们不能超然于物外(“游于物之外”),而被束缚在物质享受之中(“游于物之内”)。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缚在其中,便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不能洞察胜负的关键在何处了,于是自然就“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补充,从理论上阐述了超然则乐、不超然则哀的论点,为下文超然情事叙述的展开作了铺垫,因此下面一段便顺势入事,转入记叙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旷达情怀了。首先以对比手法,叙写作者离开了交通方便,居处华丽,山水优美的杭州,来到交通不便,居处简陋,而又无山水游乐的密州。继之描写密州的穷僻与自己的窘况。其穷僻则是天灾频仍,连年歉收,以至盗贼遍野,诉讼案件很多;其窘况则是,堂堂太守,竟至厨房空荡无物,唯靠枸杞、菊花之类野菜填饱肚子。这里自身窘况的描写,当不是作者夸大其辞,他在《〈后杞菊赋〉序》中说:“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赋中又说:“吾方以杞为根,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正是此种生活的实录。正由于杭、密之条件差异悬殊,因此人们都怀疑他定会闷闷不乐,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却因之而面容丰满,连白发也一天天返黑了。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诀。果有秘诀,且作者早已在开首言明了:超然则乐。乐则心宽体胖,表明了作者的确具有乐观旷达的胸怀,所以才不以境况之苦而自扰,反而爱上了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做出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谦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种种,作为封建官吏,正是多数人难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见出他精神的可贵、可嘉。作者的可爱之处还在于,热爱生活,兴趣广泛,每到一地总是兴致盎然地登山临水,探奇访胜。故此接着便描写他在政事之暇,修葺旧台,与朋友登临观览尽兴快乐的情事。不过,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作者并不是无是无非、一味盲目乐观的,政治上的失意,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阴影,他自有其痛楚,因之不能过分相信他的随缘旷放。当他从台上四面眺望时,他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只要细加咀嚼,就不难体味出来。他南望马耳山、常山,东望卢山,想象那里住有逃世的隐士;西望穆陵关,仰慕姜太公、齐桓公的显赫勋业;北瞰潍河,慨叹淮阴侯韩信当年建立大功而不得善终。这里,台周之景固属巧合,但他凭吊古人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者“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而不容于朝,被迫外任,因之时怀危惧,透露出仰慕隐士、欲全身远害的思想。然而,这段情绪仅如此一闪而过,下面转以轻松的笔触描写台的高大、安稳、深广、明亮,又叙写他“乐哉游乎”的逍遥自在。文章至此总归之一“乐”,可知作者尽管有隐痛,但善于自我解脱,能够保持喜乐如常的生活态度,从而使“乐”始终成为他生活中的主题歌。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同《凌虚台记》一样,作者按主题展开的需要,间错并用了议论、叙事及描写的手法,然两文彼此绝不雷同,稍加对照即可看出。全文由理入事,由事及景,再以理收煞,逐层推进,宕出兜回,其意都朝着中心凝聚的向心力———“超然”两字上:前面两段议论自正至反阐发“超然”之意,第三段叙事忽及四方形胜,忽入四时佳景,也总归在“超然”之中,即或则抒写其超然而乐的情怀,或则描写其超然而乐的情事。至此,“超然”之意只是隐伏在字里行间,始终不曾明言。末段点题,方呼应全文,而结句之中又见“超然”之意,照应开头,关合全文,堪谓极尽布局密合、收纵自如之妙了。
1 哪位大神会用浅显的文言文写读后感的,400字左右,一篇是苏洵的
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这就说明,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二是在“元丰间”,张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处境很艰难。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亦不入石”。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这时的苏轼兄弟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可能流传。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泛流传。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
2 语文文言文翻译《超然台记》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
3 《超然台记》的译文文章选自《古文观止》,译文如下:
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从台上向南望去,是马耳山、常山,它们忽出忽没,时隐时现,若近若远,也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而东面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齐桓公的遗风,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高大而又平稳,进深而又明亮,夏凉冬暖。雨雪纷飞的早晨,微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客人们没有不跟从着我的。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着,说道:“游玩真痛快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把这台命名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出于事物之外啊!
4 超然台记 阅读答案超然台记 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
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
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棱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
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子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节选自苏轼《超然台记》)5、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物有以盖之矣 盖:遮蔽,蒙蔽 。
B余自钱塘移守胶西 守:把守,守住 C释舟辑之安,而服车马之劳 服:承受,承当 D岁比不登,盗贼满野 比:接连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3分)A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发之白者,日以反黑B、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 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C、美恶之辨战乎中 乐哉游乎D自其内而观之 夏凉而冬温7下列各句中,全都直接体现作者“超然物外”思想的一组是 (3分) ①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②斋厨索然,日食杞菊。
③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④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⑤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 ⑥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A①②④⑥ B②③⑤⑥ C②③④⑤ D①④⑤⑥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作者认为凡物都有可欣赏的地方,只要有超然物外的思想,就能随遇而安。 B作者到胶西一年之后,身体丰腴了,白发逐渐变黑了,这是他超然物外的最大快乐。
C作者登台远望,联想到古人功业,可见作者虽然身在西胶但建功立业的理想尚在。 D正因为作者能够“超然于物外”,所以其弟才以“超然”二字命名此台。
9断句和翻译。(10分)(1)用“/”给文中划波浪线的句子断句。
(4分) 南望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2)翻译下面句子。(6分) ①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3分) 译文: ②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3分) 译文: 参考答案与评分标准:5B(守:应为“任职”) 6A(”之”都解为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B“以”分别解为“连词,因为”和“连词,表目的,用来”。
C“乎”分别解为“介词,在”和“助词,表感叹语气”。D“而”分别解为“连词,表修饰”和“连词,表并列”)7D(①总说。
有超然物外的思想,就能随遇而安。②是说明条件的艰苦,是客观的,而不是有意为之,因此不合要求。
③是“超然物外”的结果。④⑤⑥句是“超然物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行为。)
8B(身体状况变好,并不是他超然物外的最大快乐。)9(1)断句 南望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原文是:南望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
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
(4分,每3处1分。“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与“犹有存者”中间可断可不断)(2)翻译(6分)①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3分)译文: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3分,“安往”1分,大意2分)②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4分)译文:我既喜欢这里淳朴的风俗,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 (3分。
“乐”“安”各1分,大意1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5 超然台记译文译文: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
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
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
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
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
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
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
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
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
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
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超然台记》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也隐含了少许内心苦闷、失意之情。
这篇文章用“乐”字贯穿全文,先写超然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能超然于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即是写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再写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
以忧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不离乐字,是“一字立骨”的佳作。
6 寻 《超然台记》(苏轼)译文一份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
第二种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依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争辨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不要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争辨,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一面吃一面赞叹:
“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7 超然台记的原文凡物皆有可观(1)。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铺(2)糟(3)歠醨(4)皆可以醉(5);果蔬草木,皆可以饱(6)。推此类也,吾安往而(7)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8)辞祸者(9),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10),美恶之辨战乎中,而(11)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12)物有以(13)盖(14)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15)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16)生,而(17)忧乐出焉(18),可不大哀乎!
予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19)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20),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21)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22)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23),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超然台记》翻译: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以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魄力的景观。吃酒槽,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即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确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地分辨在胸中纠缠,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作求祸避福。
追求灾祸,不要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食物之外。
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已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前面,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争辩,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超然台记》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
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尽之矣。彼游於物之内,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鬭,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此文出自苏轼宋代《苏东坡全集》《超然台记》。
《超然台记》创作背景: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被排挤出朝廷,先任开封府推官,继任杭州通判。“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求为东州守”(苏轼《超然亭赋序》)。熙宁七年(1074)被批准改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
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忧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
唐宋八大家《苏轼·超然台记》散文名篇鉴赏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②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③,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④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⑤,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⑥,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⑦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⑧,瀹脱粟而食之⑨。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①哺(bù不)糟啜醨(lí离):吃美食,喝美酒。哺,吃。糟,酒糟。醨,薄酒。②盖:蒙蔽。③胶西:汉置胶西郡,宋为密州。今山东高密。④采椽:从山中采来椽木。比喻不加修饰,粗糙朴实。⑤岁比不登:连年收成都不好。⑥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⑦卢敖:秦博士,传说隐于卢山,修道成仙。⑧秫(shū熟)酒:高粱酒。⑨瀹(yuè月):煮。脱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本文意在说明,超然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祸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恶,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谪,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笔便暗写“超然”,直接提出“乐”字为主线,然后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遇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连,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