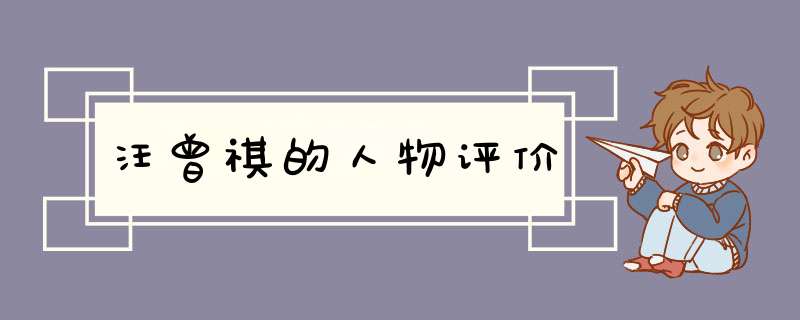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扩展资料:
文学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
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
认识汪曾祺,是从初中课本上一篇文章《端午的鸭蛋》开始的,后来又读到《昆明的雨》这篇文章 ,作者用朴实的语言 ,细腻的感情 ,将生活中的美展现给我们 ,我被感动了。汪曾祺 ,生于江苏高邮 ,江南水乡滋养了他内心的情感 ,养育了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 戏曲家、 散文家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颇高 ,他曾说过:“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从汪曾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学到他的写作风格 。朴实中蕴含着深情汪曾祺曾说:“写东西不能感伤,太过感伤,下笔就容易失控 。”他的老师沈从文去世时,他这样写道 :“这样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过多的词藻渲染 ,朴实的语言,把对沈从文先生的感情写尽了。平凡中蕴含不平凡汪曾祺看人看事的角度,往往与一般人不同,他能在平凡人的身上找到不平凡的神韵 。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人 :北京西四公交车站 ,103路无轨电车上有一个中年女售票员,很胖 。那个站经常有很多人在等车,为了让更多的人乘车,她总有办法把每个人都塞进车里,最后有几个人躲在车门口动弹不得的时候,她就会站在后面,把肚子缩进去。然后使劲儿向前一顶,三顶两顶,车门就被关上了 。这样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妥,但汪曾祺竟然调侃,这位大婶儿这么卖力 ,为的竟然是让更多的乘客早点儿回家,实在应该当劳模 。这种幽默感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有美食才是生活汪曾祺酷爱美食 ,只要是美食,他就决不会放过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个吃货。但他品完美食还不算,更要用文字记录下来,所有美食在他的笔下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有人说,如果在深夜读汪曾祺的文章,一定会被“饿疯”的 。别的不说,单读《端午的鸭蛋》我就要流口水了。总之,汪曾祺的作品 ,平凡中有伟大,朴实中见真情,生活中的美味在他的笔端流淌。生活琐事是最好的素材,朴素感情是最真情的告白。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与挫折,受到诸多不公平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淡然豁达的心态,乐观诗意的创作精神。
贾平凹曾说:“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了。”
汪曾祺自己则说:“生活须有光有影,有晴有心,滋味都合在这里了。”
读汪曾祺的《万事有心,人间有味》,真切感受到他品人间美味,过淡然人生的至高境界。跟随他一颗慧心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
肉食者不鄙。
听汪老讲吃的,让你忍不住口水直流,更有跃跃欲试做一做的冲动。很少有人把炒菜的关键处讲得如此精彩到位。平平常常的一道菜,在他的笔下精工细作成人间美味。如:
狮子头,是淮安菜。猪肉肥瘦各半,爱吃肥肉的亦可肥七瘦三,要“细切粗斩”,如石榴米大小(绞肉机绞得肉末不行)。荸荠切碎,与肉末同拌,用手团成招柑大的球,入油锅略炸,至外结薄壳,捞出,放进水锅里,加酱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汤放入深腹大盘。如此而来,狮子头松而不散,入口即化。
东坡肉,就是红烧肉,功夫全在火候。先用猛火攻,大滚几开,即加作料,用微火慢炖,汤汁起小泡即可,好吃的很。
“手抓肉”在他笔下成了“无与伦比”的美味。然,手抓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蒙古人吃出一份豪爽。一手“把”着大块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着吃。蒙古人用刀子割肉真有功夫。一块肉吃完了,骨头上连一丝肉都不剩。因为是现杀、现煮、现吃,所以非常鲜嫩。读到这里,有没有去品尝一下的冲动
“吃春天”。春天到了,是挖野菜的时候了。踏青挑菜,是很好的风俗。野菜多半带一点苦味,凡苦味菜,皆可清火,但是更重要的是吃个新鲜。譬如蒌蒿,是极清香的。苏东坡有诗“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嗅觉和味觉是很难比方,无法具体的。所谓“清香”,汪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吃野菜,就是“吃春天”。得是一颗多么恬淡的心才会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汪老的笔墨如涓涓细流,流出的是浓重的烟火气,文人的雅趣和情调跃然纸上。
自得其乐,淡然豁达
孙犁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子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汪老爱好雅趣,爱唱戏,写写字,画画画,还有一样是做菜。
到了一个新地方,汪老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构思用什么样的食材做哪样菜。做菜还是一种轻量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自得其乐,悠然悠闲。
写字可以使人得到平静。“静对古碑临黑女,闭吟绝句比红儿”,是不俗的享受。接连写几张字,第一张大都不好矜持拘谨。大概第三四张较好,因为笔放开了。写一上午字,有时一张都不好,也很别扭。那就收起笔砚,出去遛个弯去。写字本是遣兴,何必自寻烦恼。
对写小说、散文,汪老说各个部分,应该“情意真切,痛痒有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八个字,言简意赅。运用语言,要有取舍,不能拿起笔就写。做诗文要知躲避。有些话不说,有些话不像别人那样说。至于把难说的话容易地说出,举重若轻,不觉吃力,这更是功夫。
平淡是苦思冥想的结果。平淡而有味,材料、功夫都要到家。四川菜里的“开水白菜”,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奥妙在汤里,用的是鸡汤。学问无处不在,处处相通。
静思往事,如在目底
“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苏轼这首歌强调静心修养的境界。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闻世事。唯静,才能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合乎人道。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
“静思往事,如在目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时一挥。”
文如其人,汪老的散文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宁静淡泊和对人情事物的达观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随遇而安》里,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能如此调侃,这得是多么豁达的心胸!
丁玲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汪老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境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玩。生活,是很好玩的。
从《万事有心,人间有味》这本书,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汪曾祺来说,生活就像衔一颗蜜枣就接受手术,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我听到的只有汪老一人,不得不说,他秉承了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问多素心人,乐于数晨夕”的气质。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巴金
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郭沫若(1892--1978)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1》、《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一八八三—一九三一),作为哲理诗人和杰出画家,和泰戈尔
一样是近代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同时,他又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主要奠基
人,二十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以纪伯伦为中坚和代表
形成的阿拉伯第一个文学流派「叙美派」(即「阿拉伯侨民文学」)曾闻名全球。
在短暂二辉煌的生命之旅中,纪伯伦饱经颠沛流离、痛失亲人、爱情波折、债务缠身与
疾病煎熬之苦。他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区的一个农家。故乡的奇兀群山与秀美风光赋与他艺
术的灵感。十二岁时,因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他随母亲去美国,在波士顿唐人
街过着清贫的生活。一八九八年,十五岁的纪伯伦只身返回祖国学习民族历史文化,了解阿
拉伯社会。一九0二年返美后仅一年多的时间,病魔先后夺去了他母亲等三位亲人。他以写
文卖画为生,与为人剪裁缝衣的妹妹一起挣扎在金元帝国的底层。一九0八年,他有幸得到
友人的资助赴巴黎学画,并得到罗丹等艺术大师的亲授与指点。一九一一年他再次返美后长
期客居纽约,从事文学与绘画创作,并领导阿拉伯侨民文化潮流。当他感到死神将临,决心
让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加光耀,遂不顾病痛,终日伏案,直到四十八岁英年早逝。
纪伯伦是位热爱祖国、热爱全人类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写下了传遍阿拉伯
世界的诗篇《朦胧中的祖国》,他讴歌毕生苦恋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
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爱与美是纪伯伦作品的主旋律。他曾说:“整
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全部人类都是我的乡亲。”他反对愚昧和陈腐,他热爱自由,崇尚正
义,敢于向暴虐的权力、虚伪的圣徒宣战;他不怕被骂作“疯人”,呼吁埋葬一切不随时代
前进的“活尸”;他反对无病呻吟,夸夸其谈;主张以“血”写出人民的心声。
文学与绘画是纪伯艺术生命双翼。纪伯伦的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后期创作则以散文诗
为主。此外还有诗歌、诗剧、文学评论、书信等。《先知》是纪伯伦步入世界文坛的顶峰之
作,曾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一七五七—一八二七)的影
响,所以,文坛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一九0八年—一九一0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
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
家。”纪伯伦的绘画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在阿拉伯画坛占有独特的地位。
他毕生创作了约七百幅绘画精品,其中的大部分被美国艺术馆和黎巴嫩纪伯伦纪念馆收藏。
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
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善于在平易中发掘隽永,在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
另一方面,纪伯伦风格还见诸于他极有个性的语言。他是一个能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的双
语作家,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得清丽流畅,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方读
者。美国人曾称誉纪伯伦“象从东方吹来横扫西方的风暴”,而他带有强烈东方意识的作品
被视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
早在一九二三年,纪伯伦的五篇散文诗就先由茅盾先生介绍到中国。一九三一冰心先生
翻译了《先知》,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纪伯伦开阔了文学的窗扉。近十多年来,我国又陆
续出版了一些纪伯伦作品。这位黎巴嫩文坛骄子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知音。选自《人民日
报》(国内版)19931112国际副刊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汪曾祺,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真正在作品中体现了人生与人生态度的一位。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肄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解放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后在一个京剧团任编剧,在此期间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194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47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等。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八十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汪曾祺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更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宇慧撰写)
萧乾,蒙族,原名萧炳乾,北京人,1910年1月27日生,著名记者、作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至1955年任《译文》编委,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1989年4月,为美国伊斯塔德“国际文学奖”第十届评奖会评审委员。
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他又是唯一在大陆落叶归根者。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萧乾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萧乾用他手中的笔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向国内外读者介绍这一片新气象。1990年,八十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应南京译林出版社之约,着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经过四年多的艰辛耕耘,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才将这部旷世奇书联袂翻译出来,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授予的“彩虹翻译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萧乾作为一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化人,复出于文坛后,与外界的接触频繁,曾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经验交流会、研讨会以及馆员书画作品展览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为团结老年知识分子、发挥馆员专长、弘扬民族文化、继承祖国文化遗产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他倡导并担任主编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全套共五十册,约六百万字,已于1994年底全部出版,港台版也已面世,算得上是各文史馆的一大盛事。这套书汇集了全国二千多位文史馆馆员以及馆外一些誉宿名流亲闻、亲见、亲历的轶事掌故、琐闻杂记,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荣获1993年度中国图书奖。
萧乾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他的心始终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作为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他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重。
该小说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言“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受戒》营造了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宛若梦境的“桃花源”汪曾祺简介,通过描写生活在其中的一对小儿女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赞颂了尘世间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小说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真的初恋故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门净地“荸荠庵”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人间的烟火弥漫在寺宇内外。该小说以幽默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宗教环境中世俗化的一面: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荸荠庵”里没有神秘玄的气氛,也没有枯寂虔诚的膜拜,更没有道貌岸然的清规戒律。庵内的和尚学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就可以混口饭吃,可以攒钱,可以娶妻,可以斗纸牌、搓麻将、吃水烟。而且和尚们吃肉也不避人,过年时还会在大殿上杀猪。在这里,无所谓清规,甚至连这两个字都无人提起。不独是荸荠庵如此,城里的所谓佛门净地善因寺,也与世俗红尘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充满了人间的情趣和生机,比如善因寺住持自己有一个十九岁的老婆;虽然和尚们吃斋时如果发出声音会被监寺惩戒,但其实他并不是真打人,只是做个样子。总之,在这个旧社会的江南水乡,当和尚不过是谋一个“管饭”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与种地、画画、弹棉花等行当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平等自由的谋生职业。
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描述了一个温情浓郁的人性世界。佛教中超然出世的生活原则,在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化作了叙述者对宗教人生的善意的嘲讽和戏谑,而积极入世的生活理想,则与作者所提倡的市民意识紧密相联,突出了民间文化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底蕴。正是在这种世界中汪曾祺简介,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才变得顺理成章,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阻力。
作品表现他们的爱情时,既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也没有写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而是让人物植根于平凡的生活沃土,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劳动一起嬉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朦胧的爱情。这种清新纯洁的爱情,呈现出人性中健康、美好、天真的一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