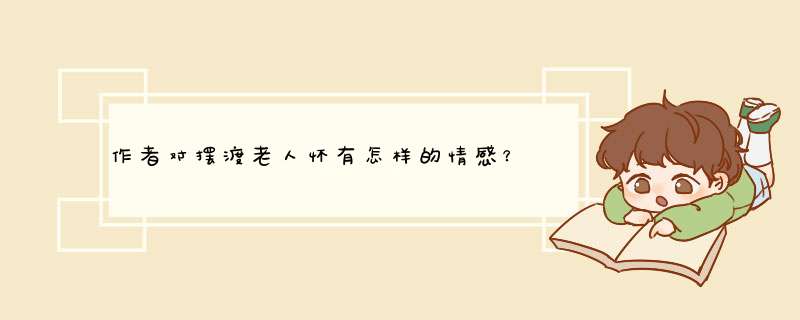
1、本文具体描述了摆渡老人接送“我们”过河上学的辛劳。先写老人因“我们”的[恶作剧(淘气、调皮)] 而手忙脚乱,一番折腾;再写因(河面结冰),老人好不容易“才把船晃过来”;最后写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特地起大早送“我们”过河上学。
2、老人为失去可爱的儿子而深感痛苦,于是把父爱转移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子),每天接送“我们”上学,所以觉得“心里好受些”。(言之有理均可。语言表达不清的要扣分)先要分析摆渡老人为什么心里不好受,再分析他这样做“心里好受些”的原因,这道题就能答得比较圆满了。第5段中“那双眼中竟满含着期望和爱意”这句话,也提示摆渡老人“心里好受些”的原因。
3、既愧疚又感激的心情。
为摆渡老人失去儿子而难过,为自己的恶作剧而难过,为自己不理解老人而难过。此时“我”的心情是愧疚。为老人对我们的期望和爱意,而感激。
4、可笑又可敬的形象。
“可笑”一词在文中出现过,摆渡老人把自己对儿子的爱转化成对一代青年人的爱,这种爱是令人尊敬的,是伟大的。孩子们了解了老人,理解他的爱意,因而尊敬他,是合乎情理的。
5、例句:①父母把儿女摆渡到成人的世界。②老师把学生摆渡到知识的王国。③医生把患者摆渡到健康的乐园。④科学家把人类摆渡到万里之遥的星球。⑤小小电脑把我们摆渡到广阔无垠的信息海洋。⑥米卢把中国足球摆渡到“世界杯”的绿茵场。“摆渡”在这里就是“帮助”的意思。
法国史家对中世纪文化怀有情感,视其为法兰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18世纪思想家认为历史会走向进步,有其历史的背景为后盾。随着科学革命的开展,西欧的一些地区在17世纪后期开始慢慢工业化,其结果是欧洲领先于其他地区,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当今的全球史家认为东西文明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大分流",便是指的这个现象。
所谓"大分流"是指工业文明取代了人类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由此,欧洲(以西欧和当时刚刚新建的美国为代表)开始领先于其他文明,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句话并不只是比喻而已,因为火车的发明和使用,无疑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工业文明的兴起,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但也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因为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制度、宗教观念和思想形态。工业社会的兴起,必然会与之对抗。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其背后既有宗教信仰分歧的原因,更是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旧制度冲击的结果。
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革命,其原因和过程各不相同,而其结果却大致相似,那就是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是这种新旧制度更替表现最为激烈的一个事件,其影响也最为深远。从政治层面来讲,法国大革命的最大遗产体现在推进了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浪潮。法国革命激烈、激进的程度,不但让尚未改革的普鲁士等地感到恐惧,而且也造成已经经历过改革的英格兰、荷兰等国的不安。英国学者对于法国革命一般都持批评的态度,其中以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1729—1797)最为典型。
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不安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有关历史观的争议。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在近代社会慢慢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中世纪。在法国革命爆发之际,前章提到过的"古今之争"已经基本结束,主张今胜于昔的学者略胜一筹。所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论辩过去是否仍然胜于现在,而在于讨论在近代化高歌猛进的时候,是否要否定中世纪的一切。
如前章所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对于中世纪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而德意志学者如赫尔德,则对此颇有异议。激烈的法国革命,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似乎要以全新的姿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由此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恐惧和不安。英国的学者则认为,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有来自中世纪的"大宪章"的遗产。
因此,完全蔑视中世纪并不明智。更有甚者,由于法国革命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拿破仑战争。而拿破仑以军事的手段扫荡了几乎整个欧洲,冲击了旧制度。所以在如何对待中世纪的遗产这个问题上,还掺杂有欧洲其他地区反对拿破仑法国霸权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
19世纪被人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其原因和特点则颇为多元、多样。批评法国革命过于激烈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对中世纪的肯定甚至怀念,在文学作品上最为明显,表现为浪漫主义,主张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维。这三种"主义",加上上面提到的民族主义思潮,都在19世纪得到长足进展,并促进了历史学的大踏步发展。
因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就是要对过去充满兴趣(以否定中世纪来提倡历史的进步观念,被一些人视为代表一种"非历史"(ahistorical)的态度)。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更促使史家缅怀自身民族的过去,所以无论是浪漫主义的情绪还是历史主义的思维,都有助于历史研究和著述的蓬勃发展。那时出现的历史作品,内容和形式多样,比如世界史的写作,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开发,让人颇有兴趣。
同时,对欧洲古代社会的研究也仍在持续。"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或Orientalism)——欧洲学者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研究——也在慢慢兴起。但毋庸置疑,19世纪史学的大宗是民族国家史学,即追溯、回顾、研究一个民族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著作,不仅欧洲如此,世界其他地区亦不例外。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有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民族史学在那个世纪的蓬勃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民族史学的写作和出版,助长了该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感情,提升了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而民族国家的成立又起了帮助民族史学发展的作用。举例而言,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又让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在期间,法国政府建立了博物馆(卢浮宫)和档案馆,其目的就是要提升公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博物馆和档案馆又是民族史学写作的得力帮手。这两种机构的雏形在古代便存在,但性质和功用不同。近代的博物馆(不少博物馆还包含国家图书馆在内,如大英博物馆)既有保存古物的意图,又有教育公民,提高其民族自豪感的目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得日益重要。
国家不但出面、出资建立博物馆,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特别是学校学生)参观。这些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民族认同感,提高爱国心。档案馆的使用者与博物馆的参观者相比自然要少得多。但档案馆逐渐向公众开放,其目的也是为了提供方便,有利于历史学,特别是以自身民族为题材的历史著作的写作。
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创建于1790年,是欧洲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档案馆。而作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卢浮宫(LouvrePalace)在1793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也是欧洲最早、最大的国家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向公众开放,为欧洲最早)。
就民族史的写作而言,法国史家也不落人后。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ut,1787—1874)和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都以不同的方式写作法国史,其中,米什莱以其高昂的热情、史诗的笔调歌颂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历史,不但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而且还是欧洲民族史学写作的典范。
这些法国史家的性格、治学和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长大,因此他们的史观又有相似之处。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不同,他们对中世纪文化怀有浪漫主义的情感,并视其为法兰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
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受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史学大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影响。基佐在年轻的时候,还曾评论夏多布里昂的名著《殉道者》(LesMartyrs),得到了后者的称赞。同时,这些史家在思想上又受到法国革命的洗礼,看到了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特别希望从整个民族的角度写作法国史。
听《二泉映月》就是在听一段凄惨的故事,整首曲子都充满了悲伤,凄沥。听着那曲子,就好像自己也偿尽了人间苦楚,饱受了人间沧桑,但同时心里边又不甘,竭力呐喊,挣扎,向着命运抗争。《二泉映月》的曲调之悲,意境之凄凉,让人听了第一遍就害怕听第二遍。但那旋律给人的印象深刻之极,让人久久不能忘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