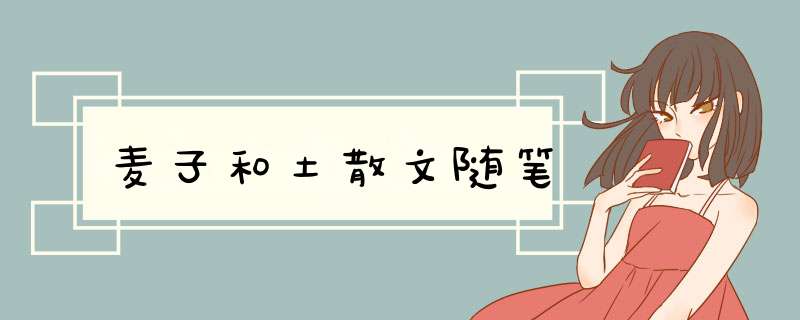
生物老师发了几颗晒干的麦种让我们拿回家做实验,我从大花盆里刨了些土放进塑料杯里,再把麦子放到土里去。
麦苗被时间一点点从土里拉出来,看着懒洋洋的,又嫩秧秧的,很羞涩。要是用新出生的婴儿比喻此时的麦苗,那泥土就是母亲了。泥土没有麦苗的新绿,没有麦苗的可爱,就像我的妈妈。岁月已在她的眼角后悄悄画上了几条细细的鱼尾纹,时光也在她曾经白嫩的脸颊上抹了一层浅**。妈妈慢慢老了。
麦苗从土里钻出了一大截,还是绿的,像根迷你的嫩葱,又直又积极向上。要是用活泼的孩子比喻此时的麦苗,那母亲就应比作泥土了,早已失去天真,也不再如麦苗挺拔向上,就像我的妈妈。也许,是去年冬天的雪落在了她的头上,染白了她的几缕头发,她的头发已经不再是全黑的了。妈妈已经慢慢老了。
麦秆上长出了嫩绿绿的小麦子,麦秆也由绿色渐渐变成了**,嫩嫩的麦子像含苞欲放的花苞,充满活力与期待。要是用青春的少年比作此时的麦子,那泥土也就是母亲了,不再充满青春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就像我的妈妈。她的我曾经闭着眼睛也仍可以摸出的滑嫩的手,也被时间磨得粗糙了。妈妈的确慢慢老了。
麦子一天天长大,妈妈也一天天老了,越来越像麦子下静静的沉默的泥土。可是没有泥土又怎么会有麦子呢?
实验做完了,我已经忘了老师到底要让我们观察什么,但我忽然发现了,妈妈的每一条细发,每一丝白发,都充满了魅力,奉献的魅力……
我的前一首七律实际上是看了夫人的短文才获得灵感的。征得她的同意,今天将她的随笔也发表在《》上,请各位方家指正!
老家的麦子又该黄了吧。
时光如梭。五一假期还没走远,已至月底了。记得老家有句谚语:“割麦不过六月六”。意思是,每年六月六日前麦子就成熟收割了。老家的麦子是冬小麦,每年国庆左右雨后播种,第二年春天返青,清明过后,气温回升,麦苗迅速生长,五月底六月初逐渐变黄后就成熟了。民以食为天,麦子是北方人的主要食粮。夏收时节多雷雨,之后将进入北方的雨季。而夏收就怕雷雨天,一年辛苦劳作的收成就可能毁于一旦。五黄六月,须龙口夺食。麦子成熟后必须在短短几天内迅速收割,脱粒晾晒入仓。如不及时收割,因麦秆又干又脆,如果倒伏将大大增加收割难度,而更糟糕的如果遇到连雨天气,无法收割的麦粒在麦穗上将发芽生长,大大降低食用的口感,甚至无法食用。因此全村老少,只要能动的都去抢收麦子。记得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有一年麦收季节,老天好像病了一样,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眼看着成熟的麦子无法收割入仓,麦子在地里就发了芽,可怜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在雨中欲哭无泪,湿漉漉抢回的一点粮食连一年的口粮都不够,更别提上交皇粮了。
70年代中期,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土地尚未包产到户。收割麦子时由生产队长统一调配劳动力。一块麦地收割工序基本是这样的:第一步,割麦。青壮年妇女是割麦子的主力军。割麦不需要太大力气,但有一定技术含量,并持续弯腰,挥汗如雨。她们三行一垄,因是纵向,应为三列一垄,左手伸出一臂距离轻揽麦子,右手拿着老爷子们早已磨得锋利的镰刀,轻轻一拉,一扑麦子被齐根割下,隔一定距离放置一堆。她们弯腰不抬头,眼不旁骛,只盯着麦垄,嚓嚓嚓嚓,只听得飞快的割麦声。割麦子谁也不愿落后,一趟割到头,腰疼得直不起来,还得急忙再去找另一趟。第二步,捆麦。割过的麦地里,成行成列地放置着一堆堆麦子,像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初中以上的半大少年,由几个老者领着捆麦子,将一堆堆散开的麦子捆成一个结结实实的麦捆。第三步,拉麦。有力气的青壮年男子负责拉麦子,他们猛一使劲把一大捆麦子扛上肩,再装满大车,吆喝着骡马,拉到麦场。第四步,拾麦。该小学生上场了,小学生被老师组织起来去收割过的麦地捡拾散落的麦穗。捡麦穗的小学生有男有女,有大有小,不分年级,不分年龄,一起干活。为了公平合理,奖勤罚懒,捡麦穗是包工活,按捡拾的斤数记工分。第五步,收尾。最后一步上场的是老太太们,也是捡麦穗。她们是日工,按出勤的天数记工分。老太太们不紧不慢,认真细致,她们捡过之后的麦地里一贫如洗。当然,收割回去的麦子,还需要经过脱粒、扬场、晾晒等工序,才能入仓,每一道工序都透着农民的辛苦劳作。颗粒归仓,是对辛苦一年的农民最大的尊重。
还记得小时候麦收季节的印象。一望无际,麦浪滚滚,大人们虽然非常辛苦,但满面的笑容无疑诠释了收获的喜悦。而这时的小孩子们也是最欢乐无比的。学校放了麦假,不用早起辛苦读书了。小伙伴们成群结队玩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当然,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教育,帮助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体会劳动的辛苦,也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内容。
说来惭愧,从小生长在北方农村的我,多年在外求学,又是家中老小,参加的麦收劳动屈指可数。小学时,跟着老师捡麦穗。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我一个小女孩辛苦一天也捡不了几斤麦穗,一个假期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好不容易上了初中,放假第一天,我欢天喜地跟着同学找队长派活,要求参加麦收劳动,为家里贴补工分。我从小学习好,一级没留。同年级的同学基本比我大两岁以上。队长指着人高马大的其他同学说,你你去这里,你你去那里,我没有被安排。我弱弱地问队长,我呢?队长看着瘦小柔弱的我,问:“你上初中了吗?”我说:“上了。”“唉!你太小了,还是去拾麦吧。”一举又被回到了小学毕业前!
恢复高考的政策带来了教育改革的春风。考上中专或大学,就可以鲤鱼跳龙门,从此逃离农村,不用再辛苦地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家长们也将孩子的未来寄托在升学上,学校不再放麦假了,而我也一路绿灯顺利考上大学,求学期间的麦收季节再没有参加过劳动。
大学毕业后,工作单位离家不太远。那时,已经包产到户。想自己这么多年求学在外,从没有帮家里干过农活,心有愧意,麦收季节,我特意向单位请假回家收麦子。然而,父母兄嫂已经基本收割完成,只留下崖下一小块晚熟的洼地麦子。能干的兄嫂不容我拿起镰刀,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我总算赶了个麦收尾巴,抱了几扑麦子帮着捆成捆。
又是一年麦收时,我已嫁为人妻。麦收季节,跟着老公回家帮工。初为人妻,腼腆胆小。去厨房帮厨,彼时正当中年的婆婆和厨艺精湛的奶奶把我撵了出去。夏收季节全家繁忙,怎好意思一人闲着?于是跟着老公、大姐去麦地割麦。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割麦子的我,挺着六个多月的身孕,怎么割也追不上快割如飞的大姐,心里一急一刀砍到脚趾头上。鞋子都被砍掉一块。得!有功之臣不用干活,打道回府。晚上,脚有伤口,身子又笨,弯不下腰,只好让老公帮着洗脚。
再后来,拖个小油瓶,既帮不了忙,也就不去添乱。再后来,时代在进步,农村实现机械化,割麦有了收割机,省时省力,又快又好。再后来,社会在发展,村里实现工业化,铁厂占了耕地,家里没了麦地。而我们也越走越远,工作单位从离家几十里,到如今离家上千里,再没有机会割一回麦子。
我终于在父母拼尽全力相助下,踩着父母的肩膀鲤鱼跳了龙门,也实现了自己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让孩子不再辛苦修理地球的伟大而庸俗的理想。
然虽不再挥汗如雨,却怀念彼时的单纯快乐。
笔锋至此,泪眼模糊,泣不能已。谨以此文缅怀我辛劳一生已升天堂的父母!
2018年5月31日
亲爱的麦子:
展信佳!
很久没有写信了,提起笔来竟忘了语言,不知要说些什么!看到这么多人给你写信,竟也跃跃欲试,你还记得我吗?尽管我的文笔才情有限,却时常喜欢舞弄墨,喜欢在美文栏目写美天一篇专题的清影,也许在你的记忆里会有一二印象,也许,毫无印象,不管怎样,你是我心目中唯一的麦编,默默耕耘、摆摊、收阅文字,辛勤付出的麦子。
最近,因为工作和各种杂务缠身,很久没有心情静下来好好思考、阅读和更新美篇了,你说,以前的生活慢,书信慢,车马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是啊,社会进步了,一切都在变化中,当我们飞速前行时,世界已缩短到触手可及时,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过去岁月,是多么珍贵,美好,独一无二,无可追寻,我们只能回味,感叹,寻幽揽胜,终究不及古人一二,那份悠然自得、"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雅致心思,已经没有了奈心,一封电子邮件,须臾可得,替代了传统,书信被封存在记忆里。还好,现在我能给你写信,真是值得庆幸。
麦子,已经到了三九严寒的天气,可人的思绪并没有被冰雪冻僵,它还很活跃,并且时常以天马行空的方式呈现,或许,人是天生会梳理纷乱,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的,自动屏蔽烦恼痛苦的动物,总有些喜好成了记忆中的宝藏,永不褪色、磨灭。我也想和你分享它,我心中闪烁而过的片断。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会被一种事物吸引,突然眼前一亮,欣喜不已,那肯定是触动心灵的声音,我搜寻记忆,穿越时空,突然就看到了它。一年冬天,站在中台禅寺寺院门前远眺,远山连绵,白雾茫茫,青嶂翠峦里,一棵奇特的树,开着一朵朵火红色的花,特别艳丽夺目,象混沌中镶嵌的红宝石,光彩照人,目极之处,心驰神往,因为遥远,不知是什么花,却定格成了一幅画。我想,我是喜欢美好事物,自然风光,花草树木的人,才有了如此震撼心灵的情感记忆。后来在香港,无意中看到路边的一棵大树,开着同样色彩的花,一朵朵似火铜铃挂在枝头,鲜艳美丽,才知道它是木绵花。
木绵花是代表男人的花,是英雄的象征。而它的花语是珍惜身边的人给予他的快乐,每个男人身边都会有爱他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他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快乐,那么作为身边人的她必定一样幸福快乐,我也希望自己温暖别人,并且得到亲人朋友的爱,只有彼此的信任,贴心,才会走的更远。
清浅时光,匆匆而过,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了,就此搁笔,祝愿麦子新的一年幸福快乐!
并祝冬安!
20181
麦收季节散文
故乡的七月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每到这盛夏伏天,艳阳一个劲地毒晒,让人感到空气仿佛都是滚烫的,就是在阴凉处避暑纳凉,身上也一股热气直冒,把个身子热得汗浸浸的。
夏日的故乡山梁坡峁上一垅垅梯田层层泛绿,门前屋后成片成片的麦子长势喜人。每到七月,沟壑梁峁田间地头小麦苫得瓷瓷实实,随着小暑的临近,那滚滚麦浪渐渐透出一抹淡淡的鹅黄,那抹鹅黄预示着麦子收割的季节即将到来了。
每到小麦收割季节,农人们天还不大亮就起来了,迎着晨曦,踏着晨露,听着蝉鸣虫叫,手持一把磨得亮闪闪的镰刀沿着田间小路径直走向田间地头。在故乡,按传统习惯,锄草、收割和干家务活是婆姨们的事,可眼下劳力有限,男人们只得放下大丈夫的派头到田间地头忙活,动作虽不麻利,但看着大片的麦子透黄,心里头也很着急,只有跟着婆姨们在烈日下手握镰刀紧割慢捆地忙活。
这几年,故乡持续的干旱使麦子的收割时间也提前了,虽然农人们盼望着年年风调雨顺,可旱魔却扎了根似的`不肯让步。人们只有开渠引水浇田,提灌抽水上坡,与旱魔展开了一场促墒保收的抗争。收割季节最要命的要数阴雨天了,几天的阴雨连绵,运往打麦场里上了架杆的麦子就要发芽,地里头未收割的也会脱粒生芽。故乡的天气要数七月天顶热,就是不下雨,阴天里露水未干割捆成束的麦垛也会霉烂的。因此在收割季节,是要趁好天色起早贪黑忙活的,大热的伏天里,人们的一日三餐便在地头田埂将就了。有时天热的口渴难忍,可为了赶活,直到嗓子眼冒烟难以顾上喝口水是常有的事,这个季节里的苦干精神和时间观念是往日里罕见的。这个时节,故乡的田间地头到处一派忙碌景象,收割的收割,运输的运输,打碾的打碾,人背畜驮三轮车拉运穿梭不停,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齐上阵,这几年随着脱粒机在农村的普及,村落里再很少听见此起彼伏的连枷声了。这个火热的季节里,田间地头麦香诱人,满山遍野一派丰收景象,到处忙忙碌碌,那阵势叫人看后也着实感到季节是不饶人的。
土地是农人的命根子,随着土地联产承包政策在农村实施以来,故乡的农人对土地的厚爱更是有加,平整土地,改造薄田,精耕细作,保墒促肥,科学务农,该浇水时浇水,该施肥时施肥,硬是把几亩薄产田侍弄成了肥气十足的稳产田,碰上好雨水再也不愁丰收了。
麦收季节,关乎到农人们一年的收成和生计,虽然整天价忙乎,可心里头乐滋滋的。一年到头的汗水要在这七月天变成丰收的果实,圆了他们一个长长的梦,农人们能不乐吗?
改革开放这二十年间,故乡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人们的生活殷实了,吃穿不再是愁事,村落里宽敞明亮的红砖瓦房多起来了,院落也变的亮豁起来,大多数农家粮丰囤满富裕起来,各类电器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故乡正在慢慢告别过去那个物质匮乏精神文化单调的年代。
2001年9月刊登于《甘南报》
散文||麦子黄了
八十年代,关中地区的联合收割机极少,大片麦子黄了都是靠人工收割。一连多日的大太阳把麦子烤成了金**,一片连着一片,一浪推着一浪,扑入视野。面对金黄的麦子,人们欣喜又着急,急着抢收,龙口夺粮,昼夜不停。若来一场大雨,特别是连阴雨,地里的麦子就会发芽,若是麦子收回来下雨,晒不干也会发霉,一年的辛苦就全毁了,所以夏收劳动十分紧张。
割麦前的一个晚上,父亲就从存放物品的南院窑洞里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排镰刀,摆放在院子里。他端来半盆水,拿来一个灰色的长条形磨刀石放在地上,开始磨镰。父亲先用左手往磨石上撩点水,水滴到磨石上就从两头流到弧形面的中间,他拿起一把镰刀,取下刀刃,两手捏住两端前后推着,发出吱呜吱呜的声音,很有节奏。父亲磨上一会就停下来,用右手大拇指在刀刃上轻轻向下滑几下,说试试刃子磨利了没有,如果觉得不行就继续磨,直到每个刀刃看起来明晃晃,亮闪闪,锋利无比,才安好镰刀,挂在前窑墙上,等着明天早上用。
母亲忙着蒸馍馍,蒸面皮,准备招待麦客,孩子们也都放忙假了,跑前跑后帮忙。父亲说割麦子是力气活,挣钱不容易,吃饭不能亏待人家。母亲蒸好了馒头,这馒头可不是现在的小馒头,而是半斤重的大馒头,白白的,虚虚的,胀胀的,随着蒸笼盖揭开,腾腾热气扑面而来,烟雾缭绕,一阵原始面香弥漫在整个厨房。一锅馒头有三四层篦子,一层一层端出来,扣到案板上,馒头一个个胀鼓鼓的,散发着自然的面香味道,像胖娃娃圆乎乎的脸蛋。蒸好的面皮在案板上一张一张摞起来,摞得高高的,散发着面香和油香。
拿一个热馒头,竖着掰成两半,里面就呈现出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小气孔,用筷子挑一块臊子夹在馒头里,两手捏紧,臊子立即融化,咬上一大口嚼着,嘴角流油,满嘴的香味往外溢,颇有“蒸馍夹臊子,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臊子的香味合着面粉的香味,蛋白质与淀粉的完美结合,充分展示着天然美食的味道。在馒头里夹上拌好的黄瓜、洋葱、莴笋、灰灰菜、人花菜、洋芋丝等什锦凉菜,吃起来又是一种面香与蔬菜清香融合的味道,咬一口夹菜的馒头嚼着,就会感觉出天然食物的纯美味道。一口气吃下一个大馒头,就是孩子也算很正常的,那么香,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家里每年割麦子都是要叫麦客的,人多就割得快,就能及时把麦子收回来。麦客们常常是前一天晚上就请来了,在家里住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全家人就都起来了,和麦客一起吃完饭,拿着镰刀去地里割麦子。每家每户的男人们在地里忙着,女人孩子也都在家里忙着,火急火燎地忙上两三天,麦子就收完了。割麦这几天,母亲起得特别早,天快亮时一大锅红豆麦仁就熬好了,凉上一会,温温的,喝起来正好。天刚亮,一碗碗红色的麦仁就摆到方方正正的石桌上,一盘盘柔软劲道、油光发亮,带着油辣子的面皮和一大盆什锦凉菜也摆上了桌,麦客们大嚼大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拿起镰刀草帽就出门了。
我们家每年都要叫四个麦客,抄着甘肃口音的麦客都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带着一把锋利的镰刀,走省过县,赶场割麦挣钱。这些麦客大都短小精悍,微黑的肤色,浓重的乡音,很有地域特征。他们干活十分利落,吃饭也特别快,特别多。在炎热的夏天里,劳动强度这么高,只有多吃才能补充体能的消耗。母亲说天热,中午就做浆水面,她用结籽的荠荠菜做出的浆水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再漂上干辣椒段、碎香芹,只看这炝好的浆水就很有食欲。
中午时分,大锅里下好的面条捞进炝好的浆水盆里,用筷子轻轻搅动,一阵热气散后,面条在浆水里根根分明,格外清爽光滑。一碗碗干面、浆水面和大馒头已经摆好了,麦客们洗把脸,坐到饭桌前,一手拿着大馒头,一手拿着筷子,从大碗里挑起一筷头面条,顺着碗边吱溜一吸,光滑的面条就进了嘴里,喉咙一鼓就咽了下去;咬上一口馒头,就着浓香的面皮和菜,品着食物的香味,很快就吃完了。每咬一口馒头,表面就凹下去一个深深的半圆形,他们吃的很快,一个馒头几口就吃完了,每人一顿能吃两三个馒头,两碗干面,两碗浆水面,还有面皮和菜,饭量惊人。吃完后他们就立起大拇指,用甘肃方言对母亲说饭好得很,好得很!
紧张的两三天一过,麦子就割完了,临走前结算工钱。早晨,父亲拿着钱站在院子那棵柿子树下,麦客们站了一圈,他们拿到谈好的价钱后往往还会再要一些,说给个路费。每每这时候,父亲就笑着说下苦出力的人不容易,行行行,于是就再给一些钱。临出门每人还要揣上两个大馒头,说路上吃,明年还来。麦客们整个夏天都是匆匆忙忙赶麦场,割一茬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从东到西,撵着太阳。等麦场赶完了,钱也挣得差不多了,就踏踏实实地回家,安心地歇息几天后自家的麦子也黄了,就又开始忙活了。
割好的麦子趁着天气好要在一两天内脱粒,晾晒,入包。这个环节往往是左邻右舍互助协作,大大提高了干活的效率。家门前的大麦场上,人们紧张而繁忙,运麦捆的运麦捆,脱粒的脱粒,扫壳的扫壳,挑麦草的挑麦草,等到麦捆都没了,麦场上空了,麦子就脱完了。金色的麦粒在麦场上堆着,高高凸起,像一个小山丘,这时父亲就说都进屋喝水吧,我抽锅烟。父亲喜欢抽旱烟,说纸烟劲太小,抽了和没抽一样,耽误工夫。抽完一锅烟,父亲就心满意足的自言自语:这回不怕了,下雨也不怕了。
午饭后,帮忙的人就都回去了,我们一家人就忙着晒麦子。金黄的麦丘在大而平的刮板推动下向周围慢慢散开,麦子越来越薄,直到单个平铺只有一层,薄薄的能看出地面,这样麦子晒一半天就干了。
傍晚时分,夕阳映红,一片火烧云不断升腾,父亲就说明天还是好天气,麦子收到麦包里就放心了。夕阳慢慢落下,树梢动了,凉风慢慢来了。母亲撑着口袋,抓住袋口两边向外一翻,向下一卷,袋口就大大的张开了,父亲用木掀挫着麦子倒进口袋里。这种细而长的粗线口袋是专门装麦子用的,装满麦子后把它立起来,就像站着的一个人。一二起,随着一声喊,母亲托着麦袋底部,父亲右手紧抓着袋口,左手托着中间,向上一抡,口袋就稳稳地扛到了父亲肩上。他扛着麦袋走进大门,走到麦包前,身子向侧面一倾,松开袋口,金黄的麦子就唰啦一声倒进麦包里。随着一袋袋麦子的倒入,麦包里的麦子就高起来,形成一个圆锥形,金灿灿的,像座金山,真是喜人!
金黄的麦粒全倒进了麦包里,麦场上只剩下一大堆麦草。白而亮的麦草被谷叉一坨一坨挑起,摞在麦场的东南角上,随着一堆堆麦草逐渐减少,一个像横断山脉一样高大而厚实的麦草垛子就摞起来了,稳稳的,坚定地立在麦场一角,一年的柴火也就有了,做饭烧炕喂牲口都够用了。
家家户户收完麦子,村子里就要走亲戚唱大戏了,趁着这个时候也能安心欢心地走亲访友,休整歇息了。
是这个吗??
花非花
作为一朵花,它的使命大抵是以其美艳娱人眼目,以其清芬醒人。于是被人欣赏,被人馈赠,赢得赞誉与喜悦。也有命运乖戾的,让人摘下后把玩一下即弃之,或者只是寂寞地开……它们的意义,或在于被摘时摘花人的心情,或在于被馈赠时,赠花人与被赠者的是否投契,或者在它盛开与凋谢时,是在一个什么人的眼里,引起怎样的叹息。
始于花,而终于花,作为花本身来说,这些花的生命是短暂而且纯粹的。
有些花则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命途一波三折,演绎成一种是花又非花的美丽。和那些花在一起,我知道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棉 花
十月的天空有着透明的蔚蓝,太阳明晃晃的,银针一般射下来,棉花正静静地仰起脸,将那光与热一点点地吸到自己的骨髓里,然后在今后的生涯里一点点地释放出来。
我站在棉花地里,身前身后无边的森林般的棉花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柔软的,洁白的,蓬松的,与我捉迷藏。
我喜欢“棉”这个字,带着草本的芳香与柔软,又是朴素而温婉的。它的后面,是温暖、包容,像母亲的胸怀。
一朵棉花,是一种果,也是一种因。
在它之前,是农人的耕耘、点种、间苗、修枝打叶、施肥、洒药,然后开出黄的白的红的花儿来,结出小小的桃。最后,有一天,当枝叶献出一切营养而变黄变黑时,棉花们吸取了足够的阳光与泥土的滋润,吐出一腔的锦绣来,洁白的,在阳光下有着银子的光泽。
在它之后,是被从坚硬的棉桃中剥出来,晾晒,然后轧成云片般的皮棉,再擀成棉条,在纺车嗡嗡的旋转与纺织女双手的高扬低俯之间,悠出一条细细长长的棉线,长得像无尽的岁月,像母亲的血脉,然后再染上五彩的颜色,然后在倒在不同的纺锭上。(我喜欢这个倒字,它让这些棉线具有了水一样的质地。)最后在梭子的穿插与经纬的交替中,织出不同的花布来,再被做成床单、被面、女儿的嫁妆、一家人的四季衣裳。
在我童年的双眸里,没有比这些更能吸引我的了。我看着姑姑、母亲、奶奶她们的身影在纺车上忙碌,这让我懂得,棉花是与女人们最亲近的一种植物。
只是,在工业化生产巨大的吞吐量面前,这种手工的纺纱织布成了一项正在渐渐失传的技艺,那最后一个纺锤,不知遗落在了陈年老宅的某一个角落时,满是灰尘,终将被不识它的真面目的后人遗弃。
行走在都市五彩缤纷的女人中间,我的目光掠过她们身上那些细致而鲜艳的衣裳,我的心里却在回想,那一段老去的时光里每一朵棉花的形象。
那些生生不息的花朵,仍然寂廖地开在乡间。
黄花菜
以花入食似乎是一件高雅的事,而黄花菜又名金针花,简直就有富贵之誉了。
而它确实是极有营养的,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必须是在那些花们含苞待放的时刻摘下,此时,正当正午,八月的阳光似乎是带着重量,压迫着你的每一个毛孔与汗腺,压迫得你只想快快地将手头的事情做完,然后到田间地头的树荫下好好地喘一口气。
并不是每一个采花的人都如陶然公那般有着诗意与浪漫的。
最关键的是,此时,你手下那些待摘的花儿,那些黄金的簪儿一般的花儿正在它们的豆寇年华,来不及盛放便被摘下,让你不由得为它惋惜。
但是,谁让它注定了是一种要被做成菜的花呢?在这之后,迎接它的还有水煮汽蒸,简单粗糙一点的,就用硫磺熏,不过那样做出来的菜虽然色泽很好,但味道不佳,可见凡事都得细致对待。在这酷刑之下,它们便萎缩了,在香消玉陨之后,又被放在烈日下曝晒。几番折腾之下,它们已面目全非,干瘪就如一根稻草或者是一根细细的枯枝,绝对没有人会想到它曾经是一种花,盛开时宛如百合般美艳娇娆。
只是,来不及。
所以,我常常以一种怜惜的心情想:如果我不摘下这些花,让它们在黄昏时分按它们本来的样子怒放,那将是多么美妙的情景。
但这不过是想想而已。我是一个农人,我也有我的本份。我在以我自己的逻辑想:也许就在我摘下它的时候,我正是在成全它的命运。
究竟怎样才是它的命运呢?是作为一朵花尽情地开放,还是作为一盘菜快人口腹,给人营养?
也许,只能这样,让它在不能做花的遗憾里做一道菜吧,那遗憾也是一种调味品。
至于那怒放的花的形象,让我在不做农人做诗人的时候怀想。
菊 花
仅仅喝过一杯菊花茶是不够的,我想知道这杯茶的前世今生。
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在家乡的小河过,无边的菊花开得汪洋恣肆,每一根枝条都缀满了密密匝匝的花朵,我坐在它们的中间。
第一步,我要摘下它们,在它开得极美极艳的时候。采花是辛苦的,但经过了记忆的过滤,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全是那些花的美与芬芳。何况有比我们更辛苦的呢。那些小蜜蜂,它们飞来飞去,在花蕊里深深地钻进去,我们看不见呀,一不小心就将它随着花一起捋在了手里。有凶猛的就用它尾上的毒刺蜇我的手,我便去找正在哺乳期的大妈大嫂,她们一边安慰我,一边将自己洁白的乳汁挤出涂在我的伤口上,以它的清凉化解毒刺的瘙痒与疼痛。因为这个记忆,每饮菊花茶,总觉得在它的清香之外还有一丝乳汁的甜润。
我喜欢找那种重瓣的菊花,因为它们稀罕而且美丽,我可以将它扎在辫梢,也可以扎一大束,放在自己家的花瓶里。现在的菊花茶多是这种重瓣菊,不过当年我家乡所种的多是那种单瓣的菊花,据说它是药菊,比重瓣菊更好。
成筐成筐的菊花被这样采摘回来,它们被放在蒸笼里蒸,发出一种扑鼻的香味来,稍带药味,沁人肺腑,让人清醒。
然后这些花像黄花菜那样被晒干、收藏。这就成了菊花茶。
用一注滚烫的开水冲下,那些看似枯涩、扭曲、支离破碎的花们,竟如还魂一般复归它往日的样子,一朵朵那么的饱满,那么鲜润,在微黄而又透明的水中漾着,像记忆在它自己的氛围里——忧伤总是比喜悦更持久而芬芳。
其实,何必忧伤?
作为一朵菊花,有比做一朵茶菊更好的吗?在适当的时候被摘下,历炼之后,被收藏,被珍惜,在适当的时候,为适当的人重新吐露出一次芬芳。
由眼睛到身体到心灵。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