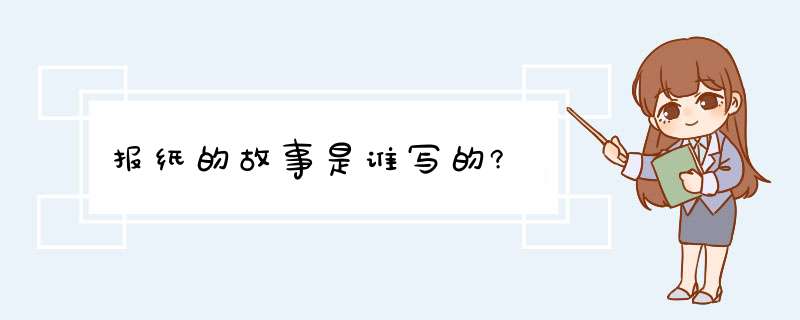
作者孙犁。
孙犁(191346-2002711)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共党员,抗日老战士,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座落在河北省安新县“华北明珠——白洋淀”畔。与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原文:
报纸的故事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刊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她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含情脉脉指饱含温情,默默地用眼神表达自己的感情。常用以形容少女面对意中人稍带娇羞但又无限关切的表情。
含情脉脉是一个成语,读音是hán qíng mò mò。
用法:补充式;作定语、状语;形容用眼神传递情意。
出处:唐·李德裕《二芳丛赋》:“一则含情脉脉,如有思而不得,类西施之容冶。”
翻译:一是饱含温情,默默地用眼神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有思而不得,像西施的容貌美艳。
扩展资料:
近义词:
1、脉脉含情:一个成语,读音是mò mò hán qíng,形容用眼神或行动默然地表达情意。
出处: 明·刘基《尉迟杯·水仙花》:“空将泪滴珠玑,脉脉含情无语。”
翻译:空将眼泪滴珍珠,眼神默然地表达情意无语。
2、温情脉脉:拼音wēn qíng mò mò,汉语成语,形容温柔的感情默默流露。
出处:宋·辛弃疾《摸鱼儿》词:“千金曾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翻译:千金曾买下司马相如的赋,这款款深情又向谁倾诉。
—含情脉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的创作成绩非凡,呈现出全方位开放的状态,散文出版物和写作的商品化,更是加速了散文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而且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生了相当巨大的文化转型,这一转型必然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当然包括散文创作,在文学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中,散文在边缘处的定位,保证了散文这一文体的从容发展;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与立场的分流,使散文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市场经济不仅使散文的创作与出版带有商业性,而且确认了市民阶层的合法性并因此使部分散文成为消费品;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散文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于是散文随着其他文体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审美时代。1992年,当《文化苦旅》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刊出后,文化散文开始在中国亮相,而“文化散文”作为一个概念,是佘树森在《九0散文谈》中提出的,这大概是最早对“文化散文”的理论描述。随后便涌现出更多的概念,比如“女性散文”、“学者散文”、“校园散文”、“大散文”、“新散文”、“后散文”、等等,可谓旗帜林立,特色迥异;随后刘亮程的出现,简直是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对于他的评价,无论是散文界,还是学界简直对他好评如潮,更有林贤治更是评价他是“二十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家”;之后格致的出现也成为散文界的一个亮点,张守仁先生曾评价格致说:“格致的出现无疑是新散文领域的一个事件。”“我等待了十多年,终于等来了打通文体界限的佳作。”1998年初,云南的《大家》杂志以开设“新散文”专栏的形式推出了一批散文作品。这批散文的作者包括张锐锋、庞培、于坚、钟鸣、陈东东、朱朱、周晓枫、杜丽、王小妮、海男等,他们的创作充满生命的激情和个性化的特色,在其中,他们试图将自己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并突破诗与散文的文体界限,进行一种将诗与散文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实验。
以上的散文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使得当下散文的创作,在感觉、形态等各个方面得以多维度地展开,进而达到一种诗性与智性完美结合的境界。他们的创作实践既是当下社会各个生活层面的折射,又是现代生活的消费品;既是一种群体行为,也是个体生命知性、智性的表述;它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立体的内涵。
而且随着诸多散文旧作的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的编选,散文刊物的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随笔”、“小品”专栏的开辟,使散文创作主体呈现一种变化与扩大的趋势,于是“散文热”在90年代成为诸多文学现象中的一个醒目而主要的现象,其中包括以汪曾祺、张中行、谷林、桂苓、止庵为代表的性灵小品散文的写作;以余秋雨、李存葆、周涛、鲍鹏山、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乐黛云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韩小蕙、赵玫、翟永明、铁凝、残雪、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张燕玲、唐敏、叶梦、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残雪、虹影、孟晖、赵园、潘向黎、楚楚、路也等为主要阵容的女性写作;以杨永康、朱千华、韩青、雷平阳、盛慧、谢宗玉、周蓬桦、马力、马叙、杨献平、黄海、习习、阿贝尔、淡舟、右额天心、蒋蓝、玄武、雪松、高维生、李汉荣、张生全、傅菲、陈洪金、宋晓杰、周闻道、李傻傻、汗漫、柳宗宣、季栋梁、齐明达等为主的“新散文”写作,还有以詹克明、朱以撒为代表的非散文领域作家的创作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选择散文这一文体来表情达意,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90年代散文家“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看到了这些散文作家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这些作家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而是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散文新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改变,使得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进而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这符合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的规律,而且中国90年代社会思想活跃、丰富,它一改80年代思想改革与保守,开放与二元对立模式,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个人化的趋势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社会因素对于作家的影响,使90年代的散文创作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的创作,或者富有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婉转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内心的倾诉,或注重文体的创造与革新,甚至是一些大众消费的散文也应运而生。因此散文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其中,老一代的博大、中年一代的厚重、年轻一代的锐利,使当下散文创作呈现着三代同堂的繁荣局面。他们为我们散文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意的启示。就如同吴秉杰在《散文时代——读当前散文作品随感》所写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散文的时代。散文写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前所无可比拟的。”
传媒中的情感倾诉是指普通人以匿名或真名通过传媒来讲述的有关个人或家庭的情感、生活经历。这类栏目最初出现在电台晚间的情感倾诉热线中,近几年来,许多报纸也开办了百姓倾诉专栏,刊登老百姓讲述的自己的情感生活故事。例如,在传媒竞争激烈的武汉,几乎所有的市民报,绝大部分调频电台都开办了这样的栏目,许多媒体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作为品牌来打造。而普通的读者、听众对这样的栏目反应都非常积极,他们或对其他人讲述的个人经历发表意见,进行热烈的讨论,或是参与其中,讲述自己的故事。传媒中情感倾诉热的出现,说明此类节目具备巨大的吸引力,那么这一吸引力是如何产生的,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人们去注视它,促使人们大胆地去参与其中呢?
既然是个人的情感倾诉,其中必然大量涉及到个人的情感隐私,或痛苦的人生经历,通常,这些内容是个人不愿对人讲述,也不愿让人知道的,大众传媒也不敢随便侵入个人的这一领域。因此,这类节目要成功开办,除了要引起了普通受众的兴趣之外,还必须吸引了倾诉者的大胆参与,本文将从视听者与倾诉者两个方面来讨论其吸引力之源。
一
从视听者或受众的角度来看,情感倾诉类栏目一方面满足了他们了解他人隐私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通人对传媒人性化、平民化的要求以及对人间真情的渴求。
日本社会学家籐竹晓认为,社会大众都有一种"窥*癖"心理,即有一种窥视、了解他人隐私的欲望,而窥视行为是一种未被社会认可的行为,"但是,在了解人们怀有的窥视心理以及接近信息的幌子下,大众传媒拥有了社会认可的机制……"(籐竹晓,第97页)。他的这一见解比较刻薄,但却向我们点明了传媒为什么会报道隐私,以及受众为什么会欢迎这类节目的原因。今天,中国传媒中此类节目的出现,虽然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却也不能脱离这一因素的影响。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一种了解他人隐私的心理,但出于社会的压力,我们并不敢公开窥视他人的隐私,也无多少窥视他人隐私的机会。而大众传媒却为我们窥视他人的隐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对名人隐私的报道一直是大众传媒的经久不衰的热点之一,许多媒体通过炒作明星们的个人私生活,或刊登政治家的情感丑闻,来引起受众的兴趣,满足受众的窥视欲望。通过了解这些名人们的隐私,我们"每天都可以窥视到英雄和当权者的弱点,……会不断产生大家都平等的感觉"(籐竹晓,第87页),即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但是传媒必须为大众也是为自身侵入个人隐私领域提供有力的借口,即"保证视听者知情权这一正当理由",正是这一借口要求公众人物应该能容忍传媒的报道,接受大众的监督。虽然许多媒体对名人个人生活的报道,常常超过一定的限度,也常常由此引起官司,但这种报道却从未中断过,大众对此类报道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我们看来,情感倾诉类栏目实际上是经过大众传媒包装后的另一种个人隐私形式,而大众对情感倾诉类栏目的关注,也正体现了其窥视他人隐私的心理需求。
不过,长期以来,传媒对普通个人的隐私,或是出于新闻价值的考虑,或是出于隐私保护法的限制,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乏介入的正当理由。但是在今天,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出于对炒作明星的厌烦,对传媒精英化的反对,普通民众对传媒人性化、平民化的需求日益上升,社会大众越来越关心自身的生活状况,关心与自己一样的其他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只有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其生活经历才更现实,更接近于自己,值得自己去借鉴回味。而大众传媒中情感倾诉类栏目,正好为大众了解其他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并且视听者所了解的,不是一种表面的东西,而是平常时刻许多倾诉者深埋心里,不被他人了解的真实情感。对于视听者来说,不但可以在了解他人的私密中获得一种窥视之后的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他人喜怒哀乐的真情倾诉中,获得某种人生启迪或情感身份上的认同。因此这种了解也是一种情感心灵的碰撞与交汇。许多情感倾诉类栏目,正是以"真情"二字作为其栏目宗旨来吸引视听者的,以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来触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共鸣。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