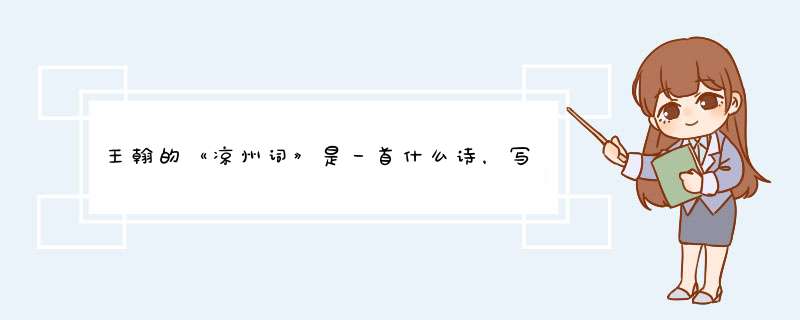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地荒寒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征戍生活,使得边塞将士很难得到一次欢聚的酒宴。有幸遇到那么一次,那激昂兴奋的情绪,那开怀痛饮、一醉方休的场面,是不难想象的。这首诗正是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写照。诗中的酒,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杯,相传是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有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乐器则是胡人用的琵琶;还有“沙场”、“征战”等等词语。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浓郁的边地色彩和军营生活的风味。 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第二句开头的“欲饮”二字,渲染出这美酒佳肴盛宴的不凡的诱人魅力,表现出将士们那种豪爽开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时,乐队奏起了琵琶,酒宴开始了,那急促欢快的旋律,象是在催促将士们举杯痛饮,使已经热烈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这句诗改变了七字句习用的音节,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强了它的感染力。这里的“催字”,有人说是催出发,和下文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三、四句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这话对我们颇有启发。为什么“作悲伤语读便浅”呢?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吧: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不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吗?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给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千百年来,这首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王之涣的《凉州词》表达了守边将士忠勇爱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
《凉州词》赏析
这是一首边塞诗。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气势雄伟,浩浩荡荡,一泻万丈,远远望去,黄河好像由天上流来。黄河、白云形成鲜明对比,塞外的空旷让诗人眼界非常开阔。然而眼前的城堡,却是那么凄凉。城堡夹在高山之中,更显得孤单冷清。
山谷中,羌笛吹奏的送别曲《杨柳枝》在回荡,笛声充满了幽怨之情,那熟悉的旋律时,诗人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你们何必借《杨柳枝》来抒发满腔的幽怨呢?原来春风是吹不到玉门关的。由景及情,抒发了守卫边疆的将士们凄怨而又悲壮的情感。
读完诗,一幅西北边疆壮美风光的画卷展现眼前,诗中隐隐流露出将士们幽幽的哀怨悲叹。达到情中有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出塞》、《凉州词》都是边塞诗,描写了壮阔苍凉的边塞景物,抒发了守卫边疆的将士们凄怨而又悲壮的情感。诗的首句写自下而上对黄河的远眺,次句写边塞环境的险恶,两句合在一起,用大笔写意的手法,渲染刻画了边塞风光的雄奇苍凉和边防战士们生活环境的艰苦恶劣。后两句笔锋一转,引入羌笛之声。折杨柳送别本是唐人风习,羌笛吹奏的《折杨柳》曲词更能引起思乡的离愁。可如今在这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想要折一枝杨柳聊寄别情也不可能,这怎能不让人更感悲伤。全诗表现了盛唐诗人悲凉慷慨的精神风貌。
简单一点:双关手法吧。前两句都是写景,后两句抒情
艾青诗选(吹号者)赏析
《吹号者》的作宅在这首诗里他为我们在中国历史的广场上塑立了一个吹号者和浸濡着血迹的铜号的形象,让我们在今天仍然能清晰地听到那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并激励这个民族奋勇前进的号声。吹号者是被黎明最早惊醒的人。天还是一片黝黑,他就把黎明的声音与光明一起吹送到宁静的远方:“他最先醒来——/他醒来显得如此突兀/每天都好像被惊醒似的,/是的,他是被惊醒的,/惊醒他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这是第一章开头的七行诗,诗人把“惊醒”这个词语重复了三次,加深了我们对“最先醒来”的吹号者被远方传来的黎明的滚动声所惊醒的印象。但其实惊醒他的并不是天边滚来的声音,而是他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他意识到自己是黎明的通知者。因此,他起身立即拿起号角。上面摘引的七行诗,朗读时三个不断加强音量和感情重量的“惊醒”形成一浪高一浪的节奏。起伏而回旋的号声是从号管里带着深情弯弯曲曲流出来的,并且带着吹号者被惊醒时的震动感。我以为这震动感正是作者创作这首诗时在心灵上引起的对黎明充满预感的颤动。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深刻地领会到一首诗的语言和节奏是怎样生成的。作者在卷首的小引里�3S邢傅娇床患难浚孀藕派沙隼础岛耪叩牧吵3J遣曰频摹U饩皇强湔胖省N掖岛挪坏揭荒辏屠鄣没剂朔尾。谝黄恼吕铮以匾涞秸舛尉D敲次业暮派镆惨欢ㄓ凶叛俊R虼说蔽叶痢洞岛耪摺返恼饧感幸保睦锓浅D咽堋N椅裁炊缘诙诟惺芴乇鹕钅兀空馐怯捎谡庖唤谑锎岛耪叩某绺叩母星樯钌罡卸宋遥骸八家栽案那逍碌暮粑�/吹送到号角里去,/——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使号角由于感激/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吹起了起身号,/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世界上的一切,/充溢着欢愉/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吹号者》不但使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还懂得了诗人都应当是向人世间通知黎明到来的吹号者。象号声一样,诗人写的每一行诗里,都有看不见的纤细的血丝,当时,我十分相信。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以及后来的《虎斑贝》等诗都夹带着来自诗人心灵的血丝。艾青是一个不惜付出生命的吹号者。诗的第五节使这首诗的悲壮的情感升华到了圣洁的境界。诗人以淳厚的笔触为吹号者的牺牲写下一曲高昂的哀歌。吹号者死得壮丽无比,直到“被一颗旋转他的心胸的打中了”才寂然地倒下,然而号声并没有中止。最后两段诗使吹号者和映着血和阳光的号角得到了永生。“听哪,那号角好像依然在响……”首先,这首诗真正体现出一种生命感和生命形态。诗的“小引”就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了吹号者和号角、号声以及广阔的原野,血肉地成为这首诗不可分隔的艺术生命的整体。如果没有面孔苍黄的吹号者发自心胸深处的呼吸和细微的血丝,号声不仅不存在,更不可能飞向远方去激励千千万万个战士。前面摘引的第二节诗生动地体现出这个完美的精神境界。我们常说一首诗写活了,说的就是诗中写活了一个艺术生命。《吹号者》从开始到结尾都充溢着强大的回荡不绝的:这正是吹号者和号声所具备的生命特征。其次,《吹号者》使我们加深了对艾青艺术个性的了解,它是朴素的,自自然然的,不露痕迹的。个性蕴含在诗的整体情境里,而不是在表面的词句里,是修辞学无法达到的。第三,对艾青的口语和节奏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没有丰富的,就生不了诗的节奏,而口语是最富于人性的亲切感的,是直接从心灵里流出的脉息。第四,艾青的诗都是心灵的自白。没有纯客观的抽象,都是有真情实感的,即使是晚年写的哲理性小诗,也是他的人生体验的结晶,带有诗人的某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的哀伤、痛苦和期望,以及诗人与现实人生的联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