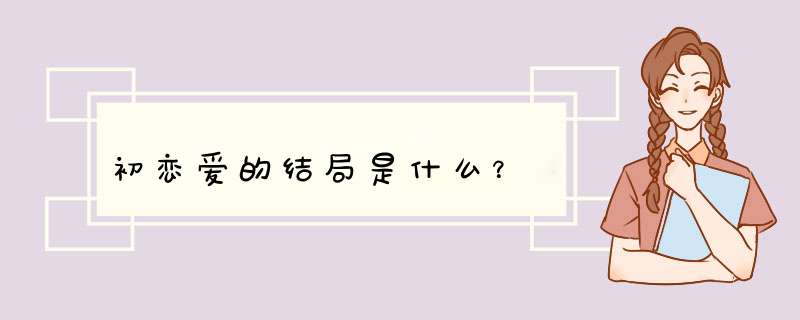
温静找齐了杂志,江桂明本来想向温静求婚最后两人发现孟帆的初恋是温静,两个人过不去坎又分开了,苏苏结婚了最后温静去孟帆遇难的地方,终于想起了第一次与孟帆见面的情景,番外是江桂明打算在孟凡祭日那天去找温静,然后作者没写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是个悬念,晓兰在孟帆墓前与他告了别,开始了新的生活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汉书·艺文志》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
一
孔子的长相颇怪。“生而圩顶”,就是说,他天生的脑袋畸型,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司马贞说,其形状恰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不知命相学家是如何解释的。这种头顶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阳光?孔子自学而成大才,其天赋必然很高。而其身长亦不凡,“九尺有六寸”,这在那时可以说是“硕人”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人人都说他是长人,感到惊异。真正的一个齐鲁大汉。不过,这个“长人”的身影也确实够长了——长到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个民族都—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干多年了,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漫漫的阴影呢
据司马迁和《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后代。那个有名的“仁义之师”的统帅宋襄公,便是他的十一世祖——难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样泥古不化,自讨苦吃。用古老的仁义道德去对付现世的流氓强盗,这也是他家族的祖传秘诀吧,只可惜常常不灵。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再属王族,姓也成了“孔”。后来孔父嘉又为人所逼而奔鲁。所以孔子确实是一位“没落贵族”。到他父亲叔梁纥,便是连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连生九女,—妾生子叫孟皮,却又是个跛子。年近七十的叔梁纥大概非常绝望了。但他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于是便向颜氏求婚,颜氏少女颜征“从父命”而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纥。所以,司马迁说这是“野合”,“野”与“礼”相对,夫妻双方年龄差别太大,不合周礼,所以这婚姻不是“礼合”,而是“野合”。“野合而生孔子”——这实在太有意味了,为什么呢?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礼坏乐崩”而头疼,而愤怒,而奔走呼号,要人们“克己复礼”,孰料他本人即是个不合礼的产儿呢。如果他的那位老父亲真的克制自己来恢复周礼,可就没有孔子了。真玄哪。要知道,这不合“礼”的产儿,竟是他们这古老家族之链上最辉煌的一环,也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物啊!
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贽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探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九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刮。
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孔子死后,鲁哀公装模作样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写了一篇诔文,似乎感伤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让我一人在鲁国孤零零的,唉,多么悲痛。”孔子的弟子子贡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其实,对孔子“生不能用”的,岂止—位鲁哀公呢?孔子一生见过不少诸侯,像楚昭王,齐景公,卫灵公……等等,有谁用他呢?天下人事纷纷扬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且是万古不变的尺子,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到处招人惹人,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同时他又像一个蹩脚的推销员,推销过时的、早已更新换代的产品。这产品不是按顾客的需求而设计,而是要以这产品的规格来设计顾客,正如韩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据脚的大小来选鞋,而是根据鞋的大小来“削足”。他这么不合时宜,被人拒绝不是很正常的么?子贡以他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天才,到处为老师打点鼓吹,也没有什么效果。子贡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责备鲁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
二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更是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一条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这个细高个冷冷的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恓恓惶惶的马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后的昏君而去寻找前面的明君。什么是“避世”?在“避人”的基础上再跨一步,彻底冷了心,闭了眼,认定天下不可能有什么诸侯还能与他一起改变这世界,于是彻底绝望;从而彻底不抱希望,回到田园中去,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告别都市、政治与熙熙攘攘的外部世界,就叫避世。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他恓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仲由了吧!)
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则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二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更是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一条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这个细高个冷冷的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
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是比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 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是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有起码的价值关怀吗?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些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这种人是难以让人生出敬意的。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三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话》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
“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这个顶重要了。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 ”,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丝—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
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既然他已经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艰苦,如此卓绝,如此寂寞,又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失败,又如此辉煌灿烂。因失败而辉煌,我以为这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而且必须是主人公已经预知的失败。他已经预先知道结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无法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剧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
孔子的“得其真传”的弟子曾参,有一段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无法不为这句话而感动,虽然我已经被那些最靠近话筒,因而最有发言权的某些人的这个“后”那个“后后”,还有什么“解构”,解构得没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译成问答句:士为什么要弘大坚定?因为他们任重道远。为什么说他们任重?因为他们是把仁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的;又为什么道远?因为他们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这副担子。这就是自讨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说,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不能因为你读了不少书,甚至读了不少洋文书,知道各种主义,就能受人尊敬。你还得有所承担。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那么—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无法摆脱的宿命了,就已经知道执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献媚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了,他们怎能不伟大,又怎能不为这伟大而颠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肠的隐士讽刺孔子,还有些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这位“丈人”对孔子的批评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
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一段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来成为不少人批评孔子的口实。是的,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厚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较易发生,并且较易引来阵阵喝彩。甚至人们还能这样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你连一个农夫都比不上。这种说法会引来更多的喝彩,因为很多人一下子从孔子的缺点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说,这种批评的荒谬性太明显了。在春秋后期,我们缺少一位农夫吗?减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农夫,我们就是这样算账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会因此更加辉煌灿烂吗?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就会更加文明吗?
另外,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连养活一位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经济能力都没有,还必须让他自己去耕种自存吗?或者,我们这个民族连给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农夫一样才心满意足吗?这些问法可以换成现代式的:我们必须分给陈景润一块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种,收获,磨粉,蒸馒头,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边求证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证出了1+2,由于他不会蒸馒头,于是我们就可以鄙夷他连一个馒头师傅都不如吗?我的这种问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这么干过。否则,要办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迟问稼问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骂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现在的某些大学教材上就有这种说法。这种批评也太师心自用了。问如何种菜种小麦,需要问孔子吗?孔子的回答:“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樊迟要学这些,你何必到我这儿来?你去问老农即是。要学腌泡菜蒸馒头切土豆丝,需要去中科院生问博士生导师吗?
以上的问题还在于,培养一个老农易,至少在孔子那时,还不提倡科学种田时是这样。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农业技术学校,但遍地是老农在种麦子种大头菜。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了。孔子的时代,传播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似乎比自己去亲自参加劳动更迫切。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行,与轻视体力劳动如何扯得上。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来耘去,也就那一亩二分地,所养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及家人。这又如何能与孔子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传留后世,还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养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孔子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农思想满脑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评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对孔子的批评,让我联想到今天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他们莫名其妙的对于鲁迅的优胜感。鲁迅的某些缺点确实让某些人孱弱的心性得到一种自信的证明。但他们对于鲁迅的批评,恰像旧时代老爷家中感觉很幸福从而很温柔的小妾,对现代独身女性的批评;又好比是青铜时代贵族几案上的玲珑的酒器或床底下温静的溺器,对铁器时代绿林好汉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我对古代的隐士评价不高。相应的,我对现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们也心存怀疑。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这几年“告别鲁迅”而麋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了比别人好—些的地位、财富、机会,使他能上大学读书,能明理,他理应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有所补偿。按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数和报考数,有一个上大学的,就必至少有一个或更多上不了大学的。这种回报与补偿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使这个社会有所进步,人们的幸福能有所增进。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应该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把这种知识当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周作人是把他的学识当小妾,只让她陪自己喝茶谈玄。而如果把知识当作取媚权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掩盖自己的智慧,就是对社会的背叛;隐匿自己的发现,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当然,这种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摘自鲍鹏山《天纵圣贤》
答:结局写的很含蓄。
最终收集了杂志发现,其实那个男生暗恋的不是苏苏,而是温静。杜晓峰没有再提,苏苏结婚了,温静和江明桂之间似乎还有发展。初恋爱故事结局是温静找齐了杂志,江桂明本来想向温静求婚最后两人发现孟帆的初恋是温静,两个人过不去坎于是又分开了,苏苏结婚了,最后温静去孟帆遇难的地方,终于想起了第一次与孟帆见面的情景,番外里江桂明打算在孟凡祭日那天去找温静,但作者没写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是个悬念,晓兰在孟帆墓前与他告了别,开始了新的生活。
故事主要讲述了温静(祝绪丹饰)与前男友杜晓风(徐子力饰)结束了7年的恋爱,在聚会上尴尬的面对着不知情的老同学,好友苏苏(黄一琳饰)怕她出事,始终陪在她身边。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迟到的班长带来一个坏消息——一直未出现的同学孟帆(李东阳饰),已在几天前去世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