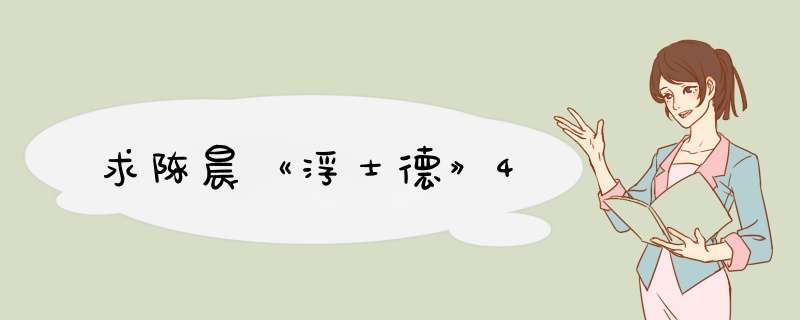
浮世德(四) 陈晨 1
下午5点半,无论教室还是办公室,都是最空旷的时候;相反,食堂就人满为患了。
冬日最后的阳光比任何季节都要来的慵散。天空像是被物理过滤镜过滤了一样,由暗黄变为深红,最后变成一抹泛出黑点的深蓝。世界被光线和阴影分为两半,他们之间没有空隙,黑夜鱼白昼也往往只在一念之差间。世界渐渐被时间冲刷的失去了纹路,我们的痛苦在光滑的外壳上显得清晰无比。 从教学楼往上看,六楼的数学办公室没有亮灯。
山岚站在办公室的窗台前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发呆。
就在大约一个小时前,年级主任满脸笑容到办公室里对新来任教的山岚嘘寒问暖。这本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年级主任随口的一句“校长明确说了要多关照你一下”却让气氛在瞬间变得尴尬和凝重起来。同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吴梅,也被分配到这所重点高中,可她的身份却是“实习助教”。这意味着她只能那助教的工资。而山岚同样是师范刚毕业的学生,身份却是正式的数学教师。
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说,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吴梅更是对山岚冷言冷语,就连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隐隐约约地冷落着山岚。 季岸拿着上午没有交的作业本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他摸索着打开了开关,日光灯啪啦啪啦的跳出白光来。 他猛地发现床边站着一个人,被吓了一跳。
“小山老师?我来交作业本”不过语气依旧冰冷而且平静。
“是……季岸同学?”山岚抬了抬眼镜。
“嗯。”身材挺拔的少年缓缓走到山岚的办公桌前,把作业本轻轻的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转身离开。所有的动作都像温水一样,温和自然。“季岸同学……你等一下!”山岚走上前。
少年在漆黑的走廊上停住了,他的眼睛如星辰般闪亮,像一片透明的湖泊,但又感觉深的可怕。刘海窸窸窣窣的遮盖着浓黑的眉毛,像是异域少年,脸的轮廓被白光镀了一层银边,在黑暗中显得更棱角分明。然而事实却像爱丽丝的魔镜般幽深可怕,无数的荆棘和水藻潜伏在华丽表面之后。在你沦陷之时,含羞草会吸干你的血液,食人花朵会嚼烂你的骨骼。
“老师真的让你们那么讨厌吗?”山岚的眼睛有些湿润。
季岸冷漠的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真的很努力了,很努力得想上好没一堂课,想让你们喜欢我。你知道吗,我每天要到凌晨四点才能睡着,我好害怕,一想到要面对你们我就害怕,真的……”山岚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或许你真的不适合老师这个职业,不如趁早转行吧。”季岸漠然的说,然后把说手插在口袋里离开了。
山岚瘫坐在办公椅上。父母的决定让她这个有着重点大学分数的考生最终选择了师范。都身为大学教授的父母似乎安排好了一切,他的职业是父母规划的:先从中学做起,最终达到他们的位置和高度。
山岚皱了皱眉头,拿出教案继续研究了起来。然而这个城市的残酷就在于,没有人理会你努力了多少,你的努力只不过能换取点同情分而已。最终的成果才是唯一的检验标准。这个城市永远存在并命的努力却一直落后和失败的人,也存在着花很少的力气,甚至可以说是侥幸成功的人。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触摸象牙塔顶。
黑暗中,无数只手握着各式各样的剪刀,想去剪断这个城市的脐带。
鲜血四溅,残酷的最深处,有我们的影子。2
寒潮来临,城市突降了一场长达两天的大雨。所有的高楼都浸泡在旺盛的雨水里。惨淡的天空看不到任何星光。天与地混合成灰茫茫一片。
气温骤然间下降了十多度,天空寒冷地颤抖起来。
城市像一个巨大的伤口般在寒冷中发霉腐朽。又一个深冬来临了。
**中的少年们,你们在干什么。季岸冲办公室回来,发现教室里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池海翔,而是班里成绩最好的缪莹,全班最高傲的女生。
缪莹合上书本,冷冷地说了句:“你去了小山的办公室,是吗?”
季岸并没有答话,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教室后面的日光灯没有开。他在黑暗中摸索出CD机。
“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惹人厌吗?因为她能进这所学校,能当我们的老师,根本就是靠她姑父的关系,她的姑父就是校长。”缪莹并没有转过头。
她接着说:
“靠着别人的关系往上爬,还拼命和学生套近乎,真可悲。”
“每个人都厌烦她的做作,每个人的数学成绩都在下降,她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可耻吗?”
缪莹说完便合上书本,然后起身向教室门口走去。她的口气和她的眼神一样,有藐视一切的锐利和寒冷。
季岸摸索着打开开关。CD开始转动,蓝色的荧光指示灯在抽屉里忽闪起来。
他套上二季,然后趴在课桌上闭上了眼睛。
耳朵里,那个略显沙哑的隔声。那首山岛纪的《赫兹森林也不睡》。
突然,手机震动起来。翻开屏幕,是一个没有署名的号码。
上面的字眼肮脏得让视线模糊。3
十七层的西餐厅,坐在窗口,可以俯瞰大半个城市。
密密麻麻的高楼。密密麻麻的人影子。 山岚有些拘谨的用刀叉切着牛排,时不时抬起头。
对面坐着的男人,国字脸,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睛,身上穿着与他气质不相符的西装。
气氛有些沉闷。
“父亲应该已经说了我们俩的事了吧。”男人用手耸了耸眼镜。
“嗯。”山岚没有抬头,把一碟精致的蓝莓蛋糕移到面前,然后一口咬下去。
他突然皱起了眉头,停顿了两秒,然后从嘴巴里拿出一枚钻石戒指。
男人看到山岚看着手心里的戒指,上面残留着奶油。他突然激动起来,口齿有些模糊的说:“小岚,嫁给我吧,嫁给我!”
男人紧紧地攥着山岚的手,山岚有些本能的向后退缩着。
眼泪在眼眶里不住的打转。
——快哭出来吧。那些像**里被求婚的幸福女主角一样。
——只是刚才牙齿咬到戒指那一刹那的感觉,确实要痛的哭出来了。4
“COCO”里面最隐秘的舞池。清一色的雄性生物。
却可以看见比女人更加柔韧的腰在电光幻影中扭动,各式各样的香水杂糅成更具诱惑力的味道。
吧台的一边,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搂着少年的腰,脸还不时地靠近。
“七爷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少年皱着眉头,脸已经被酒精烧得通红。
“我知道你没醉,来,给爷儿笑个。”肆无忌惮的笑声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舞曲里。
少年摇摇晃晃地逃避者举在他面前的酒杯。
“来,乖,把爷儿我整舒服了就送你回家!”
“哈哈哈!”少年突然大笑起来,然后眯着醉醺醺的眼睛说,“家,快告诉我,家在哪里?我……在哪里?”
男人有些疑惑,有点好奇地问:“你爸妈呢?他们做什么的?”
“爸?妈?哪里有什么爸妈,都被我杀了!他们都是混账!都是贱人!像我一样贱……”酒精的作用下,少年的头痛得发涨,语气也含糊不清起来。
“没关系,把我服侍舒服了,我就当你爸。”
男人搂着少年,摇摇晃晃地朝里面的包厢走去。
情欲的味道比震耳的喧嚣更浓烈。5
凌晨3点半。
这个城市的气温降到了一天当中的最低点。
市中心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一大片,只是偶尔有夜航飞机在天空划出一道光痕。
中心公园里几乎没有人,只是偶尔有裹着围巾的夜班族快速经过。山岚坐在冰冷的石凳上,脸被寒风冻得通红。但她并没有离开,只是看着周围依旧亮着灯过的摩天大楼,依旧做了将近两个小时。
这样的境地和心境确实是适合哭泣的。
但酝酿了半天,还是没能掉下眼泪。
已是一个人害怕和绝望,是因为他总还有其他的选择,不过如今只有一条路摆在眼前,也就没有什么担心和恐惧的了。山岚没有后路。
其实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担心和怨言,因为父母都规划好了一切。三个月前,随同他的父母一起到家里来做客的男生,满口的“幸会幸会”和“实属荣幸”。这就是山岚的父母给她精挑细选的未婚夫,毕业于最高学府的中文专业。他们第一次约会,话题便是古汉语的演变史和欧洲比较文学。男生确实是正人君子,平常的聊天都像在演讲和辩论,学问像眼睛的度数一样深厚。
其实也想对父母说“自己对他根本没有感觉”,或者“我还不想结婚”、“能让我自己找男朋友吗?”。但是每一次开始这个话题,父母就开始对那个像字典般的男生赞不绝口,什么“他的父母都是留美博士”、“你们以后可以去美国发展”、“品性非常可靠”。没有理由去反驳,因为也确实如此。
已经二十六岁的山岚,从来没向父母反驳过。
学生时期老师眼中的乖乖女,父母心中说一不二的乖女儿。
直到毕业,通过父母的关系开始了教师的工作,还没算完全步入社会,却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排斥和漠视,甚至被自己的学生欺负。对于这一切,自己也只能默默忍受。或许是父母还没有告诉她解决这一切地方法。
或许,这些都是报应吧,把二十六年没有受到过的伤害和挫折全部爆发了出来。山岚叹了一口气,然后起身准备打车回家。身子已经有点坐麻了,起身的时候微微颤抖了一下,险些跌倒。
他走到马路边,车灯刺眼的让人眯起了眼睛。
车流来来往往,却没有一辆亮着“空车”的的士。
突然,感觉自己被人重重的撞了一下,本能的死死攥住包,人后惊慌的转过头。
是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少年,高大挺拔的身材,穿着白色的衬衣,皮带的LOGO银光闪闪,身上散发着浓重的酒气。少年微微抬起头,头发有些蓬乱,只是眼神依旧熟悉。
“季岸同学?!”山岚抓住少年的手臂。少年冷漠的转过了头。——不远处的工人体育场想一个巨大的涡旋,“COCO”的巨型灯管无比夺目闪耀。
——那时山岚从未接触过的、另一个世界的狂欢和哀愁。6
凌晨3点半。
凌晨4点半。
凌晨5点半,天空开始泛白,又一个灰蒙蒙的清晨。陈丽芬轻轻打开了纪澜的房门,看了看熟睡中的女儿。然后揉了揉红肿的眼睛,抓起钥匙便出了门。
清晨的马路上,车辆和人群都格外稀少。
画面因为清晨冰冷的空气而变得格外模糊。陈丽芬紧紧地攥着巨大的扫帚,沿着马路清扫着。
湿冷的风吹的陈丽芬直打哆嗦。她清扫着地上的落叶,突然,她感觉有东西在落叶堆里,她用扫帚扒开落叶,发现一只已经腐烂的死麻雀,眼珠发白,有蚂蚁从它的身体里钻进钻出,粉白的蛆虫满足的腐蚀着它的尸体。陈丽芬突然觉得一阵恶心,蹲在地上呕吐起来。而这是被雾气笼罩着的另一个角落。新街口市中心那一片狭窄拥挤的平房。涂在平房上的大红“拆”字格外惹眼。不知谁家在用劣质收音机播放《早间新闻》,主持人的声音时而变成嘈杂的电波,时而又恢复正常。水龙头缓慢的滴着水,堆放在门口的那一大堆废铁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冰霜。
其中的一间平房里还亮着昏黄的灯。
烟焰缓缓地睁开眼睛,模糊的实现一点点地变得清晰起来。
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妈妈还没有从医院里回来,大概是又守了爸爸一夜。猛然又想起昨天晚上在医院里发生的那些镜头。
医生冷漠的说要是再不续费就要让爸爸出院。可爸爸自从被撞以后,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怎么可能出院。一向嚣张气盛的妈妈苦苦向医生求情,而医生冷漠的语气似乎没有一点余地。烟焰看着几乎要给医生下跪的妈妈,努力控制才没有像医生挥出依旧攥得发麻的拳头。
最终,医生还是叹了口气,说了句“下个星期一定要把医药费结清了”便走了。语气里充满着不懈的同情。
从来没有看到妈妈这样沉默过。
她没有骂脏话,也没有要去厨房拿刀拼命的那般架势。
她用湿毛巾擦着爸爸的额头。
烟焰在她背后,听到了他哽咽的声音。
“五万块,到哪里去抢啊”滕汐在开着暖气的房间里缓缓醒来,她摸索着打开了手机。
然后在开机音乐中,掀开被子走下了床。突然,她捂着胸口艰难的蹲下身猛烈的咳嗽起来。
颤抖着摊开手,咳出的浓痰中有大量的粉红色泡沫。7
滕汐一整天都没来学校。班主任也没有说明原因。
一整天,纪澜都显得忧心忡忡,一道题也做不进去。从上学就一直等着滕汐的信息。中午的时候烟焰来找过纪澜一次,纪澜也只是潦草地说了几句“大概感冒在家休息”、“没什么大碍”之类的话,烟焰“嗯”了两声便放心得走了。而当烟焰站在教室门口的时候,纪澜明显感觉到了后面女生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存在那么一两个人,你会莫名的厌恶他,甚至是憎恨他。当他强大优秀的时候,你会嫉妒讨厌他;而当他脆弱的时候,你又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就是这样虚伪而又真实的“好朋友”的标签。
———而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应该称得上是“重要的人”吧。同样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山岚。
去上课的时候,山岚在教室门口停顿了好几秒钟,然后吸了一口气,走上了讲台。
始终不敢朝那个位子看,但即使这样,还是因为紧张尴尬而讲错了题。底下又是一片嘘声和摔笔声。然而作为上的那个少年始终是冷漠安静的,他依旧在课堂上冠冕堂皇的戴着耳机,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在凌晨冷风呼啸的马路上,穿着淡薄衬衣的季岸被冻得瑟瑟发抖。
山岚焦急地问他:“季岸同学,你家在哪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
季岸眯着眼睛,醉醺醺的问道:“你是谁?给我让开”
刚说完,便猛地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山岚在一旁急得直冒冷汗,看来季岸醉的不轻,自己根本没办法回家。情急之下,她拦下了出租车,把季岸接到自己家里。
回到家已将近凌晨4点,她将就着靠在沙发上挨到了天亮。而季岸酣睡在她的床上,勾着身子睡觉的姿态向胎盘中的婴儿。其实这一切没有什么不正常,也不必感到尴尬。在季岸醒来之后,他依然是丢下一句冰冷的“你很多事”便推门离开。
在凌晨的夜间出租车里。喝得烂醉的他在不经意间靠在了山岚的肩上。突然,他紧紧抱住了山岚的腰。山岚惊慌地想去挣脱开季岸的手,去听到他低声的呢囔。她缓缓侧过头。车窗外,不知道是下起了雨还是雪,一滴一滴的冰冷液体拍打在车窗上。城市的气温在一股强劲寒流的冲袭下,有下降了好几度。8
确实是冷了。当烟焰战战兢兢地从道馆里走出来,猛地一阵寒风,身体剧烈的打了一个寒颤。他强忍着腿部得灼烧感,艰难的走到了公交车的站牌下。
然而在高楼里的道馆,林森在关灯之后,慢慢蹲下身,坐在了地板上。
空荡荡的训练房里,温热潮湿的暖气让毛细血管渐渐舒张开来。林森在黑暗中沉默不语。
脑中仍然浮现着刚才的那一幕。
眼神倔强的少年语气却充满着哀求:“请教练一定要给我这次机会,摆脱了!”
林森暗暗咬着嘴唇不说话。
穿着白色道服的少年猛地跪在木地板上,骨骼与地板碰撞的声音像抽着林森的心脏般让他感觉心痛。
“我一定会赢一定会”一个镜头渐渐暗了下去。
熄灭了一半灯光的道馆。
穿着道服低着头跪在地板上的少年。
林森沉默的表情和眼睛里灼热的泪光。
画面充斥着无数密密麻麻的白色线条。———我也相信你一定会赢。
———只是烟焰,你迟早会因为你的义无反顾而付出代价。9
在那个路口,纪澜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选择沿着湖山路一直走下去。
没有那些七拐八拐的弄堂,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那片高档住宅区。小区门口有站的笔挺的保安,穿着皮大衣的贵妇人抱着哈巴狗从宾治车上缓缓走下来,然后一脸暧昧地微笑着关上了车门。宾治车开走,与之一起消失的,是她脸上如桃花般的笑脸。
纪澜走进小区的时候,心里还有一些忐忑。还好,保安没有把她拦下来。
隐约记得滕汐家在B区十二楼。不敢问保安,只有自己一人摸索着走下去。可小区里面的构造却比弄堂更复杂。等找到B区,她额头上已经冒出密密麻麻的细汗来。
顺着数字一直下去,找到了第十二幢楼。
按响了楼下的门铃。一下,两下,可视屏幕依旧没有出现任何画面。倒是那个小型的圆孔摄像头隐隐约约渗着幽蓝的光线,里面像是隐藏着无数充满怀疑的眼睛。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开了过来。纪澜下意识地转了过身。
穿着干净西服的中年男士从驾驶室走了出来,他打开门,从后座走出来的女士着装素雅,手里的拎包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她扶着一个女孩缓缓走下车。那个女孩面色有些苍白,但脸上仍然露着淡淡的微笑。
“小澜?!”女生发出虚弱但惊讶的声音。
纪澜看着对面穿着光鲜亮丽的一家三口,有些紧张地掏着书包,然后把一本练习本递给了滕汐。
“这是今天化学课的笔记,后面的十个公式明天要听写。”
“啊,真是劳驾你了。”滕汐妈走过去接过笔记本,塞进了她的名牌包包里。然后扬起了一个标准的笑脸,“同学,今天在我家吃饭吧,时候也不早了。”
纪澜看了看手表,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太晚了,我今天还要赶回家去。”其实心里想问滕汐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但是嘴唇抽动着,始终说不出口。
“我今天发你短信,你没有回。”纪澜拽着书包。
“啊。我今天在医院做检查。手机忘在家里了,真的抱歉啊。”滕汐微笑着说。
“做检查?”
滕汐妈抢过话:“汐汐今天有点不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但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多休息就好了。”
“今天突然感觉胸闷气喘,但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大概是这几天排练太累了。”滕汐皱了皱眉头。
“没事就好。”纪澜拽了拽书包。
感觉场面有点僵,说了句“那我先走了”便低着头离开了。
滕汐妈还在后面喊着:“哎呀同学,留下吃饭吧”
但纪澜假装没有听见,她没有回头。夜幕已经降临,城市的灯火在夜幕里渐渐明晰起来。
远处高层公寓的某一层,“啪啦啪啦”地亮起了柔和明亮的灯光。10
与之相对的,在城市的另一个空间里。陈丽芬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一桌子的冷菜发呆。
房间里冷冷清清,女儿还没有回来。邻居在走廊上用煤炉炒菜,呛人的油烟味从门缝里一点点地渗透进来。
她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今天下午发生的那一幕,强大的耻辱感变成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今天下午的超市比往常都要热闹,人们簇拥着围观在收银台前。
一个面色苍白、头发有些凌乱的妇女和保安叫嚣纠结着。
“我凭什么要和你们去监控室!”妇女的语气强硬。
“对不起,请跟随我们去监控室核对监控录像。”
“什么录像?!我凭什么和你们去看录像?!”妇女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
“你偷东西,请和我们走一趟!”保安有些烦躁起来。
“你他妈才偷东西!”她推翻购物车,塑料袋子里的苹果哗啦散落一地。然而,在二十分钟前,一个仰角的镜头,傲慢地记录下了她的一举一动。
陈丽芬在堆满苹果的柜台前徘徊着。
犹豫了半天,还是扯下一只塑料袋,仔仔细细地挑选着廉价的苹果。
拿到称量处打好了价钱,封好了袋子。
然后,她悄悄地撕扯下塑料袋上的透明胶,匆忙地抓起柜台上的苹果往袋子里面塞,然后又重新将塑料袋封好。
这一切,旁人没有注意到,坐在监控室里的保安却看得清清楚楚。而场面正僵持着的时候,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子从排队准备付账的顾客里走了出来。他掏出皮包,用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从钱包里抽出几张人民币。
然后对保安说:“你们的损失,我来帮她补偿。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吧。”
陈丽芬狼狈地抬起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
她看到纪伟明把钱递给保安的神情,比施舍一个乞丐还不屑。
然后他转身,亲热地搂住一个大肚子的妇女,亲切地问候着离开了超市。
指甲已经嵌进皮肤里。胸腔里的耻辱感淹没了痛觉。
———为了女儿,我可以做个小偷。
———但我宁愿当一个小偷,也不愿做你的乞丐。11
有的时候,我们会幻想着自己的灵魂可以挣开脱肉体,然后浮游在城市的上空窥看我们在这个人间的处境。———高层公寓里让人温暖的灯光,打着暖气的房间,客厅里缓缓流淌着钢琴曲。
与之相对应的是充满混浊空气的狭窄房间,门外走廊大声的叫骂声,母亲房间里让人烦躁的“咔嚓咔嚓”的缝纫机声。
———英俊少年的保护、家人亲切的问候,在你身处逆境的时候,总会有人用原本已经无力的双手去拯救你,就连暗暗嫉恨着你的我,也会这样。
与之相对的是我无处可逃的绝境、无力改变的现实和无处倾诉的痛楚,唯有活在幻想里。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但我真的不甘心变得和他们一样。
12
放学回家时池海翔一天当中最忐忑不安的时刻之一。
他低着头避开人群,一个人快速的行走着。他渐渐走出了人最多的地方,于是慢下脚步轻轻地喘了一口气。然而,冷不丁地,撞上了迎面走来的一个少年。他紧张的低着头说:“对不起,对不起!”甚至不敢回头看眼前的那个少年。
“靠,有是你?上次还没有找你算账!”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巧合,一不小心撞到的那个少年,竟然就是邹凯。
“啊”吃海翔惊恐的向后退着。
“今天老子就要整死你!”邹凯冷笑了一下,然后作了一个手势,招呼着后面尾随着的两个小混混。
“来,今天大哥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怪胎!哈哈哈!把他衣服扒了,快!”
后面两个头染五颜六色毛发的少年窃笑着走到池海翔面前,有点好奇但又邪恶的打量着海翔。
突然,其中一个少年猛地向海翔的肚子踢来。海翔顿时疼得叫出了声,额头密密麻麻的冒出了冷汗。
然而,当另一个少年想上第二脚的时候,海翔从背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你们干什么?”
烟焰刚好背着训练包路过。谁都没有看到池海翔此时的表情。他在烟焰的背后,露出了笑容。这一切,他都算准了,天衣无缝,完美无缺。
但他有一点却算错了,他以为滕汐与他的感觉是一样的,那种被千阳笼罩、令人晕眩的幸福感。而他不知道,对于滕汐来说,那种幸福感的背后,是深深的绝望。13
1999年,**中的少年们还身陷在各自的迷局里,他们看不清前方的路,更不知晓这场**末尾的结局。
然而对于滕汐的父亲来说,事情的结局,他早已知晓。但当结局即将来临的时候,他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滕汐母亲靠在厨房的冰箱上,背着他不住地流泪。
“这一天总算来了”
他没有说话,眼角的皱纹渐渐叠加在一起。冰箱突然发出运作的声音,那种类似于电波的声音。
“汐汐现在活得好好的,不是吗?”他轻轻搂住抽泣着的滕汐母亲。
“不要告诉她,好吗?”滕汐母转过身。
他没有说话,闭上眼睛,深深地点了点头。
模糊的视线里,谁也看不清谁眼角的泪痕。另一个镜头模糊的场景发生在池海翔家的浴室里。
赤身裸体的少年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他面带微笑,轻轻的用毛巾擦拭着自己畸形的身体。
玻璃镜子上蒙着厚重的水滴。湿漉漉的刘海搭在海翔前额。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镜子前,用手轻轻擦去凝结在玻璃上的水滴。镜中的影像渐渐明晰起来。
打开洗手台的第一个抽屉,里面有一把有些生锈的剪刀。他对着镜子,用左手捋起前额的刘海。
“咔嚓,咔嚓”。
前额的刘海一撮一撮的掉在了洗手台上。在洗手台的第二个抽屉里,放着父亲用的剃须刀。
海翔缓缓地放下剪刀,然后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锋利的刀片上折射出尖锐的反光。
然后他拿起了剃须刀,用刀片狠狠地刮着自己的眉毛。
眉毛一缕一缕的掉了下来。浓黑的眉毛被剃得一干二净。镜子面前被剃光眉毛的少年,抚摸着自己畸形的肚子。
洗手台最底层的抽屉,藏着一把匕首。池海翔的父母都不知道。
它不算长,但足够锋利。———你想出来吗。
———我要救你,我要救你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房间外被深浓夜色包裹着的繁华都市,隐隐约约地发出了一声哥特式的叹息。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