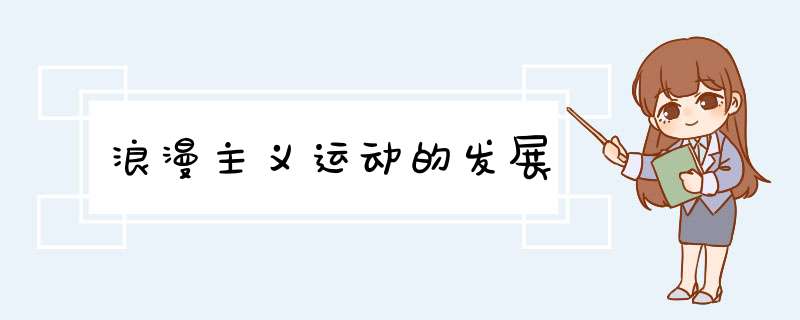
启蒙运动时期
浪漫主义运动尽管起源于卢梭,最初大体是德国人的运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们在十八世纪末都还年轻,也正是当年轻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上表现出最富有特色之处。那些没有幸运夭折的人,到末了让个性泯没在天主教的齐一模式中。(一个浪漫主义者如果原来从出生是个新教徒,他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但若不是这样,就不大能当天主教徒,因为他必须把天主教信仰和反抗结合起来。)德国浪漫主义者对柯勒律治和雪莱起了影响;与德国的影响无关,浪漫主义观点在十九世纪初叶在英国流行开。在法国,自王政复辟以后,直到维克托·雨果,浪漫主义观点大盛,固然那是一种弱化的浪漫主义观点了。在美国,从梅厄韦尔(Melville)、索娄(Thoreau)和布洛克农场可以见到近乎纯粹的浪漫主义观点;稍有缓和的,从爱默生(Emerson)和霍桑(Hawthorne)也见得到。虽然浪漫主义者倾向于旧教,但是在他们的看法上的个人主义方面,总有一种什么牢固不拔的新教成分,而且在塑造风俗、舆论和制度方面,他们取得的永久性成功几乎完全限于新教国家。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的叛逆者做得更妙:他们感觉自己并不是与神合一,而就是神。所谓真理和义务,代表我们对事情和对同类的服从,对于成了神的人来讲不复存在;对于旁人,真理就是·他所断定的,义务就是·他所命令的。假使我们当真都能孤独地过生活而且不劳动,大家全可以享受这种自主状态的销魂之乐;既然我们不能如此,这种乐处只有疯子和独裁者有份了。
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不仅是了解一般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也是了解一直到如今这运动的后裔的哲学、政治和情操的关键。在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下,哲学成了一种唯我论的东西,把自我发展宣布为伦理学的根本原理。关于情操,在追求孤独这件事与炽情和经济的必要之间,须作一个可厌的折衷。DH劳伦斯(Lawrence)的小说《爱岛的人》(The Man Who Loved Islands)里的主人公鄙夷这种折衷越来越甚,最后冻饿而死,但他是享受着完全孤独而死去的;可是如此程度的言行一致,那些颂扬孤独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达到过。
文明生活里的康乐,隐士是无从获得的。想要写书或创作艺术作品的人,他在工作期间要活下去,就必须受人服侍。为了依旧感觉孤独,他必须能防止服侍他的人侵犯他的自我,假如那些人是奴隶,这一点最能够圆满完成。然而热烈的爱情却是个较为困难的问题。一对热情恋人只要被看作是在反抗社会桎梏,便受人的赞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恋爱关系本身很快地就成为一种社会桎梏,于是恋爱的对手倒被憎恨上了,如果爱情坚强,羁绊难断,就憎恨得更加厉害。因此,恋爱才至于被人理解为一场战斗,双方各在打算破入对方的“自我”保护墙把他或她消灭。这种看法通过斯特林贝利(Stringberg)的作品,尤其还通过劳伦斯的作品,已经众所周知了。
按这种情感方式讲,不仅热烈的爱情,而且连和别人的一切友好关系,只限于在能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自我”的客观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若别人是血缘亲属,这看法就行得通,关系越近越容易做到。因此,人们强调氏族,结果像托勒密家系,造成族内通婚。这对拜伦起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瓦格纳在济克蒙特和济克琳德的恋爱中也流露出类似的感情。尼采喜欢他的妹妹胜过其他一切女子(固然没有丑事),他写给她的信里说:“从你的一切所言所行,我真深切感觉我们属于一脉同根。你比旁人对我了解得多,因为我们是出于一个门第的。这件事和我的‘哲学’非常调和。”
民族主义
民族原则是同一种“哲学”的推广,拜伦是它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一个民族被假定成一个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种“血缘意识”。马志尼经常责备英国人没给拜伦以正当的评价,他把民族设想成具有一个神秘的个性,而将其他浪漫主义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求的无政府式的伟大归给了民族。民族的自由不仅被马志尼看成是一种绝对的东西,而且比较稳重的政治家们也这样看了。这一来在实际上便不可能有国际合作了。
对血统和种族的信仰,当然和反犹太主义连在一起。同时,浪漫主义观点一半因为是贵族观点,一半因为重热情、轻算计,所以万分鄙视商业和金融。于是浪漫主义观点宣称反对资本主义,这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因为前一种反对的基础是厌恶经济要务,这种反对又由于联想到资本主义世界由犹太人统治着而进一步增强。拜伦很难得偶尔也屈尊去注意像什么经济权力那种庸俗事,那时就表达出上述看法:
谁掌握世界的平衡谁统治不论是保皇党的还是自由党的国会谁使西班牙的没有内衣的爱国者惊醒(这使旧欧洲的杂志全都叽叽喳喳起来)。
谁使旧世界和新世界处于痛苦或欢乐之中谁使政治都变得油嘴滑舌谁使拿破仑的英雄事业变成幽灵——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和他的基督教友培林。
诗句也许不大铿锵悦耳,但是感情十足是现代感情,所有拜伦的信徒向来都发出了回响共鸣。 英国的浪漫主义的端倪在讽刺作家的作品里见得到。在谢立丹(Sheridan)的《情敌》(Rivals)(1775)中,女主人公决意宁为爱情嫁一穷汉,而不嫁给一个有钱男人来讨好她的监护人和他的父母;然而,他们选中的那个富人化个假名,伪充贫穷向她求爱,赢得了她的爱情。贞·奥斯丁(JaneAusten)在《诺桑格府》(Northan-gerAbbey)和《理智与情感》(SenseandSensibility)(1797—8)中嘲笑了浪漫主义者。《诺桑格府》里有这么一个女主人公:她被1794年出版的瑞德克里弗夫人(MrsRadclieee)写的超浪漫主义的《乌铎尔佛的奥秘》(MysteriesofUdolpho)引入了迷途。英国第一个·好·的浪漫主义作品就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姑且撒开布雷克不谈,因为他是一个孤独的、瑞典宝利教派的信徒,难说是任何“运动”的一部分。《古舟子吟》发表在1799年;柯勒律治不幸由魏志伍德家供给了钱,翌年进了格廷根大学,沉溺在康德哲学里,这并没使他的诗进一步工练。
在柯勒律治、华兹渥斯(Wordsworth)和骚济(Southey)成了反动者之后,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憎恨暂时遏止住英国的浪漫主义。但是不久拜仑、雪莱和济慈使它又复活了,且多少可说支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
玛丽·雪莱的《弗朗肯士坦》(Frankenstein)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浪漫情调的景色中与拜伦谈话的灵感启发下写成的,其内容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寓言体的、预言性的浪漫主义发展史。弗朗肯士坦的怪物并不像俗语中把他说的那样,是不折不扣的怪物,他最初也是个温良和善的生灵,渴望人间的柔情;但是,他打算得到一些人的爱,而他的丑陋倒激其那些人的恐怖,于是逼得他凶暴愤恨起来。这怪物隐着身形观察一家善良的贫苦小农,暗中帮助他们劳动。最后他决意让他们知道他:
“我越多见他们,我要求得到他们的庇护和照顾的欲望越强;我的心渴望为这些温良可亲的人所认识,为他们所爱;看见他们把和美的容颜含情对着我,便是我的极度奢望了。我不敢想他们会怀着轻蔑和恐怖躲开我。”然而,他们真这样躲开了。于是他首先要求创造他的人创造一个类似他自己的女性,等这件事一遭到拒绝,他便致力把弗朗肯士坦爱的所有人一个一个杀害,不过,甚至在这时候,当他完成了全部杀害,眼盯着弗朗肯士坦的尸首,那怪物的情操依然是高贵的:
“这也是我的牺牲者!杀害了他,我罪恶满盈;我此身的这位可怜的守护神受伤到底了!哦,弗朗肯士坦!你这宽宏大量、舍己为人的人啊!我现在求你饶恕我又有什么用是我,毁灭了你所爱的一切人,因而无可挽救地毁灭了你。天哪!他冰凉了,他不能回答我的话……当我把我的可怕的罪孽总账浏览一遍时,我不能相信我还是从前那个在思想中对善德的美和尊严曾充满着崇高超绝的幻想的生灵。但事实正是如此;堕凡的天使成了恶毒的魔鬼。然而连神和人的那个仇敌在凄苦悲凉当中也有朋友伙伴;可是我孤单。”这种心理如果剥除掉浪漫主义形式,毫无不现实的地方,要想找类似的实例也并不难。旧德国废皇在窦恩对来访的某个英国人慨叹英国人不再喜欢他了;伯特博士在他写的一本讲少年犯的书里,提到有个七岁男孩把另一个男孩弄到运河里淹死。这孩子的理由是无论他一家人或他的同年辈的孩子们,对他全不表示爱。伯特博士以好意对待他,结果他成了一个有身分的公民;可是并没有一个伯特博士来担任改造弗朗肯士坦的怪物。
1例如,藏族除夕那天,人们穿上艳丽服装,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用唢呐、海螺、大鼓奏乐,奉行隆重而又盛大的“跳神会”。小伙子们狂舞高歌,表示除旧迎新,驱邪降福。到了新年早晨,妇女们便去背“吉祥水”,预祝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2案例:1990年11月,被告人彭土华所在乡村的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集体申请整修再建已破烂不堪的清真寺。作为该村治保干部的彭拒不同意。后这部分回民自己集资整修。彭闻知后,极为不悦,责令回民们停工。回民不从,彭大骂说:“老子叫他们修不成,今天就是准搞这些鬼玩艺!”回民向其恳求,彭不理不睬,并带了二十多个汉族村民把回民所修复的圣坛捣毁。回民对之极为不满。该村同另外两个村的回民知道后,联合起来,游行到县人大常委办公室,要求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经县领导做工作,才平息事态。彭土华的行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 评析:宗教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现象。在它赖以生存的根源、基础消灭之前,要强制消灭宗教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多民族的我国,由于政治、经济、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能违反宪法和其他法令,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否则,就会伤害民族感情,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了保障人民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增强人民内部的民族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中被告人彭某身为国家干部,应该了解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回民集资修复清真寺,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不仅予以制止,而且还亲自带人捣毁圣坛,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政策,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应依法予以制裁。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对。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在书中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代人的“合作事业”,不能用颠覆的方式对之进行改革;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因而它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它还将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的事例、随意地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中世纪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与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针锋相对的见解。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撰写中世纪史,将中世纪的市民阶级理想化,并以此为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寻找历史根据,因而他们也就非常重视对近代史─作为中世纪历史的必然延续─的研究,尤其热衷于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史,并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将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发展理论结合起来,把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看成为一个不间断进步的过程,并且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乃至于革命运动都纳入到了这个进步过程之中。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作对神秘主义解释及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保守派史学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讨业绩、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作为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了大肆渲染和美化。自由派史学家则着意于探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问题,并把历史上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自由精神”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把市民阶级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梯叶里甚至将“民族”与“第三等级”划了等号,认为第三等级构成了法兰西民族,而贵族和僧侣则是法兰西民族的外来压迫者。
自由派史学家也充分肯定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宣扬神意、把本民族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优越民族。但是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教会统治,而是为了肯定宗教改革和新教在欧洲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为建立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寻找宗教上的依据。
自由派史学家与保守派史学家在运用历史主义观念阐释历史运动的时候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保守派史学家把历史运动说成是完全由“前在因素”和“民族本性”决定的无意识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自由派史学家则在接受了历史主义观念的同时,承认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动作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史学家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说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其中梯叶里首先把法国中世纪史写成了第三等级与僧侣及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后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又把阶级斗争观念运用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受到了世人的好评。
上述3派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曾经称霸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里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则是自由派史学。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守派史学虽然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然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纵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就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