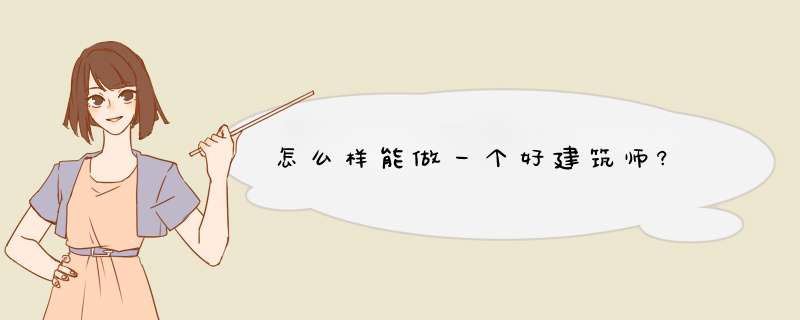
建筑教育的成果,是要培养出好建筑师,要盖出好房子
提问:我想问一个关于建筑教育的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受教育,然后也到过国外。前一阵子马清运不是很正式说起学生去美国留学,说去了也白去类似这样的话。我想问张永和先生和马清运先生,听一下你们对建筑教育的看法,我想听听雷姆·库哈斯对他们的评论,因为雷姆·库哈斯自己的建筑教育和普通建筑系的学生不一样。也想听听矶崎新的意见。
马清运:我是说过不要去美国,或者去了转转赶紧回来的话。我的意思是建筑教育容纳在真正的工作中。只有通过对问题的发掘和解决,教育才算开始。我不知道建筑师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感觉假如你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的话,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话,你去了以后也没用。我觉得其实我是希望做一些教育的移植工作,刚才有人问到中国教育有什么问题?美国教育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中国教育在中国的问题或许在西方社会就是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像一种生命体的细菌,会变成另一个生命的防疫针。我觉得一个系统的问题注射到另外一个系统中倒成了解决方法。
库哈斯:你所说的中国教育问题是什么?
马清运:在中国,建筑师拥有太多的责任,每一个毕业的学生想做研究生,想做老板,在美国,学生没有这样的雄心,他们觉得能画画图,做做细部已经不错了。
刘家琨: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特别感动,因为小时候没有读多少书,在房和树上的时间好像比地上多。没想到长大以后还可以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没有特别系统地学建筑。所以建筑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学问,它是一个常识和智慧。我不知道我在建筑学庞大学科的哪个层面工作,如果要重新来学,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系统性,也没有那样的机会。所以我就是牢牢地建立普通人的现实感,紧紧抓住问题,然后仔细看自己有什么样的条件。问题如果非常特殊就能够出现很多创作,比如说创作或者动机都会在里面。如果你有特别的条件,然后地方性、个人性都会在你的观察里面,如果你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那作品就会出来。其实我是学建筑,然后十多年不搞建筑,就把学校教育那一套忘了,然后重新搞建筑。我有一些其他参照系,比如画画、写作,我现在感觉参照系比直接学建筑好像更重要,因为修房子这件事情主要是看怎么观察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我不谈怎么教育了,我也不知道如何教育。
张永和: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成了留学咨询。有一天晚上,在北京,雷姆·库哈斯突然发问我,我要是重新来过是不是还去美国留学。我答案很坚决:不去。也不是留学不去,我今天仍认为欧洲的建筑教育情况比较更好,在座如果想留学的同学可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认为我所受的美国的教育教会了我盖房子。我回中国实践了12年再回去一看,美国所谓的顶尖的学校还没在教学生盖房子。所以这一下子使我有活干了。可能美国今天有一些学校还陶醉在自己是在提供很先进的教育,但看看过去20年美国盖出来好房子的量,恐怕已经落后于亚洲了,更甭说欧洲,亚洲还得把日本给去掉。所以这是最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建筑教育这么先进,那么你教育出来的好建筑师都跑到哪里去了,盖的好房子都哪里去了。所以我今天希望美国的学校例如MIT有一种危机感,如果现在暂时没有落后,不久也即将落后了。不会盖房子的建筑师是不可能盖出好房子的。具体怎么改有很多困难,很多工作需要做。
库哈斯:我羡慕那些参与建筑教育的人,但是可惜的是我在生活有些方面有一点玩世不恭,其中就有教育。我想唯一坚持的教育是你什么也别做只是专心学习,纵然碰到坏老师也装成好老师。我羡慕建筑教育,因为这是我唯一涉足的教育领域。将建筑师的培养扩展至那些无关的领域,我想这是在未来能够生存并设计好房子的条件。
矶崎新:当我在东大读博士学位最后阶段的时候,我决心不做一个教育者,不做一位教授。我做了一位实践建筑师。当然后来我只做学生评图的评图委员,我想我只适合做这个,而不是一个教育者。所以对我来说谈教育是很困难的。他们说到我写了很多书,一些是挺专业的(关于建筑的),但是绝大多数是更进一步的公众启蒙,让公众如何理解建筑、如何帮助创新的建筑,我就是这样写书的,这对我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但是我很在乎它。启蒙工作当然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很重要。
创新、责任、世博会及其他
提问:创新和责任,是不是对立的?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建筑师在这么多新问题下,是不是对创新有一种责任?是不是建筑师的责任改变了,是不是有新的方法去想建筑师的新责任是什么?
库哈斯: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特别以为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来重新定义建筑领域。这个学科很多方面已经沉寂了,有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把握。重新定义我们的责任可能是激动人心的,我觉得这个是要集合的力量,例如教育,一起共同定义。
马清运:雷姆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提出是非常准确,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建筑教育入手。
提问:我想问雷姆·库哈斯,如果有机会做第二份工作,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库哈斯:如果有第二份工作,我以前希望可以选择的是时装设计,或成为一个作家。现在如果做选择,我愿意选择不用脑子的工作,用身体其他部分去工作,那个工作我一定会更加激动。
马清运:今天下午说到世博会的事情,我听到雷姆在其他地方说过很多这样的话。我想代表大家再关于这个问题提问一下,我想把答案和大家共享。
库哈斯: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来谈显得太有野心了。我想其中一件事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会很有兴趣——亚洲对自我的定义,能够提供什么。和以前见到的有什么区别。
马清运:当西方对技术推进、文化交流、文化活动互换的兴趣降低的时候,他们把希望和眼光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中国世博会如果能够在三年当中站出来做出宣言的话,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会令上海更具有吸引力的。第一点就是应该走出中国世博、上海世博的圈子。第二个就是应该更多了解西方人对中国,对另一种文化期待着什么,期待一样的答案还是期待比它更有创造力的答案;最后一个想法,我本人觉得我们自己要特别了解我们处在现在历史阶段上到底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我们的能力,的确能够和以前走过的路不一样,同时又暗示着更好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中国之外的兴趣和更多的对这个活动的贡献。
提问:能否请雷姆·库哈斯先生和矶崎新先生互相评价一下。
库哈斯:评价矶崎新先生有三点:第一个是实在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有创造力;第二个是实在不容易,在创造力过程当中表现得这么不连贯、不一致,而又一直有想象力,矶崎新先生的工作有时候非常优雅,有时候伤感,有时候也粗鲁,有时候也是抽象的。第三个是他是亚洲可能是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的建筑运动——新陈代谢运动的主要***之一。这三点使矶崎新先生成为我永恒的研究对象。
矶崎新:或许我比雷姆·库哈斯长了20、30岁,这意味着他很年轻就成为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我和他处在不同建筑师年代中。这意味着种种情境都很重要。我自己在1960年代毕业开始工作,试图加入国际舞台。1960年代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情境。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是左翼运动的一部分。1960年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文化革命的年代,反对建筑、反对权利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政治处境。如果你们谈论政治学的话,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场噩梦。现在过了几十年,我们改变了很多。我想我应该顺从这个时代了。
文化机构、博物馆是我乐意接手的项目。我知道雷姆·库哈斯的客户和我的不同,库哈斯和新的资本形势结合,他影响着世界。对于他的状态,我憧憬,但我干不了,我安于在这个传统建筑领域工作。
(录音整理:晓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