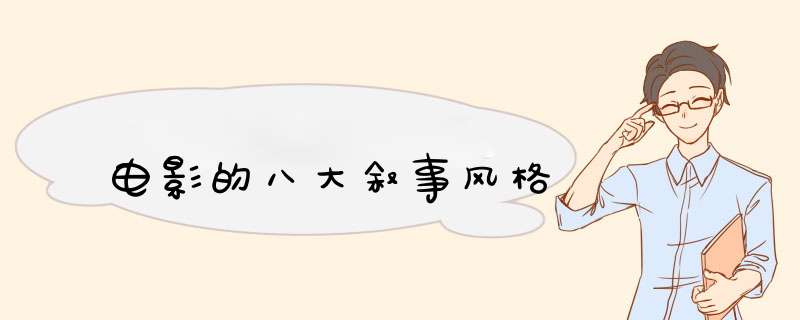
**有八大叙事风格,分别是常规线性叙事、多线性叙事、回忆叙事、环形结构叙事、倒叙线性叙事、乱线性叙事、重复线性叙事和套层性叙事。常规线性叙事是指按照正常时间模式叙事。
多线性叙事是指影片有很多个小故事组成,在一个时间段由其中的一个故事串联起其他故事。
回忆叙事是按照主人公或非主人公的回忆进行现实与回忆的交叉叙事。
环形结构叙事是指影片的开头与影片的结尾相互辉映。
倒叙线性叙事是指按照反正常时间叙事。
乱线性叙事的整部影片毫无逻辑性,可以说是把所有片段、情节、人物全部搅乱,让人无从得知现在、过去和将来,只能靠观众凭借自己的记忆力捋顺影片。
重复线性叙事的整部影片在时间上会有一个重复的时间点,每个故事都会从这个时间点上再次开始。
套层性叙事像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一层一层,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形成一种套层结构。
文章叙述风格有:
1、第一人称叙事法 2、第三人称叙事法 3、顺叙法
4、倒叙法
5、插叙法
6、补叙法 7、分叙法
8、详叙法 9、略叙法 10、直接抒情法
11、间接抒情法
12、先叙后议法 13、先议后叙法 14、夹叙夹议法
15、以物为线索 16、以人为线索
17、以思想变化为线索
18、以中心事件为线索 19、写生法
20、转动法 21、剥笋法
22、拟人法 23、化动法 24、说明法
25、运用“五觉”法 26、借物抒情法 27、托物言志法
28、物品自述法
29、远眺近看法 30、内外结合法
31、移步换形法 32、说明介绍法 33、环境衬托法
34、彩笔描绘法 35、远近结合法
36、时序变换法
37、生长变化法 38、展开联想法 39、突出重点法
40、对照比较法 41、赞美颂扬法 42、静态素描法 43、总分结合法
44、特征举例法
45、特征说明法 46、重点突出法
47、成长变化法 48、实验证明法 49、群体描写法 51、拟人法 52、动物自述法
53、议论抒情法
54、景物衬托法 55、季节特征法 56、随时变化法 57、日内变化法 58、定点换景法 59、定景换点法
60、移步换景法 61、围绕中心法
62、分类描写法
这里指的叙事诗баллада是基于传说,历史,童话,日常主题的带有叙述情节的抒情诗的一种。叙事诗与哀歌一样是莱蒙托夫最喜爱的创作风格。更准确地来说,这种叙事诗是对哀歌的继承与发展。
在这些叙事诗中莱氏将以下抒情主题作为叙述基础:孤独感,对未知的忧愁,逃离,爱与死亡。现在这些情感通过在情节中通过不同角色的情感来体现出来。
叙事诗《梦》(1841),这是莱蒙托夫最神秘和琢磨不透的一首诗。虽然在诗的第一句就已经指明了故事发生地方(在塔吉克斯坦峡谷),但是时间和地点又都带有抒情诗的不确定性,有相对的异域风情,这仅通过一些细节提现出来(悬崖的阶梯,山峰,峡谷的沙子,明亮的太阳)。
纳伯科夫分析了这首诗独创的心理和框架结构。
某人(莱蒙托夫或者准确来说,他的抒情主人公),在 梦中看见自己似乎在高加索东部山脉中的谷地上死去。这是第一个人梦见的梦。
这个带致命伤的人(第二个人)梦见,一位年轻的女士,坐在彼得堡的宴会中,而不是坐在莫斯科的豪宅里。这是位于第一个梦里的第二个梦。
年轻的女人,坐在宴会中,梦见了第二个人(这个人在诗末死去了),他躺在遥远的塔吉克斯坦的谷地上。这是第三个梦,位于第二个梦里。第二个梦又在第一个梦中。这就构成了一种封闭的螺旋式结构,让我们思维返回到诗的第一句上来。
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 梦,镜子,双胞胎人物,纳伯科夫给这个精彩的文章,三重梦自己的命名。并且发现这些环,由五个四句一节的诗组成的,与五个构成小说当代英雄的短篇故事之间的交织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独创的解说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第一个人梦和叙事诗中的第一个抒情主人公没有明确指出和描述,只是提及。但是,可以说受伤躺在战地上,等待死亡的“我”不是作者,而是第二个人:这是角色抒情诗。注意,我们以前在《诗人之死》第二行看到的形象也属于普希金(胸腔中注满铅和复仇的渴望),(心中注满铅般的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诗不命名为《士兵之死》,而是《梦》。死亡的主人公在死前的梦中看见了自己心爱的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在愉快的交谈中也经受着伤感的梦的困扰。
她梦见了塔吉克斯坦的谷地;
熟悉的尸身就躺在那里;
在他的胸口,伤口凝黑,
流出渐冷的血流。
在叙事诗中时间是流动的。在第一个诗节中主人公正在死去,在最后一个诗节中女孩看见了熟悉的尸身。可是人物之间的联系,梦境的真实性基本上没有表明出来。
叙事诗的主要事件是神秘:梦境的奇怪交合,心灵之间的神秘感应。
在别的叙事诗中莱蒙托夫在叙事中描绘了外部世界,将主人公当做自然中的现象,物体。但是与寓言作家不同的是,诗人需要这些相似的主人公,并不是为了道德教育,而是为了表现抒情对象的习惯性环境。
永远自由的乌云,与抒情主人公不同,他的故乡,他的放逐都是未知的,他向不可知的远方飞驰而去。(《乌云》)
悬崖在为欢乐的阴云的离去而哭泣。(《悬崖》)
孤独的松树幻想着,在梦中看见,在大地的另一端,在远方的荒原上生长着的美丽棕榈树。(《在北方的悬崖上》)
脱离树枝的橡树叶不能从娇贵,任性的法国梧桐那里找到同情心:(走远些,你这个怪人,我不认识!)(《树叶》)
梦想着得到某个谁垂青眼光的棕榈树惨死在斧头下,就像人一样:他们的树叶叫做理想,枝干叫做身体,他们在篝火中的燃烧被描述成一种可怕的死刑。
他们的衣服被年幼的孩子撕扯下来;
接着他们的身体被砍碎;
再燃烧至天明。(《三棵棕榈树》)
莱蒙托夫不仅仅让自然复活,也将她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动因的表现形式。
但是莱蒙托夫的浪漫主义叙事诗还有另一种形式。“他创作了一种对于俄罗斯诗歌来说新的东西-抒情短文,最短的关于现代人的诗体小说。”(ЛЯГинзбург)
《遗书》(1840)就像《梦》一样。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正在死去的主人公和另一个女人,就是那个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在想念的女人。但是相似的抒情场景里充满了对于短篇叙事诗来说大量的日常生活琐事,和心理细节。
他的同伴听着正在死去的主人公带有经常性停顿和口误的独白。准确又具体地展现了他的伤。清楚的是他是死在诊所里:“我们的医生很坏”提到了他由于被征入伍长时间没有见过和联系过的父母,可能他们很早就忘记他了,也可能认为儿子已经死去了。最后,开始提到了心灵空虚的女邻居。主人公仅仅请求转告她所有真相。
在叙事诗《梦》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不明朗的。在《遗书》中这很明显:战士整个一生爱着并记着自己的女邻居,在死前向她转达最后一声问候,指望得到迟到和无意义的同情:让她哭一哭,这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莱蒙托夫笔下人物的对话有意义,并且在意义上让人想起普希金《我曾爱过你》诗中抒情主人公最后的长叹:请让上帝让另一个人来爱你吧。
在《遗书》中,像在《波罗金诺》中一样,莱蒙托夫的主人公是带有自己语言,声音和问题的普通人。在这里,但是不是叙事诗的中心,出现了主题:战争中的人。这个主题成为主要的主题在诗《瓦列里克》中。
附注:
《梦》
在塔吉克斯坦谷地上半日的火焰中
带着如铅注般的胸膛躺着一动不动的我
深深的伤口还冒着热气
我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流出来
一个人我躺在峡谷的沙地上
崖壁从四面八方蜂拥挤来
太阳燃烧着他们**的顶峰
也燃烧着我,但我梦见了一个死亡的梦
我梦见耀眼的火
亲爱的年轻女人间饰有鲜花的晚宴
听到关于我的愉快谈话
但是有一个沉思静坐的女孩
没有加入愉快的交谈
她可爱的心被忧伤的梦折磨
上帝知道她在痛苦什么
她梦见了塔吉克斯坦谷地
熟悉的尸体躺在那个谷地上
在他的胸膛上,伤口凝黑
流出渐冷的血流
1841
作者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从始至终只运用一种固定的叙事方式是不存在的,作者会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容与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叙事视角,即便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有时也会存在不同叙事视角之间的交替运用。
而鲁迅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代表,除了他能够在作品中熟练巧妙的运用创新独到的叙事视角之间的交替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他创新独到的叙事风格,使他的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社会中更具创新性。
1运用插叙的手法
顺叙描述是大多数小说作品采用的叙述手法,对故事的发展从始至终都以第一顺序进行描述,插叙手法是作者将作品中人物的所见所闻和回忆进行叙述、介绍和说明。
通过运用插叙的手法,不仅能够使小说内容更加具体丰富,而且还能够充分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和突出,并为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提供补充。
如《故乡》中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使用顺叙的叙事手法,但是仔细深入的进行阅读之后会发现文中其实运用了大量的插叙手法。
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母亲提到闰土说很想念“我”,因此便开始以“我”的回忆为故事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原来叙述的内容中断,在文中插入了少年时代“我”与闰土之间交往的一段友谊之情,在记忆中少年时代的闰土拥有勇气的果敢少年,并且具有丰富的见识,这些让一直待在家里和私塾中的“我”特别羡慕。
通过运用插叙的手法回忆了少年闰土的形象,同时也为后面小说中对中年闰土的叙述进行铺垫,为读者展现在不同时期同一人物所产生的不同形象,使读者明显的感受到视觉的差距和内心情感的落差,抨击了当时旧中国现实社会的希望和失望。虽然有心想要改变现状,但是却又感到迷茫和无能为力,使文章更加具有张力。
2充满诗意的结尾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小说作品给人以一种富有诗情画意的审美感,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对文章有更深一层的感触,而鲁迅先生的作品则突破和创新传统的叙事方式,采用开放诗意的结尾,将读者的思索和目光都引入到一个充满诗意的深邃境界中。
充满诗意的结尾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对话的桥梁,对主题的意义与延伸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正是鲁迅先生在不断探索和不断超越的奋斗下,为读者提供一个想象的平台。
如《在酒楼上》的结尾,对“我”与吕纬甫的分手进行叙述:“我们一同走出店门——我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去,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积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从叙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心中的矛盾和痛苦是因为与吕纬甫的分手而得到暂时的解决,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能够冲出封建社会的罗网,在冲出罗网之后感受到的爽快,才是此时战胜另一个“我”取得的胜利。
作者通过描述分手的情感,使读者阅读之后在脑海中呈现当时分手的场景,并真实感受到作者心中的痛苦和爽快。
3多层次的叙述条理
叙述故事具有条理性不仅能够生动形象的塑造出人物的鲜明性格,而且还能够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精彩,引人关注。
在小说中叙述条理的多层次主要分为高级叙述、次高级叙述、主叙述、次低级叙述、低级叙述等五个层次,主叙述是整个小说的核心,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如鲁迅先生在文章《故乡》中就有四个显而易见的叙述条理。
第一层次是“我”回到故乡的所见所闻;第二层次是“我”和母亲两人对闰土和杨二嫂的回忆与见闻;第三层次是回忆少年时代闰土送予我的贝壳和羽毛,豆腐西施的杨二嫂;第四层次则是闰土少年时捕鸟、看瓜和抓猹的故事。
在四个层次中很明显第二层次是文章的重点和主叙述,从中寄托着作者内心的孤独及长大后与少年伙伴之间存在的隔膜之情;第一层次则是高级叙述,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分别时次低级叙述和低级叙述。
四个叙述层次之间一环紧扣一环并相互穿插,正如在“我”长大再次见到闰土场面回忆中,穿插了少年时代闰土与“我”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在这些回忆中的故事里包含了少年闰土捕鸟、看瓜、抓猹事件的叙述,从而使叙述条理之间的层次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