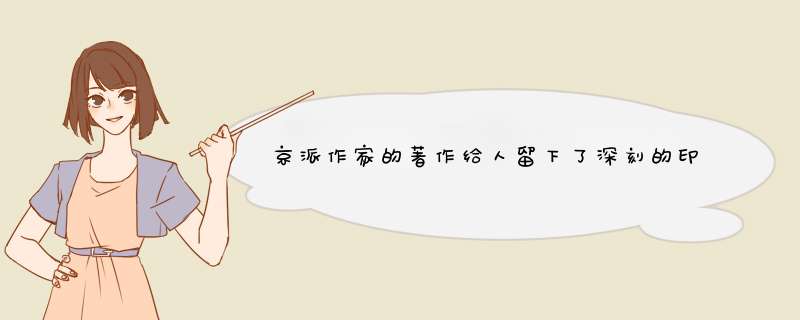
1、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又名周奎绶,后改名周作人,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2、废名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3、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男,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4、李健吾
李健吾,笔名刘西渭。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从小喜欢戏剧和文学。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31年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学习,1933年回国。历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5、朱光潜
朱光潜(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
-朱光潜
-李健吾
-沈从文
-废名
-周作人
-京派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 ,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传奇一生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学贯中西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