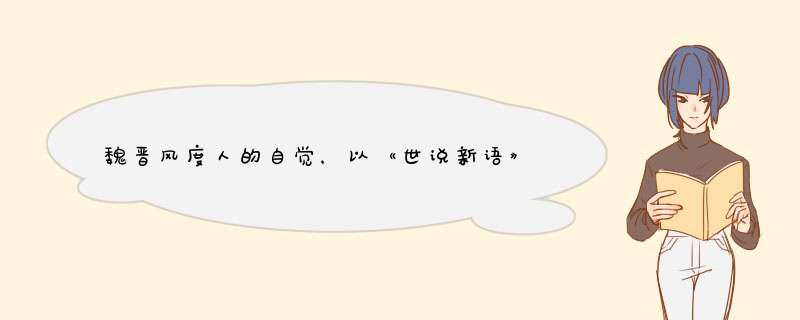
魏晋风度为中国文化抹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成为后代文人追幕的永恒的对象。有一本书是我们了解魏晋风流的捷径一一《世说新语》。冯友兰在《论风流》中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风流宝鉴。
这部书是刘义庆和他身边的文人根据以前的一些史料编撰出来的志人小说集。主要是记录魏晋文人言谈举止的一部志人小说。但是《世说新语》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有关魏晋人物大量的史料都取自于《世说新语》。它是一部集文学和史学于一体的著作,是我们了解魏晋风流的一部重要经典。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鲁迅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一种文化自觉,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一种文学创造。
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人的自觉,就是人的主体。以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自觉就追溯到中国的思想史。
第一,儒学的衰微。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成为两汉时代主要的政治思想。作为主要思想的儒家,对文人的个性起到了收覆的作用,但是儒家的经学自身走向了极端。以儒学所一从的政治基础开始走向了衰弱。到东汉建安时代,原来起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学开始走向衰弱。衰败的理由是因为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起。
第二,养生论。在汉代末年建安时期有一些哲学家,借助于《周易》和老、庄的哲学著作,来改造传统的儒家。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为"三学"。以"三学"为基础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称之为"玄学"。到了魏晋时期,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潮。玄学作为一种学说,他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本末问题"。玄学里面有另外一些问题与魏晋风度相关。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记载的,旧云,王丞相过江左,只道生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指王导他从北方来到南方(当时的健康城)之后,他讲了三个问题……言尽意之论,讨论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语言能够表达人的内在的思想感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不能够表达主体的内在的思想感情。
其中的《养生论》以嵇康的著作为代表。嵇康的《养生论》是一篇著名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我们中医学中的一篇文章。
《养生论》中嵇康提到,有两个方面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一个是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其一,指的是,平常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要大喜大悲。大喜大悲让我们的情感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影响到身体健康。平常没有什么功名利禄在自己的心中。其二,指吃一些东西来养生。直到今天我们还用这两种方法来养伤。这也是玄学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第三,生无哀乐论。这是一个音乐命题。也转化为玄学的一个讨论问题,嵇康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写过一篇音乐专论,叫《生无哀乐论》。他提出一个主要的观点,认为音乐是没有情感的,他说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节奏的声音。声音要评价,只能用好听和不好听评价,不能用情感来评价音乐。他提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音乐理论。儒家音乐理论特别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本来是合理的,但是过分的强调之后就失去了音乐的独立地位。
第四,玄学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命题叫才性四本论。《世说新语文学篇》中,除了文学,还包含哲学以及其他的艺术。曾经提到过曹魏时期有一个学者叫钟会。他很有军事能力,学问很高。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四本论》。他想请教嵇康,可惜由于嵇康看不起钟会的人品,所以钟会很难当面将这本书递交给嵇康。《四本论》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是关于才性的关系有四个不同的观点。"才"就是才能;"性"就是一个人的品性道德。又要讲道德,又要讲才能。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才能和品德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统一的。这种观点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才性评价的主要的思想。
第五,是讨论情感的,叫圣人有情无情论。生活中人是有情感的,圣人有没有情感呢?庄子在《逍遥游》中曾经说过,圣人无名……一般人在生活之中遇到好的事情会快乐,遇到悲伤的事情会难过,有喜怒哀七情六欲。但是,当时的玄学家何晏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有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叫王弼。他不同意何晏的说法。他认为圣人和我们一般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圣人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情感而不为情感所累。王弼的这个话很精彩,叫应物而无累于物。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魏晋风流的主要内涵。
了解魏晋玄学以及玄学的内涵,是理解魏晋风度的一个理论基础。
魏晋南北朝一点也不美好,并且十分的残酷和悲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历史。有连绵不断的混战和地方割据,持续不断的族群侵并,政权的交替,长年的混战导致的人口不断迁徙,加上自然灾害。在长达400余年的历史中,理不清的矛盾,就像一个巨大而又疯狂的龙卷风,将所有人卷入苦难之中。
我们先说一说魏晋两朝,只从曹丕离世之后,魏朝就渐渐衰败下来。导致司马炎上位,建立了西晋。自称晋武帝,由有司马炎出身世族,其家族在魏朝就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权贵集团。政风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在当时大量游牧民族内迁的情况之下,几乎是毫无作为。这也为了西晋的灭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之后因为后宫皇后贾南风干涉朝政,引发了八王之乱。这八王分别是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汝南王司马亮,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导致朝局动荡,人心惶恐。八王相互引兵作战,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是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的主要原因,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五胡乱华时期。
五胡乱华中的五胡并非单纯指五个部落,而是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胡人纷纷在八王之乱后,纷纷建立政权。开始胡尊汉卑,甚至称汉人为儿、奴、狗。区别对待汉人和胡人。北方汉人,被称呼为“两脚羊”,全国上下吸食五石散,在身体和精神上对百姓进行摧残。
那个时代,朝纲祸乱,战乱频繁,百姓如犬,妻离子散。上层官垄断骄奢*逸,下层民晋升不得衣食不饱。那个时代,真的不美好。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士人们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不务正业”,“纵酒狂歌,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这种背离中国传统士大夫行为规范的现象,尽管有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但却反映了传统模式被打破后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认识价值的取向。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天人感应神学曾经是权威思想之一,作为权威思想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你,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孤独生命的恐惧。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大地混乱、痛苦之中。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董卓之乱以来,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们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在传统士大眼中,无异于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抛弃了,这对于那些熟读儒学经典的饱学之士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他们痛苦、焦虑、迷惘、因此而言语癫狂、举止乖张、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这才使得人们在思想陷入极大混乱中,从谈玄开始,便诞生了“魏晋风骨”。
二、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无休止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后,“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彻底崩溃,群体意识鲜活的生命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传统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得粉碎。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们完全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和历史舞台上。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了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就顿时包围了他们。
人不能没有生活的目标,不能没有理想信念,这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种思想的崩溃,必定会引起其它思想的构建。
随着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发布,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死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试图将个体人格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理想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最终使之流产。
竹林的名士们目睹了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它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为主要特征,通过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而进行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但这种理论体系因为嵇康等人的被杀而不能稳固地长期占据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内圣外王”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糅合起来。东晋后期出现的儒、释、道三教互补 理论模式最终不断深化、完善为宋代理学,形成封建社会士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诸种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却成为了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主流。其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
这些思想行为使魏晋风度发挥到了极致。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记载魏晋士人言行举止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极力张扬的特征来。
这就是,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远没有刀光剑影中生命的存在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也远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实在。
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这便是魏晋风度对当时士人群体的一个重大影响。
结语
从魏晋风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的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还有他们共同的竹林之游,酒醉不醒
然而,他们真的彻底忘记了作为士人,传统和现实赋予的责任了吗?真的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
阮籍何以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等与猪共饮,发泄愤懑,都是在司马氏政权设置的罗网中进行无奈的挣扎,他们自残其身的醉酒、服药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性命;从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外在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痛苦万状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正是其内心压抑、痛苦万状而又无由发泄的真实写照。可见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和责任并不因他们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他们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之矛盾的万丈深渊。
我想熟悉历史的人很多人都知道“魏晋风骨”吧,而其中“魏晋风骨”要数当时的“竹林七贤”了,几个志趣相投的人混在一起饮酒作乐,功名利禄尽数抛在脑后,甚至可以不顾及儒家的各种世俗礼节,所以在遭到别人批判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人的认可。
而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在当时也很受人们的推崇,所以在魏晋时期这是“名士”的标杆,而他们的这种洒脱的行为也被后来人称为“魏晋风流”或者是“魏晋风骨”。
然而事实上当你真正了解了“魏晋风骨”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魏晋风流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事实上这个词汇在小编看来更多的像一个“贬义词”,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就来领略一下“魏晋风骨”:
名士爱嗑药,少女爱娘娘腔
由于我们曾经因为鸦片的缘故所以在近代饱受欺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这种东西如此痛恨的原因,所以在我国毒品是绝对禁止的。
然而你很难想象,在我国的魏晋历史上这居然是一种时尚,而且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居然都爱嗑药,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当时有一种东西叫做“五石散”,这种东西吃了之后会让人的神智有点飘飘然,总之是一个很伤害健康的东西,然而在魏晋史上沉迷这种东西的人还不少,许多的名士都爱吸食“五石散”这种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东西很合乎他们崇尚的“玄学”之中的空灵境界,所以在当时成为了一种风尚。
而吸食了“五石散”之后,由于“五石散”的药性会让他们的面容变得异常的洁白,在当时有一个人叫何晏,他本身是曹操的养子,虽然是男人,可是却长着一副比女人还要漂亮的脸蛋,而吸食“五石散”之后加上药性,让他的肌肤则变得更加雪白。
以至于当时洛阳城的女子见到何晏都是为之疯狂的,所以魏晋时候的男人都开始学习何晏的这种风格,将自己的脸涂的白白的,然后打扮的甚至比女人还漂亮。
用现在时髦点的话来说叫做“娘娘腔”,然而一个男子失去了血气方刚反而是以各种“娘炮”装扮来打扮自己,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所以从这点上来时“魏晋风流”没什么称颂的。
名士既清谈又误国
在现在我们总有一个词叫做“清谈误国”,而这个词汇形容当时的“魏晋名士”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开始,当时天底下名士就因为和宦官的争斗导致死伤惨重,而曹操在主持东汉末年的朝局之时,又杀了当时反对他的一些名士例如荀彧、崔琰以及孔融等等。
而司马家上位之后做的比上面更狠,“正始三大名士”都死于司马家之手,而“竹林七贤”之中的嵇康更是因为明确反对司马昭而被司马昭惨遭杀害。
所以这就导致大量的名士从此开始心灰意冷,尤其谨记“祸从口出”这件事情,于是乎私底下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谈论任何关于朝堂上的事情了,而是以“玄学”代之,这个东西实在是很虚无缥缈,小编无法解释清楚。
本身他们谈玄也没什么,然而他们谈玄最后竟然谈到了西晋亡国。
在西晋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群士大夫想的不是挽救西晋,而是和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饮酒作乐,吸食五石散。
此时西晋已经到了危亡关头,他们却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在古代粮食本身就不易获得,而他们饮酒作乐也浪费了大量的粮食。
当时名士之首的王衍贵为“三公”,可是在西晋存亡关头他并未从国家大局考虑,事事反而想的都是家族利益,把自己几个兄弟都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以此让家族经久不衰。
在司马越死后,他本该继续主持大局,可是他有不干还说什么无意朝政,最终群龙无首之下被石勒包了饺子。
在生死存亡关头,他自己又顾不上形象了,卑躬屈膝的向石勒投降,而石勒看到所谓的“天下第一名士”是这副光景之后也是大失所望。
最终一道土墙掩埋了王衍,而临死之前王衍终于醒悟了感叹道:“假如以前不那么崇尚虚荣,而是多留心民生,那么自己或者国家会是这样子的下场吗?”
所以魏晋风流的背后却不是那么风流,这群自诩风流的“魏晋名士”却是间接导致两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也正是他们造就了长达几百年的战乱。
每一个时期当时的士子所具有的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有一种风度却很奇葩,那就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士子一个个风流放荡,但却显得很清淡,这就让人感觉到有点矛盾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风度呢其实小呆也所知甚少,但是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小呆慢慢才了解到其中的奥秘所在。
动荡不安的魏晋
魏晋时期的政治局面一直动荡不安,从而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士大夫不能够一展自己胸中的抱负和雄心壮志。只能整日在家宣泄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将这些苦闷的方式通过一些渠道宣泄出来,为此他们在生活行为上经常的放浪形骸,展现出自己不拘一格的一面,这样的行为举止可不仅仅风流这么简单,有时候做出的事情真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荒诞。
在这些事情当中最为荒唐的便是吸食五石散了。古代也有很多能让人上瘾的玩意,比如风靡一时的五石散。当然啦,除此之外,魏晋的士大夫通过喝酒、吃药以及纵情山水来表现自己的不拘一格。而吸食五石散这在当时的士大夫贵族之间是很常见的,这种药物具有致幻效果。吸食五石散会让很多人能够获得心理上的一种不受拘束,超凡脱俗的状态,魏晋文人们会沉迷其中。
这些士大夫通过吸食五石散,以此来表达对当时这种黑暗社会的不满,不过也为后世吸食五石散做了一个带头作用,果真是荒唐至极。
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魏晋各士大夫之间还流传一些奇葩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体现在脸上的他们所花的妆容。这些人的当中便有曹丕以及曹操的另外一位儿子曹植,这两位特别喜欢打着粉底去见自己的宾客。在个人形象方面,当时的士大夫们都特别注重自己,这也就让他们热爱上了化妆打扮,而且最出名的的就要数何晏这位了。
何晏作为当朝驸马,经常喜欢将自己的肌肤涂抹雪白,并且通过特殊的方式使得自己的皮肤和女性的皮肤一样细腻如雪。因此,“涂抹打扮”也成了当时士大夫的一种特殊爱好,看似是因为当时的审美眼光比较特殊,但实际上是士大夫贵族不满当时的朝廷所做的一系列事情,通过这种看似奇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罢了,竹林七贤就是当中玩的最嗨的几位了。
清淡误国
魏晋时期传承的还是汉朝的文化,汉朝奉行的是儒家文化,形成了内用黄老,外施儒术之治为魏晋名士谈理、论经、说玄提供了文化背景。魏晋的清淡之风有两种,一种是率性而为,慷慨任性的自我放逐;另外的一种就是上面所说的服用五石散等药物、扪虱而谈的自我标榜。前者代表的是魏晋风骨,后者代表的是魏晋风度。
魏晋的清淡之风最为突出的贡献就是文学思维方面的思辨发展,展示了追求独立与渴望自由的精神状态。这使得魏晋名士们出现了不遵礼法,抛弃凡世、放荡不羁,他们这些人服食药物,烂醉如泥,没有一点作为文士的模样,使得人感觉到非常的荒唐。他们纵情山水,在夜色弥漫的江河湖泊中乘船遨游,他们每个人都很颓废、郁闷不满、愤懑、豁达、飘逸,不过他们依然是魏晋文化的发扬者和传承者,他们用丰富的文笔渲染着那个世界,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苦与乐。
为何会出现这种清淡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要学会适应很多事情,一方面是战争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是朝廷的冲击,尤其是当时佛教和玄学的兴起,使得当时在汉朝所确立的儒家思想面临冲击,文人们从而走上了救国之路。
随着魏晋名士们不断的探索,文人们喜欢上了清淡这一风格,他们提倡道家的"清淡无为",使得当时各个地方的名士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下,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们不再参与官场的争斗,只想偏安一隅,做好自己。为此,他们开始躲避尘世的喧嚣,走上了归隐山林的路途。
因为魏晋时期的时局动荡不安,那时的文人们一直遭受着政治的变革,统治者思想老是变来变去。只要不符合的统治者思想的名士,为了维护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权威,便会大肆杀戮那些人,从而使得想要救国的名士们人人自危,与自己救国救民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而避免这种矛盾出现的办法,只能是改变自己内心的想法与当时统治者的想法产生共鸣,要么就是继续维持自己的思想以死明志。但是名士们却选择了折中的办法,直接逃避凡世,只要自己不管,你也找不到我就可以了,我过着我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触犯统治者的管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事实,这种办法真有用,他们躲过了杀身之祸,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的不亦乐乎。
这样的局势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其实曹魏在曹操和曹丕手中治理得不错了,在三足鼎立之下也没有出现啥大乱子。当司马家族掌权之后,所提倡的思想就转变为道家的思想,“无为而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司马家族认为礼教思想就是束缚人的枷锁。这种看似是为了平稳时局,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对仕途的鄙夷罢了。
这种思想使得当时的人们开始向往起道家所说的那种自由"仙境",让文人们继承了屈原遨游仙境的浪漫主义风格,对儒家的所注重仕途这一方面再一次的进行了嘲弄。总的来说,就是当时的司马家作为统治者其实更加注重的是道家思想,提倡的也是道家的论证观点。
而当时的士大夫文人要是拿出儒家的那一套,当然会让统治者讨厌。而当时的文士一部分都是注重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其实了解甚少,所以也只能够消极避世,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统治者的思想。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