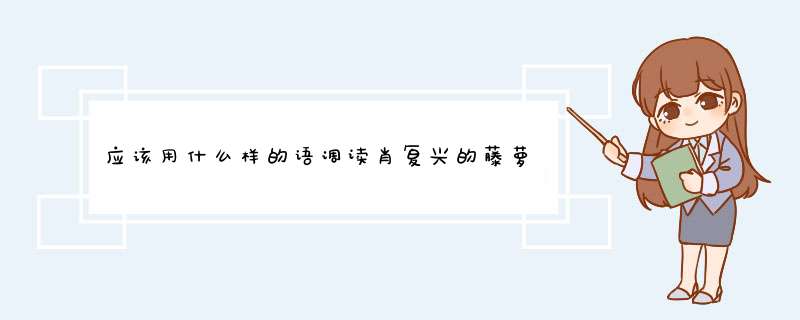
一个人喜欢去的地方,和喜欢的人一样,带有命定的元素,是由你先天的性情和后天的命运所决定的。朗达·拜恩在她的著作《力量》中,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说:“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
应该在“人和事”后面,再加上“景”或“地”。这种宇宙间的强力磁场,是人与地方彼此吸引和相互选择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属地。对于伟大的人,这个地方可以很大,比如郑和是西洋;哥伦布是新大陆。对于我们普通人,这个地方却很小。对于我,便是天坛之内,再缩小,到藤萝架下;然后,再缩小,直至这一个藤萝架下。

这是一个白色的藤萝架,在丁香树丛的西侧,月季园的北端。天坛有不少藤萝架,分白色和棕色两种,我觉得还是白色的好,春末时分,藤萝花开,满架紫色蝴蝶般纷飞,白色的架子衬托下,更加明丽。藤萝花谢,绿叶葱茏,白色的架子和绿叶的色彩搭配也协调,仿佛相互依偎,有几分亲密的感觉,共同回忆花开的缤纷季节。冬天,如果有雪覆盖藤萝架,晶莹的雪花,把架子净身清洗过一样,让架子脱胎换骨,白得变成水晶一般玲珑剔透。
一年四季,我常到这里来,尽管画得水平很臭,依然自以为是画了四季中好多幅藤萝架的画,画了四季中好多藤萝架下的人。它是我在天坛里的专属领地。


记忆中,童年到天坛,没有见过这个藤萝架。其实,童年我没见过任何一个藤萝架。第一次见到藤萝架,是我高三毕业那一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初试和复试,考场都设在校园的教室和排练厅里。校园不大,甚至没有我们中学的大,但是,院子里有一架藤萝,很是醒目。正是春末,满架花开,不是零星的几朵,那种密密麻麻簇拥在一起的明艳的紫色,像是泼墨的大写意,恣肆淋漓,怎么也忘不了。春天刚刚过去,录取通知书到了,紧跟着“文革”爆发,一个跟头,我去了北大荒。那张录取通知书,舍不得丢,带去了北大荒。带去的,还有校园里那架藤萝花,开在凄清的梦里。
第二次见到藤萝架,是我从北大荒刚回到北京不久,到郊区看望病重住院的童年朋友,一位大姐姐。一别经年,没有想到再见到她时,已经是瘦骨嶙峋,惨不忍睹,童年时的印象,她长得多么漂亮啊,街坊们说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人。不知道是童年的记忆不真实,还是面前的现实不真实,我的心发紧发颤。我陪她出病房散步,彼此说着相互安慰的话——她病成这样,居然还安慰我,因为那时我待业在家,没有找到工作。医院的院子里,有一个藤萝架,也是春末花开时分,满架紫花,不管人间冷暖,没心没肺地怒放,那样刺人眼目,扎得我心里难受。紫藤花谢的时候,她走了,走得那样突然。

是的,任何一个你喜欢去的地方,都不是没有缘由的。那是你以往经历中的一种投影,牵引着你不由自主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你永远走不出你命运的影子。那个地方,就是你内心的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的是以往岁月里的人影和光影。
我的两个小孙子每一次从美国回北京探亲,第一站,我都会带他们到天坛,到这个藤萝架下。可惜,每一次,他们来时都是暑假,都没有见到藤萝花开的盛景。这是特别遗憾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想让他们看到满架藤萝花盛开的样子。
前年的暑假,他们忽然对藤萝结的蛇豆一样长长的豆荚感到新奇,两个人站在架下的椅子上,仔细观看,然后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去摸它们,最后,一个人摘下一个,跳到地上,豆荚一下子成为手中的长刀短剑,相互对杀。
转眼冬天又到了,再来到藤萝架下,叶子落尽,白色的架子,犹如水落石出一般,显露出全副身段,像是骨感峥嵘的裸体美人,枯藤如蛇缠绕其间,和藤萝架在跳一段缠绵不尽又格外有力度的双人舞,无端的让我想起莎乐美跳的那段妖娆的七层纱舞。
想起今年藤萝花开的时候,正是桑葚上市的季节,我用吃剩下的桑葚涂抹了一张画,画的是这架藤萝花,效果还真不错,比水彩的紫色还鲜灵,到现在还开放在画本里,任窗外寒风呼啸。
肖复兴
编者按:
天坛公园是著名作家肖复兴常年光顾的消闲 娱乐 之地。他经常到那里散步、画画,并热衷于与同游人畅谈,从中体悟着四季更迭和人生情态。本版刊发他近期创作的一组《天坛春曲》,以飨读者。
早春的早晨
只要疫情稍有缓解,天坛里的人立马渐多。从这一点看人们的心情,天坛,和核酸检测一样灵。
早春二月,天气转暖,虽然花还没开,叶也没绿,地气毕竟氤氲蒸腾,特别是早晨,遛早的人,陆陆续续地进了天坛。
天坛有好多个藤萝架,分棕色和白色两种,藤萝架下,一般是北京人的天下。在运动场的西边一点,有一个棕色的藤萝架,前面是一个挺大的空场,四周有几个椅子。连翘和迎春花一开,灌木叶子一绿,藤萝花再满架紫嘟嘟一缀,这里就是个独立成章的小花园。
我来得不晚,这里已经有三拨人了。人马最多的一拨,在空场南,是十多位跳舞的大妈,在录音机播放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整齐划一,一遍遍地重复,不厌其烦,自得其乐。她们一律上身穿着毛衣,下身穿着裙子,毛衣和裙子花色不同,都很鲜艳夺目。身旁的椅子上,堆满背包、水杯和外衣。椅子旁边有两个衣架,伸着几个龙头挂钩,挂钩上,也挂满了外衣和围巾,那些外衣和围巾,也很是鲜亮夺目,好似春花烂漫,看四周灰蒙蒙的不顺眼,提前涂抹了春天的色彩。
第二拨,在空场北的藤萝架内外,是打牌的老头儿老太太。内因地制宜,人坐在藤萝架下的椅子上,牌甩在椅子中间,垫一块花布;外是自己带来全套家伙什,人坐在马扎上,头碰头,蒜瓣似地围着小折叠桌。扑克牌在他们的手中四下翻飞,蹦到椅子上或折叠桌上,像纷纷落下来的小鸟,偶尔听见一两声叫喊,很快就又安静下来。和那边舞蹈的乐曲飞扬,呈一静一动的对比。
第三拨,在空场西口,那里有一条甬道,前面有一些花木,再前面便是北天门。春夏枝叶茂密的时候,从这里是看不到北天门的。早春疏枝横斜中,西天门绿顶红墙的一角,可以看得很清楚,还能看得见三座大门中的一个半,两门之间,春节时挂上的金**的中国结,依稀可见。
不少人围在那里。我走过去一看,大家在看一个年轻的姑娘画油画。画的就是前面疏枝横斜掩映中的北天门一角。画架支在甬道旁的草地上,姑娘一手持画笔,一手拿着个简制的颜料铁盒。画面上的北天门已经清晰成型,天空格外蓝,因有红墙绿顶和中国结明亮颜色的映衬,枯树枝显得不那么萧瑟,倒有点儿像伸出的好多小手在抚摸北天门,弥漫着早春的气息。姑娘在打磨细节,一边补色补光,一边细致勾勒北天门翘起的檐角,还有和红墙相连的内垣的灰墙绿瓦。看的人都纷纷说画得真好,真像!不说话的人,眉眼里闪着光,表达的也是一样的意思。
从北天门进去,转到花甲门,转到双环亭,沿着内垣转了一圈,我回到这里,天近中午。跳舞和打牌的两拨人,都已经散去。只有姑娘还站在画架前,画她的北天门。依然有几个年轻人在看,在啧啧赞叹。
走过来一个男人,看穿着的制服,是天坛公园的工作人员,瞟了一眼画,对我顺口说了句:还没画完!我对他说:画得真不错!他说:是!昨天早晨就来了,画一天了!
早春的阳光跳跃在画面上,为画面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推轮椅的护工
在天坛,见到轮椅上的病人或老人,比其他公园里要多。大概天坛地处城内,交通方便。而且,除祈年殿圜丘有上下台阶,其他大部分是平地,林荫处也多,便于轮椅的行动、停靠和歇息。
但是,北海公园也在城内,交通也很方便,大多也是平地,为什么见到的轮椅比天坛要少许多?再一想,便是天坛四周遍布居民区,这些社区像是千层饼一样,紧紧包裹着天坛。自然,附近的人们到天坛方便,甚至不过是一条马路之隔,便把天坛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坐轮椅的老人或病人,到天坛来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最好的选择。
我到天坛发现这一现象,每逢看到轮椅从身旁经过,都会格外注意看几眼,心里会不禁感慨,这是生活在天子脚下的福分。
有一天下午,在西天门通往丹陛桥的甬道南侧,看见有好多轮椅,像约好了似的,陆陆续续聚集在这里。春天的暖阳格外温煦,打在他们的身上和轮椅上,勾勒出明亮的光影轮廓。
极个别是自己摇着轮椅来的,大多数是有人推着轮椅来的,推轮椅的人,有的是自己的家人,有的是雇来的保姆。他们都很熟,见了面,有说有笑地打着招呼,家长里短地聊了起来。显然,他们常到这里来。天坛成了他们的公共客厅。
一个小伙子俯下身来,对轮椅上的老爷子说了句话,便走到我这里来,见椅子一旁空着,便坐了下来。我打量了他一下,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眉清目秀。我问他:你是老爷子的……
小伙子说:我是他的护工。
我有点奇怪。这样推轮椅出来遛弯儿,一般请保姆,没听说请护工的。保姆是月薪,护工是每天算工钱的,费用要高很多。
小伙子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说:老爷子在医院做的大手术,你知道,因为疫情,病人住院,必须要请护工。我就是医院指派给老爷子做护工的,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老爷子看我对他护理得不错,出院的时候,要我跟着他回家继续做护工。
我说:护工是按天算钱,老爷子得花多少钱啊!
小伙子说:老爷子不差钱,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都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都有钱。
我问他:现在护工是怎么个价码?
他告诉我:我们现在都归公司管,医院和我们公司有联系,需要护工,就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每人每天公司收费是260元,给我们护工190元。
公司扣了70元,相当于工钱的四分之一还多。
在北京能找到这活儿,就算不错了。还管吃管住,干得好,病人满意,病人的家属还能私下给点儿钱。
小伙子脸上显出很满足的神情,对我说:到老爷子家里来,也不错,每天有保障,老爷子出院后恢复得不错,家里做饭,他老伴做,我就是护理老爷子的日常生活,定期带老爷子去医院复查,每天推老爷子到这里遛弯,这活儿也不累。在公司,如果没活儿干,就没工钱。
小伙子说得实在,我对他说:你找到老爷子这样的人家,是福气!
小伙子连连点头说:是!是!老爷子是个好心人,待我不错。住院的时候,他跟你一样,也问我挣多少钱,知道公司没有给我们上三险,要我自己花点儿钱,也一定上三险。我也不懂,他就告诉我为什么要上三险、怎么上三险,挺关心的。
那边,老爷子和人聊得正在兴头上,小伙子和我也越聊话越多。我知道了,老爷子家就住天坛东门附近,天气好的时候,他下午就推老爷子到天坛里,和大家伙聚聚,海阔天空一通聊,比在家里憋闷要好。
到天坛来的老头儿老太太,是分成一拨一拨的。小伙子对我说起他推老爷子来天坛自己的发现。
我对他说:是吗?说说看!
锻炼身体的是一拨,一般聚在东门的 体育 场;跳舞的是一拨,一般聚在北门的白杨树下;扔套圈的,一般在长廊西边的树下;拉琴唱戏的是一拨,一般在柏树荫下;偶尔聚会连吃带喝带照相的,一般在双环亭……坐轮椅的,一般是下午这个点儿,就到这里来聚聚了。
小伙子对自己的说法很有些得意。确实如此,天坛地方大,让大家各找各的乐儿。我想,这样一拨一拨自然而然地形成,除了喜好,主要是年龄和身体,特别是到这里来的轮椅上的老人,更是彼此同病相怜,没有别处大小圈子地位与名声等因素的约定俗成,或刻意为之。病,消弭了这些东西,除了轮椅的成色和价位不大一样,轮椅成为了平等的象征。特别是从生死线上归来的老人,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终点近在眼前,坐在轮椅上的感觉,和以前坐在沙发上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轮椅,更是帮助大家减轻了金钱欲望的分量,消除了身份认同的焦虑,甚至降低了对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孩子的期待。坐在轮椅上,大家显得一般高了,远处高高的祈年殿辉煌的蓝瓦顶,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也没什么,大家一起聊聊,能有别处找不到的开心,和病痛与衰老中的惺惺相惜。
小伙子推着老爷子常到天坛来,老爷子高兴,他也省心,还可以看看风景。如果不是给老爷子当护工,他还从来没有来过天坛呢,也从来没有想过到天坛来转转。
小伙子告诉我,他今年46岁了。这让我没有想到,我吃惊地说:你哪儿像这么大岁数,我以为你30多一点儿呢!
他对我说:我都俩孩子了,老大20,老二都13了。
小伙子是河南驻马店人,在北京干护工7年,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想回家,又怕回去回不来了。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干护工,比在老家挣钱多,一家人都靠着他挣的这些钱呢。
他对我说完这番话,轻轻地叹了口气。
老爷子挥着手,在招呼他。他站起来,朝老爷子走去,透过疏朗树枝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逆光中,地上留下长长的暗影,和斑驳的树影在交织一起。
晒太阳的教授
双方亭的中午,人气最旺。开春以后,天气渐暖,这里暖阳高照,视野开阔。不少老人坐在亭子里、走廊里的长条椅子上,老猫一样,懒洋洋地晒太阳、吃东西、冲盹儿,或眯缝着眼睛想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在心里暗暗骂骂那些恨得直咬牙根儿的恶人。
那天中午,坐在双环亭画画,忽然听见一阵歌声传过来,唱的是《三套车》,声音浑厚,用的是俄语,不禁回头一看,这个坐在走廊里唱歌的人,竟然认识,旁边围满人,正给他叫好。我走了过去,打着招呼,和他握手。天坛地方大,人又多,萍水相逢的人,在天坛能遇到第二次,不是大概率的事情。
前些日子,也是中午,也是在双环亭,也是在画画,我遇到了他。那时候,我正跟另一个陌生男人说话,他弯腰看了我的画,连声夸奖:一看就知道你画得不错,练过素描……还没等我谦虚几句,说我根本没练过什么素描,他就不容分说,紧接着又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不过,不是画画,是书法!
我赶忙夸他:那您厉害呀!
说着话,走廊这边走下来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他指着这个高个儿男人说:人家才厉害呢,是教授!
一起聊起天来,知道他们都常到这里来晒太阳,渐渐熟了起来。他家住沙子口,教授住宋家庄,离天坛都不算远。他弓着腰,笑呵呵地说:到这儿晒太阳,比在哪儿都强!然后,他问我多大了?我让他猜,他说:反正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67。教授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这时候插上话,对我说:看你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是50年出生的。我说:我47年的……
我们三个小老头儿,在这冬日的暖阳下,比谁的年龄大,像小时候比赛撒尿谁尿得远似的,还充满儿时的天真。
67岁的男人走了,教授忽然老眼尖锐地问我:你是学文科的吧?
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是学工科的,学的锻压。然后又问我: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是中央戏剧学院。没等我再说话,他紧接着说起自己,好像刚才没有说话的机会,憋得他要一吐为快: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石家庄工业学院教书。这才容得我问他:你毕业后就到石家庄了?他摆摆手:没有,先到了三线工厂搞设计……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转移了话题:教授,就是说着名声好听,一点儿没什么用。人哪,不能总调动工作,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才好,像我的一个同学,一直在上海搞设计,现在年薪30万。我的另一个同学,和我一样退休了,现在还在原单位搞设计,不算退休工资,每月还能拿一万五。
我劝他:也别这么说,心情好,身体好,比挣钱多管用!
他说:那是!我在课堂上讲起课来,就忘记了年龄,忘记一切,心情就特别好。
我们两人一直坐在走廊中的长椅上说话,面对着面。他快人快语,说话跳跃性很大,大概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在心里瞬间如水流撞击得波涛翻涌,忽然让他有些为自己的人生感慨。
突然,他说自己是学俄语的,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他学的是英语。话音刚落,见他旋风一般蓦地站了起去,黑铁塔一样立在我的面前,立刻脱口而出,高声朗读了很长一段俄语。声音高亢有力,浑厚响亮,像是平地炸雷一般,吓了我一跳。他没有看我,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眼睛注视前面,长廊外一片树木绿阴蒙蒙。他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回音在午后静静的长廊里回荡着。
朗诵结束,他告诉我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然后,他强调补充说了句: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
剪纸姑娘
三八节那天,最高温度都升到17度了,天坛公园里人特别多。想想,疫情又一年了,前些日子,春节前后,北京好几个小区疫情反复,出门的人少。现在,春天终于来了,压抑已久的心情得放松一下,天坛里才看见这样多的女人,尽管有的年纪不小了,也穿得花枝招展,手里荡漾着花围巾,伸出丁字步,到处摆出姿势照相呢。
走到丹陛桥的具服台前,我看见对面站着一群年轻女人,衣着都很鲜艳漂亮,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纸夹子。唯独一个男人,如同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般,站在她们的前面,挥着手臂,大声说着什么。
我有些好奇,今天天坛里人很多,都是三五成群,或一个人独自漫步,还没有见这么多人聚集一起,好像集体活动,庆祝今天属于她们的节日。不知是什么样的活动,每个人手里的夹子,像团体操里每个人手里的团花,或扇子舞中每个人手里的扇子吗?待一会儿,见她们蓦然打开夹子,亮出里面的宝器,要有什么精彩的节目演出吗?
我走了过去,听见那男人在招呼她们往前面去,大概是要去祈年殿。好几个女人冲他说,还有人呢!再等等。果然,好几个女人从丹陛桥的台阶上跑了上来,穿得也都很漂亮,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纸夹子。
我好奇地问跑过来的一个女人:这里面夹的是什么呀?
她打开夹子,里面夹的是一张剪纸。花团锦簇的图案,大红纸剪成,贴在夹子里,贴得不牢,风吹动得剪纸飘飘在动,像只红色的小鸟扑腾腾地想要飞出来。她赶紧合上夹子。
剪得多好啊!我夸赞后问她:是你自己剪的吗?
她点点头说是,然后,又摇摇头说:我这是用刀子刻的,第一次做剪纸,做得不好。她们做得比我好!她又指指身旁的女人。
剪纸都是自己做的?我有些惊奇。
身旁的几个女人很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是啊!
其中一个身穿浅驼色风衣的年轻姑娘,打开她的夹子给我看。她的夹子更大些,里面并排贴着三幅剪纸。左边一幅是大红灯笼下两个跳舞的孩子,右边一幅是红旗下敬队礼的两个少先队员,中间一幅是瑞云烘托中的祈年殿,因是整幅剪纸镂空,四围红纸把祈年殿团团围住,衬托得格外鲜红耀眼。
我问她:真是漂亮,都是你刻的?
她指着右边的一幅说:这是她刻的。说的是站在她前边的一个比她年龄稍大的女人。那女人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一扭身,挤到前边去了。
中间的是我刻的。她对我说。
这幅祈年殿让你刻得多好看啊,真是了不起!
听到赞扬,她抿着嘴笑了。
我问她:你们今天这么多人,每个人手里都有剪纸,是要搞什么活动吗?
她说:是啊,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待会儿我们一起拿着剪纸合影照相!
每个人手里扬起自己做的剪纸,和祈年殿一起合影纪念,这真是不错的节日庆祝,挺有创意的!
我再次由衷地赞叹,然后,指着剪纸,对她说:能让我照张相吗?
她伸出双手举起夹子,头歪在一旁,别挡着三幅剪纸,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镜头中,我看见姑娘秀气的脸庞对着剪纸微微地笑着,纤细的手指夹住夹子的边儿,让剪纸完全展露出来。我看见风衣袖口露出白衬衣蕾丝的花边,披肩发在三月春风中轻轻飞扬。
2022年3月10日于北京
绘画/肖复兴
复兴:梦回童年,我的岁月流年
这本长篇小说是1987年出版的,事隔17年,现在,朝华出版社又要再版它,总让我也对那些时刻感到惋惜,不禁让我想起许多和这本书相关的往事。
也许,这是当时第一本触及中学生男女感情的长篇小说吧,虽然早已经时过境迁,如今依然有当年的老读者和现在年轻的读者写来热情的来信,在网上依然看到许多当年读过它的读者对它的感情。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收到青岛徐鹏、于晓倩等6位高二同学的来信,他们说他们是"伴随着您的作品成长的",让我脸红;他们给予我批评和鼓励,让我感动;他们希望现在能够找到《早恋》、《一个女学生的日记》等书,我写信告诉他们,这些书就要再版了。这些素不相识的读者,即使只是三言两语,却是发自心底,毫不功利,却是那样的真诚,真的让我很受感动。我实在应该知足,仅仅因为这样的一本小说,过去了17年,还有那么多的朋友惦记着你,关心着你,在这个功利而冷漠的世界上,该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让我感到格外惊奇的是,几乎走到哪个地方,只要能够遇到和这本小说中的那些中学生一起成长的年轻人,我都能够遇到曾经读过它的人。作为一个作者,这样意外的邂逅,常常满足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我常常对自己说:你还不应该感谢这本书吗?是它延伸了文学和人生的半径,才让你能够拥有这样比艳遇更频繁也更持久的境遇。
两年前,我到湖北荆州,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所住的宾馆的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打来的,她先问我你是那个写过一本书叫做《早恋》的肖复兴吗?我告诉她是,我写过那么一本书。然后她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她现在想见我一下,因为她的手里有一本《早恋》,希望我能够为她在书上签个名,留个纪念。我说我的名不值钱,如果你愿意,我还是很乐意为你的书签名。她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我请他们两人坐下,看到了那本17年前出的书,已经翻得破烂不堪了,大概经过了不少人的手。那个男人对我说,听说您住在这里,我请我家的这位亲戚一定要找到您,是想告诉您,当年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好赶上您这本书出版,但当时老师不让我们看您的这本书,而且,班里只有这么一本,只能够在底下偷偷地传看。因为看完了还得还给同学,我就从头抄到尾把书抄了一遍,想自己留下慢慢再看。只可惜我抄的那本《早恋》最后不知传到哪个同学的手里,毕业之后也没有还给我。听了他的话,我真的很感动,再没有比中学生读者对文学更真诚、更清纯的。
我还不住想起另一个人,另一件事。
因为一本《早恋》,当时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偶尔我也回信,但一般很少。只有江苏常熟的薛雯是一个意外,我竟然和她通了16年的信,时间这样的长,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缘起于书,属于以文会友。16年前,薛雯是一个16岁的江南小姑娘,在读初三。和荆州的那个同学的老师反对看《早恋》不一样,她的老师向她推荐了这本稍稍引起一些波动的《早恋》。大概书中的内容和她那时年龄的心情很吻合,她读后很激动,给我写来了第一封信。她的字体在中学生中是绝对秀美的,现在的中学生能够写一笔那样好的字,已经很少,因此,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谁想到我给她的回信,她并没有收到,一直到了大约一个学期之后她来了第二封信时,我才知道,马上给她回了信。就这样,竟然通了整整16年。一个16岁的小姑娘,长成了32岁的大姑娘,她的孩子今年夏天过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日子过得快得让我惊讶,16年来一直坚持着最原始的手写的通信方式,让我自己都觉得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其实,不过是一本
忘记了是从哪一年秋天开始,桂花开时,她开始在信中夹一些桂花寄给我。但肯定是她迈出学校大门走到工作岗位她长大以后。桂花是一种成熟的花,和秋天许多果实成熟一起才绽放在枝头。从那以后,每年江南桂花盛开的时候,她都不会忘记寄我一些桂花。那花香很是浓郁,未拆信封,便香透纸背,弥漫四周了。
如今,还有多少成年人能有这种类似浪漫的情致呢?也许,只有她这样童心未泯的孩子了。借助现代化的电话,大人们连信都懒得写了,新年圣诞顶多寄一张画面和贺辞千篇一律的贺卡,谁还会想起那三秋桂子,一片秋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