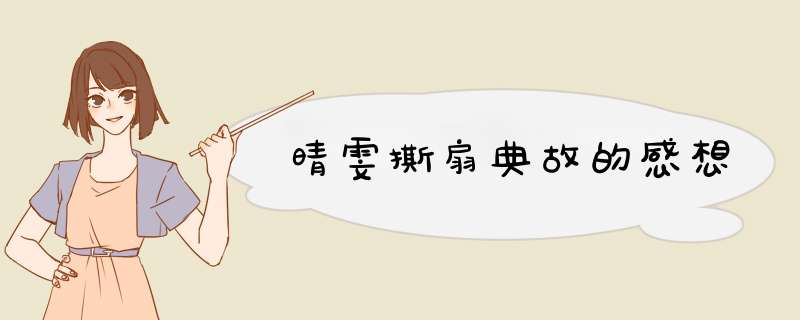
撕扇子是发生在晴雯跟宝玉吵架之后,在这边宝玉有段台词:「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再联系到前文,晴雯为何会跟宝玉吵起来呢?看看原文:
「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林黛玉倒不觉得,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平常摔了琉璃缸、玛瑙碗都没事,今天摔了把扇子宝玉就骂人蠢材了,为何?因为他本来就不开心,很明显是在迁怒,而晴雯会和宝玉起争执,核心就在宝玉的迁怒。
宝玉和一般主子的不同就在於,他跟人交往注重的是性情是否相合、相交之间是否真心,并不以身份、利益等做考量(所以他不愿去虚伪地应付贾雨村之流),也是因为宝玉的这份不同流俗(书中宝玉第一次摔玉时贾母说了「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这样的话来,可见丫头们是种什麽样的存在),所以晴雯待宝玉才有所不同,并不是因为宝玉脾气好就捏软柿子(再说宝玉脾气也不见得真那麽好,少爷脾气还是有的,前面还想撵李奶妈跟茜雪呢),对晴雯来说,宝玉以待一个「人」的方式、以真心来对待身边的丫头,所以晴雯便也以真心相待回应(我使用真心二字并不是指男女之情,而是说晴雯愿意敞开内心回应宝玉,不然就会以对待贾母、王夫人等的方式来应对宝玉了),这是合乎宝玉心意的(参看第二十回,宝玉连对贾环这种须眉浊物都「不要人怕他」、「反生疏了」,可见他多讨厌礼法依照身份地位在人与人之间所划出来的隔膜,他重视的是人的真心)。
晴雯高看宝玉,是因为宝玉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宝玉的身份。所以,当宝玉开始拿丫头出气,之前还踢了袭人,想必当时晴雯对宝玉是既伤心又失望的,由此也才引发了两人之间的冲突。
由这两段看来,宝玉之所以会说出「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样一段话,个人觉得这是宝玉在藉机跟晴雯说明,他还是那个愿意和人以真心相交的宝玉,之前是他错了。而晴雯也在这时相信了宝玉、原谅了宝玉,两人之间的芥蒂藉由撕扇子一笑泯之。
也是经由这段戏,宝玉想通了晴雯生气的原因,也是自此回之后,晴雯在宝玉身边的份量开始重要了起来,后面还让他去送帕子给黛玉,就是因为宝玉发现了晴雯也是懂他的心思的人(宝玉的心思就是希望人与人之间以真心相待),看出了晴雯那「心比天高」的本质。
当时的丫鬟,他们基本上是被当作「物」来对待的,可以随意给人、可以随意发卖,他们是被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的族群,而晴雯的「心比天高」,只不过是希望能以「人」的身份活着罢了。我想宝玉是欣赏晴雯这个本质的,所以在宝玉跟前,晴雯这个微小的愿望才算略微实现,可惜不过是脆弱的镜花水月,终难成真。
从这一回之后,晴雯在宝玉心中的份量才越来越重,最终还获得了宝玉以「芙蓉女儿诔」这样一篇奇文的赞美。
1 以钱说为题的文言文
为你奉上一篇,是关于把钱称为“阿堵物”的,表示轻视,请你参考:
1、出处《世说新语》;
2、原文是: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①。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3、翻译:
王夷甫一向崇尚玄理,常常憎恨他妻子的贪婪卑污,口里不曾说过“钱”字。他妻子想试试他,就叫婢女拿钱来围着睡床放着,让他不能走路。王夷甫早晨起床,看见钱碍着自己走路,就招呼婢女说:“拿掉这些东西!
2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用文言文怎么说1吾携尔尔携钱。
2我引汝携钱。
延展阅读:
1 文言文
文言文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加工。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定义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纪到西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六朝、唐和宋时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
特点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2这句话可能是根据网上的一首原创小诗演绎而来的。并不知道是否还有小说也有这样的话。一位上海的妈妈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写了首诗,原诗是“春天来了,我们去旅游吧!我带着你,你带着钱,三亚也好,长江也罢,横穿唐古拉山口,暴走腾格里沙漠。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哪怕是天涯,哪怕是海角!”
楼上的似乎都不是很好哦,只是我个人意见。。。
“郎顾之争”的实质是什么?
有什么更好的词来描述由郎咸平引发的这场争论,它已经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公众对经济学家从动机到学术能力的全面怀疑,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公众非理性。当然,这仍然不能准确地描述这场争论,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站在“经济学家”这一方,而有一些公众也并不同意“公众”的观点。要准确地描述这场争论是困难的,我只好用“郎顾之争”来代表这场争论的全部内容,希望不要引起误解。
简单的回顾
这场争论,是从学术圈内开始的,发生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郎咸平通过分析具体的样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国企改制”普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并提出停止“国企改制”的建议。他的研究结论虽然也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却不被经济学“主流”所认同。对于“主流”而言,郎咸平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原因有两个,第一,郎咸平辛辛苦苦地研究得出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国有资产流失”。既然结果大家早就知道,研究再辛苦也没有意义。第二。郎咸平提出“国企改制”应该停止的建议,在逻辑上就不被认可,因为“主流”的逻辑早已设定:“流失”谁都知道,但“改制”必须进行。
“国有资产流失”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主流”讳莫如深,大家都不说,只希望在这个炸弹引爆之前,尽快将国企交到私人手中。虽然时有怀疑之声出现,但“主流”都还可以搪塞,“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如果郎咸平不是用最严格的经济学方法提出这个问题,“主流”的搪塞还可以继续下去。所以郎咸平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是那个说了实话的孩子。
郎咸平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国有资产流失”由公开的秘密变成一个显问题。舆论哗然。“主流”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破坏性,马上下重手企图扭转舆论:“这是反对改革!”阶级斗争工具重现江湖。在后来对公众的指责中,有一条是说公众用了阶级斗争手法,“主流”忘记了,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使用了阶级斗争手法,只是效果非常不好。
“主流”的主张是明确的:即使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制也要继续。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主张非常有把握。但替代了郎咸平成为“主流”争论对手的公众却不接受这个主张,公众的主张实际上是这样的:甭管国企改制是否应该继续,必须先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两种主张没有办法找到交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残酷的现实:“主流”竟然找不到一种方法,既可以继续改制,又保证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存在一种方法,可以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在制度层面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发生,将这种方法交给公众评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公众绝不会像有些“主流”想象的那样不讲道理。可惜,“主流”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供公众评价的改制方法,或者叫做改制程序。于是,争论就成了关于“是否允许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正方显然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主流”的战术是试图将争论的焦点转移到“是否应该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来,但公众并不反对改革,公众仅仅是不同意“允许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即使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也要继续改制”,这种主张缺乏说服力。为了增加说服力,“主流”引入了一个辅助概念,叫做“长远利益”或者“根本利益”,他们试图说服公众,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国企改制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作为经济学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根本不存在“长远利益”的概念,甚至根本不允许存在“长远利益”的概念。“主流”丝毫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参与了将争论带离学术范围的行动,埋下了自己的阵线崩溃的伏笔。
“长远利益”或者“根本利益”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概念,它一方面表示主张长远利益的人没有自私的动机,而另一方面表示接受长远利益的人应该克服眼前利益的冲动,当“主流”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将动机引入到争论之中,他们只是到后来才发现,他们正是被“动机”所彻底击垮。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公众接受了一个概念,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个人动机。当他们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的弊病的时候,其中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企业代理人的个人动机与企业利益相冲突,而国有企业的体制决定了这种代理人个人动机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国有企业必须改制。就在国企改制的这场争论发生之后,“主流”仍然在继续这种有关动机的普及工作。结果,公众以“主流”之矛攻击“主流”之盾,提出一个“主流”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们的个人动机是什么?“主流”辩解说自己的动机是国家的富强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他们的意思等于说,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定有个人动机,而经济学家没有个人动机,这样的解释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更不幸的是,公众发现了“主流”在改制以后的企业里领取“车马费”,“主流”忧国忧民的辩解立即成了自吹自擂的笑话。动机,是经济学最有力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了“主流”经济学家最大的敌人。当动机都受到怀疑的时候,“主流”最后的底线----学术,也就必然会失守。在“主流”背上放上这最后一棵稻草的是丁学良。这种最不可接受的论战方式之所以可以发生,完全是因为“主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信誉,不要说继续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他们连自辩的信誉都没有了。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曾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明明知道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但他们仍然轻率地站出来为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担保”。他们将支持私有化和支持一个具体的私有企业主混为一谈的时候,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既然改制的程序不可公开评价,其中必然存在黑箱操作;既然存在黑箱操作,就必然存在违背市场原则的违法行为。“主流”为自己轻信某个资本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解读争论
对这个争论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将这场争论简单的总结为公众的一次不负责任的情绪发泄本身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语言,但这种非理性的语言双方都有使用;有时双方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在阶级斗争时出现的语言,但这并不是这场争论的主流。整体而言,争论仍然是基本理性的。解读这场争论,第一,它不是一场破坏改革的邪恶爆发;第二、它不是无知公众的无理取闹;第三,它也不是一次失落情绪的发泄。它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类似的争论,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缺乏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他们会以为有邪恶势力要发动无知的公众置他们这些改革先驱于死地。从他们在争论中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争论的评价来看,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几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众早已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公众关心的是权利的分配。
“主流”将这种对权利的诉求单纯地理解为“仇富”心态,这是一种偏见,或者至少是一种误解。公众,或者说公众中的主流,并不“仇富”,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公众十分平静地接受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公众不仅接受部分人通过市场“先富起来”,他们甚至将这种人视为英雄并当作自己的榜样;令公众不可接受的,是有些人通过非市场的手段“先富起来”。由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市场开放并不同步,通过非市场手段“先富起来”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谴责,公众虽然也参与到这种谴责之中,但他们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性和耐心,他们寄希望于政府以及学界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令这种现象越来越少。而“改制”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使有一部分地位特殊的人可以通过“改制”先富起来,这是公众绝对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本来还应该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学者。公众区分得非常清楚,他们并不“仇富”,他们只问致富的过程。应该比公众更清楚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个时候却糊涂了,将反对“非市场致富”说成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富”。如果这不是有意制造混乱,就一定是经济学家自己混乱了。
指责争论“不学术”是意义的,因为争论本来就不是学术争论。更糟糕的是,这种指责的后果极其严重,它肯定导致学术受到伤害。在这场争论中,“主流”从一开始就在指责公众“不学术”。这种指责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只会毒化争论的环境和气氛。公众所争并非学术问题。经济学有很多学术问题,在学术范围内争得不亦乐乎,公众从来没有参与过,也没有打算参与。学术是经济学家的事,与公众没有关系;但公共政策就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它与公众有关,公众不仅可以参与,而且应该参与,经济学家不应该将学术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混淆起来。“主流”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使用“学术”做武器,打破了学术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一旦打破,最后受伤害的一定是学术,是学术的独立性。
任何公共政策,背后都有学术背景,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取舍,没有必要知道政策背后的理论在学术上有多正确,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也要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他们和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处于完全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熟悉却有不太熟悉的政治学规律。一个对于学术来说非常重要的界限是,当公众反对并选择放弃一项公共政策的时候,对于这个公共政策背后的理论来说,它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受任何影响,这就是学术的独立性。反过来的道理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不能因为自己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就指责公共政策的反方“不学术”。如果将“是否学术”用作公共政策讨论的武器,那么这个武器双方都可以使用,当公众也拿起这个武器、指责“主流”“不学术”的时候,“主流”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只好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相互安慰:“他们不学术、他们不学术”。公众本来就不打算参与学术,你又何必以“学术”惧之?
将“是否学术”引入到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之中,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由于公共政策的取舍而影响到理论的学术地位;它还有可能产生另外的后果:使学者与社会之间应该有的相互信任荡然无存。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出发,你真的可以肯定你的理论就那么正确吗?从关于理论的哲学出发,答案是“不一定”。尤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更应该坚信这个答案。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来说,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随时都会发生,环顾其它的市场经济社会,类似是争论也时有发生,在美国的电力企业管理效率与公共用电保障之间的争论、在英国的铁路管理效率与行车安全之间的争论、在香港的公屋管理效率与公屋用户福利之间的争论,与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争论其实十分相似,虽然那里的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样的争论,但他们从来没有指责对方“不学术”,原因很简单,这不是学术争论,不能用“是否学术”作为武器。
这不是一场学术争论,也不是一次“阶级斗争”。虽然双方都使用了一些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阶级斗争术语,但那都只是“阶级斗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工具,与这场争论的本质无关。继续带着“阶级斗争”有色眼睛观察这场争论,只会使争论环境更加恶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公共政策的争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地对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引起不同的评价,这种不同的评价就形成针对公共政策的争论,这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举个经济学家熟悉的例子,经济学有足够的理论,得出一个非常学术的结论:累进税制会对市场的效率有负面影响。手里掌握了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面对相关公共政策的争论呢?类似是例子太多了,类似的公共政策太多了,类似的争论太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本上不存在举国赞成的公共政策。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取舍,与和公共政策相关的理论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基本无关。而这场争论实际上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社会将出现多元化,从现在开始,今后无论什么公共政策出台,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人群,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作为公共政策咨询人的经济学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公众诉求的实质
经销商的展销厅里有一辆最新款的奔驰汽车,每一个人都想把它开回家去,但真正把它开回家的是张三。每一个没有得到这辆汽车的人都会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张三而不是我得到了这辆汽车?张三的回答非常简单,那是因为我支付了足够的代价,如果任何人支付相同的代价,他都可以将同样是汽车开回家。这个理由足够充分地解决任何人的疑问,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这样的原理,无论是得到了汽车的人还是没有得到汽车的人都认可汽车的这种分配方式,不会引起争执。这就是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原理,也是市场之所以有效率的根本原因。即使你只需要一把葱,钱少了人家也不卖,怎么吵架都没有用。
而国企改制的情况如何呢?根据改制理论,国有企业的股份应该交给私人拥有,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争论中公众并不反对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这个意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应该交给哪些私人拥有。李四因为改制获得了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一个没有获得股份的人都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李四而不是我获得了这个股份?李四如何回答?
“主流”帮李四回答说,因为李四有贡献,所以他可以获得股份。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学里面没有这样的理论;市场中的公众反应告诉我们,市场也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市场中,要素的贡献是无法区分的。没有人知道资本的贡献有多大,劳动的贡献有多大,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在不知道贡献的时候,要素的回报如何决定呢?用事先的契约决定,而不是事后的“自报公议”来决定。企业已经做好了你要分一份,似乎是合理的,但事先你有承诺做不好你应该负什么责任吗?企业确实有用股份来奖励企业家的制度,但没有那出那么股份多来“奖励企业家”的制度。
市场制度的原理是这样的,它用自愿交换消弭了关于权利主张的争议,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市场有效率。如果没有自愿交换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争议就一定发生。大家都喜欢有自己的汽车,但没有人为汽车的归属天天吵架,因为那是自愿交换的结果。国有企业股份的归属,违背了自愿交换的原则,所以引起争议。所谓自愿交换,并不是买卖双方躲在一边你情我愿,这不叫自愿交换,这叫私下交易,黑箱操作。自愿交换必须是自愿成交与自愿放弃同时发生。市场原则是,任何权利,“出价高者得”,出价低的人自愿放弃出价,所以对权利的归属没有异议,市场就是这样降低交易成本的。国有企业股份的归属,出价者的范围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面,公众根本没有出价的机会,于是也就没有自愿放弃出价的机会,必然发生争议,这就是国企改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每天在课堂上教授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家恐怕低估了这个交易成本的巨大程度。
有这样一类公共政策,它们的目的是对社会的财富进行某种形式的再分配。我们虽然都接受市场的自愿交换原则,但对这个原则的后果却有不同的评价。这个原则有两个后果,一个是财富的增长,一个是财富的分布。虽然接受市场原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对财富必须进行再分配也已经是社会共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再分配,而在如何再分配。由于对再分配的程度有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就构成了对此类公共政策的争论或者讨论,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财富的再分配不是根据市场原则来分配的,解决这种争议的办法也是制度,但它不是市场制度,它叫做民主制度。
国有企业改制,还不是这种公共政策,它并不是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它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笔财富的分配。这种财富的分配,不适合在“效率与公平”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因为“效率与公平”只适合用来讨论财富的再分配。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对财富的再分配,而是对财富的分配。历史遗留的财富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归国家所有,比如文物;另一种是将其私有化,比如国有企业。而私有化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平均分配,另一种是“出价高者得”。如果不是这两种方法,必然引起社会中的个人关于财产权利的争议。这就是在这次争论中公众诉求的实质,它们是关于财产权利的诉求,是市场中最基本最纯洁的诉求。理解这种诉求,本来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天职,可惜却被经济学家忽略了。
有经济学家说只有经济学家研究市场的效率,这话确实不错,因为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如果发生了对财产权利的争议,用什么办法解决才最有效率;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只有通过市场手段分配财富,市场中才不会出现争议。可惜的是,“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并不意味着你是个“经济学家”就知道。
经济学家的责任
经济学家是有社会责任的。
有人以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站在大众的立场说话,错了。谁是大众?当大众分为利益集团的时候,站在什么利益集团的立场才算大众的立场?也有人以为,经济学家是责任是站在穷人的立场说话,否则就是没有良心,这也错了,经济学不是穷人的理论,它也不是富人的理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本身是不分穷人和富人的。经济学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人道关怀是另一回事。
站在社会中哪一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说话,没有人可以干涉,也没有人可以指责,这是经济学家的自由,而不是他们的社会责任。
也有人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效率。很多经济学家将在中国实现私有化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看法。企业是私人所有比企业的国家所有效率要高一些,这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多年的学术结论,当他们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对中国仍然有这么多国有企业存在感到非常着急,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就在中国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一旦有知识的人在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之后,将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危险他们没有察觉,这个危险就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很可能根本不能用来改造世界。
“主流经济学家”所知道的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的、非常关键的特征,这个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而且有些解释相当完美;但是,这个理论却不具备任何改造世界的功能。“国企改制”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学理论可以非常完美地解释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什么比私有企业低,但经济学理论却没有说如何才可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根据“改制”的理论,除非采取非市场的手段,否则国有企业是不可私有化的,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与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经济学理论说,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转让,或者叫做不可交易。解释非常完美,但如何将“不可转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呢?经济学理论无能为力。
所以,改造世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那么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是说真话,是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而随意解释经济学理论,是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随意向公众隐瞒一部分经济学结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咨询,他们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将公共政策甲的全部经济学后果如实地告知公众或者决策者,同时将公共政策乙的全部经济学后果也如实地告诉公众或者决策者,至于公众或者决策者选择公共政策甲还是乙,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事了,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已经完成,剩下的是完成公民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了。如果公众恰巧不赞成某个经济学家热爱的政策选项,该经济学家是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公众的。平静地接受公众的选择,在政策上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在学术上继续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这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经济学家,特别是有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家,绝不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来推行经济政策,这也是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人,法律都应该同等对待,穷人不能因为穷就受到忽视;富人不能因为富就受到苛责。保证这一根本原则能够得到落实的是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即使是“为民除害”,也不能违反法律对程序的规定;任何伟大的目标,都不能构成违反法律程序的理由。法律保护一切财产权利,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财产权利法律都同等对待,私有财产不能因为“自私”而被剥夺,公有财产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效率”而被剥夺。保护财产权利的方法依然是程序。法律对财产权利的转移有一系列的程序规定,违反这些法律程序的,就叫“侵犯”财产权利,为宪法所禁止。法律为保护财产权利所规定的程序中,有一个核心的程序,那就是,任何财产权利的转移必须符合财产权利人的真实意愿,一个辅助的程序是,权利代理人必须在权利所有人的授权范围内行动。即使是“改革”,也不能违反法律对财产权利转移的程序规定;任何伟大的目标,都不能构成违反法律程序的理由。坚持这个原理,是一切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在没有找到国有资产的所有人之前,经济学家不应该主张转移这些财产,这才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经济学家有为资本辩护的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只为一个局部的资本辩护,这个自由就有被滥用的危险。国企改制,社会资本并没有被赋予平等参与的机会。反对如此“改制”的“公众”中应该还包括这些被剥夺了参与机会的资本。经济学家有为“企业家”代言的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只为部分“企业家”代言,这个自由也有被滥用的危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只是企业家的一部分,而“改制”企业又只是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这些“企业家”通过“改制”,可以无偿[1]获得企业股份的比例和理由可以适用于为私人企业工作的“企业家”的身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私人企业的所有人绝对不会同意。同样的比例和理由,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估计也不会同意。
当经济学家为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或者具体的“企业家”代言的时候,代言自由的滥用危险就变成了现实的危险,“主流”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学家并不具备为某个企业辩护的专业知识,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的人叫做律师。
经济学家不仅有为资本代言的自由,而且有做独立董事的自由,同时还有对公共政策发表看法的自由。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将个人利益与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是经济学教给公众的看问题的方法。当有个人利益牵涉其中,公信力就必然下降。无论你如何坚信自己公私分明,“公”众不“信”,何来“公信”力?当然,这个问题与社会责任无关,仅仅与个人做人的原则有关。
结论
如何看待经济学家自己,如何看待公众;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知识,又如何看待公众的诉求;如何区分学术立场和社会责任,如何区分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如何认清社会已经多元化,又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处。这场争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争论本身,也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畴。
权利主张是市场效率的最终动力,财产权利一定要争,“不争论”就没有市场效率了。平息权利争议的手段只有制度,市场是这样的制度,法律也是这样的制度,民主还是这样的制度。用非市场、非法律、非民主的方法解决有关财产权利的争议,叫做专制。如果今天可以将公有财产分了再说,明天也可以将私有财产分了再说。
楚庄王初登基时,日夜在宫中饮酒取乐,不理朝政。后来臣下用“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神鸟故事启发他,并以死劝谏,终于使他决心改正错误,认真处理朝政,立志图强。楚国终于强大起来,楚庄王也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在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一个大臣叫蔺相如,因为有功而被奖赏。老将廉颇不服,就要跟他吵架。而蔺相如不跟他计较,尽量回避廉颇。他说:“秦军不敢侵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我们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一旦吵起来,国家不就危险了么?所以,我们应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廉颇听见,十分后悔,于是,他披着荆棘向蔺相如请罪。这也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