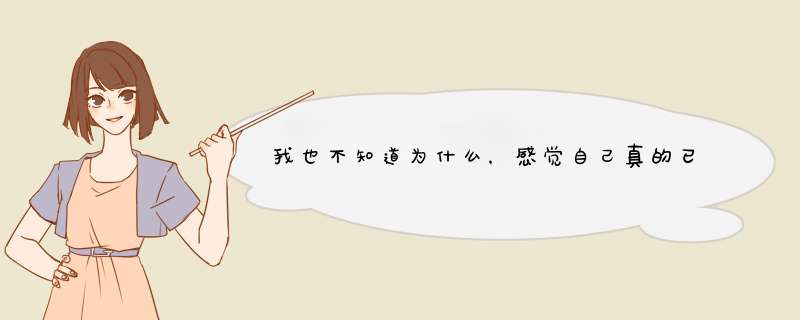
你现在说的所有内容总结一下就是,导致你现在的尴尬处境的所有原因都是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说白了就是你不肯花时间学习造成的,学校里的东西说白了弱智都会,学习成绩也是取决于你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几乎与学习能力无关,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失败和你过去的懒惰是必不可分的。你至少浪费了20年的时间,如果几句话就能改变那么也太瞧不起努力了二十年的人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大概就只有成人高考了,你可以先积累点资金,买一台电脑或者上网吧查阅成人高考的具体运行方式买书自学或报名成人高考班或者两者同时进行,然后半工半读争取拿下几张文凭,如果这点行动力都没有,只肯意*觉得生活空虚那你就永远空虚下去吧。
我们最高原则:不论对任何困难,都决不屈服。-(法)居里夫人
每一个生不逢时的人,都有不同的酸甜苦辣,而生活总让我们遍体鳞伤有人安于现状,有人不肯。因此安于现状的人这一生也就是如此了,不肯的人只好加倍努力另寻出路。
不同的人生,每一段传奇,他们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正如董竹君这样的传奇,她的一生更加的不平凡,她不肯安于当时的生活也不能安于,只能另寻他路。
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痛苦的秘密,才能度过这一生,一个人要经历了多少磨难,才能破茧成蝶飞过世间的苦海,提起锦江饭店大多数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可是对于它的创办人董竹君,却有很多人对其不甚了解。
命运最好的一端靠自己争取,不好的那一端别无选择。正如那句话所说,贫穷是万恶之源。董竹君早年的不幸,正是源于家庭的贫困,虽然生在上海,可是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母亲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因为家里太穷,董竹君的弟弟妹妹们都因为营养不良夭折了。
面对生活上的贫困,董竹君的父亲还是让董竹君去学堂上学,想让董竹君用知识改变命运。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董竹君才上学没几年的时间,她的父亲就病倒了。从此不仅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还因为给董竹君的父亲治病而欠下高利贷。
在董竹君十二岁那年,家里迫于生计,也为了还钱,董竹君被父母卖到青楼,得到了三百块大洋,而因为董竹君年纪太过于幼小所以制作清倌人,卖艺不卖身。可青楼毕竟是勾栏之地,到底怎么才能在鸨母被迫她卖身之前逃离此地。
董竹君十分担忧,后来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那个男人夏之时。夏之时当时身材高大,模样也英俊潇洒,出身于小康之家。早年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加入同盟会。
推翻清朝后,被选为当时四川省得副都督,后来成渝两政府合并,他担任重庆镇抚府总长。当时虽然已将辞官,但在所有人看来,夏之时也绝对算的上是豪门了。
当夏之时提出要为她赎身时,董竹君却回绝了他,并且讲明如若日后吵架他就无法以这个为借口,当时的董竹君才年仅十五岁,在自己身陷囹圄的时候却还有如此心思,不忘给自己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可见她的智慧与老成。
董竹君在青楼的鸨母逼她破身的前夜,她用酒把看守灌醉,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虎口,与夏之时结婚,婚后因为时局动荡他们二人就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是董竹君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日本夏之时为董竹君请了家庭教师,教她功课和日语。他们的爱情也有了结晶,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相继出生。
董竹君白天努力学习,带娃,操持家务,晚上熬夜读书,生活及充实又忙碌。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可是董竹君偏偏靠自己的努力。因为容貌终究会老去,只有让自己从心灵深处变得强大,才能真正的无所畏惧。
回国后因为政治的原因站错了队,被解除了公职,终日浑浑噩噩后来竟然吸食上了鸦片,对董竹君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好的时候是恶语嘲讽,坏的时候甚至对董竹君拳脚相加。董竹君终于忍无可忍,她提出了离婚,但是董竹君选择净身出户只带走四个女儿。
在夏之时的眼里,董竹君离开自己,是无论如何都生活不下去的。于是夏之时与董竹君打赌,赌约期间他们分居五年如果要是董竹君和四个孩子没有在上海饿死,他就把手里的肉给董竹君吃。
事实很残酷。在最初的几年里董竹君的所有努力,都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后来迫于生计董竹君先后在当铺当了自己的衣物、首饰、女儿的小提琴,生活俨然已经陷入困境。
既便如此在面对夏之时的求和,董竹君还是选择离婚,也应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自由与爱情》那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从此,在董竹君的余生里再无风花雪月,只有笑傲风云。
也许是否极泰来,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董竹君开了一家饭馆,叫锦江川菜馆。由于经营有方,服务周到,味道也是一等一的美味,生意自然是蒸蒸日上,财源滚滚,一些上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比如杜月笙、黄金荣都是那里的常客。喜剧大师卓别林访问中国的时候,曾慕名前来品尝了下香酥鸭,并对此赞不绝口。
在抗战期间董竹君开办了印刷厂,秘密印刷先进刊物和宣传报。而所有的经费都由她本人出资,她还以菜馆做为掩护,救助了大量的仁人志士。锦江川菜馆也成为了秘密联络点。
新中国成立之处,董竹君深知国家百废待兴,将多年所得的钱财都捐助给了国家,而后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委的指令,以锦江川的人员为班底,建立了锦江川饭店,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经常招待外来的政府人员。
在特殊的年月里,她不幸入狱,但是她在狱中,仍旧活的从容,她不愿意被冷酷的狱中生活打败。在七十岁生日那天,董竹君在狱中庆祝自己生日快乐。
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受到的挫折而感到挫败,可是我们的那些经历,与董竹君相比,又何足挂齿呢?对于董竹君来说她的一生都是向前走的,她的两次选择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我从不因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弃信念。
而董竹君也教会了我一个道理,没有设置限定的人生才足够精彩,当我们觉得生活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时,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跑、去跳、去拼搏,如果不这样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多优秀。
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像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会绝交,终生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33。因为周家是一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他直接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每天的生活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方式34,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她太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家里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我们想想,上个世纪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是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35。所以他觉得自己拼命做,却总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1924年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36。想像一下,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真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人和睦地来往,打架的结果就是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37,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加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知识分子表面虽然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其实还是一个谜,很多的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更有甚者说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情人之类的.我见过不少于三种的说法,我觉得以上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 但是从周作人的绝交信看来,我觉得周作人认为鲁迅有对其妻有不轨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要不这么好的亲兄弟为何就会反目成仇.只有这件事才是可能的,金钱也不会导致老死不相往来啊. 当然这很大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诬蔑.我个人认为这肯定还是跟这个女人有关,但鲁迅成为伟人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鲁迅朋友的一些说法,另一些说法就看不大到了. 当然鲁迅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我是不会带着恶意去推测他,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说法总是不能让人信服.
文|江徐
秋雨潺潺,我坐在窗下看书。哲学类的通识课程,讲到了道家的智慧。早上散步,路边折了一支迷迭香,插在瓶中。气息浓郁,闻之心痛,又神思飘远,想起远远近近的人与事。
朋友提及母亲的周年临近,忙忙碌碌,很多事情还没去做。很想安慰,又觉得旁人说什么都是徒劳,回了一句消息,自己都觉得无力。但是那种感觉,我太知道了。
三十几年前,母亲在六甲小镇上生我。不是难产,是医生操作失误,母亲死在了手术台上,据说当时血淌不止,那位医生畏罪逃跑了。后来我读书识了字,在抽屉里翻到父亲一封信,是他向有关部门申诉,请求公正解决与赔偿。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只能认命。这是母亲的命,父亲的命,我的命,也是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亲人的命。
很少想起母亲,每年生日不能不想起。
三十多年过去,医院还在那里,装修了一番,墙壁刷得雪白。去年夏天,我一个人在镇上走走,走到医院门口,看到房顶上那块宣传标语依然如故,也赫然入目:向白求恩学习。
难道有错么?
没错。所以我并不觉得讽刺。
母亲、死亡,向来是家人的禁忌话题,无故不提。小学二三年级,有一次学校要填一张表格,其中一栏,关于父母的职业,外公外婆为之为难,当校长的邻居恰巧在旁,他说,就写个亡字吧。彼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亡”字,平静的触目惊心,如同它响亮的发音。
对母亲零星的、吉光片羽式的印象,来自旁人言语间的拼凑,还有我自己的想象、领悟。
外公外婆生养了三个子女,确切说四个。第一个是女儿,八九岁时生病,死在了外婆怀里。如此,我母亲成了老大,下面还有舅舅、小姨。
外公年轻时候在上海滩拉黄包车,拉着拉着,时移势转,拉进了上海公交 汽车 公司。虽然是小职员,好歹有了个工作单位,而且在那个年代,工作职务可以由子女顶替。多大的便宜啊。
据说,本来是让老大去顶替的,母亲让给了弟弟,她要在家照顾父母。外公性格懦弱,外婆一向体弱,对大女儿很是依赖。
假若母亲去上海顶替外公的班,也就不会认识父亲,也就不会有我,也就不会有这一行字,舅舅的人生轨迹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命运无所谓好坏,凡是情理上解释不了的事,就归咎于命运吧。
从我记事起,外公那张镶在玻璃相框里的“光荣退休”证就一直摆在堂屋柜面上。如今外公的遗像挂在东墙头,他的退休证依然摆在原处,逢年过节、周年祭祀,家人都会认真擦拭。
祖母在世时,冬天会扎一条宝蓝色头巾,当年母亲给她买的。祖母告诉我,母亲很会做人。
想来母亲勤劳、要强、为人处事很周到,甚至有点强势,不然怎么早早年纪就当家呢?隔壁的寡妇兰侯多次在我面前说,你娘很能干哦,十四五岁,就一个人背着锄头下田干活了。也听其他亲人说过,母亲手巧,衣裤鞋帽,样样都会做。有一次,外婆难得心情平静地对我感慨:那时候,她看到人家做衣裳,站在边上看几眼,回来就能自己摸索着做了。
以往,每到酷夏,家人都会赶在大晴天翻箱倒柜,把陈年旧裳一件件展开来,摊在竹帘上暴晒。外婆指给我看,这件衣裳是你娘的,这双鞋子是你娘的。言语间,唉声连连。我当时不以为意,也不太知道悲伤。从未拥有、感知过,也就无所谓失去的痛苦。
前年冬天,我突然想起老屋门前屋后的黄百合 、菖蒲、凤仙花。又想起幼年晒夏,会从三门橱顶翻出很多书,有毛选集、文人传记、琼瑶的言情小说等等。后来老屋翻新,这些书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我隐隐感觉到,这些花草与书都与母亲有关。我希望它们与母亲有关。于是在微信上向舅舅询问此事。舅舅根据回忆告诉我:以前,外公在上海工作,外婆经常去上海看病休养,里里外外都交给我母亲,她除了种田,还要管舅舅和小姨读书。她很节约,不会买书看。但那些花草是我母亲种的。
1986年的夏天,舅舅23岁,半工半读,考上了上海电视大学。七月份休探亲假回老家,那是他最开心的探亲假。他哪里想到,二个月之后,是他遇到的最痛苦的变故。
那个夏天,在老家,擅长画画的舅舅还为母亲创作了一幅工笔画,他至今收藏着。
我让舅舅有空了找出来给我看看。大概忙忘了,或者别的原因,舅舅至今没有发过来。我也不会重提,有些事,说一遍就够了。
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我很想看一眼。
说起那些花儿,我对黄百合印象最为深刻。它长在东房间的南窗下,紧贴着墙。七八月,它慢慢长出一粒粒黑色的小果子,再开花,一朵、两朵地开,每一朵花都很大,因为饱满而下垂,伸出长长的花芯,顶端有花粉。每次去茅房,从它身边过,都会很小心,以免花粉粘在衣服上。
舅舅说, 这些花草,谢了之后第二年还会自己长出来。是的,一年又一年,从我有记忆起,它们就长在那里,自开自谢,直到老屋翻新,它们被拔除,没了踪影。在知道到这些花草是母亲种植之前,我就很怀念它们。
今年大年三十,要从箱子里翻出母亲的遗像。相片包裹在一条赤红色呢毯里。家人在厨房忙,我提前搬开上面的小箱子,掀开大箱盖,看到毯子上面盖着的一件衣裳。往年,也看到它,今年格突然格外在意,大概因为没人在一旁。
这件衣裳是淡紫色的,针脚稚拙,算不得精细。大概是母亲初学的“作品”,淡紫的布料,稚拙的做工,让我想到母亲的少女心。那时候,她应该还很年轻,十七八岁?二十出头?
看着这件衣裳,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突如其来的、很陌生、却又天然最深的亲切感。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再多看一会,但又不愿被家人看到我对它的端凝。
我遗传了母亲的血脉,却没遗传到她的性格。烟火生计的实务,我一直是笨手笨脚,也不感兴趣。人情世故上,我性格犟、轴、脾气臭,不会说场面话,有时伤了别人却不自知。
有一天洗澡,我观照自己与人交往时的表达——当面时木讷得不知说什么,事后在脑子里回顾,每一句都有了美妙的回应。为之羞愧,为不能重回那个场景重新将对话完美进行而耿耿于怀。
如此想着,我由儿女情长想到了母亲。听闻母亲年轻时,有时在话头上被人占了上风,回来想想,觉得这样那样回复才服气。她总要找个机会,把话补上,把理夺回,才甘心。
我有点像母亲吧,但到底也没太像。
不曾看见过的人事,不会出现在梦中。 弗洛伊德这个观点,在我这里获得亲证。从未梦见过母亲,但有梦见过她的遗像,梦里,和现实中一样,摆在堂屋柜子西头。
很多年后,我才悟出,母亲是家庭的牺牲者,她似乎是心甘情愿地牺牲。母亲把工作的机会让给弟弟不算,还决定自己留在家里,以便便照顾父母,尤其母亲。所以,要找个愿意入赘的男人。找到近三十岁,找到了我父亲,一是因为他愿意入赘,二是因为他是高中生——那时有点稀罕。
听闻,母亲在世时,经常和父亲吵架,为之哭泣,婚姻并不幸福。
头周年,我还未谙人事。往后的十周年、二十周年、五十冥寿,还有每年的新年祭祀,我因为所处位置的尴尬,非常害怕面对这类事,又不得不面对,渐渐学会了在心里安慰自己: 一切都将到来,一切都将进行,一切都将过去 。以至于到了事情当天,还不忘默默安慰:你看,现在不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吗?
人情恩怨,烟尘琐务,最烦人心。
前几年,母亲六十冥寿,照理要操办的,因为人情人心之故,作罢。外婆又为之叹气,觉得不该。我认为这样很好。兴师动众的祭祀,是世俗的仪式,活人为之劳心费神之余,还有多少精力缅怀?为了缅怀而来不及缅怀,岂不可笑?
怀念是一个人心底的事,也是生命中细水长流的情。“山月不知心底事,水风空落眼前花。”如此,足矣。
母亲亡于31岁,假若在世,今都已经65。她的生命止于31岁,在我心里、我想象中,她便永远是31岁,不再老去。
而我会越来越比她老。
作者简介:江徐,80后女子,十点读书签约作者。煮字疗饥,借笔画心。已出版《李清照:酒意诗情谁与共》。点击右上角“关注”,收看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