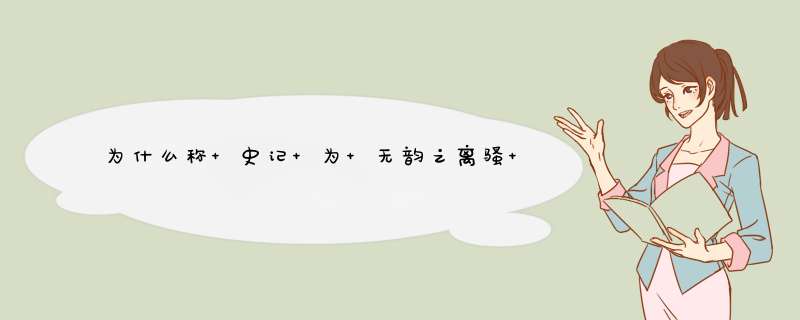
鲁迅对《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我觉得,对于第二句的解释,虽有道理,但有些肤浅,还应做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若论文学性,诗三百篇也自有特色,但
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我推测主要有两点:
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姑援引鲁迅在谈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的那段原文来看: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所说“恨为弄臣”,是说司马迁对于自己所处的“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少卿书》)的地位深为不满,“感身世之戮辱”,是说司马迁痛心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这些,都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动因。而屈原与司马迁的身世甚为相似:“事怀王为左徒”,也属“弄臣”之类;被谗放逐,怀石投江,也与司马迁遭受的大磨难相似。屈原为抒愤懑,遣牢骚,遂作《离骚》。所谓“离骚”,即牢骚、愁思也。司马迁对屈原是有深切的了解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深知,《离骚》之作,源于怨愤牢骚,而他自己也正复如此。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实际上,鲁迅本人也是牢骚忧愤之人,同心相知,他对两千年前屈原和司马迁的心境——牢骚、怨愤与愁思,是相知甚深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史记》深刻地解读为“无韵之《离骚》”。
二是缘于鲁迅对《离骚》、对楚辞的偏爱。鲁迅对《离骚》的评价非常高,他在《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中写道: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与《诗经》比较,《离骚》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因而其影响往往超过《诗经》。例如,《楚辞》是“凭心而言”,即我写我心,表现的是真性情,与《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相同。鲁迅对于《离骚》(以及《史记》)这种“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喜爱的。这与鲁迅超迈峻洁的人格和不同流俗的文学好尚有很大关系,与他喜欢魏晋文章,喜欢嵇康是一致的,与他不苟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也是不会将《史记》赞为“无韵之《诗经》”的。鲁迅对《离骚》的偏爱,还特别表现在他一生酷爱楚辞文字之美、寓意之深。他的诗文,每每借用、征引《离骚》的文辞和典故,如他写的诗句“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无题》),“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湘灵歌》)等等。他曾经集《离骚》句两度书写条幅。所集《离骚》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之先鸣”。第一次是求人书写而自勉,第二次是自书而赠友。第一次是请乔大壮书写的,这条字幅至今还悬挂在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正因为鲁迅对《离骚》的文学特质非常喜爱,又看到了其与《史记》在文学特质上的相同之处,他便将《离骚》移来评论《史记》,也因而将《史记》比喻为《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对于《史记》的这两句评价,既非常准确,又包含个人情感和好尚,通过以上对“无韵之《离骚》”的分析,可以体会出一二。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分三类,本纪、世家、列传。这是按传主的地位和影响划分的。帝王的行事关系到全国的政局,对后代政治也有很大影响,是立国之本,故其传记称“本纪”。《史记》中有十二篇“本纪”。王侯是一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世代保有其国,对全国政局有一定的影响,故其传记称“世家”。《史记》中有三十篇“世家”。列传则是为人臣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立传,如《滑稽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有“列传”七十篇。
但这仅仅是一个大略的划分,对于某些历史人物,作者有他的特殊考虑。例如项羽,他并未统一天下称帝,但作者高度评价了他在反秦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说:“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所以将他列入本纪,可算一个特例。陈涉则是又一个特例,他出身低微,是所谓“瓮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起义后虽自立为王,但为时仅六个月。之所以列入世家,是因为在秦王朝的严密统治下首先发难,的确是非常之功。司马迁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写道:“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卒亡秦,由涉首事也。”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在传后全文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来代替自己下赞文。这种不寻常的做法,更足以说明司马迁所看重的是功业,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后来班固写《汉书》,几乎完全照搬《史记•陈涉世家》原文,并去掉“世家”的名称,将陈涉与项籍合为一传,为“列传第一”,其贬抑之意不言自明。史家对历史人物态度之不同,于此可见一斑。
肯定会有些影响,作为一名撰写史书的人,比较客观的修史是最基本的素质,但主观的情感肯定也会渗透在所修的史书内,司马迁在撰写的《史记》中也有自己情感的流露,不过对历史的大方向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应该是影响不大。
摘 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者利论司马迁与班固不同的史学风格[J]科教文汇,2008(11)
[4]陈贵成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J]梧州学院学报,2009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