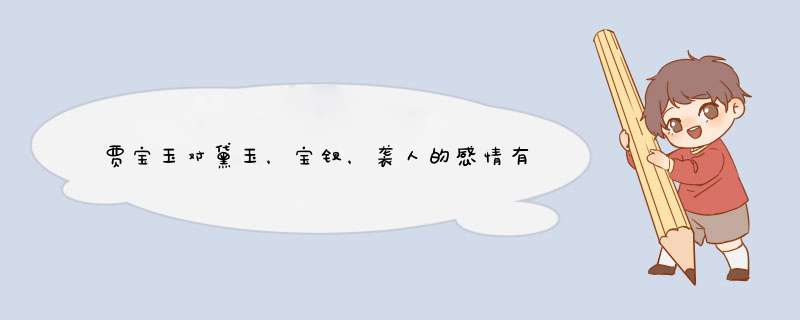
作者:泽漆
来源:知乎
1 宝黛之恋
黛玉自不必说。两人一相遇就如天雷勾动地火,一个眼神间就欲倾尽前世的情天恨海。宝玉最爱黛玉,不仅仅因为那胎里带来的纠葛,更因为黛玉乃是那个知他爱与痛的人。
鲁迅说:华林之中,遍布悲凉之气,呼吸感知于其间者,惟有宝玉一人。
宝玉的悲凉,不是为这末路中的家族,而是对生命离去的虚无感的一种恐惧。所以,他爱这世间的花草鸟兽,爱这园子里个个灵秀清妙的女孩子,成了痴,成了魔。他天真,而周围的世界却以“功名利禄”的标签来指责他不求上进。大观园初试才学时,他的敏捷和奇想被贾政斥为“一肚子杂学”。
宝玉最恨别人劝他读书,黛玉从不劝宝玉读书,宝玉并非贪玩懒惰,只是不喜欢读“正经书”而已。他愿读庄子西厢,不爱做八股文章,他厌憎仕途经济那一套,却愿意跟河里的鱼天上的鸟喁喁轻谈。
当宝玉因为跟金钏戏谑,跟琪官交往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被他老爸暴揍一顿时,来探望他的黛玉居然是期期艾艾地说了句:“你从此可都改了吧。”若是这句还可以视为黛玉有规劝之意,下面,宝玉的回答,坐实了他们是一个阵营里的:“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只有黛玉,能懂这公子哥浮花浪蕊的调笑背后,有多少悲凉,依恋,和执着。她对宝玉那些不良嗜好,从不像宝钗袭人那么不以为然,看见宝玉脸上的胭脂痕,也只怪他带出痕迹来,怕人跑到贾政那里学舌,让宝玉吃亏。当袭人开始拿“准姨娘”的俸禄,她还和湘云一块儿去祝贺,完全心无芥蒂的样子。
宝黛之恋,是缘定三生,木石前盟。然而抛却这些作者的修辞,他们的感情时建立在对于生命之美的共同感知和不舍上的——逼向生命的本真,去为所有美好的事物扼腕可惜。
2 金玉良缘
“莫失莫忘,不离不弃。”
我最喜欢这两行话。然而叠加在宝黛的三生之缘上,却又多惊心动魄。
宝玉对钗姐姐有没有感情呢?有的。且不论宝玉一直都在讨好园子里的各类女孩子,单是取麝红串子那一段,便让少年晃了心神。宝玉到底是红尘里抛不开丢不下的人,他怎么不会被宝钗的理性、冷静、智慧、通达所吸引,所带动。
然而宝玉斥责她“大好女子沽名钓誉”,因此,这两人,再无法有更近的沟通。
宝玉憎恶别人将他朝所谓正道上驱赶,男性世界的气味让他眩晕,他不能想像一个女人也对那样的世界心存向往,不管他对宝钗怀有怎样的好感,只要她一句劝学的话,就知道她与自己不是一路人,道不同,不相与谋。
所以宝玉从未想见过,和宝钗会有怎样的未来。
然而宝钗本是性本空无的人。纵使爱宝玉,纵使知道自己永不会是那人心头真爱,亦无所妨碍,有山中高士般不忧不惧的淡泊宁静。
3花气袭人知昼暖
最后要说袭人,骂她的人很多。她在宝玉房里是侍妾的身份,以“侍”而言,她是宝玉身边第一个妥当人,宝玉的生活起居、大小事务一样少不了她。她回家探望病母,众丫鬟连银子放在哪都不知道。而袭人既为宝玉的妾,批评最多的便是她的改嫁。但是实际上宝玉对袭人,并没有如黛玉一般的情深,而是更偏重于世俗一面。袭人不懂宝玉,然而她的的确确是可以埋家食井水的妥当人。
宝玉是一直害怕失去袭人的。十九回,袭人被家人接回去过年,宝玉闲极无聊,去她家探望,在一堆女孩子中瞅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大概出落得格外齐整一些,宝玉就留了心,回去问袭人。袭人说这是她的两姨妹子,又说起她各式嫁妆都备好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到“出嫁”二字,已经大不自在,又听袭人说,连她自己,也终究是要离开的,一时间情难以堪,竟至于泪流满面。
袭人这是说重话来故意警醒宝玉的。她实没有宝玉那么在乎,对宝玉的顺从和尊重,也不过是来自于柔顺的天性,就像之前在贾母那里一等一的“心地纯良、恪尽职守”一样。故之后改嫁也坦坦荡荡。这份骨气,倒也不辜负了宝玉对袭人发的一番议论。
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主要由:1、林黛玉是病秧子,和她结婚不利于繁衍后代。2、林黛玉不倡导科举,贾父贾母不会乐意。3、封建社会,家族利益占据主导地位。
实实在在的从家族的利益、从人情的角度等等各方面,来加以一种深刻的描写。所以这样的爱情故事才能够深深地打动你,才能够让你对爱情悲剧的必然性有着一种深刻的感受。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说的:“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中有价值,并且是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与林黛玉的性格,都存在着A、B两面。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世俗名利、地位和声望的追求。宝钗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圆滑世故”;但骨子里,她却实在是一个耿介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在小说里,每至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给家长们留下诸如“忌讳”、“离格”、“不祥”之类负面印象的,几乎总是宝钗;而明确表示自己渴望“邀恩宠”、“独立名”的,几乎总是黛玉。《红楼梦》全书又恰恰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无疑是作者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一种暗示。
2.从客观能力上看,宝钗显然比黛玉更善于处世,更善于解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但从主观意愿上看,黛玉对各种世俗利益、名位的关注和向往,却又远远强过于宝钗。相对而言,宝钗比黛玉处于更为优越的位置。但宝钗却根本不屑于尘世的争名夺利,甚至不屑于元妃的特别恩赏;反倒是黛玉连小小几枝宫花,都要斤斤计较,非得比出个势利不可。一个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所以,我们说,在《红楼梦》(脂评本原著)中,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3.从形象解构的角度来看,黛玉身上其实更多地承载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某些特质;而宝钗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老庄哲学的审美观。黛玉是外道内儒,宝钗是外儒内道。所以,作者用“有凤来仪”与儒家皇权意识的“双关暗合”,来暗点了黛玉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又以“蘅芷清芬”颇具道家色彩的“未扬先抑”、“别有洞天”,揭示了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人格魅力。
4.钗、黛以上这种性格上的交错、反转的关系,犹如《周易》中太极图所揭示的哲学原理:世间万物,俱负“阴”而抱“阳”。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鱼” 的“鱼眼”,恰恰为“阳”;“阳鱼”的“鱼眼”,恰恰为“阴”。由此,亦可以看出《红楼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尹、列之道家文化的尽力汲取之态。
5.在小说中,袭人、晴雯、金钏、小红,俱为钗、黛的影子人物。其中,金钏的真情与烈性,正与宝钗相通;小红的心机与世故,正与黛玉相通!袭人、晴雯,作为钗、黛的一对“外影”,对映了她们各自性格的“正面”;而金钏、小红,作为钗、黛的一对“内影”,则照出了她们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作者此种设计,亦是《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性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种直观体现。
6.《红楼梦》本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对立产物。作者尤其反对那种“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的庸俗模式。但后人对《红楼梦》的解读,特别是许多“拥林派”评红家对《红楼梦》的解读,却恰恰陷入了所谓“才子”、“佳人”加“小人”的思维定势之中,有意无意间就要把宝玉、黛玉、宝钗分别同这三种角色对映起来。而袭、晴、金、红四影结构的存在,特别是金钏与宝钗、小红与黛玉之特殊关系的存在,对于打破以上这种固化的成见,恢复原著的本来面目,无疑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和作用。
7.曹雪芹的一生始终处于“出世”与“入世”的双重困境之中。在理智上,他看得透功名利禄乃至男女情爱的虚妄,但在情感上,他又放不下对往昔繁华以及旧日情缘的留恋。而钗、黛两位女主角的设置,就多少反映了作者内心的这种两难。排除枝节的差异,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来看钗、黛,她们亦与作者一样,均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她们又同为“敏感的弱者”,都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的、惟恐受到伤害的生存状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才“使二美合一”,将她们看作了一人。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庚辰本第42回总评),以及畸笏叟所说的“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庚辰本第22回眉批)。
8.然而,作者却并不满足于仅仅将自己内心的困境表达出来,他还时时考虑着如何用理智来战胜情感,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样,原本“合一”的钗、黛二人,在小说精神救赎的主题上,又出现了“分殊”的情形。其标志即是看她是否成功地接受了“癞头和尚”及“跛足道人”这一僧一道的点化。黛玉是点化之路上的失败者。她拒绝了“癞头和尚”为她设计的疗病方案,反而代之以服用世俗的“人参养荣丸”等药,其结果是终其一生也不能摆脱世俗占有欲和小儿女之情的困扰,只能在尘网中越陷越深。宝钗却成功地接受了癞僧的点化。她的“冷香丸”乃集尽四时白花之蕊,雨、露、霜、雪,甘苦二味,苦修苦炼而成。这象征着她在历尽人间甘苦、世态炎凉之后,能最终超越一切世俗之情的羁绊,而以一种大知己之爱和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推动宝玉悟道、出家,复返大荒。诚如脂砚斋所说:“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很明显,二者的高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应该说,曹雪芹本人的情况,更接近于前者,但后者才是他所追求和向往的那种理想之态。
9.钗黛的A、B两面性,也同样反映在了她们的爱情方面。这就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三角关系:宝玉与黛玉“似近而实远”,宝玉与宝钗“似远而实近”!从表面上看,宝玉与黛玉好似心心相印、呼吸相通;但实际上,他们在内心深处却始终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刻的隔膜和疏离。宝玉把黛玉当作唯一“不说混帐话”的知己。可事实上,黛玉的头脑中却并非没有所谓的“混帐思想”,她也并非真的不拿“混帐话”来劝谏宝玉。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一类“禄鬼国贼”的态度上,宝、黛二人的价值取向几乎判若天渊。宝玉宁死也不愿与贾雨村一类的人物相接触,而黛玉作为贾雨村的学生,却从未对她的恩师表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所谓“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宝玉却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邀宠”、“立名”的思想!宝玉与宝钗的情形则正好相反。从表面上看,钗、玉二人好像“志不同,道不合”,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实际上,他们的深层次性格中,倒反而蕴藏了更大的相近和共通之处!宝玉最厌恶那些贪鄙官僚。无独有偶,宝钗也是这么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她的那首《螃蟹咏》即是对以贾雨村为代表的那些贪官污吏的最为尖刻的讽刺。宝钗劝宝玉读书仕进,并非是要他也成为贾雨村一样的“禄蠹”,恰恰相反,乃是希望他通过掌握权力,来惩治、消灭这些丑类。正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二人的选择看似相悖,其实却正好反映了其根本一致的立场!而更重要的是,宝玉、宝钗都对佛、道一类“出世”理念,有着几近于本能的偏爱。宝玉《天上人间》谜:“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关心的是来自仙家的消息。宝钗《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则感叹世人难以领会佛法、禅宗的真谛。而事实上,宝玉对禅宗的最初感悟,也正是来自于宝钗的引导和推介(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对宝玉思想意志层面的影响,其深度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黛玉。所以,脂砚斋才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10.以上情形,也就决定了宝玉一生的情感,必然会有一个巨大转折的过程:由开初的独“专情”于黛玉,最终转向放弃这种“专情”,反过来与宝钗亦建立起同样的真情至爱。黛玉是宝玉富贵年少时,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知己。而在宝玉贫寒落魄之后,能与他一道战寒斗霜、患难与共者,则不能不惟宝钗一人而已。显然,原著中这样的转折,应该发生在八十回以后的佚稿之中。但实际上,也用不着等到八十回以后,在现存的八十回本中,曹雪芹即为这一转折的过程,提供了多处暗示。譬如,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金玉姻缘赞》、第34回“宝钗探伤”、第35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58回“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确例证。
11.上述这些暗示宝玉终将移情于宝钗的文字,与小说中那些看似表现宝玉独爱黛玉的地方,亦构成了“风月宝鉴”之“反照”与“正照”的效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原著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六组针锋相对的正、反面文字组合:第一组:正面文字:《终身误》(第5回);反面文字:①《金玉姻缘赞》(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②《红楼梦引子》(第5回)。/第二组:正面文字:①宝玉拒斥湘云(第32回),②黛玉的心理活动(第32回),③宝玉“诉肺腑”(第32回);反面文字:①黛玉探伤(第34回),②宝钗讥讽贾雨村(第32回),③宝钗探伤(第34回)。/第三组:正面文字:“情中情因情感妹妹”(第34回);反面文字:“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35回)。/第四组:正面文字:“宝玉焚书”(第36回);反面文字:①黛玉劝学(第9回),②黛玉《騄駬》谜(第50回),③“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第五组:反面文字:宝玉梦中的喊骂(第36回);反面文字:“通灵玉蒙蔽遇双真”(甲戌本第25回回目)/第六组:正面文字:“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第57回);反面文字:“茜纱窗真情揆痴理”(第58回)。——脂砚斋提醒读者:“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又云:“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眉批)显然,如果读者仅仅从上面列举那些“正面文字”,来解读《红楼梦》,而看不见其针锋相对的“反面”,那么,十有八九是会把小说的本旨给弄颠倒的!
12.最后,作者以“莫怨东风当自嗟”和“任是无情也动人”,分别概括了黛玉、宝钗同宝玉的情缘。何谓之“莫怨东风当自嗟”?因为在曹雪芹的原稿中,宝、黛之不能结合,并非是出于什么外部势力的干涉。相反,贾母、凤姐等人,倒始终是“木石姻缘”的支持者。而恰恰是他们自己在深层次性格上的隔膜与疏离之处,才导致了其爱情上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隙”。黛玉之未嫁而逝,绝非宝、黛的不幸,从某个意义上讲,倒是因此而避免了更大的悲剧!又何谓之“任是无情也动人”?因为如前所述,在原著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凭借自己在禅宗、老庄一类“杂书”、“杂曲”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悟道”,推动他出家为僧,进而得以复返大荒。——《山门寄生草》、《邯郸梦赏花时》二件,即为明证!在当时那个社会,一般妇女都是嫁夫从夫,终身相倚。宝钗既嫁宝玉,做了他的妻子,亦理当如此。可她这个做妻子的,却主动地引导了丈夫出家为僧。按世俗的观点,这应该是非常“不情”之举了。但宝玉却深知,宝钗的这种“不情”之举,倒恰恰是出于对他的一片至爱,一种感天动地的自我牺牲式的至爱!宝玉自己亦深深地为之感动。故而才以“任是无情也动人”,来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钗抽得“牡丹”签,黛玉抽得“芙蓉”签,那“芙蓉”签上,还特别注明:“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芙蓉”为何还必得“牡丹”陪饮呢?原因无他,因为在小说中,宝钗与黛玉又同为宝玉的知己。二人合起来,则构成了宝玉不同时期的最爱!
13.在《红楼梦》的“色”、“空”二字当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而宝钗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小说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宝玉、黛玉的“木石姻缘”,更多地同作者放不下往昔繁华的心态相联;宝玉、宝钗的“金玉姻缘”,却更多地与作者看得透人生虚幻本质的理智相通。所以,小说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一个承载了作者的“悲情”,一个寄托了作者的“高情”!在《红楼梦》末回“情榜”中,黛玉得到的评语是“情情”,宝玉得到的评语是“情不情”,宝钗得到的评语是“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黛玉何谓之“情情”?因为她以“情”为情——以小儿女之情为情,以世俗之情为情,故终其一生也跳不出为情所困、为情所陷的孽障。宝钗又何谓之“无情”?此“无情”,非彼“无情”也。“无情”正是至情!看似“无情”,却是情到极点,感人至深。故又曰:“任是无情也动人”。而宝玉的“情不情”,就正好处于黛玉“情情”与宝钗“无情”(至情)之间。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三人一体”的结构!
14.《红楼梦》问世至今已正好二百五十年。什么是这部小说最本真、最永恒的精髓?笔者以为,这既不在于《红楼梦》“批判”了什么“封建主义”,也不在于她“歌颂”了什么“伟大的爱情”。而恰恰体现于其所宣扬的“色空”思想之中。《红楼梦》的“色空”,是“大色空”,是包罗人间百态、世上万象的“色空”。其中,宝、黛、钗的故事,是“情”之“色空”。元、迎、探、惜的故事,是“运”之“色空”。王熙风的故事,乃“势”之“色空”。秦可卿的故事,乃“*”之“色空”。如此等等。而红楼一梦,万境归空,给情天孽海里的痴男怨女们当头棒喝;替功名富贵场中的仕子儒生辈警钟长鸣;为普天下的失意者指引脱离苦海的道路;向尘世间的孤独人提供聊以慰籍的精神家园。这样的人文关怀,才是此书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形态而永放光芒的本质所在!
在《红楼梦》中,黛玉主要代表了“色”的这一面。前面,我们在第一、二章里,分析了黛玉的性格。从表面上看,黛玉应该是清高的、孤傲的、叛逆的、纯情的;但骨子里,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名利、地位、声望的强烈渴求。而事实上,她所谓的“清高”、“孤傲”、“叛逆”,在很大程度上,还恰恰是其求名求利却求之不得的产物,具有一种“酸葡萄”式的情结!我们看到,在元妃省亲的节骨眼上,恰恰是黛玉的“攀高”、“邀宠”表现得最为积极(第18回);在贾母率王夫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关键时刻,又恰属黛玉的潇湘馆处,接待得最为殷勤、礼数最为周详(第40回)。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些赞美皇权、渴慕功名的诗句,亦多出于黛玉及其恩师贾雨村之手,诸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第1回)、“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第18回)、“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第18回)、“双瞻御座引朝仪”(第40回)、“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第50回)、“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第76回)等等。[注26]甚至,连黛玉的居所,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精雅无比的潇湘馆,也起了个了正名,叫做“有凤来仪”,被作者有意地赋予一层“颂圣”的含义!小红是黛玉的“内影”。第24回,小说描写小红“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却被秋纹等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处,脂砚斋一连写下了三条同黛玉有关的批语。一曰:“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二曰:“争夺者同来一看。”(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三曰:“争名夺利者齐来一哭。”(庚辰本第24回双行夹批)另一处,脂批则毫不含糊地指出:“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可见,无论是曹雪芹,还是脂砚斋,在他们这些“圈内人”的眼中,黛玉都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灵慧过人,却持才傲物,争名夺利,不肯罢休的人。黛玉固然也有非常“纯情”的一面,是所谓“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但这种“情”,却又是建立在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占有欲的基础之上的。她爱宝玉,便不许宝玉再同别的女孩(确切地说是像她一样的贵家**)单独接触,仅仅因为这些女孩有可能威胁到她的地位,却丝毫不顾及宝玉“爱博心劳”的本性。她将宝玉认做“知己”,却并没有宝玉那种憎恶官场、厌绝名利的思想,相反,倒时不时地幻想着能依靠“木石姻缘”的成就,来实现自己“立名”傲物、“压倒众人”的夙愿。所以,黛玉的所谓“纯情”,落脚于现实之中,最终还是脱不了一种极其世俗的价值观的窠臼。这就是杜丽娘所说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可见,所谓“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所“通”、所“警”者,还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儿女情长这些东西,亦有这种爱情观背后的名利之心![注27]从《红楼梦》神话开篇的角度来看,黛玉显然是一位思凡下凡的仙子形象。她来自于“西方灵河”,却把世俗的名位观、价值观,当作自己情感的最终归依,终其一生亦不能自拔。故一言以蔽之,我们说,黛玉是“身处世外而心向世内”!
而宝钗却主要代表了“空”的这一面。前文中,我们亦分析了宝钗的性格。小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描写,道出了她原是一个素性淡泊、深具老庄气质的女子。宝钗从小便不喜簪花抹粉,不爱富丽闲妆,只偏好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见甲戌本第28回侧批)。第7回,薛姨妈说:“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脂砚斋随即批云:“‘古怪’二字,正是宝卿身份。”(甲戌本第7回侧批)宝钗的居所蘅芜苑,正名“蘅芷清芬”。这“清芬”二字,也的确合乎她的此种身份!人言宝钗“世故圆滑”、“八面玲珑”,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关键时刻,真正敢于坚持个性,以至于得罪家长权威的,恰恰不是黛玉,而是宝钗!第22回,在元宵节灯谜诗会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直抒胸意:“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就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见蒙府本、戚序本第22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的节骨眼儿上,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说:“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第28回,面对元春的特别恩赏,宝钗居然“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反过来竟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为幸。这种蔑视世俗权威的态度,在黛玉而言,则更是绝不可想象的了。与黛玉诗“缠绵悲戚”中夹藏着“邀宠”、“立名”相反,宝钗的诗风往往是“端庄敦厚”里暗含着“孤高”、“愤世”。这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譬如,《凝晖钟瑞》:“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第18回),《白海棠咏》:“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第37回),《螃蟹咏》:“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第38回),《牙牌令》:“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第40回),《镂檀锲梓》谜:“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第50回)等等,均带有一种高人隐者讽时骂世,又洁身自好的意味。甚至,就是那首被后世许多陋儒狂骂不已的《临江仙柳絮辞》,所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实际上,也正体现了陶渊明“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见梁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风骨与气概!故众人皆为之“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第70回)[注28]而更重要的,宝钗的这种淡泊名利、愤世出世的思想性格,还恰好为癞僧、跛道择中,成为了太虚幻境对宝玉的精神世界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关联点、介入点。如前所述,在曹雪芹后三十回佚稿中,正是宝钗以自己在禅宗、老庄等方面的“博知”,启迪并引导了宝玉的“悟道”、出家,宛如何仙姑之劝吕洞宾莫要贪恋人间的风光,应尽快返回天界一般。《寄生草》、《赏花时》二件,俱为明证!从《红楼梦》的神话结构上讲,宝钗显然没有黛玉那样明确而显赫的前世来历(“西方灵河”畔的“绛珠”仙草),但这个生活于红尘世界中的女子,却被癞僧、跛道赋予了推动所爱之人,即全书男主角贾宝玉,下定决心,拔离凡尘,复返仙界的任务。她的爱情与婚姻,也最终摒弃了一般世俗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占有欲,而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自我牺牲、自我超越的精神,放在了首位。所以,我们说,宝钗是“身处世内而心向世外”!
作者把钗、黛二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就昭示了“色”与“空”两种精神对宝玉的吸引和争夺。概要地讲,黛玉之“色”,是由“世外”指向“世内”,正与宝玉的“情迷”联袂;宝钗之“空”,由“世内”指向“世外”,正与宝玉的“情悟”相通!通灵宝玉下凡历劫,他的前半生自然离不开黛玉之“色”的陪伴——非如此,则无以将“情迷”发挥到极致。可如果宝玉当真同黛玉结合了,他的后半生就会欲海深陷,永堕泥犁,无法完成由“情迷”到“情悟”的转变,“佳偶”也将终成“怨偶”——除非宝玉对黛玉也敢撕破脸面,情断义绝,但这显然是作者所更不愿写,也不忍写的局面。怎么办呢?要想让通灵宝玉拂去其心上的迷尘,复显其本来的真性,则又少不了宝钗之“空”的龙象之力了。读者如果仅仅从一般小儿女之情的层面——也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A面”上着眼,自然会感觉宝玉对宝钗、黛玉、湘云三人,“素厚者惟颦、云”,而独与宝钗“素不契”;但如果真要上升到超离凡尘的大知己之爱——就是本章所称“宝玉情感的B面”的高度,一切就全都颠倒了过来:宝玉与宝钗是“素不契”中包含着更大的“素契”!——“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为了一个共同的“愤世”、“出世”的理念,他们可以“眼向云霞”,把世俗的爱情观、占有欲搁在一边,“情极”生“毒”,“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而宝玉同黛玉(甚至也包括湘云),却是于“素厚”中隐藏着深层次的隔膜和疏离,始终无法由相爱相知而相谅。“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这正是“情迷”与“情悟”,在宝玉身上此消彼长,又各自作用于不同深度所造成的效果。“情迷”是一种短性的大力,“情悟”却更有一种持久的韧性。两者犹如老子所言“牙”与“舌”的比赛:牙比舌坚固,但到头来,人至迟暮之年,舌却比牙存在得更长久。宝玉的一生亦复类此。他虽多“情迷”于“色”,却终将“情悟”于“空”。所以,脂砚斋用“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这十二个字原则,来概括曹雪芹笔下宝玉情感的A、B两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三回,“宝黛初会”: 林黛玉别父进京都,初次见到贾宝玉,先是听见丫环笑道“宝玉来了”,之后宝玉近来,林黛玉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何以眼熟至此?”,宝玉先去见了他妈,又换了衣服,贾母叫他来见过“远客”,宝玉也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又问黛玉读过什么书,名字是什么,有玉没有?听得黛玉说没有玉,便一时气恼,把玉摔在地上,引得大家慌乱不已。
第五回, 贾母怜爱黛玉如宝玉;宝钗来后,人多倾向之,黛玉不忿;宝玉视其如一,略偏于黛玉;二人因亲密后生口角。
第八回,宝玉到梨香院看宝钗,薛姨妈热情接待。宝钗急于看通灵宝玉,莺儿说玉上的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与宝钗锁上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正好一对儿,宝玉因要了锁看。宝玉要吃冷香丸,宝钗不给。
黛玉来了,见宝玉、宝钗在一起,心下不悦。雪雁给黛玉送手炉,黛玉趁机奚落宝钗。
第十九回,宝玉脸上带着胭脂膏子去看黛玉。黛玉说自己有俗香,无罗汉真人给的香。又说奇香、暖香、冷香的话。宝玉胡诌耗子精盗香芋的故事给黛玉听,使其不致睡出病来。宝钗来了,讥笑宝玉忘了芭蕉诗,急的满头汗。
第二十回 ,宝钗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典。 李嬷嬷骂袭人“哄宝玉”“妆狐媚”“配小子”,袭人气哭。宝玉守袭人,劝袭人,给袭人喂药。宝玉给麝月篦头,睛雯讽刺,宝玉说她“磨牙”。湘云至,黛玉因宝玉恋着宝钗而使气回房。宝玉对黛玉讲“亲不间疏,先不僭后”的道理。
第二十二回,凤姐说贾母喜爱的龄官象一个人,宝钗笑而不说,宝玉不敢说,湘云说象黛玉。湘云、黛玉和宝玉为此事闹矛盾,宝玉心想目下两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何为。袭人劝宝玉“大家随和”,宝玉说自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笔占一偈,又填一《寄生草》,心中自得。宝钗说她是引起宝玉说疯话的罪魁。
第二十三回, 宝玉偷看《会真记》,抖花瓣于水中,遇见葬花之黛玉。宝玉用《西厢记》中词句相戏,黛玉竖眉瞪眼,带怒含嗔,说宝玉“欺负”她。黛玉在梨香院听《牡丹亭》,感慨缠绵,点头自叹,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眼中落泪。
第二十五回, 凤姐给黛玉等送暹罗国进贡的茶叶。取笑说黛玉给她家作媳妇,黛玉骂她贫嘴贱舌讨人嫌。宝玉、凤姐一齐发疯。糊涂发烧。和尚道士持诵“宝玉”,宝玉病愈,黛玉念佛,宝钗说如来佛管林姑娘姻缘,黛玉骂钗与凤一样是贫嘴烂舌。
第二十六回,宝玉来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宝玉用《西厢记》中词曲相戏黛玉,黛玉变了脸,说宝玉拿她取笑。黛玉来看宝玉,晴雯不给开门,又听钗、玉说笑,黛玉不禁伤心落泪。
第二十七回, 黛玉看到定钗从宝玉房中出来,心中不忿回家依栏闷坐,二更方睡。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闺阁兴祭饯花神,众女孩在园中玩耍,宝钗欲寻黛玉,看见主进了潇湘馆,一怕宝玉不便,二怕黛玉猜忌,便要回来,路遇蝴蝶,赶至滴翠亭,细听小红和坠儿正说那贾芸拾帕之事。黛玉不理宝玉;探春在宝玉面骂赵姨娘,主动提出要给宝玉作鞋,被拒绝。黛玉葬花,宝玉痴倒。黛玉葬花:芒种时节,大观园中众姐妹祭花神,黛玉想起之前那天晚上去看宝玉时,晴雯没开门,一时感怀身世,于是有了千古传世的葬花之举,宝玉寻找黛玉,听到了《葬花吟》,一时痴了。
第二十八回宝玉与黛玉葬花诗发生共鸣,恸倒山坡。宝玉说黛玉把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主在心坎儿上,倒把他不理。宝玉、黛玉已清除误会。 端午节的礼物元妃赐了,宝、钗一样,黛玉心疑。宝玉却还想着宝钗的膀子要长在黛玉身上就好了。
第二十九回黛玉用手帕打了呆看宝钗的宝玉眼睛。宝、黛为张道士提亲事闹别扭。宝玉砸玉。黛玉“剪穗”。薛蟠生日,宝、黛、贾母等未去。宝玉对月长吁,黛玉临风洒泪。贾母从中为难,说:“老冤家遇见小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自己埋怨着也哭了。
第三十回宝玉给黛玉道歉,说就是自己死了,魂也要来一百遭。宝玉说黛玉死了他做和尚。黛玉用指戳宝玉额颅,又给宝玉绡帕叫擦泪,宝玉要拉黛玉去往老太太跟前。凤姐跳了进来拉黛玉去见贾母,说两人都扣了环了。宝玉比宝钗为杨妃,宝钗借靛儿来找扇子,发泄对宝、黛不满。宝钗又借李逵负荆讽刺宝、黛。
话说那一天,宝玉因为与蒋玉菡从忠顺王府逃走和金钏儿跳井自杀之事有脱不开的关系,被贾环加油添醋告了一状,就挨了父亲贾政好一顿打,几乎打个半死。
直观的记录是,从王夫人的眼里看,“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从袭人的眼里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宽的僵痕高了起来”,着实叫人触目惊心。
宝玉此番挨打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咱不管它,只说宝玉通过这一顿打得到的 “收获” 。
宝玉有收获吗?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日后宝玉就按着父亲的愿望去行事啊,似乎反而是可以借着挨打受了身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惊吓,更加自行其是了。这算收获吗?
我的想法是,宝玉是有收获的,不过不是这个“收获”,而是他得到了一种来自宝钗和黛玉的 情感上的新认知 ,姑且概括为 “两同两不同” 吧。
01同样被心疼,感受却不同
宝玉挨了这一顿打,不消说来看他的人很多,毫无疑问,就像是现今有重要人物生病住院时那样,前来探视的人中,有的是带着真情实感来的,有的是带着功利目的来的;有的是来慰问的,有的是来“打卡”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正常的。
就宝玉这次挨打的“收获”来说,前来探视他的人中,最有回味价值的大概就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
宝钗与黛玉是分头先后来怡红院探视宝玉的。
宝钗来看宝玉时,宝玉已经可以“睁开眼说话”,等于已经过了危险期,宝钗一看就“宽慰了好些”,大概就因为心里一宽,平日里的十分谨慎也随着原先的担心消解了两三分,就说出了一句半句“敏感”的话来: 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
这句话一下子把她对宝玉的关切给暴露了。不过宝钗却反应很快,一下子又意味到话语中的敏感成分,“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但宝玉是天生情根,兼得了警幻仙子的调教,早就把宝钗那未曾从容说完的话语中的关键信息给抓住了:
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他为宝钗话语“亲切稠密”地心疼他而非常畅快,把身上的疼痛都忘了—— 这“心疼”于他,是一种享受。
对,这里我们需要细品的是,宝玉就宝钗对自己的心疼,回馈的并不是类似“ 我用所有报答爱”这样的方式,而是 “扩大、深化这样的心疼”。 看他怎么想的: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你看,宝玉是把宝钗对他的心疼当作一种 特殊的美感 来享受,当作一种 客观主体 来欣赏;为了能够享受和欣赏,他甚至愿意“一时遭殃横死”。
这真是有点像日本的“物哀”,重要的不是哀伤,而是哀伤所呈现的特别的美感。
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宝钗那隐隐约约的“真情流露”,宝玉的感受并不是“怦然心动”,进而报答这种感情,而是去感受这种流露本身的美好,表明他对宝钗是真的没有多少爱情。
因为, 为爱而报答是拉近距离,目标是融为一体;而享受和欣赏却要保持甚至拉开距离。
这里我想起了《父母爱情》,一个画家爱上了女主人公安杰,为她画了好多画,有一次江德福问她是不是喜欢那个画家,安杰的回答是: “我没有喜欢过他,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 江德福不是很懂这话的意思,但我相信我们都会懂; 懂了这个,我们也就懂了宝玉对宝钗的态度。
而宝玉对黛玉就不同了。
黛玉来看宝玉的时候,宝玉正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她,“犹恐是梦”,“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才认出是黛玉。这一方面是刚在做梦,是被黛玉推醒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宝玉其实下意识地一直在等黛玉来看自己。不过,真的来看他了,面对“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的黛玉,宝玉应该感到她对自己的 万分心疼 了吧,按对待宝钗的方式,似乎该是“心中大畅”,感到“可玩可观,可怜可敬”才是,但宝玉说的却是这个(照他在黛玉面前说话的方式,所说即所想):
你又做什么跑来!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的余气未散,走两趟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
他先责备黛玉不该冒着暑气来,万一中了暑可怎么办;再说自己挨打其实并不重,只不过是装出来吓唬人的,让黛玉不必伤心。
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宝玉的话里明明白白。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就黛玉对自己的心疼,他的回馈方式也是“心疼”,并且是更多的心疼:只因心疼,他的话变“重”了;只因心疼,他把伤说“轻”了。
在我们直观感受里,是不是就是对女朋友的态度? 我想,这也正是宝玉和黛玉的感受。
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宝玉对黛玉的感情的确与对宝钗不同了吧?
02同样是心疼,内涵却不同
而从宝钗与黛玉的角度看,她们同样对宝玉挨打感到心疼,但内涵也还是不一样的。
先看宝钗和黛玉分别为宝玉带来了什么。
宝钗为宝玉带来了一丸药,这是治伤良药,“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很见宝钗心意的。
只不过,她是“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怡红院的,倒似要告诉大家她专程送药来似的,也可见其一路款款走来从容不迫,虽说也在担心宝玉的伤,总还是不那么急迫,脸上恐怕也没有多少伤感焦虑神色。如果其后来看宝玉的凤姐到得早一点,宝钗也不会有什么尴尬的。
黛玉则不同,她没给宝玉带什么药来;她肯定不是像宝钗一样手托药丸大大方方地来的,只怕是衣袖掩面连走带跑地避着人来的,因为她的”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 分明已经哭了好久好久。 她知道这是招人笑话的,所以后来凤姐来看宝玉时,她赶紧从后门走了。她只是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
那么她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痛”。
与宝玉一样的痛,只不过,她不是痛在身体,而是痛在心灵——或许更痛,痛彻心扉。
清楚了: 宝钗给宝玉带来治伤的药,黛玉给宝玉带来一起受伤的心;或者说,宝钗给宝玉治伤用药,而黛玉的方式是与宝玉一起痛苦。
这“心”,就是恋人之心;这“痛”,就是爱。
再看宝钗和黛玉分别对宝玉说了什么。
话不止一句,考虑到她们这次来看宝玉是因为他挨了父亲的打,那么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她们针对这一事由对宝玉的劝诫。
宝钗: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
黛玉: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语,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话虽不同,但意思好像差不多,就是让宝玉再也不要像以前那样没谱了,要好好走父亲所要求的路!
但事实上,方向虽一致,内涵却大不相同的。
从宝钗的话语可知,她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并且早就劝过宝玉,无非是他不肯听,以至于在歪路上越走越远,弄到今天挨父亲的一顿好打,这反而正是对她以前的话的正确性的一个证明;现在是该好好反省,浪子回头了。这是一个有点顺理成章的结果, 这句话里甚至包含着心疼之外的某种先见之明式的自得。
黛玉就不同了。
从她好不容易说出的这一句“改了吧”,正表明她向来与宝玉的观点一样,并不稀罕那“仕途经济”,而追求自由自在,但舅舅的这一顿毒打,让黛玉陷入了巨大的冲突里;可以确定地说,黛玉在听闻宝玉挨打之时起,她就以泪洗面,在与宝玉一起感受那种痛苦的时候,也挣扎在是继续我行我素还是听从家长安排的冲突里;她说“改了吧”是一个沉重的决定,而之所以做出这个沉重的决定,是因为她怕宝玉会再受到伤害。 这是一个扭转她与宝玉人生观念的结果,里面有着撕裂般的疼痛。
所以,同样是对宝玉的关爱,可以说, 宝钗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生走向的关切,而黛玉更多的是对生命苦乐的共情。
总结一下,通过以上的“两同两不同”,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确宝玉与宝钗、黛玉之间,感情是不同的呢?
对以上说法,朋友们以为妥否?欢迎留言讨论!
(网图侵删)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