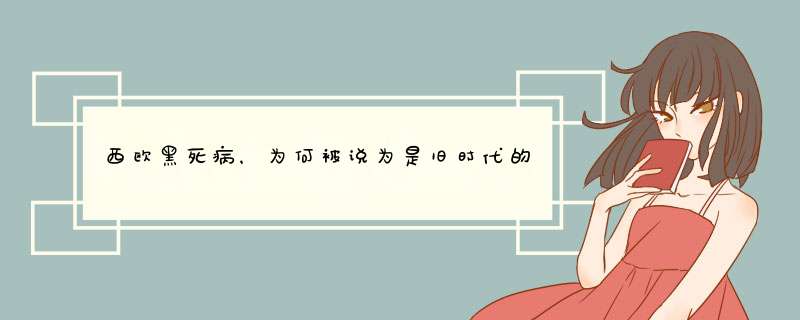
1362年的初夏,辽阔的地中海吹来湿热的海风。年轻的西蒙医生伫立在船舷边,浅绿色的瞳孔倒映着远处铅灰色的天空。风雨将至,天际尽头的陆地一片昏暗。三桅帆船破开起伏的海潮,向着亚平宁半岛的热那亚驶去。
这是第二轮黑死病肆虐的第二年,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灰色的死寂当中。西蒙曾在春天来临时赶往伦敦参加了老友的葬礼,根据伦敦市政厅的规定,每位亡者的葬礼只允许两位亲属参加。不过西蒙的老友已经连两位亲属都凑不足了,他们大都死在了爆发于1348年的第一轮黑死病肆虐期,剩下的也都四散流亡而去。
老友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曾奋力奔走在对抗黑死病的最前线,可他所信奉的主却并没有给予他祝福,疾病迅速夺走了他的生命。
实际上,当黑死病于1348年传入英国,直至1350年疫情消退,全国总计有近一百万人死于瘟疫。人口总计十万人的伦敦城,到了1350年,有超过五万人病死,全城人口直到五十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可怕的疾病正在一步步摧毁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人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正在崩塌,动乱与谣言充斥着街头巷尾的每个角落。在安葬了老友之后,西蒙决心接受另一位医生故友的邀请,前往意大利中部的贸易古城锡耶纳,那儿有一群人正在研究当下黑死病的起源与防治,正在打一场关乎文明存亡的战役:抗击黑死病之战。
扩散:黑暗笼罩西欧大陆1347年10月,一支来自热那亚的船队驶进了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船上载着几名濒死的水手。医生在为他们诊断病情时,发现染病水手的腋下与腹沟呈现出大小不一的黑色肿块,肿块渗出了脓血,并伴随着腐坏的恶臭。
根据同行船员的描述,这些水手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之港出发的,在半路上便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及呕吐现象。港口的医生对神秘的疾病束手无策,只能坐视病人在极度的痛苦中煎熬。仅仅五天之后,船上的病患悉数病死。
医生与船员们为病死的水手感到惋惜,并请来牧师为他们举办葬礼。随后,船队继续向着法国的马赛港起航。
茫然中的船员们还不清楚,一场即将波及亿万人的超级瘟疫,已然于温床中酝酿了。
当年年末,法国马赛出现感染病例,随后经由内河河运与商贸传入法国腹地;
在沿海贸易中,病毒从马赛出发,经由维哥、瓦伦西亚、巴塞罗那等港口流入西班牙,次年春天,病毒已然在西班牙腹地开始肆虐;
在意大利,病毒席卷了罗马、佛罗伦萨等大型城市,又随着船队一路向南,经由突尼斯进入北非;
与此同时,病毒在1348年的夏天渡过海峡进入南英格兰,同时也在意大利北部爆发,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在瑞士及匈牙利肆虐。
到了1349年,病毒由英格兰扩散至爱尔兰及苏格兰,一路向北传至挪威。北冰洋上的水手们流传着一个传说,有一艘载着一船尸体的幽灵船,一路飘荡来到了瑞典,由此病毒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传播。
无论传闻真假,可以确认的是,疾病于1350年自瑞典传播。随后,丹麦、普鲁士、冰岛乃至格陵兰相继沦陷。到了1351年夏天,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均出现大规模疫情,连俄罗斯也未能幸免。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传播迅速、高致死率、极端危险的瘟疫。
因为所有染病的患者身上皆会呈现出散发脓血的黑色斑块,那时的人们便将这一疾病称之为,黑死病。
炼狱:文明体系的破坏黑死病患者的体现出的症状极为显著:
最初患者浑身会遍布的黑色斑块,而后开始渗出脓血。随着病情的加重,病人会出现剧烈咳嗽与连续高烧的症状,汗如雨下。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咯血、腹股沟腺出血,排除血尿及发黑的血便,恶臭难闻。患者从确诊到死亡平均天数为三天,重病患甚至会在病发一天内丧生。
阿维尼翁是法国东南部的贸易大城,位于罗讷河畔,交通往来发达。根据当时教会的粗略统计,疫情肆虐期间,城内每天都有超过400人丧生(在巴黎,这一数字为每日800人),超过7000所房屋因为人口死绝而空置,有的坟场在六周时间里收纳了超过一万一千具尸体。当坟场不足以容纳庞大的尸体数量时,人们不得不将尸体抛入罗讷河内,进而污染了生产生活的水源,形成恶性循环。
类似的情形也在伦敦上演:
伦敦的城市发展在14世纪初便迎来了严峻挑战,市政系统的建设与城市扩张的速度远远脱节。
城内没有公共的下水道及垃圾站,城市居民将生活垃圾与排泄物直接倾倒在街面上,动物的尸体也常常扔在街头任其腐烂。十万居民每日行走在臭不可闻的污秽与污水之间,河流水源早被污染,同时也为病毒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1348年,黑死病传入英国,在伦敦城内迎来大爆发,当泰晤士河水几近被病死者的尸体铺满时,人们不得不在城外开挖巨型坟坑以掩埋尸体。由于尸体数量太过庞大,人们不得不将尸体层层堆积,直至接近坑面为止。
在素有“百花之城”称号的艺术之都佛罗伦萨,有超过四万人死于瘟疫。亲人们将病死的患者扔在街头,或是草草扔进大坑,“任由街犬将他们拖将出来,大口食之。”
第一轮黑死病肆虐了整整五年,于1351年逐渐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的终结:
1361年至1363年、1369至1371年、1374至1375年、1380至1390年,黑死病一再复发,严峻、冷酷、迅猛地掠夺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黑死病肆虐的半个世纪里,欧洲有超过两千四百万人丧生,人均寿命整整减少了十岁,城市人口死亡率超过50%,劳动力人口减少25%。
城市是病毒肆虐与滋生的温床,另一重灾区便是修道院及监狱。人口密集聚集的场所,倘使有一人感染往往意味着全军沦陷。在马赛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中,就曾出现一人感染致使全院发病身亡的案例,这一病毒的凶狠程度远超当时人们的理解与承受能力。
而疫情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文明体系的崩塌:
地方的行政系统完全失灵,面对汹涌的疫情,没人能够进行有效防控。
无数村落与农田因此荒废,道路破败无人修缮,谷物烂在农田里而无人耕种,水利设施垮塌,道路、田地一片泥泞,形成无法通行的区域。
而最可怕的变化在于人心。在肆虐的黑死病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人们互相排斥、攻击、防备,对染病的亲人避之不及,更有甚者抛弃家庭而出逃,有人聚集起来掀起对抗封建政府与教会的暴动,而连续的战乱与动荡又加剧了疫情的肆虐,人们的感情因恐惧而麻木,变成了教会记录中所言:“出丧无哀痛者,婚嫁无笑颜。”
在黑死病面前,文明的色彩正一点点变得灰暗。
鼠疫:古老的中世纪医学接受重建商船在热那亚靠岸,西蒙医生搭上了前往锡耶纳的马车。黑死病肆虐下的热那亚已然不复昔日的繁荣,身披黑袍、头戴鸟嘴帽的医生步履匆匆地穿行在行人寥寥的街头,蒙着白单的尸体随意横放,没人想要多靠近他们半步。远空乌云低垂,初夏的雷雨在穹顶之上酝酿,映得大地一片昏沉。
西蒙清楚,目前医学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医生们正纷纷聚集起来,研究当下疫情的应对方法。但关于黑死病的防治措施,秉持各流派的医生们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中世纪的医生普遍重视理论而轻视实验与观察,对病理学及传染病学一无所知。在黑死病肆虐期间,医生们根据旧有的知识体系为疾病防控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医生们普遍认为病毒的传播途径是空气,因此首要任务是净化已经被瘟疫污染的地区,具体措施则是通过烟熏火烤的方式驱逐病毒。
此外,盖伦学派的医生提出应“尽可能避免政治集会,因为它可能使感染者与未感染者混在一起。”动物的内脏与尸体也应选择远离城镇的地区处理,吃健康的食物,喝干净、透明、流动的水。还有医生认为人体的污垢能有效组织空气中的病毒,建议人们减少洗澡次数,甚至主张不洗澡。
这些措施虽然有荒诞不经之处,却也有一部分恰好符合科学的防治措施。但在对鼠疫几近全无了解的大背景下,这些五花八门的防治手段最后皆收效甚微。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黑死病的一再爆发,使得原本长久止步不前的医学思想逐渐产生变化:
早先的医院皆由修道院创办,所承担的功能更多是隔离麻风病人而非治疗。黑死病爆发后,医院的功能开始出现转变,从单一的隔离功能转向功能的多样化,出现了专门的病房划分,提供单独的床铺与定期换洗的床单,并修建专门的排污管道。人们从黑死病中获得的经验正在逐渐改造古老的中世纪医学,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医疗体系正在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成型。
而随着后辈对黑死病病理的不断探寻,我们终于得以揭开黑死病的全部秘密。
今天的我们可以基本确认,黑死病就是现在的鼠疫,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引起。尽管这一病原体直至19世纪末才被发现,距离黑死病肆虐的时代已经过了整整500年。鼠疫可通过老鼠或跳蚤叮咬传播,也可通过空气传播。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扩张迅速,垃圾成堆,人口密集,为鼠疫的传播制造了绝佳的条件。这一鼠疫的全名为淋巴腺鼠疫,一般呈两大类型:一为跳蚤蚊虫叮咬,侵害血液,引起黑斑、脓血及恶臭;更为可怕的是第二类型,学名肺炎型鼠疫,病毒会侵害两肺,引发炎症,造成发烧发热、剧烈咳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极强。
两种类型同时感染的病患死亡率居高不下,一旦感染,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点。
14世纪的欧洲,医生们对黑死病知之甚少,但依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对抗瘟疫的战线中去。因为密切接触患者,无数医生倒在了前线,其中不乏当时久负盛名权威。
德国、法国、勃艮第的宫廷医生,服务于教皇克莱门六世的3名内科医生与2名外科医生,法国蒙彼利埃城内的全部医生……由于记录的缺失,人们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医生死于瘟疫期间,尽管他们大部分都坚守着过时的乃至错误的医学理论,但他们所展现出的勇气与责任,仍使后人敬佩不已。
思潮:一场风波之后的文艺复兴光明大雨倾盆,世界笼罩在浓厚的水幕中。马车在向着锡耶纳行进时,经过了一支长长的教徒队伍。他们人数超过千人,在教士的率领下向着罗马前进。他们是要为黑死病中煎熬的人民祈祷,这是教会所能做的最后的努力。
如今教会的腐朽与无能几乎人尽皆知,教会极度的禁欲主义压迫与自身内部的荒*放纵对比鲜明,无数人对上帝的信仰在疫情中破碎殆尽,新的思潮正在人民心中无声的酝酿。
民权运动正在欧洲大地上传播,即使在意大利也出现了针对圣经“胆怯而谨慎的批判”。在英国的肯特城里,教士约翰鲍尔向英国民众宣扬他生而平等的学说,神学的帷幕被狠狠揭下,无数人民从神学压迫下的蒙昧中睁开眼来,意识到“自己本是独立的精神个体”。
黑死病激发了文明顽强倔强的生命力,针对文明自身的反省逐渐成型,并即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掀起名为“文艺复兴”的磅礴思潮,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城市建设领域,新的思维正不断提出:
1351年,伦敦首次设立了街道清洁员的职位,这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维护城市清洁的公务员职位,政府通过立法对公共卫生事务进行了统一管理,对民众统一进行了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
1361年第二轮黑死病肆虐之际,意大利设立了常备的公共健康委员会,对防疫时期的行医活动进行统一调度与监督,对食品质量及药物生产进行控制。而在医疗体系领域,随着医生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医院的建设与医学理论的建立日渐提上议程。
尽管上述改革措施在守旧气息浓厚的中世纪遭遇了重重困难,但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雏形却由此开始逐步确立。
勇气的赞歌与斗争的果实锡耶纳古城近在眼前了。这座城市自1186年便与佛罗伦萨的教皇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领土之战,但战争并没有击垮这座城市的居民对生活的坚持,纵使加上当下肆虐的黑死病也不行。
不远处,一座巨大而宏伟的教堂浮现眼前,那是正在建造中的锡耶纳大教堂,倘若建成,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不过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半数居民丧生,教堂被迫停工,开工之日遥遥无期。
实际上,直至21世纪的现在,锡耶纳大教堂也没有完全修建完成,这座残缺的教堂好似对那段灰暗岁月的见证,记录并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勇气。
来的路上,西蒙阅读了一名修士的临终记录。修士名叫约翰克林,来自爱尔兰基尔肯尼的方济各会,也是那座修道院唯一的幸存者。他详细记录了修道院里发生的一切,人们的抗争,对生活的渴望,以及那些鲜活生命的凋零。他在最后写道:
“时间冲淡了不该忘却的记忆,后人将之遗忘,似乎整个世界都落入了恶魔的掌中。我等候死神的降临,将羊皮纸留存以备此用。倘有存活者,有亚当之同类免于瘟疫者,续我未竟之功。”
西蒙在朦胧的细雨中注视着远处残破的锡耶纳大教堂。他知道,这里将是自己奋斗的战场。
从伦敦到莫斯科,从挪威到佛罗伦萨,他看见人类的悲痛与勇气同时浮现在眼前,看见无数人迷茫或热情的双眼,他看见辽阔的大地上,旧的时代正如潮水般消散,新的时代在一片废墟中徐徐升起。
而在抗击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浩劫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认知,将如火炬一般不断传承,直至成为新时代人们对抗病毒的,新的勇气。
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感谢阅读
致敬!“人民英雄”张定宇决定捐赠遗体用于渐冻症研究,此举有何意义?医者仁心,张定宇医生有着人间大爱,大爱无疆。渐冻症,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从病名就可以看出来,患上这种疾病的人,全身会逐渐地像是被冻住一样,压根就活动不了,最后甚至会因为参与呼吸的肌肉也不能运动,最终窒息而亡。而患上这种疾病的医生张定宇,并没有就此消沉。在新冠肆虐之时,他拖着病躯,步履蹒跚,走在抗击新冠的一线上。这是什么?这是英雄!而如今,张定宇医生决定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医疗事业,进行关于渐冻症的研究,希望国家能早日攻克渐冻症这个难题。
这无疑是伟大的,并且十分具有意义的决定。首先,这是张定宇医生的生命的延续。未来的某一天,英雄医生张定宇会离开我们,永远沉睡,但是,他的灵魂与精神永存。正如一句话说的那样:“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张定宇医生就是这样,他的遗体,将会像他活着时那样,继续发光发热,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也会为国家对于渐冻症的研究,带来几分力量,也为渐冻症患者们,带来几分希望。
这将激励着一个个医学生和医疗工作人员。张定宇医生的感人事件,不知感动着多少人。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他忍着躯体的不适与病痛,带领医院的人们,奔波在一线。他不仅与疾病抗争,也与新冠病毒抗争,他的精神与勇气,将会鼓舞着一个个医疗工作者。张定宇医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的至高无上的奉献精神,他身上的白大褂,就像是天使的翅膀,熠熠生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