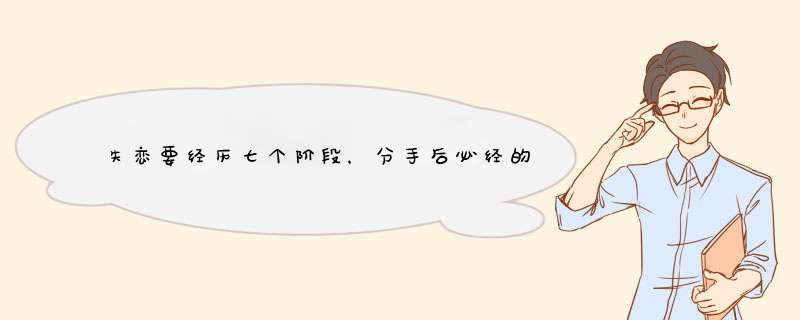
分手时,如何处理问题体现了你是否成熟、是否具备了维持长久恋爱关系的能力。
那么分手这个如此典型的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将给对方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为以后的挽回打好基础呢?
分手必经的四个阶段,你经历过哪一个呢?
第一阶段
很多人分手后第一阶段根本不接受分手这件事甚至压根没有引起重视,照旧和对方吵的不可开交、企图以自己的强势或者道理让对方妥协。
拼命否认,是分手第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
这个阶段对方还能勉强说一些祝你幸福做朋友之类的话,局面尚且还不算糟糕。
第二阶段
这时候基本上以哭闹求和、纠缠对方为主,目的是想改变对方当下的决定。
这个阶段很多人会拼命给对方认错道歉承诺自己会改过自新,处在这个阶段的姑娘是最可悲的,为了不让对方离开,苦苦哀求,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在自己身上,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环节把事情变糟糕的,你的狂轰滥炸已经严重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并且只要对方不傻就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是想改变他。
由此勾出一连串你曾经类似的行为作风,这时候对方除了觉得你死性不改之外还会在心里轻蔑的来一句:”诺,这个人离不开我”。
这时候一般会听到一些老死不相往来的狠话或者被拉黑删除什么的。
所以老师想对处在这个阶段的姑娘说一句: 不要“贱卖”自己,因为贱了未必能卖掉!
第三阶段
否认对方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
常常听到很多失恋患者像告状一样在我这里数落着前任有多绝情,很快就找到新欢了,从来不懂浪漫,从来不主动关心我
这个时候我的回答是:既然这个人这么不堪,那你赶紧丢包啊!
处在这个阶段的姑娘无非接受不了对方的绝情。
曾经有个姑娘问我:他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呢。
请你扪心自问一下,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一下子的改变的吗。
每一次对方不能准时赴约时你的阴阳怪气;每一次没有及时回复你信息报告行踪时你的口不择言甚至破口大骂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分手只是一个爆发点,事情不是一下子变这样。
因为一些错误就抹杀对方的全部,不如问问自己,这是求而不得的恼羞成怒还是对方真的如此不堪?
第四阶段
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尽管放下很艰难,但挽回比放下还要困难得多,要不要为难自己是你个人的选择。
这个阶段选择挽回的姑娘已经开始前任攻略四处求助,希望别人的一个点子一个主意就能让前任回心转意。
要知道,当你决定挽回的那一刻起,就要知道,分手是个烂摊子,你要做的就是收拾烂摊子。
很多人从分手这个烂摊子能脑补到世界毁灭去,没这个必要。
尔朵有话说
选择挽回的姑娘内心必须是强大的,如果你还活在对方放的那几句狠话里,如果你还在脑补对方有新欢的场景
如果你还处在这种状态,最好别着急去行动。
这类型的姑娘我会问一句:你们是玻璃做的么?
是不是对方要对你说一句:宝贝儿,我等着你来挽回我,我不对你狠心!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不用分手了。
所以玻璃心的姑娘要知道,现实就是这样,挽回一个人不是百分百的,有的人经过漫长的煎熬努力成功复合,有的人因为忍受不了痛苦的过程中途败退!
有哭鼻子的时间最好去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挽回当中的风险和压力,能就去做,不能就趁早放弃!
一般人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老师见过一小部分人在第一第二阶段就能打住及时纠正自己的情绪,这部分人往往懂得自我观察,他们能清楚看到自己的情绪并且不受情绪的控制。
但很多人往往是在第二阶段会把情况搞得很糟糕。
挽回就像打仗一样,你能和对手一较高下的前提是他有枪有炮,你也得有枪有炮。
所以请大家挽回之前先看看自己有哪些软实力,不要空有一颗上战场的心,连点实力都没有急着冲上去,只能是送死。
关注微信公众号 尔闻咨询 ,解决更多情感困惑,获取更多女性情感心理干货;添加情感助理 小尔朵(微信号:erwenqinggan2018) 加入高质量情感交流群。你的情感问题,交给我们来解决。宁宗一《小说学通论》说唐传奇的韵文“虽然最终仍然是作者的一种叙事方式,但它只属于‘人物叙事观点’,也就是说,这些诗歌、韵文都是作品人物发出的,而不是出自作者的角度,这是与宋元话本中的诗词的根本不同之处”。如果借用托多洛夫的语言分层方式①,我们不妨说,上述“只属于‘人物叙事观点’”、“都是作品人物发出的,而不是出自作者的角度”的韵文实际上便是“第二语言”,宋元话本中的韵文则主要是“第一语言”。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是唐传奇,在唐以前小说中,韵文所形成的“语言层面”绝大多数都是“第二语言”,甚至,此种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文贯穿于整个文言小说史中,是文言小说中韵文与白话小说中韵文的主要区别所在。
在白话小说中,作为“第一语言”以描摹背景、刻画物象的韵文极多,可是,在唐前小说中,具有此种功能的韵文几乎找不到。除了极少数作品(如《汉武内传》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的场景),先秦两汉小说涉及环境、物象时常常只是作出极简单的叙述,魏晋以后因审美意识的发展倒是注意了修辞与润色,但那些修辞润色不过是多了一些描写性的句子,至多有些骈偶化,并未形成韵文。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概与古人的叙事传统有关。刘知几《史通·叙事第二十二》概括古代的叙事传统云:“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视“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为“体兼赋颂,词类俳优”而嗤之以鼻;钱钟书先生曾说中国的史传“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背景”(《管锥编》第303页),也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并不重视对背景的描摹。固然,我们不能把唐前小说与史传等同起来,但应该看到,这些小说在叙事传统上主要受到史传的影响,大多数唐前小说在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甚至还都被归入史部的《杂史》、《杂传》类里。既然如此,唐前小说的背景、物象的描摹刻画自然就很少,连以骈偶化的句子描摹刻画都会有“体兼赋颂,词类俳优”之讥,它们如果再用韵文来“练饰”、“雕彩”,就很难被当时的叙事传统所容纳。
史传中其实也是有韵文的,史传中的韵文主要出于人物之口,也就是说,属于“第二语言”。以《史记》为例,荆轲的形象“虽千载之下犹虎虎有生气”,不用说,易水送别那一段文字起了很大作用。而在那一段文字中,读者不正是通过荆轲慷慨悲歌的场面领略到他的奇情壮采吗?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越王被幽禁时所唱的歌也都是《史记》中的著名韵文。此外,《汉书》中乌孙公主的《悲愁歌》、《华容夫人歌》,《后汉书》中称颂美政的《五袴谣》、《续汉书》中预言董卓将要败亡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童谣也常常作为典故被后世的诗文所引用。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唐前史传中的韵文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唐前小说与史传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的韵文基本上也都是出于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属于“第二语言”。
“‘第二语言’就是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要刻画、表现他们,要表明他们的个性、抒写他们的情感,这样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第一语言’描写他们的肖像特征,描写他们的外在举止、内在心理,也可以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个性,让人物自己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动机。无疑,‘第二语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托多洛夫《小说的修辞与语言》)。在“人物语言”方面,唐前的一些轶事小说、志人小说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志人小说,通过极简短却富于个性化特点的“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达到了生动传神、清新隽永的艺术效果。可是,应该看到的是,在唐前志怪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其实是不多的,个性化特征也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中国很早就有着“诗言志”的文化心理,如《尚书·尧典》中明言“诗言志”,《礼记》、《毛诗大序》中亦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也者,志之所之也”,后代沿用这些说法的更是不胜枚举。古人还常常从诗歌的写作风格推断出作者的为人乃至一生的荣辱,如薛涛八九岁时替父亲续了两句诗“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她的父亲并不为女儿的才思敏捷感到高兴,反而“愀然久之”,因为他就由这两句诗断定他的女儿后来会入乐籍。明人杨士奇的《沙江村楼诗序》中又有这样一段——“是日雪霁酒酣,以予两人循溪行咏,命各赋小诗言志。孟洁对曰:‘十年勤苦事鹤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香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予即一时景趣塞责曰:‘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时人便从两人的诗中断定孟洁将是“风流进士”,杨士奇则是“太平宰相”。当然,现在我们不会这样理解诗歌与人的关系了,但是不妨说,在唐前的一些志怪小说中,主人公的人格与形象因“诗言志”的功能得到了凸现。不是吗?读着《紫玉》(《搜神记》卷16)“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意欲从君,谗言恐多。悲结成疾,汲命黄泉。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曰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迩,何曾暂忘”这样的韵文,一个忠于爱情、深情而又忧郁的女性形象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唐前志怪小说中以人物所作的韵文来塑造人物、表现人物个性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不乐康王”的韩凭妻(《搜神记》卷11)、聪明伶俐的采桑娘(殷芸《小说》),还是情深意切的清溪庙神(《齐谐记》)、温柔多情的刘惠明女(《续齐谐记》),这些形象之所以能够生动感人,作为“第二语言”的小说中的韵文起了很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前小说中,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文多是口唱的“歌”。这些“歌”有的是徒歌,如《搜神记》中的《紫玉歌》、《穆天子传》中的《白云谣》、《吴越春秋》中的渔父歌、《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侍女歌、《列女传》中的赵津女娟歌、《列仙传》中的采薪者歌、《搜神后记》中的丁令威歌、《还冤记》中的徐铁臼怨歌等;有的歌则是有伴奏的,如《拾遗记》中的皇娥歌、帝子歌,《搜神记》中的《淮南操》,《幽明录》中的郭长生歌、陈阿登歌、方山亭魅歌、水底弦歌、费升所逢狐精之歌等。不论是有伴奏还是无伴奏,由于是唱出来的,“唱”在很多时候便提供了颇有审美价值的细节。紫玉“左顾宛颈而歌”,这样的形象不是很美吗?而且,读到“歌毕,歔欷流泪”的时候,虽然歌声在文中已经停止了,《紫玉歌》袅袅的余音却似乎还在读者的耳畔回响。《拾遗记》中的《少昊》,《齐谐记》中的《清溪庙神》,《幽明录》中的《费升》、《陈阿登》,这些小说的情节都很简单,可是,由于男女主人公或“抚桐峰梓瑟”,或引箜篌弄琵琶,或独唱,或对歌,通过“唱”营造出美丽的意境,同样也达到了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
志人小说虽说也是篇幅短小,虽说也并未摆脱“丛残小语”的性质,它们却能够“于细微处见精神”,颇有一些具有审美价值的精彩细节。《世说新语》中以王蓝田食鸡子的细节表现他的“性急”,以谢安下棋时的音容笑貌表现他的指挥若定,这些细节描写不用说是非常成功的。可是,许多唐前小说的“丛残小语”形式却只是粗陈梗概,具有“美事不举,殊甚简略”(葛洪《神仙传序》)的缺陷,缺少生动传神的细节。可以看出,由于上述韵文是被“唱”出来的,“唱”提供了一些颇有审美价值的细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那种缺陷。
《幽明录》中一些精怪所唱之歌颇有意思,常常是在歌中进行自我介绍。如《郭长生歌》——“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长生”,又如《陈阿登歌》——“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欲知我名姓,姓陈名阿登”。前者在自我介绍时还带有隐语的性质:“郭”是拟鸡鸣声,“长生”谐“长声”。唐代的一些小说如《元无有》、《东阳夜怪录》中精怪所咏之诗也都是以隐语来自报家门,这些小说的构思有可能受到《幽明录》中上述韵文的启发。
在唐前小说中,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文还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文以情动人”,“情”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唐前小说的美学品位。
《列仙传》里,郑交甫表达自己恋情的方式是赋诗;《搜神记》中,神女与凡人相会、离别时也常常赠诗(如《卢充》、《弦超》、《杜兰香》等)。如果把这些小说中的韵文抽出来,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很简陋的叙事,这些叙事能吸引人的地方也不过就是事情比较离奇。可是,有了韵文效果就不一样了,那些韵文是作品中主人公表情达意的载体,能够把读者的审美对象由“事”转移到“情”,使读者由颀赏“事”之奇转移到颀赏“情”之美,审美品位于是也就由“悦耳悦目”转移到了“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层次。
与“写”出来的韵文相比较,“唱”出来的韵文有时又会有独特的抒情效果。以《还冤记》中的《徐铁臼》为例,这篇作品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徐铁臼被继母虐待至死,后来,他的鬼魂还家得以复仇。徐铁臼还家时唱了这么一首歌——“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早已落”。可以想见,在小说中,由鬼来唱一首哀伤的歌是非常凄凉、甚至有些恐怖的,效果强烈,能够很好地抒发徐铁臼的“自悼”之情,也更能引发人们对徐铁臼不幸命运的同情。
另外,“唱”出来的韵文也许没有经过遣词造句上的深思熟虑,可它们常常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在表达情感方面更直接、更自然。汉武帝因思念李夫人而唱《.3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拾遗记》卷5)!词藻当然说不上华艳,汉武帝对李夫人的眷恋之情却在这篇韵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搜神后记》中的《丁令威歌》简直就是大白话——“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依旧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可是它浑然天成,虽说也是劝人学仙的,诱导人学仙的心理基础却是源之于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容易引人共鸣,甚至成为了一个典故而经常被后人引用。如白居易曾有“郑牛识字吾常叹,丁鹤能歌尔亦知”的诗句,王维亦曾云:“当作辽城鹤,仙歌使尔闻”。
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二引张衡的话说:“�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晋书·天文志》云:“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嫈惑降为儿童,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在古人看来,歌谣常常可以预示吉凶、微言祯祥。萧绮《拾遗录》云:“童谣信于春秋,谶辞烦于汉末”,连史传中都有不少预言吉凶的歌谣,小说中有这样的歌谣当然就不足为奇了。在唐前小说中,《拾遗记》、《搜神记》、《幽明录》、殷芸《小说》等都含有此种类型的韵文,它们多是迷信思想的反映,不必多言。需要指出的是,后世一些小说就是以此种类型的韵文为线索来组织结构的。以《传奇》中的《裴航》为例,这篇小说在开始就提到了樊夫人的一首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区区上玉京”,暗示着裴航将来的结局,在后面的篇幅里作品正是围绕着这个暗示性的预言编排情节、组织结构的。类似的例子在古代小说中极多,简直不胜枚举。
《汉书·五行志》中说:“君亢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唐前小说中有不少歌谣便是抒发“怨谤之气”的,如《异苑》中“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飨吾饭,以为粮,行到沙丘当灭亡”怨谤的是暴君;《述异记》在记叙了封邵化虎的异事之后又有这样一个歌谣——“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这就使得前面的记叙不是一件只满足了猎奇心理的异事,而具有了讽刺鞭挞的功能,表现出“苛政猛于虎”的主题。当然,唐前小说中也有一些赞美歌颂的歌谣,如《新序》中有赞美魏文侯礼贤下士的歌谣——“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说苑》中又有称颂令尹子文的歌谣——“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这些歌谣都是在叙事之后给出,既表了褒贬的态度,又因形式上的通俗易懂、琅琅上口而有利于传诵。
综上所述,唐前小说中作为“第二语言”的韵文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有的弥补了小说中人物语言不足、缺少生动细节的缺陷;有的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在叙事之外产生了以情动人的审美效果,提高了小说的美学品位;有的微言大义,给叙事以概括与褒贬;有的琅琅上口,使事迹更好地得以流传……它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①托多洛夫在《小说的修辞与语言》一书中曾经以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为坐标把小说中的语言分成“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与“第三语言”三个层面。所谓“第一语言”是指“人物语言之外的叙述、描写、议论”,“第二语言”便是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在托多洛夫那里,“人物语言”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小说中人物的独语与对话,而且还包括小说中人物的诗文、书信等。“第三语言”则是指“被小说中人物引用的语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与“第三语言”有着不同的特征与作用。
律诗的中间二联要讲求对仗。所谓对仗,就是颔联、颈联的上下二句,每个字的平仄、词性、意义都是相对的。对仗之法,古人归纳为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风秋池是也。”但即使是唐人,对仗也从未严格执行这六对之说,如同类对本要求飞鸟对飞鸟,而唐人很多是用僧对鸟,这个现象还被写进了宋人的诗话中。对于对仗,应该讲求,但不应过执。我以为,只要词性、意义、平仄相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过工整。太过工整的,往往显得雕琢而死板,要不然就伤于纤巧缳薄。对仗的原则是宁粗毋弱,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只要不流于俗野——大白话就好。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对仗不允许上下句是一个意思,这种情形叫合掌,是极不能犯的错误。比如“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虽是名句,但却犯了合掌。又如“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也都是合掌。 好的对句,往往是以纤微对宏大,如“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或以阳刚对阴柔,如“崩石攲山树,清涟曳水衣”、“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或以实对虚,如“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绿尊虽尽日,白发好禁春”。这种阴阳相生相济的思想发源于易经,也一直贯穿在古代诗家的创作实践中。 有时候,诗人故意突破格律,让首联对仗,而中二联只有一联对仗,如下文所举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诗即是。又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或者首联、颔联、颈联都用对仗,如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又或首联不对仗,但后三联均对仗,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种情况,通常只出现在七律当中。 五律的谋篇布局,不外起承转合四字。一般而言,都是首联第一句起,首联第二句承,颔联、颈联是衬贴题目,尾联上句转,下句合。中间二联或就景物加以渲染勾勒,或就人事加以点染,或叙写,或议论,或引事,或比拟,皆为深化题目。如:王维的《送张道士归山》: 先生何处去(起),王屋访茅君。(承) 别妇留丹诀,驱鸡入白云。(引事) 人间若剩住,天上复离群。(议论) 当作辽城鹤,(转)仙歌使尔闻。(合) 又如杜甫的《李监宅》: 尚觉王孙贵(起),豪家意颇浓。(承) 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勾勒) 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点染) 门阑多喜色,(转)女婿近乘龙。(合) 下面大略说一下五律起承转合的方法。 一、起法 1、对景兴起 如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起)秋水日潺湲。(承)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点染)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勾勒) 复值接舆醉,(转)狂歌五柳前。(合) 复如杜甫的《重题郑氏东亭》: 华亭入翠微,(起)秋日乱清晖。(承) 崩石攲山树,清涟曳水衣。(渲染) 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勾勒) 向晚寻征路,(转)残云傍马飞。(合) 2、比起或引事起 如王维的《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杨子谈经所,(起)淮王载酒过。(承) 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点染) 迳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点染) 严城时未启,(转)前路拥笙歌。(合) 是以扬雄比杨氏,淮南王比歧王。 复如杜甫的《崔驸马山亭宴集》: 萧史幽栖地,(起)林间蹋凤毛。(承) 洑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勾勒) 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点染) 清秋多宴会,(转)终日困香醪。(合) 是以萧史比崔驸马。 而王维的《送平澹然判官》: 不识阳关路,(起)新从定远侯。(承) 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勾勒) 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叙写) 须令外国使,(转)知饮月氏头。(合) 则以班超定远的典故引出。而引事,说到底也是一种比。 3、就题直起 杜甫诗法,往往就题直起。不作铺垫,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 如《晚行口号》: 三川不可到,(起)归路晚山稠。(承) 落雁浮寒水,饥乌集戍楼。(勾勒) 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叙写) 远愧梁江总,(转)还家尚黑头。(合) 《月》: 天上秋期近,(起)人间月影清。(承) 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勾勒)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议论) 干戈知满地,(转)休照国西营。(合) 《一百五日夜对月》: 无家对寒食,(起)有泪如金波。(承)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议论) 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点染) 牛女漫愁思,(转)秋期犹渡河。(合) 此种起法,必作者具充沛之情感,写诗时激情澎湃,不可遏止,否则起句突兀,后面承接不上,殊碍通篇圆融浑化。初学者不宜尝试。 二、承法 1、写自家心意承题 如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寒更传晓箭,(起)清镜览衰颜。(承) 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勾勒)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点染) 借问袁安舍,(转)翛然尚闭关。(合) 又《寄荆州张丞相》: 所思竟何在,(起)怅望深荆门。(承)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议论)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叙写) 目尽南飞雁,(转)何由寄一言。(合) 复如杜甫《登衮州城楼》: 东郡趋庭日,(起)南楼纵目初。(承) 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渲染)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勾勒) 从来多古意,(转)临眺独踌躇。(合) 又《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晓,(起)来时悲早春。(承) 转添愁伴客,更觉老随人。(议论)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勾勒) 望乡应未已,(转)四海尚风尘。(合) 2、直书事承题 如王维《奉和杨驸马六郎秋夜即事 》 高楼月似霜,(起)秋夜郁金堂。(承) 对坐弹卢女,同看舞凤凰。(引事) 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点染) 结束平阳骑,(转)明朝入建章。(合) 复如杜甫《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 秋水清无底,(起)萧然静客心。(承) 掾曹乘逸兴,鞍马去相寻。(叙写) 能吏逢聊璧,华筵直一金。(议论) 晚来横吹好,(转)泓下亦龙吟。(合) 3、就首句直承 如王维《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 旧简拂尘看,(起)鸣琴候月弹。(承) 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议论) 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勾勒) 羡君栖隐处,(转)遥望白云端。(合) 复如杜甫《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起)飘然思不群。(承)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比拟)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比拟) 何时一尊酒,(转)重与细论文。(合) 次句承接首句,须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若有意,若无意者最佳。 三、尾联转合之法 1、就题转合 如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 公门暇日少,(起)穷巷故人稀。(承) 偶值乘篮舆,非关避白衣。(叙写) 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议论) 君但倾茶碗,(转)无妨骑马归。(合) 复如杜甫《捣衣》: 亦知戍不返,(起)秋至拭清砧。(承) 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点染) 宁辞捣熨倦,一寄塞垣深。(议论) 用尽闺中力,(转)君听空外音。(合) 就题转合,往往流于平板直白,如能似杜甫此首,运用诗人的联想,写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扣题而又不为题为囿,那就非一般水平所能及了。 2、推开一步转合 如王维《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 贫居依谷口,(起)乔木带荒村。(承) 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叙写) 渔舟胶冻浦,猎火烧寒原。(勾勒) 唯有白云外,(转)疏钟闻夜猿。(结) 复如杜甫《初月》: 光细弦岂上,(起)影斜轮未安。(承) 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勾勒) 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渲染) 庭前有白露,(转)暗满菊花团。(合) 此种转合法,词有尽而意无穷,摩诘时时用之,最是五律正格。 3、承颈联意转合 此种结法,惟老杜最善用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 莽莽万重山,(起)孤城山谷间。(承)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点染)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叙写) 烟尘独长望,(承上联转)衰飒正摧颜。(合) 同题之十: 云气接昆仑,(起)涔涔塞雨繁。(承) 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点染) 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勾勒) 所居秋草净,(承上联转)正闭小蓬门。(合) 《萤火》: 幸因腐草出,(起)敢近太阳飞。(承) 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议论)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勾勒) 十月清霜重,(承上联转)飘零何处归。(合) 《蒹葭》: 摧折不自守,(起)秋风吹若何。(承) 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沈波。(渲染) 体弱春风早,丛长夜露多。(勾勒) 江湖后摇落,(承上联转)亦恐岁蹉跎。(合) 4、用事作转合 用事作转合,实际就是用比为转合。如王维《送李判官赴东江》: 闻道皇华使,(起)方随皂盖臣。(承) 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叙写) 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勾勒) 遥知辨璧吏,(转)恩到泣珠人。(合) 复如杜甫《巳上人茅斋》: 巳公茅屋下,(起)可以赋新诗。(承)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点染) 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勾勒) 空忝许询辈,(转)难酬支遁词。(合) 最后,再来说一说中间二联的章法。 颈联和颔联,在诗中的作用都是为了深化题旨,但要注意颈联下意要和颔联相应相避,要有变化。变化的方法之一是颔联既然写景了,颈联就要写人事;颔联写了人事,颈联就要写景。如果二联都是写景,那么一般颔联侧重写整体,骋目四顾的远景,颈联则着重勾勒细节;同写人事,往往颔联写他人,颈联写自己。这种在诗的内在意脉上的转折,须多读古人名作,自然有得。白居易《金针诗格》说“第三联谓之警联,欲似疾雷破山,观者惊骇。”这一联,如能用上精心锤锻的警句,则一篇生机,大略已备。兹举二首杜诗为例: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百顷风潭上,千重夏木清。 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即细微之物加以勾勒) 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八):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 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议论正大,气象开阔) 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老杜诗法,往往首联第一句关合颔联,第二句关合颈联,这是杜甫律诗的一大特点。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 宋公旧池馆,零落守阳阿。 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 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 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 “宋公旧池馆”是“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二句之主,“零落守阳阿”又是“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二句之主。复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三: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 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 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 露翻兼雨打,开坼日离披。 “万里戎王子”是“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二句之主,“何年别月支”则是“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二句之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