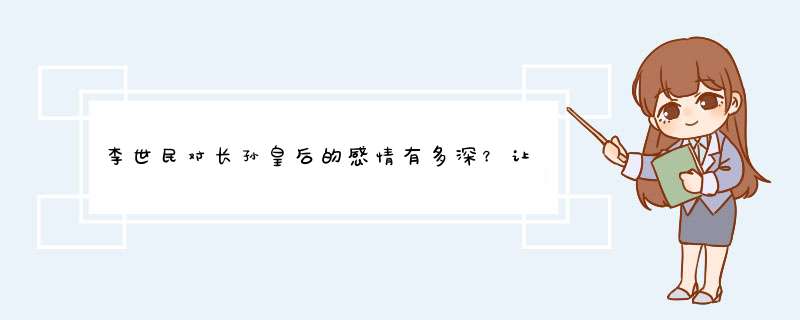
唐朝的宗庙制度有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唐高祖李渊时期只有四庙,据《旧唐书·礼志》记载:
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于太庙,始享四室。
贞观九年,李渊去世,太宗命令有司详议庙制,扩充为六庙:
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从之。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
也就是说,贞观九年以后唐朝宗庙为六庙: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武皇帝。
但是,《旧唐书》在记载贞观十四年定宗庙庙乐时,却记载了七庙的庙乐:
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 。七庙登歌,请每室别奏。
两相对比,增加了文德皇后庙。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妻子长孙皇后的神主直接祔于太庙,而不是另立别庙等自己驾崩再祔于太庙呢?这里暂且不表,下面会有另有分析。
关于长孙皇后所用的这首庙乐《光大之舞》,首先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在长孙皇后之前和之后,都是什么身份的人在用这支光大之舞。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
凡有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焉。 献祖之室,用光大之舞 ;(黄锺宫调。)懿祖之室,用长发之舞;(黄锺宫调。)太祖之室,用大改之舞;(大簇宫调。)代祖之室,用大成之舞;(沽洗宫调。)高祖之室,用大明之舞;(蕤宾宫调。)太宗之室,用崇德之舞;(夷则宫调。)高宗之室,用钧天之舞;(黄锺宫调。)中宗之室,用文和之舞;(大簇宫调。)睿宗之室,用景云之舞;(黄锺宫调。)孝敬庙,用承光之舞。诸太子庙,用凯安之舞。
《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七》:
孝昭帝皇建元年九月诏议定三祖乐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帝庙宜奏武德之乐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宣政之舞 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政之乐光大之舞 诏曰:可。
《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九乐考二》: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之乐,群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亚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焘》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虻兀奏登歌;其四祭庙及丿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 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 ;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出入之仪,同四郊之礼。
《全唐文》:
○定宗庙乐议
近奉德音,俾令鸶铮嘉名创立,实宜允副。伏惟圣祖宏农府君宣简公懿王,并积德累仁,重光袭轨,化覃行苇,庆崇爪瓞。诗云:“稣芪商,长发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夏二代,发祯祥也。三庙之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其登歌则各为辞。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豳岐,胥宇之志既勤,灵台之萌始附。诗云:“君子万年,永锡祚允。”今遐远之期,惟天所命,以长福祚,流於子孙也。庙乐请奏永锡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鸿绪,克绍宏猷,实启蕃昌,用集宝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言德应天道,行不失时,刚健靡滞,文明不犯也。庙乐请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驭历,揖让受终,奄有四方,仰齐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祜,式崇勿替,诞保无疆。《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谓其终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时成六位也。《诗》有《大明》之篇称文王有明德。庙乐请奏大明之舞。 文德皇后厚德载物,凝辉丽天。《易》曰:“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静,柔顺利贞,资生庶类,皆畅达也。庙乐请奏光大之舞 。谨议。
《唐会要卷三十二》:
(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豫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乐。其封泰山也。登歌奠玉币。用肃和之乐。迎俎用雍和之乐。酌福饮福。用寿和之乐。送文迎武。用舒和之乐。亚献终献。用凯安之乐。送神用夹锺宫元和之乐。禅社首送神。用林锺顺和之乐。享太庙迎神。用太和之乐。 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 。懿祖光皇帝酌献。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献。用景云之舞。彻豆用雍和之舞。送神黄锺宫永和之乐。
《唐会要卷三十三》:
献祖宣皇帝室酌献。奏光大之舞 。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室酌献。奏崇德之舞。
先是。 文德皇后庙乐。贞观十四年。颜师古请奏光大之舞 。许敬宗议同。及太宗祔庙。遂停光大之舞。乐章阙。
由以上史料可知,在长孙皇后之前,北齐文宣皇帝的庙乐用的是《光大之舞》,而继长孙皇后之后,以《光大之舞》作为庙乐的是唐太祖的祖父唐献祖。
也正因为一直以来《光大之舞》只用于皇帝,所以无论这支庙乐的赞颂内容如何改动,整支乐曲的曲调都必然符合皇帝的身份与气势,而将长孙皇后的庙乐定为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光大之舞》而不是另选适用于皇后的庙乐,显然已经逾制了。
为什么说长孙皇后的神主入的是太庙而不是别庙呢?除了“定 宗庙 乐议”“ 七庙 登歌”这些再明确不过的记载外,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唐德宗的昭德皇后王氏。这位王皇后与长孙皇后一样,都是生前就册封为皇后且死在丈夫之前的,那么她的神主及庙乐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唐会要卷第三》:
德宗皇后王氏。贞元二年十一月。册为皇后。其月二十一日忌。三年正月。上尊諡曰昭德皇后。其諡册文初令兵部侍郎李纾撰。上以纾谓皇后为大行皇后。非也。诏学士吴通元为之。通元又云咨后王氏。亦非也。按贞观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諡册文曰。皇后长孙氏。斯得之矣。其年二月。皇后发引。梓宫进辞太庙於永安门。升轀輬车於安福门。从阴阳之吉也。三月。 以皇后庙乐章九首付有司。令议庙舞之号。礼官请号坤元之舞 。从之。其乐章初令宰臣张延赏柳浑等撰。及进。留中不下。又命翰林学士吴通元为之。时上务简约。不立庙。令於陵所祠殿奉安神主。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常博士李吉甫奏曰。 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 。若於大行皇帝陵所祠殿奉安神主。礼经典故。检讨无文。伏以元献皇后。庙在太社之西。今请修葺。以为大行皇后别庙。敕旨。宜依。仍付所司。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待诏杨季炎等奏。奉进止。宜於两仪殿虞祭毕。择日祔庙。准经勘择。用三月十八日一时。两仪灵座。便请除之。诏下太常。详求典故。太常卿董晋。与博士李吉甫张荐等奏曰。伏惟古礼。合用今年七月卒哭祔庙。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睿宗十月而葬。并葬讫便卒哭。祔庙。圣朝典故。伏请遵仍。令所司於今月十八日已前择卒哭位。哭讫。以十八日祔庙。制曰。可。
《旧唐书·后妃传》:
又 命宰相张延赏、柳浑撰昭德皇后庙乐章 ,既进,上以词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学士吴通玄别撰进。
《旧唐书》:
《曲台礼》云:“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祔于祖姑之下。”此乃 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肃明、元献、昭德之比 。昭成、肃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献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肃宗在位。 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 ,当为太庙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飨。其神主但题云“某谥皇后”,明其后太庙有本室,即当迁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暂立别庙耳。
由以上史料可知,尽管王皇后与长孙皇后一样,都是死在皇后之位上且死在丈夫之前,但是王皇后却只有别庙,而且她的庙乐也并非是皇帝才能使用的那一级别,而是唐德宗专门令人编撰的适用于皇后的庙乐《坤元之舞》。
并且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唐会要》中还记载到:“准国朝故事。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并置别庙。”《旧唐书》中亦记载了:“四后于太庙未有本室,故创别庙。”
这两则史料在提及立别庙的皇后时,用词都非常严谨。因为唐朝死在丈夫之前的皇后有不少,但立过别庙的只有睿宗的原配刘皇后,玄宗生母窦皇后,肃宗生母杨皇后,德宗的王皇后,而中宗的赵皇后没有别庙,太宗的长孙皇后是直接进了太庙,对于这些不立别庙的皇后,国朝故事与四后的名单中,自然就没有出现了。
当然,也有人提到《旧唐书》中记载过唐朝的宗庙制度就是皇后先崩时,她的神主只能进别庙而不是太庙,但规矩是死的,而掌权者的心思却是灵活的。
想想和思、昭成、肃明都是都是死在丈夫之前,虽然日后都被登基的皇帝丈夫追封为皇后,但和思连个别庙都没有,中宗驾崩后这才跟着入了太庙;昭成在睿宗活着时就有了别庙仪坤庙,睿宗死后神主被儿子玄宗迁入太庙;而肃明作为睿宗原配,却直到睿宗死后才能挪进昭成空出来的仪坤庙,开元二十年才进太庙。
同样是死在皇后先崩死在丈夫之前,所谓的规矩就摆在那,结果还是一样有区别,甚至大有不同。
不仅如此,无独有偶,恐怕大家还对贞观十四年大臣们一提到文德皇后庙时就算在七庙里面,动辄就是“七庙”“七庙”的情景记忆尤深吧。
贞观君臣直接将文德皇后庙算在七庙里面,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七庙全部都在太庙,不存在哪个是别庙,因为太庙与别庙,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
《新唐书·肃宗本纪》:
庚戌,朝享于 太庙及元献皇后庙 。
《旧唐书·沈皇后列传》:
自后宫人朝夕上食,先启告元陵,次告 天地宗庙、昭德皇后庙 。
之前《唐会要》与《旧唐书》上说得很清楚,元献皇后立的是别庙而不是太庙,毕竟太庙是太庙,别庙是别庙,两者的等级大不一样,在封建等级社会是要严格加以区分的,不会把太庙与别庙混淆在一起。所以肃宗与宪宗在祭祀的时候,太庙与别庙是分开进行的,可没有类似“七庙”这种一并提及的说法。
综合以上史料记载可知,贞观十年后,长孙皇后的神主进的正是太庙,而不是别庙。
虽然女性皇室成员的神主被直接祔入太庙的事情并非前无古人,但出于男尊女卑的思想,这种行为还是备受时人的批评。南朝梁武帝曾将其夫人郗氏列入五庙,称帝后又将其排除只立六亲庙,恐怕也与当时对女性入太庙的批评有关。
《南齐书》:
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 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 ?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南梁的史官萧子显对西晋武帝将自己的原配杨元后祔入太庙一事并不反对,因为“不以元后为世数”,也就是说,杨元后的神主不在七世庙之列,所以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南朝宋把臧后迁入太庙并作为世室,即“以臧后为世室”,萧子显是十分反对的,直言“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
滥者,多余也。萧子显的意思很明确,太庙世室祭祀的是皇帝的祖宗,而皇后是与皇帝平辈的,怎么能搞出这种多余的祭祀呢?
所以到了唐朝开国初年也只立四亲庙,不过《册府元龟》上的一条记载似乎提供了不同的看法:
(贞观)三年正月戊午,帝有事於太庙。至太穆皇后神主,悲恸呜咽,伏地不能兴。
那么这条史料是否能证明太穆皇后的神主在唐高祖在世时就已经奉入太庙了呢?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各处史书的记载均记录了武德年间立的宗庙只有四亲庙,祔于太庙的神主并没有太穆皇后。
至于太穆皇后的神主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庙里,应当与贞观三年正月举行的“禘祭”有关。根据“别庙皇后,禘祫于太庙”的礼制,太穆皇后的神主是可以临时奉入太庙接受祭祀的,所以这与唐高祖立四亲庙的记载并不冲突。
关于唐太宗为什么要将长孙皇后直接祔于太庙与祖先一同接受后人的祭祀,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为了凑足七庙之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妨先看一则史料。
贞观九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去世,同年七月唐太宗借此调整宗庙制度,谏议大夫朱子奢提出建议,请求将太庙扩建为七庙,如果确有百世不迁的“王业之所基者”就尊为始祖,如果没有,就虚位以待。
《旧唐书》:
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
如果唐太宗一心想凑足七庙之数,又或者唐太宗自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百世不迁之祖,那么朱子奢的这番建议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大可顺势接受建议,直接将太庙增修至七室,留出太祖之室虚位以待,等着以后自己的神主慢慢地升进去。
但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而是命令只增修至六室,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凑足七庙之数也好,对于自己成为百世不迁之祖也罢,并没有看得很重。
甚至不仅仅是唐太宗没想过要凑足七庙之数,日后唐中宗复辟后,太常博士张齐贤也曾建议将太庙增加为七室,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而唐中宗也决定“依贞观之故事,无改三圣之宏规,光崇六室”。
由此可见, 从初唐到中唐,唐朝君臣对凑足七庙之数这种事情并不热衷 ,所谓唐太宗将长孙皇后神主迁入太庙是为了凑七庙之数的说法,缺乏史料证据。那么会是因为当时宗庙制度不健全的缘故吗?
事实上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就算制度不健全,也不会出现把妻子和祖先放在同等高度祭祀的事情。比如唐德宗在爱妻王皇后薨逝后,并没有将她的神主直接祔入太庙而是另立别庙,祭祀王皇后所用的庙乐也并非是皇帝才能享受的庙乐,而是专门令人编撰了适用于皇后的庙乐《坤元之舞》。
所以如果没有合适的皇后庙乐,唐太宗完全可以安排人另外编写一个,没有必要非用皇帝的庙乐不可,更没有必要因此将长孙皇后直接祔入太庙——所谓制度不健全一说,显然也无法成立。
那么唐太宗究竟是为什么要将长孙皇后祔于太庙,而当时朝中大臣魏征房玄龄等人又是为何没有对如此不符合制度的事情提出反对,甚至是直接就“七庙”“七庙”地从善如流了?
在这里,可以稍微回顾一下长孙皇后生前的作为,无论是武德年间和房玄龄等大臣同心影助李世民,还是玄武门之变中亲自去鼓舞士气,又或者是贞观年间屡屡劝谏李世民乃至保护朝中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不反对唐太宗让长孙皇后直接进太庙,享受李唐先祖的祭祀待遇,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太宗会给予长孙皇后这么高规格的祭祀待遇,是因为长孙皇后在他的心里值得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而大臣们不反对唐太宗这么做,也同样是因为他们敬重长孙皇后,认可这位母仪贞观的皇后,我们甚至可以看看当时的唐人是如何评价长孙皇后的。
李世绩《请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表》:
文德皇后亻见天作合,曾沙表庆,功侔 十乱 ,化被二南。
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
文德后以 十乱 乘时,恭赞涂山之业。
《旧唐书·后妃列传》:
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 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 每能规谏,补朕之阙 ,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褚遂良《论房玄龄不宜斥逐疏》:
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於谟谋,犹服道士之衣, 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 。
《旧唐书·宋璟列传》:
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谢于征。此则 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 。
所谓“十乱”,即指辅佐君王治国平乱的人。唐人直接将长孙皇后摆在“十乱”的高度,而各处史料也证明了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匡赞之功,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群臣心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综上所述,比起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所谓凑足七庙说以及制度不健全说,长孙皇后凭借自己对贞观君臣的影响力入主唐朝宗庙,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聊明武宗朱厚照和夏皇后的感情之前,先来捋一捋这对帝后生前的大致情况,关于这对帝后间的感情,史书没有确切的记载,后人只能从仅存的点滴记录中去猜测。
不准百姓养猪吃猪肉的明武宗朱厚照一起来看看这位生肖属猪,不准百姓养猪吃猪肉,自己又照吃不误的怪咖皇帝。明武宗朱厚照(1491年10月27日-1521年4月20日),明朝第十位皇帝,1505年—1521年在位,明孝宗朱佑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年号正德。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朱佑樘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朱厚照是孝宗的长子,在弘治五年(1492)春,年仅2岁的朱厚照就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就有皇位等着继承的,说的就是这位仁兄了。因为孝宗朱佑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只有一位皇后没有嫔妃的皇帝,所以,根本没有其他兄弟跟朱厚照来争这个皇位啊!
在登上皇帝宝座前,朱厚照尚能专心读书,学习能力很强,通晓藏语、阿拉伯语和蒙古语,他在孝宗面前小心翼翼,虽然喜爱骑马射箭,但比较节制。
朱厚照坐上龙椅后,逐渐暴露出贪图享乐的本色。他整天与刘瑾、张永等内臣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张永这些人原来都是东宫的宦官,武宗对他们极其宠信,让刘瑾掌钟鼓司,后来又让他提督十二团营。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相互勾结,被人称为“八党”,也称作“八虎”。
“八虎”想尽办法迎合武宗。在他们的诱导下,年轻的武宗终日游戏,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时间一久,武宗觉得这样玩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后来,武宗甚至出宫游玩,把孝宗遗诏中要求兴办的事务,全都搁置一边。
朝中大臣见武宗与太监整天耽于逸乐,不仅怠于政事,而且开支大增,于是,纷纷上疏劝谏。武宗表面上表扬他们,实际上仍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的言辞开始激烈起来,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武宗有些支持不住,想除掉八虎。刘瑾得知后,在武宗面前一番哭诉求情,武宗心又软了下来,第二天他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但是被武宗欣然批准,群臣失去了领头人,只好做罢。
“八虎”在战胜了群臣之后,气焰更加嚣张,擅权跋扈。刘瑾又建立了豹房,供武宗日夜作乐。武宗更加肆无忌惮,只知寻欢作乐,对朝政一概不理,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
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武宗借宁王朱宸濠叛乱南巡亲征,途中,获悉朱宸濠被王守仁擒获,但武宗为了畅游艰难,竟然压着捷报,秘而不宣。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将朱宸濠拘禁在船上,在南京举行“受俘仪式”后,才勉强回师。途经清江浦( 今江苏淮安),武宗在积水池打鱼取乐,落水染病,回京后病情恶化,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便去世了,年仅三十一岁。葬于康陵。
皇帝死了也不能做太后的夏皇后弘治五年(1492年),夏氏生于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夏氏是夏儒的女儿,静定端庄。
正德元年(1506年),夏氏选秀入宫。同年八月,金秋时节,十六岁的武宗举行了隆重无比的婚礼大典, 册立夏氏为皇后。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武宗生前无子,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迎立就藩湖广的兴王(今湖北钟祥)朱厚熜为皇帝。
嘉靖元年,明世宗朱厚熜入继大统,因为与夏皇后为叔嫂关系,故夏皇后不能当太后,但又要与世宗的陈陈皇后区别,因此上尊号为“庄肃皇后”。
嘉靖十四年(1535年),夏皇后崩逝,葬于康陵,附太庙。
朴素迷离的帝后感情武宗朱厚照与夏皇后的感情到底如何,史书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明代的藏书家杨仪在《明良记》中曾写到“武宗久不御内 ,自大同还, 忽趋入宫 ,夏后见帝因泣下 。帝曰:“皇后如何日来太瘦?”着光禄司进膳 ,加肥鹅一双。”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武宗与夏皇后的感情还是说得过去,没到相看两厌、死不往来的状态。但武宗朱厚照又多年居于宫外,沉湎女色,可见,夏皇后在其心目中也没啥地位,因此,也导致夏皇后没有子女。
见面能关心自己的皇后,玩起来又将皇后、朝政抛诸于脑后!这么个皇帝,能说,他只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官二代吗?
据史书记载,夏皇后曾经劝谏武宗远离声色犬马,专心朝政,结果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看来,武宗朱厚照,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男孩,他肯定不知情为何物,何谈与皇后的感情呢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一则故事:一个武士犯了重罪要被处以死刑,这位武士去向王后求情。王后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限他一年内作答,如果武士回答得正确就免去他的死刑。王后的问题是:一个女人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这位武士游历全国,寻求正确的答案。一年后他来到王后的面前说:“一个女人最渴望的就是被男人爱。”这样的答案放到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女性主义者不能答应,但在当时就是个圆满的正确的答案啦,王后因此赦免了武士的罪行。
有些女人是可爱的,她们生下来就是被人爱的,而有些女人却不那么可爱(可以爱的,值得爱的),但她们也要生下来就来寻找男人来爱自己。通过古希腊神话“金羊毛的故事”和美狄亚在同名悲剧中的表现,我们更愿意说美狄亚是第二类的女人。美狄亚靠巫术帮助伊阿宋获取了金羊毛,背叛自己的城邦和伊阿宋私奔,甚至砍死自己的兄弟以阻止父亲的追赶。等他们到了伊俄尔科斯,美狄亚首先做的就是替伊阿宋报复珀利阿斯,设计将之杀死,被珀利阿斯的儿子阿卡斯托斯赶了出去,一家人流落在科任托斯。他们住在这儿,美狄亚倒停讨科任托斯人的喜欢,夫妻间也十分和睦,直到后来他的丈夫抛弃了她。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就已经能看出美狄亚热烈奔放的性情和她的冷酷残忍,为了自己与伊阿宋之间的爱情她能将自己的兄弟砍成肉块,将来她手刃自己的孩子实在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美狄亚爱伊阿宋,她渴求伊阿宋像她爱他那样爱自己。美狄亚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是一个爱情的奴隶,情感的化身。
伊阿宋:理性的嘲弄
我们看伊阿宋在金羊毛故事和在《美狄亚》一剧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伊阿宋并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事迹,他只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负心汉”。在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中,伊阿宋靠着天后、雅典娜和一船英雄的帮助航到了埃厄忒斯国,又在美狄亚的全程帮助下获取金羊毛并顺利逃脱,回到祖国伊俄尔科斯后后,又是美狄亚设计替他报了杀父之仇。如今在科任托斯国,他要抛弃美狄亚和两个孩子来和科任托斯国的公主结婚。伊阿宋面对美狄亚对自己忘恩负义行为的责难,他的答复是:“至于你骂我同公主结婚,我可以证明我这事情做得聪明,也不是为了爱情,对你和你的儿子我够得上一个很有力量的朋友,——请你安静一点。”(547-549)①依着伊阿宋的解释,他之所以和公主结婚,是为了“得生活得像个样子,不至于太穷困。”(555)“救救你,再生出一些和你这两个儿子作弟兄的、高贵的儿子,来保障我们的家庭。”(595-597)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想:当初伊阿宋和美狄亚的结合也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即获取金羊毛,而没有太多的情意在里面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伊阿宋对美狄亚对自己的感情有着清醒客观的认识,他理性地看待着美狄亚投到他身上的热情。“你过分夸张了你给我的什么恩惠,我却以为在一切的天神与凡人当中,只有爱神才是我航海的救星。”(523-525)这句话远不是说爱情是伊阿宋的指路明灯,恰恰相反,他貌似无辜地把美狄亚施给他的火热的情意归咎为爱情女神的安排,这样子他自己的“负心”行为也就是个伪命题啦。伊阿宋接着说:“可是你——你心里明白,只是不愿听我说出,听我说出厄洛斯怎样用那百发百中的箭逼着你救了我的身体。我不愿把这事情说得太露骨了;不论你为什么帮助过我,事情总算做得不错。”(525-528)美狄亚曾说原是她救了伊阿宋的性命,但伊阿宋却说是爱情逼着美狄亚救了他。紧接着伊阿宋说了这么一句话:“可是你因为救了我,你所得到的利益反比你赐给我的恩惠大得多。”(528-529)在这里伊阿宋赤裸裸地提到了“利益”这两个字,而且直言他们两人的结合给美狄亚带来了更多的利益。我们说美狄亚是爱情的俘虏,无怪乎美狄亚听到伊阿宋对于自己结婚的辩解,并且允诺“来保障我们的家庭”时所作出的反应,美狄亚说:“我可不要那种痛苦的富贵生活和那种刺伤人的幸福。”(598)
美狄亚——恋爱的女人
我们说歌队在本剧中始终属于道德的宇宙,戏剧刚开始歌队(由科任托斯妇女组成)对美狄亚抱有很大的同情,歌队和美狄亚一同咒骂“那忘恩负义的丈夫”,并且说:“美狄亚,我会替你保守秘密,因为你向你丈夫报复很有理由。”(267)而当歌队知晓美狄亚残酷的报复意图后,歌队对美狄亚的态度起了巨大的反转,先是好言相劝,“我为你好,为尊重人间的律条,劝你不要这样做。”(811-812)但当传报人来传报“公主死了,她的父亲克瑞翁也叫你的毒药害了!”(1126)歌队长说:“看来神明要在今天叫伊阿宋受到许多苦难,在他是咎由自取。”(1231-1232)歌队对于公主与克瑞翁的被害似乎还可以接受,但她们不能容忍美狄亚——一个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歌队诅咒着拿起宝剑就要伤害儿子的美狄亚:“你这天生的阳光啊,赶快禁止她,阻挡她把这个被恶鬼所驱使的,瞎了眼的仇杀者赶出门去!”(1258-1260)并且她们对“咎由自取”的,但失去了了两个孩子的伊阿宋产生了同情。“啊,伊阿宋,不幸的人啊,你还不知道你遭受了多么大的灾难。”(1306-1307)
我们说歌队的态度也就是欧里庇得斯心目中剧场观众们观剧时被激起的态度,也是普通读者对剧情的第一印象。很显然美狄亚杀子的行为引起了我们强烈的道德上的反感,我们说美狄亚是一个狠心恶毒的女人,甚至有人说她是个疯狂的巫女。
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恋爱的宇宙来看,美狄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情至上者,她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抛弃,她更愿为了爱情付出;当她遭受了背叛时,她一往情深的爱情转化为无边的嫉妒与怨恨,爱人爱得那么深,痛恨人也能痛恨那么狠。
在剧本中,美狄亚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不论是歌队、克瑞翁、埃勾斯还是伊阿宋,她所说的话都是一个弃妇的愤懑,而且是一个被弃后仍深爱着的女人的愤懑。我们说剧本中只有美狄亚一个人置身于恋爱的宇宙,其他人都处于道德或现实利害关系的立场上,因此美狄亚的话语自成系统,除了与埃勾斯谋划寻求庇护,美狄亚与他人的对话基本上都不在一个系统。这是她独身面对世界的结果,没有人帮着她,甚至她最爱的人反而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她要施给最爱的人双倍的痛苦,目睹爱人心碎是这个嫉妒的女人所想到的最狠毒的方式,这全是美狄亚对伊阿宋深厚的爱情所驱动的。
在戏剧第一场克瑞翁要赶走美狄亚的对话中,克瑞翁暗中责备美狄亚背叛了她的祖国。美狄亚回复道:“唉,爱情真是人间莫大的祸害!”(330)美狄亚好像在向克瑞翁解释,是爱情在作祟,使她背叛了她的祖国。第二场伊阿宋向美狄亚解释:“我并不是为了爱情才娶了这公主。”(594)而是为了给他们一家子提供地位保障时,美狄亚说:“我可不要那种痛苦的富贵生活和那种刺伤人的幸福。”(598)美狄亚不能忍受丈夫的不忠,任何外在条件(富贵生活、幸福)失去了真情都不复存在。我们尤其可以通过美狄亚与埃勾斯的对话了解到美狄亚这位爱情至上者嫉妒的根源:
美狄亚:他重娶了一个妻子,来代替我作他家里的主妇。
埃勾斯:他敢于做这可耻的事吗?
美狄亚:你很可以相信,他先前爱过我,现在却侮辱了我。
埃勾斯:到底是他爱上了那女人呢,还是他厌弃了你的床榻?
美狄亚:那强烈的爱情使他对我不忠实。(694-698)
美狄亚首先强调了她和伊阿宋之间先前的爱情,“他先前爱过我”;继而用愤懑的语气说现在伊阿宋与公主间“那强烈的爱情”冲毁了他们之前的爱情。美狄亚认定了伊阿宋与科任托斯国公主之间的结合是因为爱情,这位爱情至上者推己及人,把伊阿宋的理性经营理解为爱情的安排,而不顾第二场中伊阿宋反复向她解释的“并不是为了爱情”,我们说这位面对不忠的丈夫而怨恨的女人压根儿都不听伊阿宋的辩解。伊阿宋的“移情别恋”使得她悲痛不绝,呼天抢地。她的嫉妒之火燃起,她预谋绵细的残忍的报复手段对这两位新人施加。我们看美狄亚杀死两个孩子后,面对伊阿宋的责难,她是这么回复的:
伊阿宋:你认为你为了我的婚姻的缘故,就可以杀害他们吗?
美狄亚:你认为这种事情对于做妻子的,是不关痛痒的吗?(1367-1368)
美狄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女人攫取她的爱人,她的幸福。在这里,她的性格也参与了报复行动。
情感和理性,性格和命运
戏剧一开场,通过保姆的开场白,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主人公是个情感动物,“她躺在地上,不进饮食,全身都浸在悲哀里;自从她知道了她丈夫委屈了她,她便一直流泪,憔悴下来,她的眼睛不肯向上望,她是脸也不肯离开地面。”(22-24)美狄亚甫一出场,就是呼天抢地,这个女人任她的情感外泄:“哎呀,我受了这些痛苦,真是不幸啊!哎呀呀!怎样才能结束我这生命啊?”(96-97)美狄亚这样子的情感流露甚至惊动了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克瑞翁执意要把美狄亚驱赶出境,因为克瑞翁担心美狄亚陷害他的女儿:“我不必隐瞒我的理由,我是害怕你陷害我的女儿,害得无法挽救。有许多事情引起我这种恐惧心理,因为你天生很聪明,懂得许多的法术。并且你被丈夫抛弃后,非常气愤。”(282-284)美狄亚也很清楚自己一直被情感所驱使,在第二场美狄亚对伊阿宋说:“只因为情感胜过了理智,我才背弃了父亲,背弃了家乡……”(479-480)在第五场美狄亚得知公主已经亲手接过了浸满毒液的礼物,料定她必死无疑后,美狄亚下定决心,要将她的两个孩子杀死。美狄亚内心几番挣扎,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我的痛苦已经制服了我;我现在才觉得我要做的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罪行,我的愤怒已经战胜了我的理智。”(1077-1079)美狄亚已经把还未实行的罪行当做了预定的事实。
在剧本中有关美狄亚情感压倒理性的句子有很多,上面两则只是她直接提到了“情感”和“理性”,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美狄亚本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她为什么不好好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使得事情不致如此悲剧地收场呢?
我们知道近代西方悲剧在基本精神上来源于欧里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它从探索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索人的内心。爱情、嫉妒、野心、荣誉、愤怒、复仇、内心矛盾和社会问题——这就是莎士比亚、拉辛或易卜生这类戏剧家作品中的动力。②那么我们看看《哈姆莱特》中关于情感与理性的态度。哈姆莱特赞扬霍拉旭:
因为你
虽饱经忧患,却并没有痛苦,
以同样平静的态度
对待命运的打击和恩宠;
能够那么适当地调和感情和理智
不让命运随意玩弄于指掌之间,
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③
哈姆莱特自己是“感情的奴隶”,他羡慕他的朋友那种斯多葛式的平静和无动于衷的态度。问题在于哈姆莱特羡慕归羡慕,这位忧郁的王子还是要完成他的复仇行动,了却自己内心的挣扎。
这些悲剧主人公都表现出“感情的奴隶”的样子,并且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理智已被情感压倒,明知这样子下去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而义无反顾。我们从古希腊悲剧一直到近代的悲剧,总能从悲剧人物的口中听到他们自己是如何被情感所控制,压倒了理性。这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理性应该大于情感,一个人更应该被理性的力量所控制,这一印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可事情真得是这样吗?我们说在文学形象中,一个感性的人更易获得读者(观众)的审美同情,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完全被理性控制的伟大的文学形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艺术不仅是表现,还有交流。
具体到《美狄亚》,我们说情感一直就是美狄亚行动的动力,即便是后面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所设定的缜密的复仇计划,也是一颗渴望看到伊阿宋痛苦的心所驱动的,我们说理性是从属于感情的,首先是想做,其次才是对具体过程的理性安排。在这里,我们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对第二场埃勾斯的出场颇有微词。
我们说美狄亚的复仇计划是一种“理性”安排的产物,不如说那是情感驱动的一套设计,一类规划。而美狄亚在第三场与埃勾斯的对话,却真属于一种理性的安排,而这样子势必会削弱美狄亚作为情感化身的形象,从而影响读者对美狄亚的审美同情。
在第二场美狄亚与伊阿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去你的!你正在想念你那新娶的人,却还远远离开她的闺房,在这里逗留。”(624-625)而到了第三场,美狄亚就有礼貌地对着埃勾斯打招呼:“埃勾斯,聪明的潘狄翁的儿子,你好?你是从哪里到此地?”(665-666)美狄亚颇为热情地与埃勾斯交谈,乞求埃勾斯能够收留她。“就这样吧。只要你能够给我一个保证,你便可以完全满足我的心愿。”(731-732)这是在做很清醒的交易。美狄亚得到埃勾斯口头上的承诺后,还要他宣誓必须庇护她,连埃勾斯都说道:“啊,夫人,你事先想得好周到啊!”(741)在这一场美狄亚表现得多么清醒、理性!她给自己找到了后路,她心满意足地说:“祝你一路快乐!现在一切都满意了。等我实现了我的计划,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就赶快逃到你的城里去。”(757-758)在这里,美狄亚因为提前确知了埃勾斯的庇护,以后她的行动就减了许多“终已不顾”的悲壮。但我们怎么能责怪欧里庇得斯呢?④美狄亚不是在先前也说过:“但是,如果厄运逼着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亲手动刀,把他们杀死。我一定向着勇敢的道路前进,虽然我自己也活不成。”(392-394)
我们在文章最后来听一下戏剧开场保姆的开场白:
但愿阿耳戈船从不曾飞过那深蓝的辛普勒伽得斯,飘到科尔喀斯的海岸旁,但愿珀利翁山上的杉树不曾被砍来为那些给珀利阿斯取金羊毛的英雄们制造船桨;那么,我的女主人美狄亚便不会狂热地爱上伊阿宋……”(1-4)
可是美狄亚就是狂热地爱上了伊阿宋。当伊阿宋咒骂着美狄亚和她那巫术一样恐怖的的爱情时(1323-1350),他应该明了他自己远远地不够承担起这份爱情。
[i]
① 《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括号内数字为所引句子所在行数,下同。
②《悲剧心理学》朱光潜,中华书局,2012年。摘抄自本书第六章:《悲剧中的正义观念:人物性格与命运》
③《莎士比亚悲剧五种》朱生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④《古典诗文译读》刘小枫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欧里庇得斯与血气》,特斯托雷撰,李小均译。本文中提到了《美狄亚》戏剧第二场埃勾斯的出场所引发的争论与合理性。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