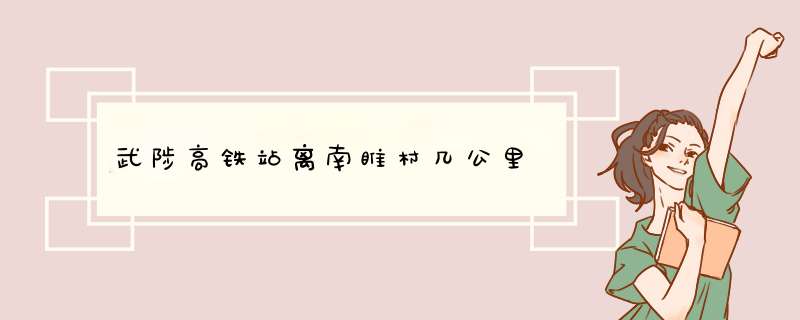
武陟高铁站即武陟站。
公交方案:
公交线路:武陟1路,全程约160公里
1、从武陟站步行约600米,到达火车站
2、乘坐武陟1路,经过18站, 到达后龙睡村站
3、步行约43公里,到达南睢村
驾车方案:
驾车路线:全程约152公里
起点:武陟站
1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行驶340米,调头
2行驶930米,左转
3行驶810米,右转
4行驶940米,左转进入兴华路
5沿兴华路行驶27公里,过右侧的瑞丰纸业园,右转进入黄河大道
6沿黄河大道行驶420米,左转进入沁河路
7沿沁河路行驶38公里,直行进入S104
8沿S104行驶800米,右转
9行驶32公里,右转
10行驶510米,左转
11行驶150米,到达终点
终点:南睢村
绛县雎村盗墓贼都有王某和张某以及于某等人伙。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盗墓贼王某和张某以及于某等人伙同当地的两个惯犯在雎村墓地发现了一个古墓,约定好在晚上行动,到达目的地后,却找不到原来发现的墓地了。
水族婚俗保留较浓的传统色彩,讲究明媒正娶。实行“同宗不娶”的族外婚,实行一夫一妻制。过去较盛行姑舅表婚习俗。解放前婚姻的缔结,基本上是依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长到十五六岁就订婚,十七八岁即结婚。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要结婚也必须通过明媒正娶的途径婚娶,否则会被认为不合利规而受到谴责和轻视。
水族是生活在我国的云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总人口约三十四万。操水语,属汉藏语系 壮侗语族 侗水语支,多数水族老人说来自江西省(说是江西吉水等地),有的说来自中原睢水一带,也有的说与古代“骆越”有渊源关系,但是其文化是水书,根源上只能来自中原地带。另有说法是,水族原为隋朝皇族后裔,618年隋朝灭亡其中没落皇族率众南迁,历经辗转由江西到达贵州三洞地区于当地苗布依族族共处,历经借鉴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在南迁过程中为了不忘祖先,自称“隋”人,因发音一致也称“睢”人,至今仍有“睢”人自称贵族。
水族婚俗简介 :
水族婚俗保留较浓的传统色彩,讲究明媒正娶。实行“同宗不娶”的族外婚,实行一夫一妻制。过去较盛行姑舅表婚习俗。解放前婚姻的缔结,基本上是依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男女长到十五六岁就订婚,十七八岁即结婚。自由恋爱的男女双方要结婚也必须通过明媒正娶的途径婚娶,否则会被认为不合利规而受到谴责和轻视。
青年男女相爱之后,先托人告诉双方家长。若家长表示愿意,男方才请媒人去女家送礼定亲,并择定吉日,派人抬着猪仔去女家“吃小酒”。正式迎亲时,再抬大猪到女家“吃大酒”。酒宴上要唱敬酒歌,女主人每唱一首歌,客人就得干一杯酒,以喝醉来表现主人的盛情。接亲与送亲男女双方的家人不参加,除少数地方由新娘的兄弟背新娘送至夫家外,多数是盛装的新娘打一把故意撕开一条缝的红纸伞步行在前,接送的伴郎、伴娘及抬着嫁妆的长队紧随其后。一般是新娘于中午出娘家门,傍晚六七点钟进夫家门,吉时不到,不得进门。新郎家的亲人在新娘进门要外出回避,新娘进屋后才能回家。新婚之夜,伴娘与新娘同宿,第二天新娘即回门去娘家住。婚期之后,新郎再去请新娘回来 ,开始夫妻生活。有些新娘第一次回门就长达一两个月时间,谓之“坐家”,实际上是“不落夫家”婚俗的残存余音。新娘出嫁的路上,最忌讳打雷变天,因此婚期多在秋冬举行。
水族婚姻形式演变 :
在水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其婚俗,经历过人类所共有的血缘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等婚姻形式。由于水族地区原始社会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反映在婚姻习俗上,仍不同程度地保存有男子出嫁、姑舅姨表婚、一夫多妻等原始社会的残迹。
男子出嫁
即所谓入赘,女子招郎上门的婚俗。一般是女方父母无子,为了传宗接代和生活有所依靠而招郎上门。另外,有的女家父母虽有子,但因父母年迈体衰,而子又年幼,缺乏劳动力,故招郎上门。前者入赘的时间较长,一直到女家父母去世“养老送终”。老人去世后,赘婚继承其全部财产。后者入赘的时间则较短,一般待妻弟长大懂事后,能独立生活和待奉父母时,女方父母便分给女儿女婿部分财产,另立门户。赘婿无财产继承权,凡入赘生的子女也都没有财产继承权。
水族的“入赘”之风,“招郎”之俗,过去在一些边远地区是普遍流行的。解放初期,外出去参军(当地方兵)过几年回乡的青年,打从小路经过边远山区,就有被招上门去做女婿的事例。这种婚俗的渊源,初期很可能是在一个民族内禁止血缘亲属结婚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禁止血缘亲属结婚的禁忌,可能渊源于母系氏族时期禁止血缘亲属之间结婚的规定。在当时,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婚姻禁例,才为从群婚制过度到对偶婚创造了条件,也才有可能使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一起过偶居生活。水族的这种男子出嫁,女子招郎上门的婚俗,是水族从群婚制发展到对偶家庭时产生的。因为只有男女青年成了亲密的伙伴,至认为对偶,男女才有可能到女方家为赘婿。
水族的入赘之风,以及禁止同宗男女之间的婚配,是水族婚姻家庭史上的巨大转变和进步。
姑舅姨表婚
过去,有些水族地区还残存着姑舅表婚和姨表婚的习俗,即舅家有娶外甥女的优先权,姑母生的女儿要优先许配给舅父的儿子,特别是生得美丽的姑娘,更是不允许外人“捷足先登”。否则,要闹出人命案来。还有姨表婚的习俗,也是如此,大姨妈和二、三姨妈之间的儿女,也优先许配,凡长得秀俊的姑娘,更不许外人抢去。非许配给姨妈的儿子不可。长相不美的女子,那倒不在乎。
水族的这种婚俗似乎不够文明、大方,近于自私一点,不管男女年龄是否相当,更不问当事人双方是否情投意合,只要舅家、姨妈家提出,即强行成婚。如果姑妈家的女儿不愿嫁给舅父家的儿子,而硬要嫁到别人家去,那男方就要备足一份彩礼,送给女方家的舅家,称为“赔娘钱”。姨妈家的女儿,若要另嫁,也同样赔送彩礼。但这种婚俗在水族各地区并不完全一致,如三都九阡地区的水族,则不竟然。解放以后近十几年来,这种姑、舅、姨表婚的习俗,已逐步自觉改变。男、子自由恋爱,自愿结合,感情融洽,直到结婚,已向进步方向转变了。但个别地方,还存在着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因此,结婚后,男女双方感情破裂便闹离婚,这是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宣传婚姻法,应多从这方面善加开导,移风易俗。
一夫多妻
旧社会,水族的婚姻以一夫一妻为主,但也有一夫多妻的。考察其历史原因,有以下三种情况:
1、有权势的男子,仗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力量,多娶妻纳妾。水族大地主一人有四、五个小老婆。如三都九阡区水董村的大地主原国民党联保主任潘炳兰,解放前就有12个小老婆。
2、夫妇婚后,多年不育,男子为了要孩子传宗接代,并为自己养老送终和继承财产,所以另娶妻纳妾。
3、旧社会,人们重男轻女,水族也不例外。如四十岁以上的已婚男女,尽管婚后已生了几个女儿,但没有生男孩,便受到社会上的舆论和讥讽,特别是女人受讥讽,更感难堪,因此男人争取大老婆的同意再娶妾想生子,以延续后代。
水族地区一夫多妻的家庭,有的分家,有的不一定分家。如因丈夫极为宠爱小妾,也有带其妾另居的。
异族通婚
过去水族通婚的惯例,一般多为本民族内部男女互相发生婚姻关系,但并无严格禁止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禁例,有的父母虽然不同意子女与其他民族的男女通婚,但一般父母并不硬性阻止,族内和社会舆论也不干涉。水族地区自从封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后(约自清代康熙以后),反映在婚姻习俗上,青年男女自由婚姻,逐渐转变为父母包办婚姻,青年男女就无婚姻自由了,因不满婚姻而又不能离婚,于是往往发生各种悲剧。解放后,水族青年男女婚姻比较自由,而且异族通婚之风,越来越盛,水族男女,可以自由与汉族、布依族结婚,组织的家庭也很幸福。这也是水族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
自由恋爱
1、几个青年男子共邀几个青年女子,晚上在寨脚、田坝“玩月”对歌。互相有好感后,男方就主动托媒人到女方家去说亲,若女方父母不同意,多数婚事即告吹,但也有姑娘本人同意并渴望成亲的,便先逃婚,逃到男方亲友家躲避数日,以观察动静看父母的态度有无转变。也有当事人男女双方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迫使父母同意而达到结婚的目的。
2、利用探亲访友的机会互相结识。当男青年进寨访亲会友时,本寨的姑娘闻讯后,便主动相邀前来探望。夜晚即在该亲友家对歌欢唱。对歌时,男女各自选择对象,就算初次结识,以后再找机会相约见面,或在赶场天再图会面。然后男方便托媒人上女方家求亲。此后,双方经常往来接触。逐渐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3、当男的在某种公共场合,如赶场等,对某姑娘钟情后,就主动托熟识女家的人,先去摸底,试探女方父母的态度。如博得女方父母的好感,男方则乘机经常携带些酒、肉、粑粑、红糖和叶烟等礼物,主动登门拜访。若女方家乐意接收礼物,就意味着情况将会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这样,男方就更加积极主动,拜访也就更加频繁。使其他男子都知道这两家已结成姻亲之好后,也就不会再有人上门说亲了。经过多次往返,女方也就正式允诺这门婚事了。解放后,水族地区青年男女婚姻的缔结,一般也要经过三个阶段,即自由恋爱、媒人说合及最后由老人决定。接着,还要履行订婚和结婚仪式。
水族 婚姻程序:
说亲
解放前,水族办婚事,聘礼高昂,男女双方的家庭负担沉重,铺张浪费很大。一般婚嫁要经过说亲、订婚和结婚三个步骤。基本上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
如某家男子的父母看中了某家的女儿,认为该女可做其儿媳,或某男喜欢某女,即告知父母,若父母也以为合适,首先男方托媒人到女方家去说亲,说亲时须通过“吃媒酒”,议定婚约。一般是男方请媒人二人携带礼物上门讨喝媒酒(事先通知女方)。若女方表示不反对,第二次媒人便带礼金再去。礼金除现款外,还要备有姑娘的银项圈,其它银饰和衣物。如女方同意并收下礼物,就备酒席设宴款待媒人,女方亲戚中除每家出席一人作陪外,也有两名媒人入席,媒人一般多为女方的亲戚。席间互相交杯喝媒酒。这样才算说亲(谈婚)成功。接着,女方的所有家族,不论几家或数十家,也都轮流宴请男方媒人,男方媒人必须各家都要走到,不能怠慢无礼,否则,婚事又会出现波折。
订婚
水族对履行订婚手续和举行订婚仪式,历来都普遍重视。订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男女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这样婚姻也就变成了买卖性的交易,女子就成了事实上的商品。订婚就是预订产品,把女子的所有权在未到结婚年龄时,就先为确定,使别人不能染指。在水族谈婚成功婚约议定后,女方又须索取高额彩礼。结婚前男方必须将彩礼全部付清。到将近结婚时,男家择定了吉日,把聘金及其它礼物送到女家。彩礼除现金三、四百元外(也有高达八、九百元的)还要送银饰二十到五十两不等。当时每两价值现金约五元,及酒、肉、红糖、粑粑和烟叶等。
女家设宴招待,男女两家的媒人四人都在场,桌上放四碗酒,四人对席入座后,各将面前满碗的酒一口喝尽。若女方认为男方送来的彩礼过少,即事前告知女方的媒人暂不喝酒以示要挟。于是男家媒人就得当场加码若干(男方媒人即要离席外出找本寨或附近寨子熟识的亲友暂借现金若干来应付场面),到了女方满意后,再双方同饮。饮毕,女家家长即撒席。女方家也回赠给男方二十几尺布及糯米饭、粑粑等,数量必须成双。订婚那天,女方要把男方送的彩礼包括现金及银饰等物当场公开摆在女家的堂屋供亲友观赏,以示男方的家境及姑娘和身价。这样订婚仪序才算完结。
结婚
水族的结婚礼节极为隆重。结婚前,男方先要女方的“八字”,女方将“八字”写好,用红纸包好后,送给男方,男方请巫师根据男女双方的“八字”择吉日决定结婚日期。
结婚那天,新娘打新布伞,穿盛装,佩项圈等银饰,由本寨亲友中四至六位姑娘陪送步行(近几年来多坐车)去男家。女家陪嫁除被、帐等床上用品和一两口木箱外,还有大衣柜(解放后送缝纫机)等各种嫁妆。有的还根据经济情况陪嫁马一匹及糯谷若干挑。新娘出嫁前,其母、姐、妹及嫂等都要互相哭泣送别,表示舍不得姑娘离家。新娘出家门时,双脚不能着地,必须由同胞兄弟或血缘较亲的兄弟背出去,并且打伞遮着姑娘出家门。途中如需过桥或涉水,也要由亲哥弟背行,男方派亲朋到半路去迎亲,还送去糯米饭和菜,使女方送亲来的亲戚们半路吃晌午。女方的嫁妆等当即交给男方的迎亲者。
新娘出娘家门和进夫家门,都必须严格遵守巫师规定的时辰,即使进了寨子,未到预定的“良辰”也不能踏进夫家的门。新娘进门时,仍由其兄或弟背进去。当新娘将进夫家的村寨时,寨上的姑娘们守候在村寨入口处,故意不让新娘进寨,大家都争抢新娘的鞋,“抢鞋”据说是看新娘的针线活做的好不好,手脚是否灵巧。有些地方还有新娘只穿一只鞋进夫家的门的习俗。新娘在等“良辰”时,也有拿新娘的鞋抛耍,或故意抢女方送亲人的雨伞等东西的,当然,这些嬉戏的场面是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
在新娘进男方的家时,夫家的全部女眷,即丈夫的母亲、姐、妹及嫂嫂,必须离家暂时回避(姑娘在离娘家时,母亲也要回避),不能目睹新娘进家。待新娘进屋坐定后,才能陆续返家和新娘见面。意思是在家里见面,将亲如手足,会永远和睦相处,全家人会更加团结。结婚头三天,新婚夫妇不同居,也不许任何男客进入新房。新媳妇于第四天,即由男方姐妹带些糯米钣等礼物陪送回家。住一夜后,男方派女眷去接,新媳妇即返夫家,于是新媳妇才正式和丈夫同居。有的水族地区,则比较守旧些,就是新媳妇回娘家后,暂时不去夫家,要在农忙或节日,男方专派女眷去迎接,新媳妇才返夫家,但也只是短住数日。这样经几次往返,历时半年后,新媳妇才能长住夫家,并和丈夫同居,新婚才基本稳定。
水族婚嫁习俗 :
洞房对歌
水家人的习俗,新娘出阁不兴拜堂,也不准闹洞房。但当晚男方青年歌手们可以找女方陪娘对歌。对歌时,男歌手只能在洞房外面唱,女方歌手就在洞房里面唱,一里一外,一唱一答。所唱的歌都是传统古歌,不能乱编唱。场面严肃而热烈。唱到深更半夜,男家就摆酒席请歌手们吃夜宵,双方就在酒席边相对而坐,继续对唱,欢歌达旦。
哥弟送亲
水族姑娘出阁,必须有亲哥弟或堂哥弟陪同往返。按习俗新娘出大门两脚不能着地,就由弟弟打伞,哥哥背出家门。然后与陪娘一道步行。若在途中遇到重踩别人脚印的时候,哥弟又需背新娘走过交叉路口。进入男方家门时,仍由哥弟两人,一个打伞,一个背新娘进门。这种习俗,体现兄弟姊妹互相关心的手足深情,亦为水家人独有。
新娘拜井,挑水认亲
新娘到男家的头一两天,要去拜井,这是水家的例规。抽空邀约几个亲姑娘一道悄悄地去拜井,一则了解水井的位置和远近,二则为几天后挑水认亲作好思想准备。有的地区新娘去拜井时,必须随身带去两个鸡蛋放在水井里,若两个蛋是相依相靠,就说明夫妇白头到老,姻缘美满。待新娘回门归来,就履行挑水认亲义务。由新郎妹妹陪同,挑着水桶给家族伯叔兄弟每家每户送一挑水,表示认亲。这种习俗至今仍然保持不变。
水族婚姻禁例 :
水族具有传统的优良道德风尚,反映在婚姻习俗上,形成了一套有关婚姻习俗方面的禁例习惯法。在水族历史上,这种习惯法曾对民族内部的团结、对水族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等起了巨大作用。对男女的不轨行为,不仅会受到族人社会舆论的普遍强烈谴责,而且惩罚也极严。因此,很好地调查研究、总结水族婚姻习俗的习惯法,加以推广,对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凡已婚的男子与有夫之妇通奸,男子必须赔给奸妇的丈夫金钱和衣物,同时还要罚奸夫备酒肉,请奸妇丈夫全寨的人大吃一天。否则,奸妇男方家族的男子就结伙到奸夫家,将其妻的全部衣物和银饰掳掠一空,并把家具全部捣毁。最轻也要牵牛杀猪并饱餐一天。
男子跟未婚女子通奸,一般不作任何处理。如女子怀孕,男方要向女方家赔礼道歉,必须成婚。如男方不愿成婚,一旦女子嫁不出去,则要男子抚养一辈子。与未婚女子通奸生的孩子,由男家抚养。未婚女子怀孕后,不能在寨内生产,必须在寨子外边搭棚子分娩,分娩满月后,才能回寨子。但私生子不能和外公及父母居住在一起。
每天读点故事作者:宁汐染
1
燕娘被卖进筒子楼里四年了,这四年里,若不是有莺歌护着,她只怕是成了筒子楼后院花园里的一抔黄土。
筒子楼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而莺歌是安乐坊里的前头牌,她生来就一副好嗓子,唱出来的曲儿勾人魂儿,只是后来着了道,嗓子毁了。
这世道艰难,生活着实不易,莺歌在筒子楼的地位一落千丈,也护不住燕娘了。
燕娘望着麻姑送来的纱衣,换上纱衣后,莺歌为燕娘上妆,燕娘惊呼:“莺歌姐姐,上完妆,我真好看。”
听到这句话,莺歌鼻头一酸,眼泪就落下来了。她背过身擦擦眼泪,伸手点了点燕娘的额头,“傻孩子,在这个安乐窝里,太过美就是一种罪。”
燕娘何尝不知道呢?她和莺歌用四年时间存了近百两的银钱前去赎身,麻姑抽了口鼻烟,拎了拎钱袋冷笑道:“小丫头片子,就这点钱还想赎身?这就算你孝敬麻姑我的了。”
纠结良久,她摸了摸胳膊上的疤,绝了赎身的念头,一个姑娘家在窑子里待了几年,出去后多被人瞧不起,隔三差五的就会被骂上几句。
“燕娘,时间到了,该下去了。”燕娘收敛了心神,走出房门后转身冲莺歌笑了笑。
今儿晚上安乐坊里有八位姑娘成了待价而沽的货物,麻姑早就严厉地训斥过所有人,要好好表现,实现自身最高的价值。
燕娘是最后一位上台的。她肌肤白嫩细滑,桃花眼,瓜子脸,眉间有颗美人痣。刚上台,就有一位手戴玉扳指、大着肚子的商人喊道:“麻姑,我出一百两。”
“杨老爷,出手阔绰。起步价一百两。”
熙熙闹闹的人群,整个厅里乱哄哄的。燕娘望着台下原形毕露的男人们,哪一位才是她第一次的恩客呢?
喊到八百两的时候停了,燕娘看了那人一眼,是大黄牙刘品。突然又有人喊:“一千两。”
“燕娘以后就是顾督军的人了。”麻姑捏着银票喜笑颜开。燕娘偷偷看了顾督军一眼,又低下了头。
2
城里传遍了顾绍玮督军的流言,褒贬不一。他是一个大老粗,驻守睢城不过两月,就以铁血手段著称。那些有文化的官老爷们既惧怕他又看不起他,堂堂督军竟像土匪一样不讲理。
顾绍玮摸了摸腰间的枪,大步走上台,脱下披风包好燕娘,抱在怀里走了。
深秋的天带着萧瑟的寒意,马蹄踏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发出哒哒哒的回响。燕娘听到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可她却觉得很温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内心深处的。
在安乐坊里,教习嬷嬷只会教姑娘们穿得越少越好,来的客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脱掉姑娘们的衣裳,只有他给了她一件披风,给了她应有的久违的尊重。
回到督军府里,燕娘沐浴过后穿上寝衣,坐在床沿。时不时地瞟一眼顾绍玮,双手紧紧揪着袖口,不一会儿棉质衣服就起了褶皱。
顾绍玮松了松袖口,嘿嘿一笑,露出了一口大白牙,“燕娘,不用紧张。我又不是大老虎。”
“督军说笑了。”
“不用喊督军,我名唤石生,就是个粗人,顾绍玮还是我发家之后花了十两银钱取的,那些个读书人说能兴后世之业。”
“好。”顾绍玮的这一席话倒是让燕娘的眉眼舒展开来。
隔天下起了秋雨,打散了一地菊花,从此督军府里多了位燕夫人。顾绍玮送来了两个丫头明月和松芝,她觉得这督军府里丫头的名字都比其他人的好听几分。
燕娘名叫燕婉,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村子里,她能有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归功于她的秀才爹,若不是时年不济,爹娘相继去世,她也不会被二婶卖给安乐坊。往事浮上心头,总有些意难平,便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顾绍玮回到房里,伸手抚平燕娘的眉头,屋子里虽烧着煤炭,但他带着深秋的寒气的手温还是让燕娘哆嗦了一下。
“燕娘,住不惯?”说罢退到炭炉旁温温手,祛祛寒气。燕娘摇了摇头,为他倒了一杯热茶。他伸手摸了摸燕娘的小脸,满眼怜惜。“燕娘,日后好好养着,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石生,多亏了莺歌姐姐的照顾。”
3
燕娘托松芝帮忙找人给莺歌送去了些银钱,这两个月顾绍玮送了她不少首饰,她都攒起来了,等哪天他厌弃她了,她便拿出去当了,买个一进的小宅子,陪着莺歌度过余生。
腊八节到了,燕娘早早就起了,泡上糯米、红豆、绿豆、莲子、红枣……熬了一锅香软浓稠的腊八粥,吩咐好明月好好保温,等督军回来。
下雪了,这是离开安乐坊的第一个冬天。燕娘站在园子里,伸手接起了雪花,一片片的雪落在手心里,瞬间成了水珠。
顾绍玮回府看见燕娘站在原地发愣,头发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他喊了一声燕娘,冷不防地吓了燕娘一跳。燕娘抬头一笑,眉间的朱砂痣在白雪的衬托下,愈发鲜艳。
拉着燕娘回房,顾绍玮先让人熬了驱寒的姜汤,还呵斥道:“多大的人了,还不会照顾好自己。”
燕娘换了身衣服,喝了一大碗姜汤,被顾绍玮盯着捂了一身汗,这一件事才告一段落。他喝着燕娘熬的腊八粥,喝出了家的味道,如今世道不平,他都忘了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待在督军府里的第一个年如约而至了,燕娘陪顾绍玮守岁时提起小时候的一些趣事,因着家境不好,十一岁还面黄肌瘦,反倒是被卖去安乐坊里的那几年才被养得胖胖的。
燕娘提起这些,眼睛里亮晶晶的。顾绍玮揉了揉她的头发,取笑她好养活。是呀,她也没想到风月场的自己能成了督军府的姨太太,唯一的姨太太。
守到后半夜,燕娘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她梦见了才到安乐坊里的日子,梦见了莺歌向她伸出了手。
大年初一,顾绍玮就忙碌起来了,直到二月份,才算闲下来。燕娘总是听府中的下人说政局不稳,督军要靠联姻维系如今的平衡局面。
4
燕娘病了,一直不见好,请了一波又一波大夫,总是说夫人体质不好,忧思过重,郁结于心。
顾绍玮从临城赶回府,已过了近半月。他胡子拉碴的坐在床前,燕娘吃力地抬起手,摸了摸他的鬓角,望着他眼底的青灰色,埋怨道:“又不好好休息。”
“石生,我想莺歌姐姐了。”说完燕娘喘了几口气。
顾绍玮摸了摸燕娘的脸,这大半年养的肉都没了,他不免有些心疼。“好好养养,等身体好些了,请莺歌来。”得了顾绍玮这句话,燕娘才沉沉地睡去。
顾绍玮怎么也没想到活蹦乱跳的人儿成了这般模样。当年他被人偷袭,换了便装趁乱躲进了安乐坊,是燕娘让他藏在柴火垛里,又割伤了自己的胳膊,才救了自己一命。
他记住了那个小丫头眉间的朱砂痣,等他占领睢城,处理了公务前去寻她,她站在台上神色平静,好似这一切与她无关,正是她当初的沉着冷静,才让自己上了心。
过了三日,莺歌随着顾绍玮的副官到了督军府。看到的就是坐在躺椅上晒太阳的燕娘,脸色苍白,眼神没有任何焦距。
“燕娘。”莺歌笑着流着泪走了过去。
“莺歌姐姐,你终于来了。”
让明月松芝退了下去,燕娘抱着莺歌哭了一场,把近日里这些委屈都哭了出来。哭着哭着又笑了,燕娘觉得自己太贪得无厌了。
顾绍玮带她逃离了牢笼,给了她衣食无忧的生活,她却想一个人独占他,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莺歌在督军府待了小半月,她陪着燕娘去赏花游湖,讲讲官僚人家的风流韵事,燕娘倒也不想太多了,苍白的脸色又慢慢红润起来。
莺歌辞行那天,燕娘偷偷找来了很多珠宝首饰,用小木盒装着塞给了莺歌。“莺歌姐姐,这些首饰你拿去当了吧。这些够你赎身再买个小宅子了,指不定哪天妹妹就要去叨扰你了。”
“傻姑娘,这些督军都已经替你想周到了。你听姐姐一句劝,现在这世道哪个男人不是妻妾成群,这督军府中如今只有你一人,哪怕督军成亲了,也会善待你的。”
莺歌终究没收下那盒首饰,燕娘笑笑没有言语,她是以色待人,容颜易逝,顾绍玮给她的宠爱又能延续多久呢?她也该歇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5
莺歌走后,燕娘一人时常胡思乱想,就跟着花匠在花园里养养花,消遣消遣时间。有时心里想着花就顾及不了顾绍玮,这使得督军非常不满,狠狠地惩罚了她一番。
顾绍玮决定十天后宴请同僚,燕娘作为督军府里的半个主子要制订好流程,中间不能出差错,好在有管家的帮衬,她才不至于手忙脚乱。
宴会那天,顾绍玮送了几套衣服,有改良的旗装有旗袍。燕娘没跟风新式,仍旧是黑直长发,便选了旗装。
装扮好,她随着顾绍玮坐在主座上,看着各个军官虚伪谈笑,真是好生无趣。顾绍玮私下里捏了捏燕娘的指尖,倒让燕娘红透了脸。
这场宴会宾主尽欢,临结束时,顾绍玮宣布要娶妻了,日子订在两个月后。听到这个消息,燕娘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总要来的。
服侍顾绍玮沐浴时,燕娘轻轻为他按摩太阳穴,他舒服的闭上了眼睛,忽然听到燕娘说:“若是夫人来了容不下我,督军便放我出府吧。”
顾绍玮突然睁开双眼,把燕娘拉下浴池,抱着她的腰轻声问:“你怎知夫人容不下你?”
燕娘垂眸不语。
“傻姑娘,难道你自己还容不下自己吗?”
燕娘愣了,不知该作何反应,她自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身份。而顾绍玮趁着燕娘发愣,低头吻了下去。(作品名:《燕婉》,作者:宁汐染。来自:每天读点故事,看更多精彩)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