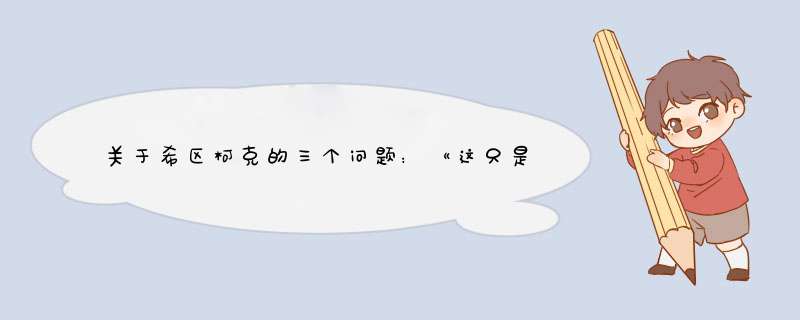
《这只是一部**》是一本好八卦。作者夏洛特·钱德勒对希区柯克周遭世界的探访,仿佛叫读者经历悬念版爱丽丝梦游仙境,得以在希区柯克每部**的片场外偷窥、窃听,揣摩永远着西装领带的希区柯克将导演怎样的谋杀,设置怎样的奔逃,安排怎样的调度。有时也观看他的私生活,瞧他怎样带女儿帕特丽夏去商店买她不爱穿的拘谨衣裙,瞧他怎样在电梯里当着陌生老太太与友人在电梯里说:“你把刀上的血擦干净了吗?”
八卦使原先脑中单调而遥不可及的大师丰满起来,成为有趣的人。此外,散落于这些八卦中的一些细节,令我特别注意到,并促使我分析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我想应是关乎希式**本真的。
希区柯克是完全的**生物。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每次正式开拍一部**前,他已在大脑中“拍”好了这**,到现场,每一个布景如何安置,每一个镜头如何走向,这场戏与下场戏的剪辑点,了然于心,毫不犹豫。他不过是要成为指挥家,叫乐手们将自己创作的乐谱演奏出来。当然,拍**这事情并非完全靠“大脑”,便是乐谱,也要抄写下来。在拍摄之前,希区柯克会画详尽的故事板,制作人员会惊奇地发现成片后的构图、光线、角度、景别,与最初的故事板毫无二致。也因此,希区柯克没有“导演剪辑版”的烦恼,任何制片人企图收回最终剪辑权,拿走他拍好的胶片,最终还是徒劳。这些胶片只有一种剪辑法——希区柯克式的剪辑法。
也即是说,希区柯克的创作在开拍前便完成,所有的创作乐趣也已享受,拍摄本身只是一种劳累的苦力活。所以他觉得——“**最无聊的一部分就是拍摄阶段。”在大脑里“拍”**这种本领的发端,据本书的采访,是在1923年。当时还只是他同事的阿尔玛**在剪辑一部影,请希区柯克帮助拍一些过场镜头。他到布景舞台上,冲摄影机取景器向被摄物观看,摄影师杰克·考克斯对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只要看着它前面的东西就可以了。”
从此,希区柯克开始向考克斯学习镜头、取景、拍摄角度的知识,并训练自己像摄影机一样观看事物并想象成场景。他知道什么光圈、焦距的镜头有什么特色,知道什么型号的光有什么阴影。所以“在大脑里拍**”并非神话,不过是希区柯克看待**的方式,他逼自己用画面思维组织一切,包括故事、悬念,直至深层意义,只要置身**创作,他所操持的语法只是画面蒙太奇。这种画面语言之随心所欲,入化境。比如在《惊魂记》的著名浴室砍杀中,刀从未真的落在女人身上,杀手也未露面,女主角甚至用替身,但无所谓,希区柯克操纵画面,并完全操纵观众的注意力,迫使观众以自己的想象补齐刀刀入肉的恐惧感——于是吓得不敢洗澡了。
希区柯克的“胸有成竹”,也强迫他要对**拍摄技法(包括构图、调度、剪辑)做刷新。因为一旦设想出画面,他一定要想办法来实现,这便需要在拍摄现场思考许多新特技。我们得以在《迷魂记》中看到无数旋转体并铭记于心,在《后窗》中看到仅靠室内的偷窥就能完成一出好戏,在《鸟》中看到群鸟攻击,在《海外特派员》中看到**史第一回海水灌向飞机驾驶舱的惊心场面……《鸟》的美术指导罗伯特·鲍伊尔说:“希区柯克会将任何一个镜头的技术层面推向极致,如果这么做可以满足他试图表现的那种内在感觉的话——无论是悬念、恐惧还是其他感觉。”
我便觉得,对待希区柯克的**,时常该从故事、意义抽身出来,单单去享受每幅画面怎样连接与运转。
“演员是牲口”这话令希区柯克显得十分霸道。但书中许多采访,演员都否认希区柯克曾这样说,最多是在《鸟》中,希区柯克发现一只鸟有表演欲,于是开玩笑,希望演员能像鸟一样受摆布。希区柯克自己觉得即便他说过这句话,也是玩笑,他真正意思是希望演员们为他提供一种“消极表演”。他在片场不给演员表演方式上的指导,通常只让他们“走到这里,走到那里”或者“看左边,看右边”。这种简单的导演方式令方法派演员十分困惑。《冲破铁幕》的主角保罗·纽曼便因此与希区柯克不能融洽合作,他写了人物大纲,向希区柯克请教人物的背景与动机,希区柯克不耐烦:“动机就是你的薪水。”
《艳贼》的主角肖恩·康纳利十分晓得并尊重希区柯克的导演法,“对他来说,任何的讨论都是‘过分讨论’。”
这问题与希区柯克在脑中拍**的方式是相通的,希区柯克一早安排下情节、悬念,演员最重要的是以正确的动作还原他脑中的想法,而非考虑动作之外的动机与背景,不需要做即兴的发挥,这样做反而要破坏早已经设定好的故事氛围与走向。“方法演技派的演员演话剧可能没问题,但拍**时,我们从他的脸部切到他看到的东西,即摄影机的主观镜头,这就必须得有纪律了。”
这“纪律”正是希区柯克式画面语言。方法派演员演技的发挥,企图令画面重点转移到人身上,这就偏离了轨道。希区柯克的**中,人的作用常常不如打火机(《辣手摧花》),或一座风车(《海外特派员》)。演员在动作之外要求得更多,便威胁导演对故事、画面的掌控,演员突出,故事的流畅就被捣乱。希区柯克不喜欢,或者痛恨这一点。至于人物形象,希区柯克宁愿用食物去丰富:“对食物的偏好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我影片中的人物绝不会吃与他性格不符的食物。”对方法派随心所欲诠释角色概念的做法,希区柯克说:“那不是表演,那是写作。”
所以,“演员是牲口”是希区柯克装配**的重要原则,他希望演员是活动道具,与所有道具一般平等地打造好每一幕场景,这样许多“本分”的场景仿佛火车的车厢,剩下的任务专看希区柯克怎样将它们连接,得以顺轨道疾速前行。装配好场景的所有目的是令观众激动:“希区柯克说重要的不是演员如何感受,而是观众如何感受。他想从演员那里得到的是‘动作,而非动机’。”
“这只是一部**”这句话在书里重复许多次。前言里便有英格丽·褒曼希望找希区柯克问诠释角色的动机,希区柯克说:“英格丽,假装就行,这只是一部**。”
拍《阴谋破坏》,演员西德尼对片中弄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十分不满,她认为没必要,并告诉希区柯克,得到回答:“这只是一部**,西尔维娅。”
拍《辣手摧花》,主角法利·格兰杰有时自己想出一句台词,说出来并不适合表演,对希区说:“哦,妈的!我很抱歉。”希区柯克不在意:“这只是一部电……影。”
拍《迷魂记》,金·诺瓦克就角色动机问了希区柯克一个问题,希区柯克严肃地看着她,说“我们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挖得太深。这只是一部**”
……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好像他总觉得自己的**并不值得深入“动机”的层面,这便是他对**的态度?自然不是,他说,“每当我因为拍**遇到的问题过分紧张时,我都会对自己说,‘记住,这只是一部**。’但这话从来都不起作用,我从来都没能说服过我自己。”
这句话好像镇定剂,在片场能够让演员贯彻“活动道具”的原则,把演员从游走的神思中拉回来,专注于“向左走,向右看,拿刀砍”之类动作指令。另一层意思,希区柯克从未将**看做思想或意义的载体。与特吕弗的谈话录中表明,他最讨厌影评人从他的**中分析道德话题,反感别人对影片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而不是影片的效果好坏感兴趣。他也蔑视**审查部门对影片“接吻不能超过三秒”,否则便道德败坏之类的限制,他在《美人计》中,将长达三分钟的吻戏拆分十五次,“每次不超过三秒钟”,以此做一种挑战与嘲讽的姿态。
希区柯克关注的,只是令观众“激动”。当他的悬念情节起作用,他的惊悚镜头有效果,一部**便完成使命,而他自己也得到创造的满足。观众的激动与自己的满足,便是希区柯克**的最大目的,他的**不承担别的用途,所以他愿意总说“这只是一部**”。但这简单的目的,终究还要一条丰富而扎实的道路来达到。终其一生,希区柯克都在“惊悚悬念”这种技艺中沉浸,并以此创造不胜数的**技巧。他专注一个类型,却令此后所有类型影片的叙事技巧承继无限丰富的遗产。“这只是一部**”便成为所有**的路碑。
我只能将“这只是一部**”这句话做这般勉强的解释。其实满不止这么简单,我浅薄的学识,没本事深入了。
看完这本书,最叫我最喜欢的八卦是关于希区柯克与他妻子的。希区柯克真正爱上的事情,一是他的**,他一生以此为乐,并且除了**,“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比**更爱的,是妻子艾尔玛。自希区柯克求婚起,从一而终,厮守五十八载。
末了,把这八卦抄两段,做标记,并与大家分享。1979年,美国**学院给希区柯克颁终身成就奖,他按俗例致一份不俗的感谢词:“在曾经为我做出贡献的所有人里,请允许我提到四个人的名字,她们给予我最多的关爱、欣赏与鼓励,以及长期的合作。四人中的第一位是个**剪辑师;第二位是一名编剧;第三位是我女儿帕特的母亲;第四位是位一直在厨房中展现奇迹的优秀厨师。她们的名字都是阿尔玛·雷维尔,我要与她分享这个奖,正如我与她分享我的生活。”
他也在采访中对本书作者说,“**是我的生活,但即使不能再拍**,我也希望能继续活下去——和夫人一样长。她生病,我的每一天也都过得不再精彩。”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电视剧似乎还残留有一点现在中国所谓的小资的调调,跟故事本身倒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就看片头曲的话,cheers和 growing pains的主题曲都是很舒缓的曲子,配的图都是静态的,很传统的照片。cheers的主题曲"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尤其讲的是人在城市里的孤独,故事讲的是北美的文化故都boston,片前放些还蛮欧洲感觉的老照片。growing pains作为一个leave to the beaver式的宣传美国家庭观,很有粉饰太平之嫌的去advocate american dream的电视剧居然不叫growing gains,却把重心放在pains上,虽然整个剧情其实很轻松,很理想化,起名起的还是挺闷骚的。
无聊下揣测一下,那一段时间从Ronald Reagan到George H W Bush,似乎是美国价值重建的一段时期,从冷战的危机中爬出来,经济开始复苏,伤感也慢慢退去,baby boomers们沉淀下来。不过接下来的和平和繁华似乎又带来一点浮躁,1994年的hollywood**很特别:Pulp Fiction,Color of Night,Natural Born Killer,九十年代初的大片给人的感觉特别的sensual and raw。剧情比今天的**简单很多,拥有跟多的象征意义和一点偏执狂式的艺术感。今天的**速度快很多,更实际,冷静,讲究画面和音效创造的fancy。
另一个看老电视剧的趣味在八卦,看龙套演员,Leonardo Dicaprio唯一一次和Hillary Swank演对手戏似乎就是1989年了。Hillary Swank真真正正还是跑龙套的小屁孩儿,Leo慢慢开始崭露头角了。在当时看来,leo蛮可爱的,但是其实没有演他两个兄弟的Kirk Cameron和Jeremy Miller帅。Kirk当年真是英俊阿,现在显得苍老而颓废,演艺圈里面好多人只有那15 minutes of fame,不是每个人都能像leo一样有天赋有运气。Mathew Perry的头一如既往地一申一缩的,演到一个还算二线主角的戏,可惜戏里面年纪轻轻的女主角的男朋友,NYU的sophomore居然被车给撞死了,让人联想到friends里面的Joey,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来Matt跟人解约了什么的。Brat Pitt从1987年就是他一向花花公子的风格了,笑的时候喜欢用舌头砥住下嘴唇。
一个女人的美丽似乎有一半是瘦出来的,让人看到她的瓜子脸和性感的颧骨。Tracey Gold在第一二seasons里面圆脸,团团的鼻子,带一个大大圆圆的棕色框的眼镜,跟英俊的Kirk和笑起来两个巨大的酒窝的Jeremy比起来实在不算是漂亮的童星。戏里面哥哥Mike老是叫Carol, toilet face或者pig。据说常年这些笑话在小演员心中留下阴影。1988年开始19岁的Tracey减了23磅,1991年厌食症开始威胁到Tracey的内脏,女孩子开始面临死亡。1992年初Carol离开columbia去london实习,其实是因为Tracey的skeletal look太过惊人,被强制离开剧组。不过91,92年的时候Tracey确实很漂亮,也是因为女大十八变吧,瘦出棱角以后很像Jennifer Aniston,哥哥也只会骂她讨厌,不会嘲笑她丑了。
Chelsea Noble 1989年和Kirk在Growing Pains里面演对手戏,到1991年和21岁的青春偶像Kirk结婚,Chelsea又回到剧组。看一个女人对漂亮的苛求不是看她脸(大家都懂得要打扮脸),而是看腿,脸看上去可以使为了自己赏心悦目,脸可以靠妆和头发,腿的线条是要牺牲健康才能得到的,腿是用来勾引男人的。Chelsea的腿一看就知道她确是模特出身的。正如Carol在戏里面说的,Kate grazes。猜想现实生活中Chelsea也是同样的人。
片子结束于 Maggie Malone在DC找到了一个Senator手下的工作,一家人于是要离开Long Island。Sitcoms的主角其实是一幢房子,而不是屋檐下来来往往的那些人。这些三堵墙的房屋里面的生活是给四堵墙里的人看的。我总觉得 sitcom是很政治性的,给那些同样生活在一堵堵墙后面的人催眠,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生活。Maggie Malone作为家里唯一一个拒绝叫Seaver的人,从名字里面就看出这个角色在引领80年代末继续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此结尾,只是想说这一家的生活不是围着男人转的。Maggie在倒数第三集里面对自己说,When I think of my family, my marriage, my career, I realized I am one of the few women who really have it all。似乎在告诉大家,一个女强人,一个career woman也是会有好下场的。
我想大部分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 都会羡慕这个家庭氛围当中的那种宽松 我们国家的家庭很少有这种教育方式 主人公的选择又恰倒好处 记得同时期还有另一部令我印象深刻的电视剧 叫<电脑娃娃>还是<机器娃娃> 里面有个小女孩是个机器人 每天欺负家里的那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隔壁有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非常喜欢他 并且说出来的话相当成熟 甚至都表白了 她说'给我一个爱 给我一个人 给我一个爱人" 小男孩做完呕吐状后 说'给我一个没 给我一个门 给我一个没门' 我到现在还记得。
很小的时候看过译版的growing pains,可能翻译后语言的曲解,也可能那时候也从来没体验过什么pains,总之那时候都不知道剧里的观众为什么而笑,更谈不上会有什么感觉了。
可是多年后重新一集一集地体会,却被里面的一家幸福的人儿感动。
Jason是幸福的。在我看来,对事业来说,没有什么会比从事一份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更幸福的了。在人生中可以通过工作给一些人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这比在工作中赚很多的钱更重要也更困难。Jason也曾经怀疑过自己作为心理医生的工作价值,但是当他通过开导一个问题少女而拯救她的时候,自己也发掘到了工作的意义。同样有价值的是,他把自己的工作本领用于和家人的沟通上,培养出一个又一个各有各的缺点,却都在不懈寻求自我实现的孩子。能有比Jason更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幸福的吗?
Mike是幸福的。虽然他在传统看来一无是处,前途一团乱麻。可是他珍惜生活中每个让他感动地瞬间,每当他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每当他从小小的成功里得到了快乐,每当他发现了可以尝试的人生方向,每当他感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每当他学习到了人生的哲理,他都会在心里感动一下,偷着乐一下。只要人生中还存在一些能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和一些能偷着乐的事情,人生就不是麻木的,人生就还有希望,这样的人生就是幸福的。
Ben是幸福的。作为一个成年人,能做到像他那样,今天不去烦恼明天的事很难,毫无顾忌地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更难。当我们进入这个社会,生活的压力自然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远虑近忧,人际的压力也会让我们表现很多的虚伪。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忧虑,都会影响快乐的心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虚伪,都会受到自己的谴责。所以我觉得,跟随并展现真实的自我,而不屈服于外因,虽然对成人来说不太现实,但仍然应该我们尽力追求并且实现的理想状态,因为这才是幸福的根源。
Maggie是幸福的。虽然和所有拥有或者即将拥有家庭的人一样,她也无数次面临事业和家庭的选择,但每次关键的时候,她都作出了伟大的牺牲。最难得的在于,她可以为自己的牺牲而感到自豪和快乐,这是因为她有一个值得她牺牲的家庭。人生作出无数选择,绝大多数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或者最优的答案,很多人在作出选择后都容易看到消极面而忘了积极面,所以永远觉得自己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能珍惜自己因为选择而得到的更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放弃的那部分,同时又有一些自己关心和爱护的人支持自己的选择,并且不后悔自己作出的选择,这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吗?
Carol本来看似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她最优秀,而且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之所以优秀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优秀的名声,自己得到的宠爱也多是源自过往成功的光环。当她定位自己努力的目标是切实地提升自我,实现自我的时候,她才真正得到了幸福。一直以来,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追求优秀的目标其实只是寻求内心的虚荣感,让自己在人群中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永远不会有充分的幸福感,因为如果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别人的目光有所转移,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不满,瞬间可以毁灭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幸福感。所以,关注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才会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才会时刻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上网搜索了一下剧中主角的现状,虽然他们现在远没有那时候的一些配角,比如里奥纳度-迪卡普里奥,布拉德-彼特或者胡凯利红,可是每个人都像剧里一样过着充实的幸福的生活,或许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对于他们自身的影响吧。
可是,现在呢?当初年轻的人们已经不再年轻。或许只有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人才能铭记这些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Friends,Lost和South Park当然也很好,但是那种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了。Seaver一家带给我们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影响,是无法言语又无法磨灭的。因为只有那里,才有我们不容践踏的青葱岁月。看到那个有皱纹的Mike,已经变成成熟**的Carol和长了胡子而且发福的Ben,我更强烈的感受到,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汇——即使容貌不变,气质难再。
Seaver一家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全世界的人关注他们的growing pains所以即使当他们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也无需遗憾。《Growing Pains》,绝佳的名字。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当时,发行公司没有把名字定成《Growing Gains》。这样岂不是更加符合片子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内容吗?观众可以从每一集中找到一些珍贵的东西,发现一些自己缺少的东西——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在成长中我们不断地在收获。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名字,直接说出了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在成长过程中不停的摸索,不停的蜕化的人的心声。每一次蜕化,伴随着痛苦。我们难免在泥潭里摸爬滚打,甚至迷失自己——哪怕仅仅是因为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一个物。在每次蜕变中,我们要努力撕去原先的外皮,这是痛苦的。在接受每一次的挫折时,也是痛苦的。Pain,直截了当的说出了我们的真实感受——不加任何修饰地。
从片子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似乎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映射。Mike,其实就是我自己。叛逆,捣蛋,满肚子想着如何满足自己的要求。无论愿意承认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Carol,有时候很善解人意,有时候却也有反叛的一面。Ben,纯洁可爱,第一集中因为父亲没有和他Kiss bye而闷闷不乐。这不是自己小时候的写照吗?渴望父母的关怀,渴望别人的疼爱,其实到现在,更是如此!
它不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部生活写照。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大受好评。
妻子疑心丈夫杀了人,具体描写妻子的心理感受的。当知道高尔夫球场案找到凶手了,凶手是个精神患者,用的球棒。妻子后悔怀疑丈夫。在临睡觉时,想起五年前的谋杀案,是用的千斤顶。而丈夫又是个汽车修理工。这典型的希区柯克小说模式。至于丈夫是不是凶手那要看读者理解了。我认为丈夫看到了那篇新闻,同时也知道妻子怀疑自己,丈夫说“一个人,只要开了杀戒,就有可能不停地杀下去。”按照希区柯克的逻辑丈夫是个杀人犯。可以在迅雷上下载《希区柯克短篇集》找到。我这里有这这篇短文。留个邮箱可以给你。
《美人计》,又译作《谍网情鸳》。
《美人计》是雷电华影片公司出品的爱情片,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英格丽·褒曼等主演。
该片讲述了莉亚与美国特工迪普相爱;然而莉亚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嫁给塞巴斯蒂安,并在婚后因为身份暴露而陷入危险的故事。1946年9月6日,该片在美国上映。
扩展资料:
剧情简介
1946年4月,佛罗里达法庭判德国间谍约翰·赫伯曼20年徒刑。约翰开朗、热情、迷人的女儿莉亚·赫伯曼对父亲的罪恶既反感又痛苦,从法庭回家后找来朋友以小型舞会驱除烦恼,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出现了。
凌晨,所有人都醉倒以后,醉酒的莉亚拉着这个陌生人开车兜风,在警察拦截之后才发现这个陌生人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官员迪普。
莉亚在迪普的说服下,答应为国家效力。两人来到纳粹余孽聚集的巴西里约,在那里得到了约翰在狱中自杀身亡的消息。很快,迪普就与莉亚共坠爱河。
就在此时,迪普接到命令,莉亚要诱惑纳粹首脑亚历克斯·塞巴斯蒂安以取得情报。迪普丽以国家利益为重,让莉亚去执行任务,而莉亚却以为迪普并不爱她。
聪明机警的莉亚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很快得到塞巴斯蒂安的信任和爱情,在对迪普的失望和上级的指示下,莉亚答应了塞巴斯蒂安的求婚。
婚后的莉亚为情报部门探听出不少重要情报,并感到家中的酒窖很可疑。迪普借莉亚开舞会的机会来到塞巴斯蒂安家,莉亚为他弄到酒窖的钥匙,他们查出酒窖中有装有矿石的红酒。塞巴斯蒂安察觉了莉亚偷了自己的钥匙,明白了莉亚的身份和企图,十分愤怒。
-美人计
“昨夜,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曼德丽庄园。”这是小说史上一个著名的开头,它的原著叫《丽贝卡》(Rebecca),中文翻译成《蝴蝶梦》,蝴蝶梦的典故出自庄周,而庄周又装死试妻,最后鼓盆成大道,与小说中一对夫妻死了一个的情境很契合,所以这真是一个很高妙的译名。
《蝴蝶梦》完成于1940年,是希区柯克前往好莱坞发展后拍的第一部**。在此之前,凭借《三十九级台阶》、《擒凶记》、《贵妇失踪案》,他已蜚声大洋彼岸的英国**界。恰好米高梅花高价买下了《蝴蝶梦》的版权,制片人就让他一试身手。
《蝴蝶梦》是一部不太希区柯克的**。希氏**的模式是:一个无辜的好人被卷入一场大麻烦。而这部中琼·芳登扮演的女主角--“我”(她在片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是被称作“德温特夫人”)显然是因为郎有情、妾有意,才主动进入曼德利庄园的。希区柯克的高超之处,就是把一个并没有太多悬疑元素的故事,拍得揪心夺魄、悬念丛生。
这部两个多小时的**,有一个稍微冗长的引子,交代了“我”与劳伦斯·奥利弗扮演的男主角麦克西姆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我”是贵妇人范库帕太太的仆从,通过她跟麦克西姆相识,并且发展出朦胧的好感。范太太临时决定要去纽约,而且马上就走,“我”不想跟意中人不辞而别,就去房间找他。麦克西姆通过一次漫不经心的求婚,改变了“我”的行程。在这段戏里,范太太是关键人物,她对“我”严厉,对麦克西姆崇拜,起到了连接、催化二人关系的作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编剧技巧,二人之间关系的发展,需要通过第三方用制造障碍的方式来助推。
这对新婚夫妇来到曼德利庄园,故事才正式展开,“我”走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遇到一个咄咄逼人的仆人丹佛斯太太。奴大压主,即便是在英国也不正常,丹佛斯太太之所以感藐视新女主人,皆因为她的背后有已经死去但又在庄园里无处不在的丽贝卡。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跟麦克西姆的纵容分不开的。至于,他为什么不敢得罪这位老仆人?**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只能任观众猜测了。
希区柯克不愧是善于营造气氛的大师,一条狗,一扇窗,一道蕾丝花边,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都能传达令人惊恐的效果。故事草蛇灰线,处处照应,看似不紧不慢,实则按照大师设定的进程,进入圈套。
麦克西姆到伦敦出差,留下“我”在家主政,是影片故事的转折点。前半部分是出谜语,后半部分是揭谜底。丽贝卡表兄费弗尔的出现,让影片增加了新的悬念,也增添了一些喜剧气氛。丹佛斯太太带着“我”去参观丽贝卡的卧室,在梳妆台前讲自己每晚会给丽贝卡梳20分钟的头,边讲边用梳子比划了几下。对照剧本才发现,梳头这个细节在“我”刚进庄园就出现过,当时“我”正在自己梳头,丹佛斯太太敲门进来。丹太太讲得太投入,不但编出丽贝卡经常走动的话来吓唬“我”,而且还展示薄如蝉翼的丽贝卡的睡衣。她弄巧成拙,反而倒逼出“我”的勇气。“我”立即行使女主人的发号施令权,让丹太太把丽贝卡的东西统统拿走。不但如此,“我”还上奏麦克西姆重开化妆舞会,决定重整家风。
接下来,影片叙事加快。任何人都可以猜到,“我”在制作cosplay衣服的时候,被丹太太给耍了。就在我受到麦克西姆的斥责,伤心欲绝,在丹太太魔鬼细语的诱导下,准备跳窗的时候,沉船事件发生了。在丽贝卡的海滨小屋,麦克西姆说出了真相。他讲述了丽贝卡临死那天的情景,讲到那儿,空镜头就跟到哪儿,仿佛丽贝卡依然坐在那里一样。接下来,影片达到了高潮。
麦克西姆:我知道丽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在船舱里,沉在水底。
“我”:(恐惧地)你怎么知道的,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因为……是我把她放到那儿的。
在原著小说中,麦克西姆用手枪打死了丽贝卡,但是按照当时好莱坞的**道德准则,“杀害配偶的人不能逍遥法外”,所以希区柯克把她改成摔倒头磕在船具上而死。至于为什么摔倒,**巧妙地戏耍了一下观众。
按照麦克西姆的讲述:“我当时气疯了,我可能打了她。她站在那里,盯着我……她微笑着走过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摔倒了。”
很多观众会以为麦克西姆失手打死了丽贝卡,但是影片埋下的伏笔却是让他脱罪,丽贝卡是得了癌症而自杀。她想激怒丈夫,让他打死自己,从而让自己的表兄兼情人要挟勒索,让这个曼德利庄园依旧摆脱不了自己的影子。一看麦克西姆不上当,丽贝卡故意摔倒,恰好撞死(这难度比C罗在禁区内假摔还要大!)
麦克西姆讲完这段故事,无奈叹息道:“丽贝卡赢了。”
“我”争辩,丽贝卡没赢。
接下来的戏,即表现麦克西姆如何惊险脱罪,又表现费弗尔如何敲诈勒索。费弗尔形象非常鲜活,咄咄逼人又不失礼节,带着那么点滑稽。如果没有他,这部**会沉重而黑色。最后,丽贝卡得癌症的秘密揭开,麦克西姆也逃脱了杀人的指控,并且摆脱了负罪感的控制。一切看上去皆大欢喜。
只不过,麦克西姆说对了一点,丽贝卡会赢的。她的忠仆丹佛斯太太点着了庄园,自己葬身火海。丝丝的火苗,烧着了绣着丽贝卡名字首的枕套,全剧终。
老子说“圣人无弃物”,大师的**里也没有废弃的人物,连一条狗都有独特的用途。丽贝卡的爱犬——名叫贾斯帕的一条可卡犬,在**中起到了引导、推动作用。
1、“我”初进庄园,狗守在丽贝卡的房间门口。
2、“我”走进丽贝卡以前写信读书的Morning Room,趴在壁炉旁的狗一见我就不屑一顾地走了。
3、“我”跟麦克西姆散步,狗引导“我”去海边找到了丽贝卡的小屋。
4、丽贝卡的表兄偷偷来访,狗对他摇头摆尾很是亲热,一看就知道此人跟丽贝卡关系非同一般。
5、“我”在房间,抱着狗睡着了。丹佛斯太太拿着蜡烛走进来,准备点火连“我”一块烧死。**没有交代后来的事,但从“我”牵着狗逃出火海,不难推断,此刻狗已经完全接受我作为它的新主人,从而救了我一命。
这部**中,琼·芳登扮演的“我”处处受压、笨拙紧张,劳伦斯·奥利弗则时而柔情,时而暴怒,神秘莫测。**的主题十分暧昧,站在丽贝卡的角度看,麦克西姆绝对不像自己表白的那样戴着绿帽子清白无辜,事实上,从他暴怒的脾性,把“我”当成玩偶的举动,观众也能猜出此人也非善类。倒是丹佛斯太太,举止稳重,忠心耿耿,真爱无敌,让人觉得性格完整统一。难怪她被美国**协会评为**史上TOP100坏蛋第38位。
这部**为希区柯克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但他没有得到最佳导演奖,因为这一年有一部更伟大的**与他竞争并最终获胜,那就是约翰·福特的《愤怒的葡萄》。
《蝴蝶梦》是一部不错的**,但是跟希区柯克巅峰时期的《迷魂记》、《惊魂记》、《后窗》等**相比,还差一大截。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