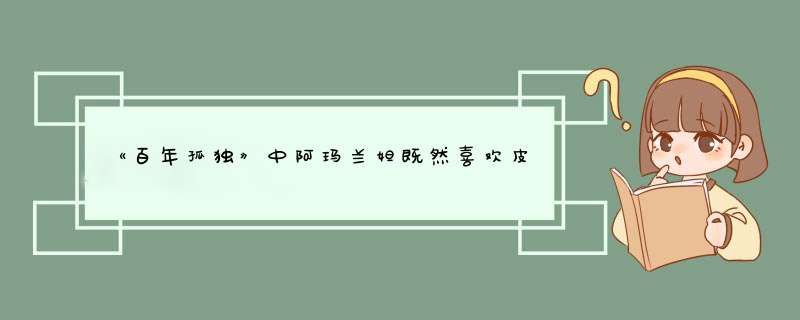
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
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百年孤独里面的阿玛兰妲,既然喜欢皮尔修斯,但是却拒绝了他的求婚,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阿玛兰妲内心相对自卑一些,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皮尔修斯,所以说他拒绝了皮尔斯的
31岁的劳拉答应嫁给小布什前与他有言在先,不在公开场合代表他作政治性发言。而今天,她却鼎立协助夫君,在美国第54届总统竞选中获得成功,自己也成为全美瞩目的第一夫人。 随遇而安的独生淑女 五十年代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一个小户人家的劳拉,是一边吃着汉堡、一边坐在车上看露天**长大的一代。她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独生女的成长环境使他从小喜欢独处。劳拉四十多年的朋友评价他说:“她总是随遇而安,不需要什么生活中的刺激就能使自己快乐起来。而且她从来没有追求过什么荣耀。” 劳拉年轻时从不把时间过多地花费在穿衣打扮上,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多年来劳拉一直留着一头短发,她是同伴中最后一个结婚的人,而且对此一点也不在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她的朋友一直在为她介绍男朋友,但是她都拒绝了。劳拉通过努力学习,终于取得了图书管理学的硕士学位,直到结婚前,她一直做图书管理工作。 命中注定的美满姻缘 劳拉对小布什的爱称是“布西”,而小布什一谈到妻子就两眼放光,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他总是妙语如珠地说:向劳拉求婚,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完美的一件事;劳拉是他人生最大的财富,她给了他足够的力量和信任。虽然他们30岁才走到一块儿,但两人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双方都在米德兰长大,并同时就读圣-哈辛托初级中学的7年级。1975年小布什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回到米德兰从事石油业工作,双方的朋友都试着为他和劳拉穿针引线,但她当时并没多大兴趣。当她听到“小布什”的名字时,她就联想到了她不喜欢的政治。最终,两人还是在参加了一伙年轻人举行的烧烤野餐会后走到了一起。 小布什夫妇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小布什是出了名的懒汉,劳拉则是那种每次淋浴后都会把浴室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人;小布什偏重阅读管理方面的书,且看完后到处乱丢,而劳拉博览群书,自己的书柜总是摆放得井井有条;丈夫在外喜欢出风头,爱耍嘴皮子,遇事不冷静,妻子则不事张扬,遇事沉着冷静,话不多却总能切中要害。小布什曾对记者说,是劳拉让我集中精力干事情,而且提醒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劳拉说自己给小布什的生活带来了平和,而小布什则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兴奋与激情。也许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使两人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 不事张扬的内贤外助 1977年11月5日,劳拉在自己31岁生日的第二天嫁给了小布什。虽然劳拉在结婚前曾信誓旦旦发誓自己绝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嫁的是个有政治志向的人,她已经没有办法回避这个事实了。 作为贤妻良母的劳拉,充满着闲情逸致,除在家里一心一意照顾她的一对双胞胎千金外,常和朋友们一起利用假期到伯利兹城去观察野鸟的生活或者到大峡谷去划船。虽然劳拉不能对小布什的政治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她却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丈夫的生活。劳拉曾因小布什酗酒而与他发生争执,并严厉告戒他把酒戒掉。小布什对于妻子的劝告一开始无动于衷,但在劳拉的一再劝说下,在自己40岁生日时痛快地喝了个酩酊大醉后,终于把酒给戒掉了。小布什多年的朋友说,乔治能有今天,劳拉功不可没,他们是一对在多方面可以互补互助的夫妻。 今天,53岁的劳拉处于聚光灯下却不想抢镜头,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宁愿读书或干些园艺活,她觉得这才是快乐的事。她仍有些腼腆,但却有着冷静的自信。今年7月底,小布什在得州奥斯汀的一次选民集会上正式推荐前国防部长切尼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这位得州州长在他新的竞选伙伴开始发言时,往后退了一步,站在妻子身边。切尼每讲一句话,人群中都爆发出一阵鼓掌声,劳拉-布什也击掌欢呼。可是她旁边的丈夫却无动于衷。于是,劳拉向小布什挪了不易为人察觉的一步,靠近后,她以敏感,几乎看不出的细微动作,稍稍向小布什的肘部温柔地靠了一下。她拍手微笑时,将手臂再次稍稍伸向丈夫身边,直到手肘触着他的手臂。小布什立刻心领神会,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目光接触。在切尼又讲完一句精彩的妙语时,小布什也加入了振臂欢呼的人群。 美国国内一直有一些人质疑和嘲笑小布什不够聪明,智力有问题,谈起这个问题,劳拉说:“我们早就知道如果竞选总统,肯定会被人贴上与本人不符的标签,肯定得冒在午夜电视节目中被贬低的风险。乔治和我的内心都很平静。我们了解自己,我们站在一起相互支持,我们知道我们与他们所说的正好相反,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没事的。” 小布什说自己的妻子劳拉将是一位活跃的第一夫人,而且将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问题上。而劳拉-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不会学婆婆芭芭拉-布什,也不会学希拉里-克林顿。她说:“我认为,我就是我--劳拉-布什。”
尔·马克思的后代
卡尔·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和恩格斯的《***宣言》,使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一生共有过6个孩子,但他却经受过3个孩子过早夭折的丧子之痛。1858年,他在一封给挚友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结婚生子,使自己被家庭琐碎的小事束缚起来。”
马克思先后遭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政府的驱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在一套只有两间狭窄房间的公寓内,进行他那伟大的工作,抚育他的孩子。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可不幸的是,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几年后,马克思的境遇有所好转。法国共产主义者保罗·拉法格向他的女儿劳拉求婚,不久,两人结为伉俪。马克思给他的女婿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不会再结婚了。但是,今生我非常想将我女儿从困苦生活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不要像她母亲那样,为了生计而身心疲惫。”
马克思的3个女儿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为此受到了政府的迫害。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劳拉的丈夫保罗逃离法国,马克思的长女珍妮和小女儿埃莱诺在去看望劳拉的途中,遭到了法国警察野蛮的裸体搜查。后来,珍妮在父亲的帮助下,向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投稿。几年后,她与法国记者查尔斯·朗吉特结婚。由于朗吉特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同劳拉与保罗一样,珍妮结婚后绝大部分日子是在流亡中度过的。
马克思对3个女儿在贫困生活中成长,一直深感内疚。其中,他觉得最对不住的是长女珍妮。1862年,他在书中写道:“珍妮的年龄不小了。在她这个年龄,已经能够感受到全家生活的重担以及贫困的境遇。我想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珍妮的确非常不幸,她的一生几乎受尽了病痛的折磨。1883年1月,她死于肺结核,年仅39岁。她的去世,给了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两个月后,马克思,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也与世长逝了。
至于马克思的小女儿埃莱诺,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时光。在她的记忆中,马克思会经常和孩子们嬉笑玩耍,给他们讲故事,星期天带她们外出游玩。她常说,她的父亲是无以伦比的故事天才。在劳拉和珍妮结婚后,埃莱诺一直留在马克思的身边,当他的私人秘书。1881年,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去世了,埃莱诺主动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职责。虽然长久以来,她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而且偶尔也在业余剧团参加演出,但她还是将一生奉献给了父亲。1874年,她不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在马克思拒绝了她与一位法国革命家的婚事后,她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马克思在给劳拉的信中,提到了埃莱诺,他说:“埃莱诺实际上一直是在忍受和我在一起生活,她没有离开我,完全是为了照顾我。”
马克思去世后,埃莱诺写信给她的好友道:“如果你在我家里生活过,见过我的父母,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就会理解我多么渴望爱与同情。”不久,埃莱诺和戏剧家兼评论家爱德华·埃夫林同居。为了在事业上支持爱德华,埃莱诺不断地向他提供多年积累下来的马克思作品的出版版税,以维持生活。1897年,爱德华病重期间,埃莱诺像照顾她父亲那样细心地护理爱德华。
1898年春,由于爱德华久治不愈,埃莱诺极度消沉、抑郁,两人决定一起服毒自杀。3月13日,埃莱诺身着白裙,先服下毒药。但是爱德华却未追随她而去,他乘火车去了伦敦,4个月后,他死于肾脏病。
劳拉是马克思3个女儿中,活得最年长的。然而,她的结局也非常不幸。她和保罗生育的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1911年,劳拉和保罗饱受着贫困的煎熬,而且对于长期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厌倦,在寓所双双自杀。
但是,马克思的家庭轶事并未因此结束,尽管鲜为人知。马克思和其忠实的管家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虽然恩格斯一直自称是腓特烈的父亲,1895年,在他去世之前,还是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恩格斯还告诉埃莱诺,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埃莱诺和腓特烈后来成了挚友。
腓特烈后来当上了一名技术熟练的机械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他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的孩子。
马克思后代开“的士”
2004-06-17 文章来源:知音杂志社 文章作者:名裔 责任编 辑:嘟嘟鱼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大街上乘坐一辆出租车,发现司机的相貌很有特点,一脸又浓又密的黑络腮胡。最让记者吃惊的是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记者问道:“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司机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递过一张名片。记者看到安东尼·马克思的名字,于是问道:“你们同姓?”司机笑着说:“您不觉得我们长得很像吗?”记者仔细端详起来,他与无产阶级学说奠基人的相貌的确有相似之处。司机淡淡地说:“他是我的高祖。他的女儿是我的曾祖母……”
记者提问:“您从他那里继承了什么?”
安东尼笑着摸了摸大胡子说:“就继承了这个。”他拿出一本夹有许多书签的《资本论》。
记者边翻书边问:“你还记得对马克思的一个调查表吗?在回答‘您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是‘读书’,大概您也喜欢读书吧?”
他回答道:“不太喜欢。我喜欢收拾园子和汽车。我们俩只一点一样,那就是爱喝啤酒。”
“卡尔·马克思还有多少后人?”
“说不准,有很多……听说过卡塔琳娜·马克思吧?是个著名**演员,参加了戛纳**节,她喜欢穿红裙子,这是无产阶级旗帜的颜色。我们马上要路过海格特公墓,我的高祖埋在那里,想去看看吗?”
“不,我还有急事。”
“几年前凡是从俄罗斯来的人,都会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现在大概只有我还带去鲜花……”
“在德国,卡尔·马克思的纪念像都还在,即使在柏林也是这样。”记者安慰道。
“那就好,砸掉纪念像就是毁掉历史,历史无论怎样都应当保留……”安东尼似乎陷入了沉思。
记者付过钱准备下车,安东尼递过一张名片,背面印有卡尔·马克思的肖像,他说道:“一天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叫车,随叫随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