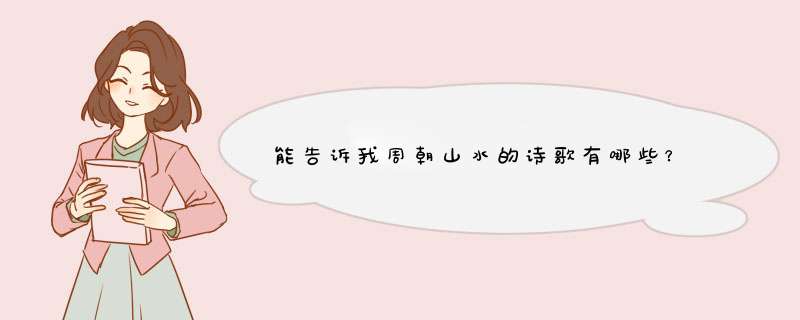
一、可以说先秦时期的东周还有西周是我国山水田园诗的滥觞,也就是起源,及时当时没有田园诗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尤其是《诗经》当中的《七月》篇中的很多的农事诗就是田园诗的雏形。
二、详解如下:
1、解释山水田园诗这个概念:
山水诗,是指描写山水风景的诗。在一首山水诗中,并非山和水都得同时出现,有的只写山景,有的却以水景为主。但不论水光或山色,必定都是未曾经过诗人知性介入或情绪干扰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须保持耳目所及之本来面目。当然,诗中的山水并不局限于荒山野外,其他经过人工点缀的著名风景区,以及城市近郊、宫苑或庄园的山水亦可入诗。
2、先秦田园山水诗的简介:
《诗经》中的田园诗的第一道风景线: 田园与农事是分不开的,即便是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田园诗也离不开农事的内容,由于后世写田园诗的人能真正接触农事的不多,所以他们笔下的农事往往是变了味的。在这种情况下,周代的农事诗便显出了它独特的价值。
2、先秦时期田园山水诗的具体诗作:
现存《诗经》中的周代农事诗约有十一首,这十一首农事诗即是我国田园诗的滥殇。 《周礼》将这十一首农事诗分为《幽诗》、《幽雅》、《幽颂》三类。依《朱子集注》的意见,《幽风》中的《七月》为《幽诗》;《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为《幽雅》;《周颂》中的《思文》、《臣工》、《隐嘻》、《丰年》、《载荃》
诗经·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言私其豵,献豜[7]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注释:
《豳风》是豳地一带的诗歌,共七篇。豳,又写作邠,是周朝的祖先公刘迁居开发的地方,在今天的陕西省栒邑,邠县一带。这一工区多存周人旧俗,“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汉书·地理志》)诗风宽大,乐而不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注)
流火:火星在七月黄昏时就已西沉了
觱发:风寒盛。栗烈:凛冽
一之日,二之日:夏历十一月,十二月
三之日,四之日:夏历正月,二月
于耜:整修农具。举趾:举足耕耘
馌:音夜,给人食品
畯:音郡,管农事的管家
仓庚:黄莺
懿筐:采桑用的深筐
女:女子,女奴。殆:恐
萑苇:长成的荻苇。
斨:音枪,斧,受柄之孔方形
鵙:音局,伯劳鸟。载绩:纺麻
孔阳:甚为鲜明
葽:草名,即远志。蜩:音条,蝉
陨箨:草木之叶陨落。箨音唾
同:会集。缵:继续
豵:墐豜:音间,三岁的猪
穹窒:堵好墙洞。墐:音尽,涂
郁:树名。薁:音玉,李属
断壶:摘葫芦。叔苴:收拾青麻。苴音居
荼:音涂,一种苦菜。樗:音初,臭椿树
穋:音路,晚种早熟的谷类
綯:音陶,绳子
凌阴:冰窖
兕觥:音四公,酒具
赏析:
《七月》叙述农人一年到头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反映了丰富的生产劳动的内容和浓郁的节气风俗,应该说是不可多得的生活风俗画。诗以时间顺序为主线索,按月描写,又兼归类,纵横开合,一节一个内空容,一幅画面。从农事耕作开始,到收获举酒祭献结束,送饭的妇子,采桑的女郎,下田的农夫,狩猎的骑士,公室的贵族,人物众多,各具面貌,其间又以物侯表时序,构成整体风格的统一,而且避免了叙述的呆板,增强了诗歌的形象,尤为突出了风俗画的特征。
周朝(约前11世纪—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西周的文学水平已经较为发达,主要有《周礼》《周易》《尚书》,以及《诗经》。东周时期的春秋与战国,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百家争鸣”,文学作品也丰富了很多。春秋时期的文学,有《春秋》、《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等。战国时期百家里的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道德经》《庄子》,墨家《墨子》,法家《韩非子》《商君书》《管子》,兵家《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名家《公孙龙子》,纵横家《战国策》《鬼谷经》等。主要文学家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孙武、孙膑、鬼谷子、吕不韦等。
周朝古籍作品列表更多
《禽经》[谱录-鸟兽虫鱼] 师旷
《灵枢经》[医家-医经] 佚名
《素问》[医家-医经] 佚名
《论语:定州汉墓》[四书] 孔丘
《洞灵真经》[道家] 庚桑楚
《金人铭》[道家] 轩辕黄帝
《文始真经》[道家] 尹喜
《申子》[法家] 申不害
《邓子》[法家] 邓析
《尉缭子》
《小雅·鹿鸣》是表达周朝礼乐文化。
礼乐是周朝典制的重要内容,被称作规范周朝天下的四大制度之一。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而乐则是宫廷乐官创制的音乐舞蹈。"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即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是上层社会的重要统治手段。
在周朝,上至祭祀典章、军队征伐;下至社会风俗、人才推举,其包罗万象之种种,都离不开典籍《礼仪》一书。而每种礼制所对应的乐,就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进一步教化。乐引导着人民的心理情感,使得崇高、肃穆与和谐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潜移默化着西周人民。礼乐制度的本质,其实是阶级的固化。
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
《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御王事。”说明以桃木制成的弓,楚人以为可以抵御一切灾害。《左传》(成公四年)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说明在古代,祀典和战争是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大事件。“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所谓“王事”就是国家大事,楚人最初开辟荆山时期,唯独只有桃弧、棘矢用于祭祀和战争之中,可见楚人对桃弧的崇拜。桃弧在周初作为楚人进贡周天子的方物而被用于“王事”,这表明了桃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既有驱邪除祟之神力,又有保卫家国的奇能。楚国神射手陈青即说,楚国“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
桃作为图腾与生殖的关系也是明显的。《本草纲目》(果部):“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山海经》:“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言其面积之广也。再从桃的品种和成熟期来看更有“红桃、绯桃、碧桃、胭脂桃”及“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等繁多种类,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桃的繁殖能力很强,使古人对桃产生了生殖崇拜。另一方面,原始人对妇女怀孕的原因有时也就解释为是桃的感应或桃花、桃子的感应,于是认为桃是这个部落原始人的生殖祖先,从而桃就成为了一种部落的图腾。
由此可见,《桃夭》本是楚地先民的咏桃之作和祭桃之歌。歌辞前两句既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又祝愿桃能茂盛生长;后两句则是赞美桃被人们采用之后可以福泽其族人。当然《桃夭》在周代社会里已发生了改变,其内容由以前的赞桃逐渐变为赞人。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楚人迈入了发达的农业社会,采集、渔猎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对桃的依赖也就不象先民那样密切了。这样,在楚地的社会生活中,祭桃的宗教仪式便日益减少,加之社会小家庭的出现,婚丧嫁娶的礼俗仪式也日益增多。传统的祭桃仪式歌也就被借用和演变成婚礼仪式歌。这种借用,出于历史上形成的认为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心理,也出于世代形成的爱桃、敬桃的情感。楚人在喜庆的婚礼上歌咏桃,将桃视为幸福的象征,礼赞桃能“宜其家人”。这样祀典歌也就成了称颂新娘“宜其家室”的礼俗的歌,这一变化也包括了对歌辞的修改,使《桃夭》成为一首形式整齐、音韵和美、语言生动的诗歌。
“二南”诗歌除了《桃夭》之外,还有《樛木》、《螽斯》等都是祝辞,也都反映了当地的民俗,是当地民俗的仪式歌。除此之外,“二南”中明显显示了楚歌特色的,当然是情歌。25首歌谣中有13首可以看作是爱情婚恋的作品,占总数的52%,这些情歌有的明显地体现了南方诗派的特色,如《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萎。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歌讲到了汉水、长江,显然是产生于汉皋江上的楚歌。而且,歌辞中的“楚”,即江汉流域的山林中茂盛生长的灌木名。《说文解字》说:“楚,从木,一名荆也。”在江汉流域,“跋涉山林,以处草莽”的楚人,在生活中是离不开荆楚的,故在商代楚人被中原人称为“荆蛮、楚蛮”。这首情歌是一首男子求偶的情歌,主要是传唱于男女出游于水滨、会聚于野外以互相求偶的习俗活动中,这与《郑风•溱洧》、《郑风•狡童》等南方诗派的情歌内容一样。所有这些情歌与今天布依族的情歌也相类似,都是一种风俗民情的产物。这首情歌以其浪漫的风格、地方的语言、婉深的情调和舒缓的节奏,显示了楚歌的特色,三章歌辞虽然朴素通俗,却委婉缠绵,循章进意地抒发了歌者苦求恋人而不可得的感伤和惆怅之情,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位在烟波浩渺的江汉之间来去无踪、若隐若现的美女形象,并将丰富的想象和深厚的感情寓于直率反复的咏叹之中,兼以巧妙的比兴和真切的描绘,使之蒙上浓重的浪漫色彩,形成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产生了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它代表了楚歌谣在春秋中叶以前的较高水平。而且在句式上把语助词“思”缀于句末,且很有规律,在形式上也与后来的楚辞体相似,显示了楚歌谣独有的特色。
“二南”中的爱情诗如《江有汜》、《关雎》与上面分析的《汉广》一样,都具有南方文化的轻松,而少含有北方诗派的凝重。其实,正是因为这些轻松的情歌和《郑风》、《陈风》中的一些挑逗戏谑的情歌相呼应,反映整个南方文化在《诗经》时代不同于北方文化的深层的社会风俗和文化心态。
“二南”诗歌虽然未必全可以定为楚歌,但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也就是说,楚是“二南”地区之侯经过伐隋、伐申、伐蔡、伐邓而逐渐强大的。故“二南”诗已初具楚辞雏形,甚至被称为“楚辞的先声”。(注:以魁英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4月版)
综上所论,就《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来看,“二南”诗歌和《陈风》、《郑风》相结合,明显地反映了除中原北部以外的中原南方及楚地的南方文化特色。
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2.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3.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5.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鹿柴》)
6.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
7.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
8.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归园田居》)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