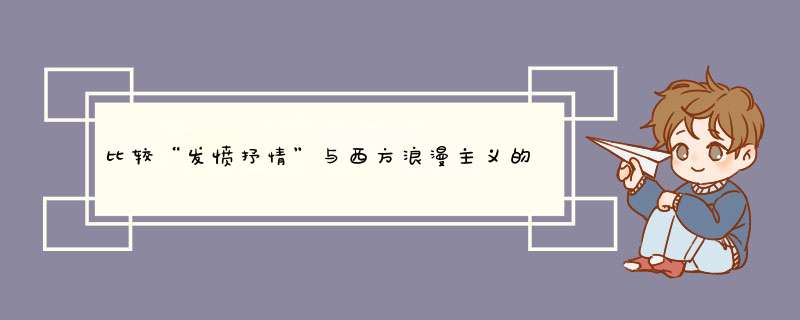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大国,没有一个国家的诗歌如此普及,如此深厚,如此达到诗性智慧峰巅。在中国所有一切艺术中,都深深打上中国诗性智慧传统的烙印。话剧这个“洋玩艺儿”,也被中国的诗性智慧改造了,于是出现了话剧的诗化现象,直到形成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从文明戏阶段,即看出中外戏剧撞击所带来的特点。当时,正是易卜生戏剧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但中国人偏偏对西方话剧中的浪漫主义戏剧产生兴趣,无论是选取剧目或改编,如《茶花女》、《热泪》、《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等,都洋溢着浪漫主义慷慨悲壮激情。这些剧目,在“情”字上沟通着中国人的欣赏心理,联系着中国戏曲的诗化抒情的传统。当时就有人说,西方浪漫主义戏剧的特点是“用情之痴,用心之苦”,“盖以为至诚感人,金石可开”。文明戏浪漫主义之倾向,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诗化最初之征兆。
话剧与诗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五四”话剧在艺术上的最突出的特色。特别是浪漫派和现代派的戏剧创作,以田汉、郭沫若、向培良等为代表。他们大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自然使他们很容易把诗切入戏剧;同时,他们都从理论上看到戏剧诗的本体特性。郭沫若就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五四”浪漫派戏剧,无论是戏剧的内涵,还是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戏剧视界,都是诗化的,具有诗意的。它们着意从人的心灵感情世界透视人生现实,特别是从人的悲剧的“灵”的痛苦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其艺术特征便是抒情性、人物的性格、戏剧的结构和语言,都以抒情为纽带。如郭沫若的王昭君(《王昭君》)、卓文君(《卓文君》),田汉的林泽奇、白秋英(《咖啡店之一夜》),白薇的琳丽(《琳丽》)等人物形象,都是诗意抒情化了的人物。其主情性,又导致他们追求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注意诗的氛围的营造。他们有时将音乐、诗歌直接融入作品之中,以增强其抒情性。
这种诗化倾向,自然同接受西方浪漫主义以及新兴的现代派戏剧(当时称为新浪漫主义)的影响有关。不可忽视的是接受主体的投射作用,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开放的艺术精神,一方面把民族的艺术精神、民族戏曲的质素融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话剧浪漫派现代派戏剧的诗化倾向,正是中国“剧诗”传统的潜力的传递和勃发。中国的曲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所谓“诗变而词,词变而曲”,故对戏曲也叫“剧诗”。所以说,是中国戏曲的诗意抒情传统同西方浪漫主义,甚至同西方现代主义戏剧融合起来,形成了“五四”浪漫派现代派戏剧的诗化倾向。
对现实的关注,始终是中国话剧的特色。一方面是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予以关注,对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时事焦点给予追踪式的戏剧反映,这种现实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报道式的戏剧。另一方面,也是成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的,是诗化现实主义。它以田汉作为开创者,曹禺和夏衍作为奠基者。
这种诗化现实主义,在真实观上即渗透着中国人的特色。如果说,西方话剧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倾向于客观生活的再现,当然也熔铸着剧作家的主体审美创造;而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是更注重情真,在“真实”中注入情感的真诚和真实,甚至是缘情而作。曹禺说,他“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恐惧的表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感情的发酵。”这正是中国剧诗的传统,如汤显祖作《牡丹亭》就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把“情真”提高到一个超越一切的境界,同时也把理想的情愫铸入真实性之中。曹禺、夏衍的剧作都渗透着一种目标感,于残酷的真实和灰色的人生中,写出希望的曙光。夏衍虽然多写一些卑琐的小人物,写一种龌龊的生活,但他却从中发现:“眼睛看得见的几乎是无可挽救的大堤的溃决,眼睛看不见的却像是遇到了阻力而显示了它威力的春潮。”在诗化现实主义中兼容着浪漫主义的因素。那么,对这种真实,我们称之为“诗意真实”。
再版记
我在北大的哲学硕士论文题为《从诗的本体论到本体论的诗》(全文约四万字),论文的内容就是本书的雏形。一般说来,在一篇论文中容纳这么多的内容,是不那么符合论文写法的。当时我只想,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到现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有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说一直无暇去注意。但德国近、现代哲学又一直是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重点,如果这条线不清理,未免给人以偏概全之误。所以,我甘冒泛而不精的危险,拼拼凑凑地把这条线粗粗拉出来了。不过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把它扩写成一本小书。
以上是1986年初版“后记”中的一段文字,时过境迁,这部二十年前的习作本来没必要再印。毕竟,虽问题脉络清晰,细部却过於粗疏——当然,再印也未尝不可,毕竟,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国朝学界对浪漫主义思想的认识没有什么进展,认识浪漫主义的需求倒增强了。
二十年前,笔者孤陋寡闻,并不知道一些重要的西方思想史家已经强调过审理浪漫主义思想的迫切性。据说,20世纪的思想几乎没有不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的(1):还有人说,浪漫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继希腊晚期(廊下派)和近代初期(马基雅维利主义)两次重大转折之后的“第三次重大转折”(2)
同样值得注意:在浪漫主义兴起的时代,就已经有人出来反驳浪漫派的审美主义了。思想史上一般讲基尔克果如何攻击黑格尔,其实,如果不看到基尔克果也攻击谢林、施莱尔玛赫的审美主义,就令人遗憾了。(3)
如果什么是精神不能被审美地定义,美学怎么能回答一个对它来说显然不存在的问题呢?否认个别异教徒和所有异教国家已取得的那些曾经激发过并仍将激发诗人灵感的惊人业绩是十分愚蠢的,否认异教徒夸耀的那些从审美上讲简直难以充分赞美的光辉范例也是非常愚蠢的;否认在异教世界中自然人能够并确实过着一种从审美愉悦上讲非常丰富的生活,否认他能以最优雅的方式用任何可爱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甚至让艺术和科学加深、美化、精炼他的欢乐,似乎也非聪明之举。不,问题在于,无精神的审美范畴不提供什么是、什么不是绝望的标准。(基尔克果:《致死的疾病》)
早期浪漫哲学侈谈有限与无限及其综合,审美就是这种综合的绝对中介。在基尔克果的主要论著(《恐惧与战栗》、《致死的疾病》、《哲学片断》、《不安的概念》,均已有中译本)中,主题恰恰是这个审美精神无法应付的绝望精神。基尔克果显然是针对早期浪漫派、而非黑格尔。然而,对于审美精神来说,既然绝望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没必要反驳它,除了这样一点:审美精神自以为比绝望精神高超。
基尔克果用什么来反驳审美主义?
基尔克果的思想有两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分别由西方精神史上的两类灵魂的典型形象来代表:犹太先知亚伯拉罕和雅典哲人苏格拉底。亚伯拉罕的“恐惧和战栗”与苏格拉底的理性怀疑在绝望中相遇(参见《哲学片断》,翁绍军译,北京三联版1996)。基尔克果对审美主义的反驳,主要继承的是苏格拉底对戏剧诗人的反驳——柏拉图《王制》中记叙的哲学与诗的争纷,变成了活生生的思想争纷。
不过,浪漫主义哲学并非古老的哲学与诗之争的简单重复:浪漫哲学反驳启蒙理性哲学、捍卫所谓“真正的”哲学,主张哲学应成为诗——诗与哲学的同一,使得现代语境中的哲学与诗的争纷更为错综复杂。
在基尔克果那里,我起初注意到的并非其先知亚伯拉罕和哲人苏格拉底的立场,而是其思想的复调言述。通过假名写作,基尔克果一再彰显审美精神据说有一个“欺骗性”的意图:不从要表达的主张出发,而是从其他想象出发。审美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想象,但不是幻想;也不能说它是一种低于基督徒精神的生存状态,毋宁说是另一种生命感觉——从这里倒是可以看到狄尔泰在二十世纪初提出世界观类型论的用意:消弭审美主义带来的新的精神紧张。在基尔克果的复调言述中,如此审美精神得到堪称极致的发挥,以便让它在撞上绝望时把自己的窘态暴露得一览无余:“每一种美的生活观都是绝望的,每一个按审美方式生活的人,无论他知道与否,都处于绝望之中”(基尔克果:《或此或彼》,阎嘉译,北京华夏版2007,下卷,页202)。
写作《诗化哲学》时,我还没有感觉到这现代之后的审美思想中的惴栗,绝望的主题便历史地留给了《拯救与逍遥》。《诗化哲学》的论题倒是已经触及到我后来处理的现代性问题。理解“现代性”及其思想渊源,是20世纪思想界的基本诉求——中西学界皆然。从汉语思想的传统及其现代性问题出发进入这一问题,不仅德国浪漫哲学思想,而且整个欧洲的审美思想与中国审美思想的内在亲和性就完全不同了。
“诗化哲学”的提法在当时国朝学界某些同行眼里是黏糊糊的提法……现在看来,这些朋友过于低估了这种看似黏糊糊的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
“诗化哲学”的提法不准确?
1999年五月,我去德国讲学,碰见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史家Peter Koslowski。他研究过、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当我们从施米特聊到德国浪漫哲学传统时,他拿出自己的《现代性神话:恽格尔的诗化哲学》(Der Mythos der Moderne :Die dichterische Philosophie Ernst Jüngers,München 1991)一书送给我。我对他开玩笑说:我的书早于他的书十五年,而且“诗化哲学”的德文用法(diedichtendePhilosophie)比他更准确,因为,我采用的是诗化哲学的大师自己的用法:dichtend一词尽管是生造,但并非笔者所为,而是德语大师海德格尔的构造。
恽格尔是文人,从魏玛民国后期到纳粹年代那段时期,与海德格尔、施米特并称时代精神的三杰。他以类似鲁迅杂文的短作见长,称现代世界以孤独为条件,因而是难以概括的“紧要关头”。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鲁迅讴歌毛泽东称赞的“硬骨头”精神,恽格尔夸耀士兵精神:“进攻不过是一种休养、一种愉快的行动”(恽格尔,《机器之歌》,见拙编:《德语诗学文选》,华东师大版2006)。
士兵精神还在德国思想文化的血液中,正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还在滋补无数中国文人、学者的脊髓。鲁迅精神是否是我们根本还没有认识的那种与恽格尔精神具有同构型的浪漫精神?鲁迅无论读过还是没读过恽格尔,都与我这里所说的同构型不相干。这种同构型产生自一个时代中民族及其神圣帝国的精神传统,甚至人的某种类型的性情血气,并不需要靠文字来传递。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浪漫派哲学与后现代的关系:本书初版时,后现代哲学在西方正挥洒自如地形塑着自己,随后便有熟悉那段19世纪思想史的学者Ernst Behler出来指出德里达与施勒格尔的关系。到了21世纪,德国学界也出版了一本书叫“诗化哲学”(Ansgar Maria Hoff,Das Poetische der Philosophie,Bonn 2002),说的就是施勒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
初版后记说:本书“拼拼凑凑把”德国浪漫主义这条思想线索“粗粗拉出来”,不是自谦——“拼拼凑凑”凭着一种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感觉、甚至初生之子的大胆。我至今没有读到过西方学者“粗粗拉出”这条线索的专著,然而,我的这种感觉从别的相关论著得到了证实。这并非是说,我的理解和把握足以堪称切实、深透。恰恰相反,当时学界时髦的异化理论和所谓作为“人类学”的美学理论妨碍了我对德国浪漫主义及其问题的理解。对我来说,这部习作既无法扔掉,又不能一字不动重印(十年前坊间出现了重印本,既非我的过失、也非出版社的过失,而是国朝法律秩序的疏漏,让盗印的书商占了一回便宜)——本书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它提供了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反面教材:德意志哲学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如果我们今天再不遗弃康德、黑格尔,从近代哲学的根子上往前探索,而是追随海德格尔往后追逐后现代,即使再有一个二十年,我们对西学的认识仍然不会长进。
除订正初版中的讹诶、删削重复和辞不达意的文辞,这次再版在内容方面没有改动,尽管一些说法如今看来实在雅气十足。对汉语学界来说,理解西方哲学是非常艰难的历史任务,需要数代学人不懈努力,能否完成也还是未知数。不消说,本书对浪漫哲学的理解相当初浅,不少表述囫囵吞枣,一些原文的翻译也颇为生硬,显然尚未吃透原义——倘若现在来写这样一本书,即便框架和线索不变,也会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我不想、也没必要修改或重写本书。当然,“浪漫美学”的提法是当时应付所学专业编造出来的(为混到文凭),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浪漫哲学”,现在改过来,亦算文辞上的改动——我无意让本书变得面目全非,倒是想尽可能让它保持原样,作为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踉跄步态立此存照。
本想补充一些文献,做了一点后发现收不住,干脆算了;注释形式仅免除了重复,无法按现在的学术规范补足(比如说书名原文之类)。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自明代以后颇受评论家的重视和推崇,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称:“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当我们重读这一经典的时候,除了被那强烈的宇宙意识和由宇宙意识所升华的宇宙精神深深震撼之外,更被那作者诗意化的心理时空折服了。这种折服简直是哲学的征服,即诗化哲学的征服。
诗化哲学是德国浪漫美学。诞生于1795—1800年德国浪漫派哲学理论,在对工业文明的忧虑、反思和批判中,敏锐地发现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归宿与科学技术的尖锐冲突,于是“有限生命的永恒精神家园在哪里安放”就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诗学理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美有重要的启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以江月起笔,可谓“横绝”。江连海,海生月,月照春江,这样一幅连环的美景呈现于千万里的阔大时空,极见诗人胸襟之大,眼界之广,有一种仰视宇宙的气魄。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之绕,花之林,汀之沙,用来衬托月之光。其美似霰,似霜,感觉的物化让人在静谧和清丽中获得瞬间的生命享受。心灵体验微妙极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皎月当空,江天无尘,一色净美。这美出自诗人的内心,又以何人何年来叩问:有限的个体生命能够超越时间的规定而获得永恒无限的价值吗?千古奇问,触入永恒之谜。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生命却一代传一代,没有穷尽,如同江月永恒于宇宙天地。莫非江月也属情种,它在等待自己的情人吗?如果江月有情的话,那么人就应该更有情;但是有情的个体生命有限,看看长江流水的永恒,那后浪推前浪不正像人类的代代相传吗?诗人似乎从宇宙天地顿悟到有限与无限的平衡。这是诗化了的时间,诗化了的哲学。施勒格尔说:“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部的未分割的整体。在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糅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7世纪的中国诗人与17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哲达到了一种默然相契,这是多么有趣的中西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是哲学的!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永恒的时间里,情永恒,情纯洁;爱也永恒,爱也纯洁。“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由江天而游子,而思妇,由宇宙之大而人间相思,足见纯洁爱情是超时空的。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本来就是《古诗十九首》和古题乐府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在张若虚的笔下更加典型化和更加诗意化了。在浪漫美学那里,“所谓美不过就是客观化了的精神意义,美只能出自关照者的内心,它只能是有情感所激起的直观的内容。”由于审美直观排除的是经验的世俗的考虑,它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要返回内心以追求诗意化的心境,它要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过的内在时间重组重构一个新的时空心境,它要在把握的同一心境下把感性个体引出有限性的规定,达到“在主体的心意状态中所呈现出来的直观主体与直观对象的交融统一境界。”而且浪漫美学认为“真正的诗就是同一心境的客观显现。这是一个绝对超时间的永恒世界,人生价值的寄托之所。只有在那里,时间才被取消了,刹那凝化为永恒。”以此来观照在诗中出现的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大概是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吧。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终以江月落笔,回扣起笔,同样妙绝。王尧衢《唐诗合解》卷三评曰:“此将春江花月夜一齐抹倒,而单结出个情字,可见月可落,春可尽,花可无,而情不可得而没也……千端万绪,总在此情字内,动摇无已,将全首诗情,一总归结其下。”斯言得之。不过,这里的“情”的确像是从浪漫美学所说的瞬间体验中得来。“个体在瞬间体验中,以想象为根基,不断把自己的过去投向未来,超时空、超生死,化瞬间为永恒。”从月出到月落,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从碣石到潇湘,这又是一个地北天南的宇宙空间。诗人在想象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诗化时空世界,即“强烈的宇宙意识”和“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宇宙永恒,“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永恒,所以“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样,个体自我遂与永恒化一而成为宇宙之我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以江月起笔,以江月落笔,在仰观孤月、俯察江海的诗化巨大时空中使宇宙意识和人间真爱展示出美好的境界,在感悟人生有限和追寻人生归宿无限的心灵叩问中冥思永恒的千古之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价委实不为过誉。有一种"蕴藉的抒情法","虽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样写出,却把所感的对象隐藏过去,另外用一种事物来做象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首诗虽在写春江花月、游子思妇,却不是要告诉读者有这么一种风光,有如此一桩世事。他只是要表现自己的美好憧憬与淡淡哀愁。开头写月下春江,宽广、静谧、优美,毫无尘俗气,是个全新的境界,颇能象征初唐士子的精神风貌:他们未经挫折,入世不深,热爱生活,一片纯情。接着,作者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两句,写出宇宙无垠、人生有限的矛盾,既具哲理,又像儿童提问那样天真烂漫,加上和永恒的江月连在一起,更烘托出他的内心世界:因为身处美妙境地而把握不住宇宙人生的真谛,所以产生淡淡而执著的哀愁。下文写的楼头思妇,只不过是象征事物。作者表现的仍然是自己的哀愁与憧憬。--春色撩人之际,思妇在楼头看明月,月的正身在天,倒影在水,光辉无处不在。她希望在天者如鸿雁,在水者似鱼龙,可以乘坐着到"何处春江"去作良宵的欢聚。然而天上的月光固然不能乘坐,水中的月光一样无可依托。梦里飞花,眼前流水,无不标示着春光渐歇,而牵情的明月更西斜而且坠落了。春江花月夜是美妙的,然而美中不足:两地分离辜负了今夜的春江花月。作者笔下的离愁远远不是悲痛。古乐府的"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显得沉重。而在《春江花月夜》里,尽管有哀愁,但掩不住轻快;虽然有叹息,却决没有悲观。这正是初唐士子的精神风貌!他们刚踏上人生之路,有理想,有信心,有活力,然而欠缺阅历。这个群体面对着国势上升期的大千世界,一面感到美好,一面又感到还有点什么不足,应该更美好。究竟哪里不足,如何才算更美好,他们又一概说不清,只模模糊糊地感到这是个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要准确表现这么复杂的内心体验,不能依靠逻辑思维和逻辑表述,按梁启超的说法,是要找到个象征,但如按中华诗学实情,倒不如说是要找到个寄托。张若虚用不知是谁家和在何处的游子思妇作寄托,是个最佳选择。诗中苍茫深阔的景象,优美清丽的文辞,悠扬舒泰的音调,再加上运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把"江"字"月"字忽合忽分,分开时又各自和别的词合合分分,瞬息变幻,精彩而神秘,表现出最典型的初唐情调。
古有识宝者,曾说张若虚"以孤篇横绝盛唐"。"绝",意为"渡"。这话的意思是:一篇《春江花月夜》,标志着诗坛从初唐向盛唐过渡。初唐青春活力弥漫,但总还带几分稚气。盛唐大诗人则已成熟,对宇宙人生有更深刻的感受。而这个"过渡"呢,刚刚是在幼稚和成熟之间。现代的理论称: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有九个阶段:自在,自然,自知,自我,自失,自觉,自强,自为,自由。其中以"自失"为关键:它否定了幼稚的自我满足感,从而萌发自觉的新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憧憬的士人们,当时也如人之处于少年时代,踏入自失阶段,就不期然地出现些哲理性问题,对宇宙人生提出些永远得不到完整答案的追问;而在这不断追问中,又逐渐觉得自己对宇宙人生加深了领悟,从而逐日成长。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写的正是这个自失阶段。他不写思考,只写情绪、氛围,很符合诗歌艺术原则。
散文强调的是情感,诗歌强调的是意象。
在散文写作中,运用了很多意象化的语言,就是诗化散文。
譬如说:舒婷的散文中,“姐姐”的眼睛,带着“太阳的光芒”。
鲁迅的散文诗,“暗夜”“野草”“爱得翔舞”等。
都有意象化的语言和意境。
诗话散文和散文诗的区别是,散文诗往往有一定的韵律,更加上口。不过,现在的区别已经渐渐模糊。
正文如下:
《聊斋志异》是一部奇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顶峰、“短篇小说之王”。它不仅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还大量取材于有关神仙鬼狐、犬鼠獐狼。狮虎猴象、蛇虫鱼鸟、花草树木乃至烟云泉石的各种传说;它的艺术构思,“驰想天外,幻迹人区”,人奇、事奇、景奇、情奇,如梦似幻,变幻莫测。
它所展现给读者的生活画面,既有凄风苦雨的人间,又有琼楼玉宇的天堂,既有昏天黑地的地狱,又有晶莹碧透的龙宫,寄托了广泛的社会理想。题材的怪异性,构思的奇幻性,寓意的深广性,构成了这部奇书有别于其他任何一部小说的独有的特征。形成了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的创造。
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古典文学巨著。在艺术实践上,追求真、善、美的美学思想;在形象塑造上,讲究形象化、鲜明化、神韵化;在情节发展上,推崇曲折美、波澜美的艺术情节。
在语言风格上,重视民间语言,大胆运用成语典故;在美学特征上,主张开拓创新,追求浪漫主义的艺术本质,奇特的幻想情节。现在,我就其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创新性强、浪漫主义色彩浓、幻想构思奇而进行赏识。
一、创新性强。
《聊斋》所体现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如:题材的新开拓,传统主题中的新发展等等。
在题材上的新开拓。综观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全貌,普通劳动群众及其生活并不是小说的真正主角。但在《聊斋》中,占主要分量的题材,则是社会普通民众及其他们的生活,它是庶民活动的舞台。《聊斋》中,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题材,是多方面的,诸如家庭生活、朋友交往、征服自然等等。
劳动人民的生活题材如此大量地出现在《聊斋》之中,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在题材领域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这还体现在:一、必须善于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以劳动人民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题材去揭示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展现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
如《白莲教》、《梦狼》等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题材。二、必须以鲜明的审美情感去处理这些题材。《聊斋》就以这空前未有的规模,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一批劳动人民鲜活的艺术形象,如田七郎、农妇、张氏妇、窦女、牧竖、胡氏兄弟、红玉、乔女、成名、白莲教少女等等。
总而言之,劳动人民作为庶民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大量入选为《聊斋》的题材,这是《聊斋》审美视野的新扩展,题材领域的新开拓,同时,它还提供了处理这类题材的新成就、新经验。
在传统主题上的新发展。生与死、情与爱是文学艺术的传统主题。在《聊斋》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很多生与死的悲欢离合,情与爱酸甜苦辣。但蒲松龄在这类主题的开拓上有所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生与死,在《聊斋》中,不仅仅是一种生命起始与终结的自然现象。事实上,它容贮了深广的社会内涵,而不是生与死的本身。
通过生与死的社会内涵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审美感受,寄托自己的审美理想。《聊斋》对生与死的艺术表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种审美形态。宋涛的死而生、生而死,连城与范十一娘的生而死、死而生;连锁和聂小倩的死而复活,莲香和鲁公女的转世再生;林四娘和公孙九娘对死亡的追忆,汤公亲身所体验的死亡过程……如此纷纭多样,唯《聊斋》所仅见。
《聊斋》对生死主题的开拓和发掘,除了寓寄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之外,还有极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表达人生价值观。人,既然有生,也就免不了有死。那么,除了不可抗拒的生死规律外,一个人的生与死,怎样才有价值?
《聊斋》通过塑造了一系列生气勃勃的艺术形象来作出了回答:是为孝、为义、为情、为人格尊严。为孝的:《考城隍》。为义:《王六郎》、《娇娜》、《褚生》等。为情:《连生》、《香玉》、《封三娘》等。为人格尊严的:《梅女》、《侠女》等。
在《聊斋》中,生死主题得到了广泛的表现,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思想内涵上,从价值观上对生死作了比较集中的艺术思考;在艺术处理上,不但创造了生死转换的多种审美形态,而且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作品主人公生而死、死而生,反复渲染,不断强化,从而使生死主题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
情与爱,是《聊斋》的一大主题。 《聊斋》中的爱情主题可归纳为:1、生死不渝的真情追求。2、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3、“春风一度,即别东西”的性解放。4、“礼怨情制”的婚姻观。但《聊斋》对这一主题的开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创意。
首先,在价值观念上,把爱情置于生死之上;在道德观念上,把爱情置于封建礼法上,并提出了“礼怨情制”的首创性构想。其次,“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是《聊斋》的独特发现和创造。再次,它为那些实行“性解放”的青年男女树碑立传,其观念之新颖,人数之众多,空前未有,令人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生与死、情与爱在《聊斋》中得到了广泛的艺术表现,但它的独特的审美创意,又使这一传统主题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聊斋志异》究竟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多数研究者将它纳入浪漫主义范畴;也有人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我通过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后,我认为它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当然并不是全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现在就让我来说说,我这样认为的原因:
首先,蒲松龄是一个富于理想的作家。他善于通过丰富的想象,塑造理想人物,描绘理想的境界;借助大胆的幻想,设置铺叙离奇的情节,运用奇特的夸张塑造非凡的艺术形象。这一切,恰恰说明了蒲松龄又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艺术家。
其次,《聊斋》中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还表现在作者善于运用独特的构思,诡谲万端的幻想,设置丰富多彩的离奇情节。但离奇情节不等于荒诞和向壁虚构。如《促织》、《石清虚》等名篇,它们都真实地、深刻地概括了生活中的矛盾,故事情节确实离奇、曲折、出人意表,处处显示了绚丽的神奇色彩。
再次,蒲松龄笔下的勇敢地诛除鱼肉乡里的霸占人妻的乡宦,儆戒草菅人命。残民以逞的县官。他所表现出的扶危济困,嫉恶如仇,保护被压迫者,打击封建势力的可贵品质,寄托着作者的美好愿望,这也可以称作是浪漫主义的艺术美。
《聊斋》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还表现在他的小说富于诗化的情感和诗化的意境。对诗化的情感,主要体现在主观色彩强烈。在对客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他所作的是情感性观照;在对表现对象进行审美开掘时,他首先重视的是情感世界的开掘。
在审美创造中,他特别注重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在情节推进。时空转换、命运安排等诸方面,明显地表现出创作主体对作品的情感性支配痕迹。在作品的艺术形象中,注入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情感体验和意绪。也正因为这些情态体验和意绪。使作品更具有主观色彩,浪漫主义色彩更浓。
《聊斋》中所创设诗境大体可分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两类。《翩翩》中当罗子浮带着儿子再去看望翩翩时,只见“黄叶满径,洞口云迷”,不得不“零涕返”。此刻罗子浮恋情怀思的召唤下一齐云集于篇末,成为“黄叶满径,洞口云迷”,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了。
“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不言天空之月而言水中之月,让人由水中之月去感知天空之月;不写对面之花而写镜中之花,让人由镜中之花去欣赏对面之花,这是诗歌意境创造的常见手法——以虚映实。在《聊斋》中,对人物心境的揭示,就常用这种以虚映实的手法进行开拓。
如《胡四娘》、《小翠》、《王子安》等作品。王子安种种醉态中所映照的,是他平时深埋于心底的种种梦想;小翠日事嬉戏的荒唐行为,映照了她的忧患在胸和机心运筹等等。
《聊斋》中的浪漫主义色彩,都来自于蒲松龄对生活精细的观察和真切的感受,也因为这样,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貌和价值。
三、奇特的幻想情节。
高尔基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成长和构成历史。”那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是密不可分的。《聊斋》中写了那么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同情节的丰富是分不开的。
在情节的提炼上,做到离奇不失其真,曲折不失其严,丰富不落窠臼,这是《聊斋》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它那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首先表现在情节的光怪陆离,神出鬼没:什么冤魂复仇、神仙下凡、鬼变人、人化虎,等等,真实变幻莫测,想想瑰丽;鸟鱼花卉以及狐狸的千变万化,更是如窥万花筒,无奇不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孙子楚爱慕阿宝,既可以“魂随阿宝去”,又能变成鹦鹉。“生自念倘得身为鹦鹉,振翼可达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
在情节的提炼上,要做到离奇而有真实、曲折而又严谨、丰富而又新颖,主要靠作家的真知灼见、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聊斋》这部名著的诞生,正是作者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善于将“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的大量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化为如此丰富的情节。
总的来说,蒲松龄的《聊斋》中的幻想,是奇特的,神奇的,自由的,充满悬念的,贴近生活的,超越现实的幻想。而正因为是这些幻想,使作品中的故事构筑成一个个奇异的世界;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位位生动的形象;让作品中的情节充满悬念和波澜起伏。
从《聊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楚辞》以来诗词文赋用语的固有特色,又可以看到《左传》以来史传文学造句的传统技巧。我们既可以看到左转右折、陡起陡落的情节演化,也可以看到节奏鲜明,旋律生韵的时空流程和阴暗相生,浓淡有放的结构布局。
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真挚感人的情感寄托,还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资兴,对时空遐想,以及其哲学感悟……总之,《聊斋》以独特的思想,独特的人物,独特的艺术构思,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立足于我国古典文学之林,占据于世界文学宝库的一席之地。
首先,早期散文诗是从诗歌中发展而来的,是诗歌大类中的一员,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中间的一个文体。所以有人说它非马非驴,是骡子,是杂交。有人考证说,这种文体是五四期间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是泊来品。其实,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这种文体。比如庄子《南华经》中的许多片断,就具备散文诗的特点,屈原的《渔父》也是散文诗。到了唐代,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是散文诗,宋代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可以说是日记体的古典散文诗。但是,作为散文诗正式提出来,还是欧洲法国的诗人波特莱尔,他出版的《巴黎的忧郁》,自称为小散文诗。因此说,散文诗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后来法国诗人贝尔特朗大量使用散文诗这一文体。俄罗斯最著名的散文诗作家是屠格涅夫,他写有《爱之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也是散文诗。在亚洲,最早写散文诗并卓有成就的是印度的泰戈尔,他的《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也是散文诗。纪伯伦是黎巴伦著名散文诗大家,出版有多种散文诗集,如《笑与泪》《暴风集》等。在中国,五四时期写散文诗最有名的是鲁迅,他的《野草》就是散文诗集。冰心写有《繁星》《春水》两部散文诗集。当代较有成就的是柯蓝,郭风、耿林莽等。 其次,散文诗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从诗歌中脱离出来,具备了更多散文的特征。其一是不押韵,当然也有押的,属于可押可不押之类。这就与诗歌有了区别,诗歌一般是要求押韵的。其二是较多寓意和哲理。其三是散体化趋势越来越大,短小精悍。所以,有人在写文学理论文章时,多把它归类为散文的一种。但是它与散文还是有明显区别。 再次,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散文往往求全,完整叙述事物过程,诗和散文诗则取其一点、一线、一角,以点代面,以一当十,作简约性勾勒;散文多取块状结构,洋洋洒洒,铺叙成篇,每有冗长拖拉、烦琐罗嗦之弊。而散文诗多取跳跃流动、轻捷灵活、多节段的结构,既适应语言精炼简洁、节奏起伏跳荡的要求,也体现了建筑美的视觉快感。散文诗的构思是诗化的,讲究诗的情绪,诗的精魂,讲究铸炼意境 。散文诗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都追求寓意和哲理,散文诗的语言具有以一当十的张力,是压缩饼干。另外,散文诗多是可以朗诵的,如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历来是朗诵的必选篇目。诗歌与散文诗的区别是:诗歌是格式化的,古典诗词讲究五言绝句或五言律诗,七言绝句或七言律诗,字数与平仄都有严格要求。而且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是押韵的,根据汉语的读音分为十六(新韵是十四)个韵部,写诗词要从韵书中找韵脚,不同部的韵不能相押。而散文诗则没有这些要求,既没有字数限定,也没有押韵的限定,是自由散漫的文体。 至于什么叫散文,什么叫诗,什么叫散文诗?我在其它文章中都有概括。《辞海》《辞源》中也有介绍。我就不用多费口舌了,大家翻翻就能看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