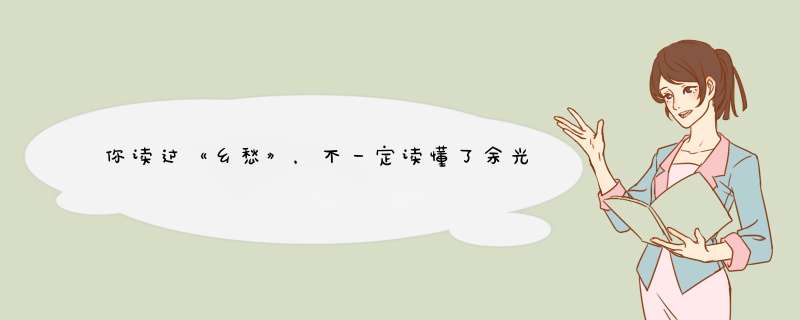
2017年12月14日,华北大陆多个城市迎来了2017年的第一场雪。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有一位耄耋老人与世长辞。
检索他的资料时,一片压抑的黑白色调。这位老人一生非凡,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事业逾半个世纪,多篇作品被选入课本。
他是“文坛五彩笔”,他是爱国的“乡愁诗人”,他就是余光中。生于1928年重阳,卒于2017年初雪,享年90岁。
1928年10月21日,余光中出生于南京,家居紫金山麓、玄武湖畔的龙仓巷。为顺“光耀中华”之意,族人给他取名“光中”。
余光中九岁那年,祖国山河沦陷,战火纷飞,母亲用扁担把幼小的他挑在肩上,一路逃亡到常州,后辗转避难于重庆。
在巴山蜀水凄凉地,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十几岁的少年,厌恶这段“蒲公英的岁月”,面对眼前战火绵延、交通封锁的闭塞落后,一心想着逃离,去看看海那边自由辽阔的天空。
因此,余光中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但因母亲的挽留,同时考取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他,选择留在了南京。
20岁时,擅长写诗的余光中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诗集。
就连大作家梁实秋也曾称赞他说:“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他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他写冷雨:前尘隔海,古屋不再,杏花,春雨,江南。
他写绝色:你带笑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
他写诀别:莲只开一个夏季,为你,当夏季死时,所有的莲都殉情。
最后,他写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的诗成就极高,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那首《乡愁》。 这首20分钟一挥而就的作品,背后是长达20年的沉淀。
他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几番辗转,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他缺乏归属感,因此读他的诗,迎面扑来的是一种深刻见骨的苍凉。
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思念着自己的思念,孤独着自己的孤独,穿越时光的缝隙,信步拾阶而来。
他始终在思考着生命的因缘来去,心底明知宿命不可违,却偏要用挡车之力,与心中的永恒决一死战。
余光中说:“婚姻是一种妥协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正是这样的爱情观,帮他组成了世人称羡的“模范家庭”。
孩提时代的余光中生得浓眉大眼,剃着小平头,聪敏过人,十分讨喜。因此,母亲常带他到外婆家去玩。
舅家姐妹众多,青梅竹马。长辈们常开玩笑说,将来干脆就让光中娶了哪个表妹吧。谁知一语成谶,长大后的余光中,竟真的娶了一位远房表妹,范我存。
相识不久,余光中便给范我存及寄了一份刊物,上面刊登着他翻译拜伦的诗作。
因为不知道表妹的大名,余光中便在信封上署了她的小名“范咪咪”,这昵称一直沿用到今。
时势造英雄,患难见真情。范我存在台北女中就读时,因体检发现肺病,不得不休学在家将养,瘦得像棵水仙,楚楚动人。
在那个年代,肺病是不治之症,传染性又极强,令人闻之色变。但余光中毫不在意,常去探视安慰。
还在文中深情地写道:“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飘逸,羞涩而闪烁,苍白而瘦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范我存痊愈后,两人更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面对双方家长的反对,范我存把心一横,表示“非余光中不嫁”;余光中也用小刀在树干上刻下“余爱咪”,此情昭昭,日月可鉴。
除了爱情,两人在事业上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受范我存画作的启发,余光中迷恋上了梵高,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洋洋洒洒五十万字的《梵高传》。
每译就一章,先拿给范我存誊清,再送给报纸连载。浪漫的是,文稿的正面是译文,背面竟赫然是余光中写给范我存的情书。来自爱人的小小惊喜,简直要暖化人心。
就这样,相恋六年后,两人终于在1956年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上,余光中性格使然,不苟言笑,范我存却开朗大方,自然亲和。
性格的互补增益了家庭的和谐,所有朋友都称赞二人是最佳“牵手”。
结婚35周年的纪念日上,余光中轻吟《三生石》、《红烛》,情真语挚,催人泪下。被人问及婚姻保鲜的奥秘,范我存说:“结婚后的信赖,是最重要的。”
余光中则表示:“ 夫妻之道,主要是沟通。我们不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价值观,婚姻怎么会不牢固呢 ”
有人说:“爱情最好的保鲜之道,就是把已婚过成未婚。”这一点,余光中做到了。
他就像一个负伤的泳者,只为采一朵莲。隔着黄昏,隔着细雨,无论你在哪里,这朵莲都是你。
余光中先生才华横溢,尤以诗见长。但他不仅写诗、评诗、译诗样样精绝,就连平时的“恶搞”也颇见诗思。
据古远清教授说,他在某学术活动中结识了余光中。两人喝酒聊天,相见恨晚。席间,不知是谁吟起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句诗,随后大家便聊起了台湾的社会现实。
余光中慨叹台湾世风日下,政坛乌烟瘴气,便顺口将这句耳熟能详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颠倒过来念成了:酒逢千杯知己少,话不半句投机多!
同样十四个字,语序稍微一变,讽刺效果顿显,语意精妙,立时惹得满座叫好。
有人说:“人无癖,便无趣。人有癖,功夫花在所癖之事上,物我两忘,不是高人,便是妙人。”
余光中不但“癖”诗,还在诗上“花功夫”,堪称妙人。久而久之,这“妙”便超脱了诗作,进而体现在言谈举止里了。
论语言艺术,他幽默深刻:
某次,余光中和散文家思果谈及他们的另一个朋友高克毅,行西礼向两位女士虚拥亲颊的事情。思果思想保守,再三慨叹道:“怎么可以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呢?”
余光中则立即回答说:“怎么样,当众不得,难道要私下做吗?”
论功名利禄,他宁静淡泊:
某次,余光中和几位文人聊到演讲费,有一位文人说他拿过一个小时一万元,有一位说他拿过两万元,有一位说他拿过三万元,接下来,轮到余光中出声了,大伙儿以为他会继续加码,余光中却说:“我拿过一个小时五百元的……”
论事业追求,他笔耕不辍:
提起余光中,捆绑着想起的就是那首《乡愁》。可以说,是他成就了《乡愁》,也是《乡愁》成全了他。
但余光中自己却说:“‘乡愁诗人’固然不是一个坏的称号,但我的作品还是要比这个称号复杂一些。”
一首小诗立了大功,但也好像一张巨大的名片,有时会遮住他本人的面孔。
对于余光中来说,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没有出现,所以他还要继续笔耕不辍。
如今诗人已去,但那些用心的经典作品,那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将永远留存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闪烁,历久弥新。
特此声明: 文中插图及视频片段均来自网络,仅供分享,著作版权属于原作者
文|只有青春
早就想为余光中先生写一篇文章,可是,等静下心来,自己也有了点时间,准备写点什么的时候,先生已经于2017年12月14日去世,那晚我彻夜未眠,草赶了一首诗,怀念余先生:
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也可能有几座每年清明都祭奠不了的孤坟。从我们离开故乡以后,归路就显得困难重重,或没时间,或被工作所拽,又或者拖儿带女在居住的城市的城郊公墓祭奠,新坟。故乡的老坟,早就杂草丛生。
余光中先生生于一九二八年,正是民国最困难的时期,北伐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混乱,民不聊生。
他一生求学时光都颠沛流离,一九四九年去了香港,一九五零年去了台湾,不想,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等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以后,我们在讲台上、电视上看到的余光中先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先生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不过是白鹤银发的少年。
《乡愁》这首诗流传出来,早于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的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就在所有华文圈里,流传一时,每一位游子读起来都湿了眼眶,走了心,还有的人普了曲吟唱。
一九七二年,先生四十四岁,离开大陆已经二十三年。旅居欧美的华人,港澳台的中国人,都在“外面的世界”,思念着故乡大陆的“母亲”,因为当时的文化隔断,让这些人只能念着《乡愁》,唏嘘低吟,泪眼婆娑,这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撕裂感。而大陆这时期还没有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说实话,这时的大陆文化人,没有几个诗人,文人能对中国的文化用一首诗表达出: 撕裂感, 历史 认同感,中华传统美德的善孝,唯有《乡愁》。
①撕裂感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的文化人刚刚结束文革,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即使他们有“走出去”的想法,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往”,出国游学,访同学,走亲戚,会老友,成了奢望,这时的大陆文化人都在埋头做学问,低头写文章,如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等等(不限于以上)。
而欧美,港澳台的文化人,这个时期“想回来”,也一样被阻断,每当想着大陆的“母亲”,“新娘”,清明的祭奠,家乡的“小吃”,乡愁是苦涩的,是”欲得之而不能得”的遗憾,这期间有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等(不限于以上),当然肯定也包括,余光中。
所以,《乡愁》成诗的背景时期,中国的所有文人墨客,都 有撕裂感。
② 历史 认同感
中国人的 历史 认同感有哪些?
我们中国人同华夏之祖先、儒道佛互补之宗教、汉语言、五千年之 历史 、善孝优先的价值观、黑头发、黄皮肤,繁体字,简化字都是方块字……这些 历史 认同感的东西不是靠盘点,罗列,搬运,堆砌起来的,它已经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中国人血脉里,特别是《乡愁》时期的所有文人墨客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我查不到这个时期那一个文人否定自己是中国人(一些西化了跪惯了的文人政客除外,政客不等同于墨客)。
一九七四年,余先生在《听听那冷雨》里写到:
余光中先生强调的方块字,仓颉造的字,是汉族人民心灵的祖先,有中文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肯定都爱自己的故土,这份 情感 是有向心力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汉文化具有凝聚力,不论身在何方,中国的文人墨客,都有一颗赤城的中国心,这就是中国人的 历史 认同感。
余光中先生继续在《听听那冷雨》里写到:
这雨可听,可看,可舔,其实我们细细品味文章中,从字面以外能感受到余先生是把“雨”当成大陆母亲送来的信使,雨季来了,清明来了,乡愁来了。
这雨,同样把中国的乡愁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 历史 认同感。
③中国传统美德的孝善
出国的游子,旅居海外的华人,港澳台同胞,或者离开故乡在城市中闯荡的人,谁没有乡愁?
想家了,就是想老母亲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里有两句“母亲”,一个母亲指的是大陆,一个母亲是养育自己的亲娘,思娘者孝善,“慈母手中线”,“低头思故乡”,这是中国文人墨客都具有的传统美德。
但是,每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他的人生肯定是不精彩的,所以,华人都有走出去的精神,闯关东,走西口,美国华人街,下南洋,留学欧洲,这些人的乡愁都是一样的,想近孝,身却在他乡,这种思绪万千被古今的文人墨客,反复柔进他们的诗歌当中,每一句都与孝敬父母,善良的心无处寄托而惆怅, 所以中国的文人墨客,都是孝善的传承者。
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
余光中出生在大陆,长成少年,中年在台湾毕业,大部分在台湾教书育人,后来又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育人,晚年又回到大陆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做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做过驻校诗人,晚年的余光中先生,穿梭于大陆港台澳,美国之间,做文化及学术交流。
这就是一个游子的一生,而他的诗歌《乡愁》将会与天下的华人游子一道,同音吟诵,一诗千年。
余光中的《乡愁》是我小时候在课堂上能背的滚瓜烂熟的为数不多的诗歌,几乎刻进了脑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后离家越来越远,再去逐渐多了解余光中,从此对余老先生这位乡愁文豪崇拜的五体投地。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此后的二十年,余光中虽因战乱颠沛流离,却从未离开过这片初生之地,大学也就读于金陵大学(1953年并入南京大学)。
成长于长江之畔的他,生来就带着江南文人雅士的才华,仅二十岁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
随后不久,余光中随着父母举家迁往香港,一年后入台湾,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家乡深深地思念……
为了求学,也为了理想,我已离家三年,近日于喧嚣闹市的书店中,于茫茫书海中,偶然发现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余老先生已过世近三年,这本散文集是他生前最后一本亲自审订的书,算是他的绝笔了。
晚年的余老先生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那道“浅浅的海峡”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存在,他也借此书表达了自己的“乡愁”得到了安放。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题目化用苏轼《定风波》中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本散文集饱含着余老先生对故乡和人生的思考与怀恋。
生于江南,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载,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模样,余老先生何尝不想再回到她的身旁。
那些无数于秦淮河畔的桨声灯影中,朱自清寻回思乡,不愿做过路的蜻蜓。那些辗转成歌的岁月里,余老先生意图于大海之中寻得长江之水,聊以慰藉成长于金陵的灵魂。
2017年12月14日,“江南诗人”余光中走了,安眠于异乡,没能如他诗中所愿。历经九十个春秋,将才华横溢的少年磨炼成眉目间尽是思念的老人,但还是抵不过岁月漫长,这位当代诗坛最后的守夜人永眠于黑夜之中,如同网友说的“长江黄河若有知,定会为他长歌一曲”。
古有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有三毛故乡的橄榄树,有李荣浩的《老街》。中国人的乡愁情结在这颗蓝星上是独一无二的,纵然如蒋介石,也有一直想要回去的奉化老家。
在如今高速发展的时代,无数人为了理想,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离故土,但他们无论身处于怎样的繁华中,心中的那片净土无不是属于他们的家园。
也庆幸我们生活于这样高速发展的时代,家的距离不再遥不可及,一封封难以送达的家书进化成如光速般的讯息。
时代的变迁使得中国人的思乡情绪得以慰藉,但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乡愁情结,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抹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