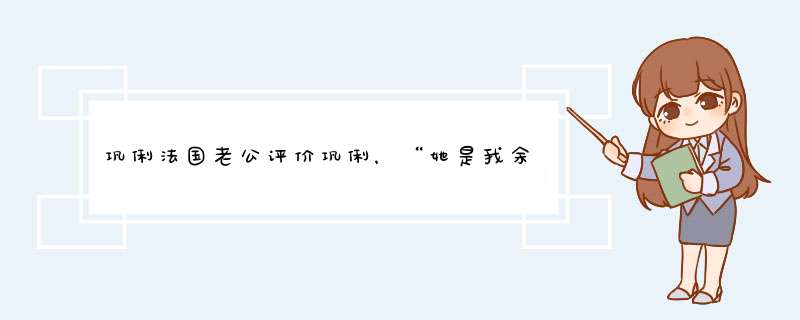
巩俐的法国老公简直是女神收割机,三任妻子其中两个都是影后,如果再加上巩俐,那么他的妻子的容貌毋庸置疑都是让人惊叹的。而他并不仅仅只有这几个女人,还包括了一个和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未婚妻。可以说他的情史让很多男人自叹弗如。
巩俐法国老公评价巩俐,“她是我余生的女人”,这句话其实我们都相信,毕竟他的年龄也让他应该不怎么会折腾了吧。那么再来谈一下她的法国老公让·米歇尔·雅尔的情史。
我们都知道法国人非常的浪漫,而很多女人在浪漫面前就会束手无策,只能让男人手到擒来。而让·米歇尔·雅尔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男人,还是一个帅气的男人,更是一个艺术家,再加上还比较有钱,那么受女人的欢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他结过三次婚,除了第一位是不出名的女子之外,其他的妻子都比较出名。他的第二任妻子是英国女星夏洛特·兰普林,第三任妻子是法国女星安娜·帕里约。难道说妻子就是他所有的女人了吗?不,在这中间还有一个爱得痴缠的未婚妻阿佳妮,三位都是国际影后。而现在的巩俐又是一位影后。
生长在法国让他这一生都是一个浪漫的人,所以在七十岁也不怕秀恩爱。而此次他和巩俐也是在大肆的秀恩爱,但是无论怎么样,也希望巩俐是他余生的女人,不过感觉在他余生应该不会再折腾了,毕竟年纪也在这里了。
以花传达心意。
相比国内只有在重要节日才送花,送花在外国是很普通的行为,是法国男士的基本日常操作。法国男人不仅过节送花给女友甚至结婚数十年的伴侣,甚至平日路过花店也会顺手带上一束给伴侣。
愿意赞美,渴望分享。
法国人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男人觉得女人很美、很可爱,会直接说出来,跟国内情人的“内敛”很不一样。
另外他们在意生活品质,喜欢和情人分享各种感官体验。外国人更为直接,“冷战”是他们讨厌的行为,自然也比较少会有逃避讨论沟通的情况发生。法国人的浪漫并不是“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而是”我渴望与你分享一切”。
对女性的绅士行为。
另一个给予法国人很浪漫的原因,来自于法国男人至今仍坚持的“Galanterie”(可以翻译为殷勤)。这个词源于17世纪的法语,原来指骑士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现在多指男人在所有动作和言语中,皆以女性为优先考量的礼貌准则。
虽然这样的观念在各年代都有争议,但法国男人仍把它当成一种对女性基本的礼貌,包括赞美女性、帮女性开门、给予女性优先路权、礼让公共座位给女性等。
巴黎是什么巴黎就是毕加索。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得没错。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巴黎,虽然聚集了全世界最先锋也最优秀的一批艺术家,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可能比毕加索更配担当起伟大二字,更富有巨匠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而言,毕加索不仅是这一批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而且无形中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他爱过的女人,他周围的朋友(不管是画商、诗人抑或同样具有绘画天赋的同行),甚至包括他的对手(譬如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恐怕都无不承认这一点。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能量在巴黎发迹了的西班牙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王者之气。“毕加索到巴黎五年之后,便成为了他周围那一帮人的中心人物。他犹如一把火炬,无论他拥有权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都向他靠拢,他对所有靠近他的人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和震慑。所有这些人一致承认画家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旗手。”当然,毕加索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果然像一路飙升的股票一样所向披靡,直至成为巴黎这座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中心中的中心——他刷新了一个时代。艺术史因之而改写。
巴黎曾经属于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属于莫奈、高更、梵高。在毕加索之前,巴黎还属于过波德莱尔——这位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鼻祖,写过一部《巴黎的忧郁》。然而在毕加索出现后,忧郁的巴黎才真正开始变得放荡了,以苦难为宿命的饥饿艺术家们迎来了自己的狂欢节,这位绘画界首屈一指的暴发户也带给了他们以希望。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气候转温,春意萌动,一个可能大施身手的全新的时代终于姗姗到来。他们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朦胧的使命感:自己不仅是为现实而活着,也在为未来的艺术史而活着。于是,现代艺术的飞船选择了巴黎作为着陆的地点:立体主义、野兽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推动了历史。不管怎么说,跟梵高、高更等人相比,毕加索这一代艺术家基本上还算是幸运的,更有身逢其时之感。
《巴黎的放荡》这部书,堪称是这一代艺术家的集体传记:卢梭、布拉克、莫迪利阿尼、藤田、朱勒·帕森……他们的生活与创作都在其中占据了相应的篇幅。尤其重要的,还记录了跟这些画家同根共生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学活动:阿波里奈、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乃至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不管他们是巴黎的主人抑或过客,都以各自的膂力推动过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进程。但必须承认:毕加索的影子一直贯穿这部书的始终。或者说,他是那个时代艺术家群像后面至关重要的背景。要想彻底地了解放浪形骸、恃才傲世的那群人,只能从了解毕加索开始。这是走进现代艺术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同时还打开了离我们很远又很近的一个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放荡的巴黎。巴黎的天空与巴黎的星相图。
塞纳河右岸蒙特马特洗衣船的画室内,曾经蜗居着一大批落魄的艺术家——有的人甚至老死在那里。青年毕加索初到巴黎,也曾在这座后来名扬四海的贫民窟栖身,后来就头也不回地搬到富人区去了——可见毕加索也体验过一段捉襟见肘的生活,只不过他知道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它。贫困对于毕加索仅仅是中途换车的驿站,对于大多数艺术家则是难以抗拒的宿命。毕加索几乎是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他身后的大多数难友,不仅因为他懂得以与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挣钱、生活,而且因为他不愿过多回首早期的贫困:“西班牙人毕加索要比整天泡在酒吧的那些人混得好一些。他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可靠办法:作画,卖画。那时他已经表现出自己与其他人的既相似又不同。所有在蒙特马特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当中,毕加索不仅是最富有的,而且是手头拮据时间最短的一个。”被巴黎所重新塑造了的这个毕加索,在绘画创作中充满 ,在人情世故方面都掩饰不住他内心极端的冷酷:“他对周围可怜小人物的悲伤和人们对他的看法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时刻昂首挺胸、盛气凌人地在他们中间晃来晃去,尽情享受着他已经占有的‘帮主’的地位。”我们只能善意地揣测,他并不是厌弃周围尚在贫困中挣扎的同行,而是厌弃贫困本身;虽然他一生只有过短促的贫困,却是很记仇的,他永远都把贫困视为头号敌人——这导致他爆发出非凡的能量,几乎是借助某种类似于报复的心理获得了成功。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幸运儿,反而使其他人遭受的不幸显得更为强烈——那些生病的画家,欠债的画家,失恋的画家,醉酒的画家乃至自杀的画家,对毕加索只能望尘莫及,他们理解不了毕加索的奋斗精神(也可以说是世故),也无法分享到毕加索的那种胜利感,这多么悲哀。我更愿意相信:毕加索这么做,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他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而且多多少少维护了集体的尊严。至少,画商们乃至世人在艺术家面前下意识流露的那份傲慢与偏见,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毕加索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毕竟,有更多的画家,追随毕加索的足迹走上了一条新路。不仅有一个毕加索的巴黎,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可见阿波里奈既是立体主义的命名者,又是毕加索艺术最忠实的吹鼓手。在立体主义初问世而四处碰壁之时,阿波里奈最先跳出来为其担任辩护的律师:“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里奈。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里奈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于是他成为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作为其主帅的毕加索本人还要激进、还要狂热。
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0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神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他身后依次是其他画家、诗人。或许在那一瞬间,铁石心肠的毕加索才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这几个细节串联在一起,也是挺微妙的。巴黎是这些艺术家共同的故乡。巴黎,不断举行着婚礼,又不断举行着葬礼——就像那些艺术家的喜怒哀乐,在不断地飘散,不断地变换。谁能够分得清自己是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客人即使毕加索称得上是艺术天空一颗难得的恒星,但在他周围,乃至在他之前之后,更多的则是流星式的人物——在重复地表演着一闪而逝的命运。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谓的卢浮宫(或其他艺术品博物馆),不过是他们的集体墓园。然而,他们的消失丝毫未影响巴黎存在的意义——即使那样,他们永远是巴黎缺席的在场者。
先泡名模后娶歌星
与球场内的精彩表演相匹配的是巴特斯同样让人羡慕不已的场外生活,巴特斯1998年时与著名模特琳达·伊万吉利斯塔的恋情轰动了整个法国,而他现在的妻子温特则是一名在欧洲小有名气的歌星。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人生的奇妙,那些长相独特的法国球星似乎特别能够受到青睐——先是有卡伦布,接着又有巴特斯。琳达曾将巴特斯称为“世界上最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这一爱称后来干脆被法国媒体恶搞为“最有男子气概的卡通男人”。
1998年琳达与巴特斯相恋时已经33岁,拥有一次维持了六年的婚姻,以及一次未果的订婚仪式。在与巴特斯相识之后她一度淡出了时尚圈,但最终由于无法忍受伦敦的阴雨气候以及空虚乏味的生活而回到繁华的欧洲大陆,并声称曼彻斯特与巴黎相比就是一个小农村——其中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小段子是巴特斯曾因为与琳达约会而错过了自己在曼联的第一堂训练课。2002年8月,巴特斯与琳达分手,之后巴特斯曾高调要求复合,不过在财大气粗的纽约富商与F1车手等竞争者面前巴特斯很快便败下阵来。
不过巴特斯很快便找到了新的避风港,在一个月后的一次时尚PARTY上,他与温特相遇并迅速坠入爱河,11个月之后,温特为巴特斯生下一名男孩,而巴特斯则送上钻戒,奉子成婚。
勾搭空姐染指艳星
法国人浪漫、不拘小节的天性在巴特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自己的两任女友都是标准的美女,但巴特斯的心依旧是那样的热烈与不安分。在与琳达热恋期间,巴特斯就曾被媒体发现与法航的一名空姐打得火热,后者曾一度住进了巴特斯在伦敦包下的酒店套间,而当巴特斯在与这位空姐逛街时发现记者偷拍之后不但没有躲避或者上前警告,反而是大方地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英国小报曾为此大发感慨,认为这就是法国人与英国人的差距,并号召贝克汉姆等人好好向巴特斯学习。
不过这段感情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巴特斯很快便有了新欢,而这次他的选择则更让人无法猜透:《太阳报》的三版女星斯西。媒体无法理解巴特斯为什么要这样自甘堕落,他的女友毕竟是琳达,曾经的世界十大模特之一。好事的媒体甚至将这件事与好莱坞影星休·格兰特召妓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成功后的空虚心态:没有目标,缺乏动力。
在妻子温特怀孕期间,巴特斯也曾被媒体发现有过出轨行为,不过让人欣慰的是在结婚之后,巴特斯终于收敛了自己。现在妻子和孩子成为了巴特斯的快乐之源,在他宣布退役时特别提到了家庭给他带来的快乐,并称正是因为有了家庭的存在,他才有勇气作出退役的决定。
更愿意赞美,也更渴望分享。法国人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男人觉得女人很美、很可爱,他会直接说出来,跟亚洲情人的内敛比起来,更愿意对另一半给予称赞。另一位则说:我们不浪漫,而是比较感性。原因是他们在意生活品质,喜欢和情人分享各种感官体验,也因为民族性使然,比较少有逃避讨论沟通的状况发生。换句话说,他们的浪漫,并不是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而是我渴望与你分享一切。
另一个给予法国男人很浪漫的原因,来自于法国男人至今仍多少坚持的Galanterie(较接近的翻译为殷勤)。该字源于17世纪的法文,原来是指骑士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现在则多指男人在所有动作和言语中,皆以女性为优先考量的礼貌准则。该原则可延伸到赞美女性、帮女性开门、给予女性优先路权、礼让公共座位给女性等。这样的观念在各个年代都有其争议:18世纪时哲学家卢梭曾批评这样的观念给予女性过高的重要性与评价;而在西蒙波娃眼中,Galanterie只是父权社会的陋习,企图把女性绑在附属地位。
即使如此,法国男人仍把它当成一种对女性基本的礼貌。曾在巴黎日本餐厅打过工的我,对此有很深的感触。餐厅时常有人点整瓶红酒,而桌边侍酒的基本步骤就是要先到两三口请该桌主人品酒,同意后再一一倒给该桌其他客人。日本桌的主人绝大多数是年纪最长的男性,品酒的主人几乎不可能是女性(除非年纪相差悬殊),时常不用加以询问就能判断出来。一天来了一桌法国人,有男有女。在倒第一杯酒时,我习惯性把酒瓶凑往该桌张罗点餐也较微年长的男性,但他却立刻大手一张盖住杯口,跟我说:该让女士优先喔。这让我猛然意识到法国「女性优先」与亚洲的传统观念有多么不同。在我的观察里,尽管对于Galanterie的女权争议不断,多数的法国男性仍以保有尊重女性、女士优先的原则为荣。
开放自由的性爱,其实是很晚近的事。大众对法国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对性爱相当开放。的确,法国如同许多北欧西欧南欧国家,相对于亚洲国家,对性爱是相对开放的;但跟邻近国家比起来,法国却又保守了一点。几年前TNS Sofres一个针对法国女性的有趣民调显示,只有41%的法国女性能和朋友轻松谈论性,且仅44%的女性能轻松和伴侣谈论性爱。一份严谨的研究指出,法国人对性爱议题的解放是这几年才开始的。
法国人眼中的爱情观进化史 -评《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九百年来的激情与罗曼史》
文/信实的精灵
“让女性获得完全的平等是文明最不容置疑的标志,这将让人类的思想力量和幸福机会翻倍”,这是索莱尔斯笔下的妙不可言的米娜最喜欢的司汤达的一句话。对于法国人而言,爱情和性似乎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让我们来评价世界上哪一国人最浪漫,那应该是法国人无疑。法国人已经从骨子里面继承了来自于祖祖辈辈的浪漫血统和优雅天性。
法国人,在美国作家玛丽莲·亚隆的笔下,似乎是从十二世纪开始就隐隐约约有着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对于爱情的勇敢追逐,不管是骑士对于自己所钟爱、所衷心服侍的女主人的爱情,抑或者男子对于自己喜欢的女人的强烈爱情,这都在亚隆的这本书中为我们一一呈现出来。
玛丽莲·亚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克莱曼性别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法国文学教授,这就是在这本书中为何她能够对法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关于爱情的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一样的原因。对于一本书,她能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反复阅读,同时给出我们关于她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悟。她也曾著有《妻子的历史》、《乳房的历史》、《象棋皇后的诞生》、《干姐妹:女性记忆中的法国大革命》、《母性、死亡和癫狂文学》、《暴风时代:女贵族、女资产阶级和女农民的故事》以及《美国人的安息之地:公墓和墓地的四百年历史》等多部作品。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玛丽莲是一个对不太入流尤其是看似冷门的学问尤其是关于女性角色、女性身体,甚至于女性定位颇感兴趣的人,并且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女性作家,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明。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