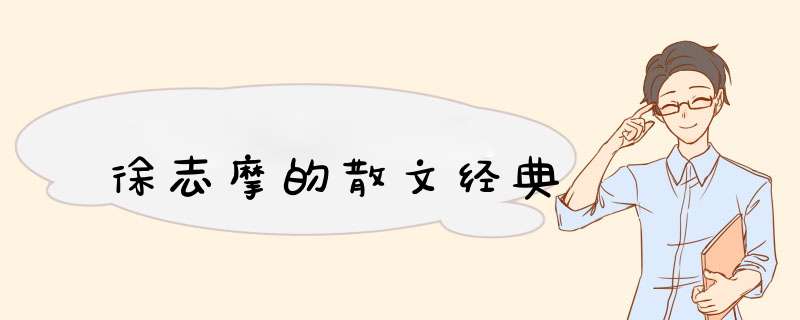
徐志摩散文经典全集如下:
《徐志摩散文经典全集》收集了徐志摩的全部经典散文,通过这些文章,你可以体会到徐志摩《浓的化不开》的感情、《自剖》的真诚、《迎上前去》的勇气、《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决心、《艺术与人生》的思索以及《爱眉小札》里无尽的深情。
徐志摩散文经典语录:
1、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个破碎了的梦。花凋花谢。最后还是一片凄楚。相识相爱。最后还是不和而散。
2、毕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成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碰到你。
3、小人知进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主义,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到,从不以人为单位。
4、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和你寒暄,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5、是时候了。好好地做个女人。穿裙子。扎辫子。不和别人吵架。不翘课。不说脏话。一日三餐一个不能少。点之前睡觉其实这些,我做不到。
我过的端阳节
泰山日出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落叶
秋
翡冷翠山居闲话
海滩上种花
欧游漫录(选二)
巴黎的鳞爪
我所知道的康桥
自剖
再剖
想飞
天目山中笔记
关于女子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泰戈尔
再说一说曼殊斐儿
“迎上前去”
对沈从文《市集》的批语
吸烟与文化(牛津)
“话”
海粟的画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猛虎集》序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伤双栝老人
家德
西湖记
志摩日记(选录)
情书一束
致梁启超(片断三则)
致王统照
题赠郭子雄
致周作人
致父母亲
致胡适
————————————————————————
徐志摩《落叶》
前天你们查先生来电话要我讲演,我说但是我没有什么话讲,并且我又是最不耐烦讲演的。他说;你来罢,随你讲,随你自由的讲,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这里你知道这次开学情形很困难,,我们学生的生活很枯燥,很闷;我们要你来给我们一点活命的水。这话打动了我。枯燥,很闷,这我懂得。虽然我与你诸君是不相熟的,但这件事实,你们感觉生活枯闷的事实,却立即在我与诸娇君无形不讲情理的怪物,他来的时候,我们全身仿佛被一个蜘蛛网盖住了,好不容易挣出了这条手臂,那条又nie住了。那是一个可怕的网子。我也认识生活枯燥,他那可厌的面目,我想你们也都很认识他。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附在各个人身上,他现在个个人的脸上,你望望你的朋友去,他们的脸上有他,你自己照镜子去,你的脸上,我想,也有他,可怕的枯燥,好比是一种毒亮剂他一进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皮肤就变了颜色,而我怕是离着生命远,离着坟墓近的颜色。
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几天西风到了,那天早上我醒人时候是冻着才醒过来的,我看纸上人颜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窝里的肢体像是浸冷水里似的,我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一颗枣树一有枯叶,一阵一阵有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发响,有的飞出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我因此就想起这西风,冷醒了我的梦,吹散了树上有叶子,它那成绩在一般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凄惨。那天我出门有时候果然见街上有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一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的命运,那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的闷,差不多发愁了。
因此我听着查先生说你们怎样的烦闷,怎样的干枯,我就很懂得,我就很愿意来对你们说一番话。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思想一不来的时候,我不能要他来;他来的时候,就比如穿一件湿衣,难受极了,只能想法子把他脱下。我有一个比喻,我方才说秋风的枯叶;我可以把我的比作树上的叶子,时期没有到,他们是不会掉下来的;但是时期到了,再要有风的力量,他们就只能一片一片的往下落;大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多数也许是已经没有生命了的,枯了的,焦了的,但其中也许有几张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就是红的,海裳叶就是五彩的。这叶子实用是绝对没有的;但有的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它们初下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了。除非你保存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叶一样没用,至多有时有几恨生命的颜色就是了。你们不爱的尽可以踩过,绝对不必理会;但也许有少数人有缘分的,不责备它们的无用,竟许会把它们捡起来揣在怀里,间在书里,想延留它们的幽澹的颜色。感情,真的感情,是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该应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与压住泉眼不让上冲,或是掐住小孩不让喘气一样的犯罪。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地地整体。但有时线索继续的产品,有破烂的地方去补,有涣散的地方去拉紧,才可以维持这组织大体的匀整,有时生产力特别加增时,我们就有机会或推广,或是加添我们现有的面积,或是加密,像网球板穿双线似的,我们现成的组织,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势力与破坏的势力,建议与溃败的势力,上帝与撒旦的势力,是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势力是天平一比着;他们很少的平衡的时候,不是这头沉,就是那头沉。是的,人类的命运是在一架天平上比着,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是我们集合的化身,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里满拿着分两的法码,一会往这头送,一会往那头送,地球尽转着,太阳/月亮、星星,轮流的照着,我们的命运永远是在天平线上称着。
我方才说网球拍,不错,球拍是一个比喻。你们打球的知道网拍上的那几根线是最吃重,最要紧,那几根线要是特别有劲的时候,不仅你敌时拉球、抽球,可格外的经用。少数特别的强的分子保持了全体匀整。这条原则应用到人道一,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力量加密,加强我们最普通的同情线,那线如其穿连得到所有跳动的人心时,那时我们的大网子就坚实耐用,天津人说,就有根。不问天时怎样的坏,管它雨也罢,云也罢,霜也罢,管它水流怎样的急,我们假如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网子,那怕不能在时间无尽的的洪流里——早晚网起无价的珍品,那怕不能在我们命运的天平上重重的加下创造的生命的力量强大?
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份。初起也许只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但这震动,不论怎样的微弱,就产生了极远的波纹;这波纹要是唤得起同情的反应时,原来的细的便并成了粗的,原来的合成了强的,原来脆性的便结成了韧性的,像一缕缕的苎麻打成了粗绳似的;原来只是微波,现在掀成了大浪,原来只是山罅里的一股细水,现在流成了滚滚大河,向着无边的海洋里流着。比如耶稣在山头上的训道还是有限的几句话,但这一篇短短的演说,却制定了人类想望的止境,建设了绝对的价值的标准,创造了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宗教。那是一件大事实,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再比如释迦 感悟了生老病死的地位,富与贵,家庭与妻子,直到深山里去修道,结果他也替苦闷的人间打开了一条解放的大道,为东方民族的天才下一个最光华的定义。那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奇迹。但这样大事的起源还不止是一个人心灵里偶然的震动,可不仅仅是一滴最透明的真挚的感情滴落在黑沉沉的宇宙间?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他的逻辑。有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掷在平面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他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论他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块石头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一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
但是我们自己的网子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张大了我们的眼睛,认明白我们周围事实的真相我们已经含糊了好久了,现在再不含糊的了,让我们来大声的宣告我们的网子是破的,坏了的,烂了的;让我们痛快的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我们的心窝为成了蠹虫的家,我们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大谎!那天平上沉着的一头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我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还是炮火呢?我们周围有一哭声与笑声,哭是我们的灵魂受污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魔了的狞笑,那比鬼哭更听的可怕,更凄惨我们张开眼来看时,差不多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哪一处不是叫鲜血与眼泪冲毁了的;更没有平安的所在,因为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还是躲不了你自身烦闷与痛苦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只要不是我的份,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是,我着重的说,怯懦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份,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是,我着重的说,懦怯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的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些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承认我们
——————————————————
天目山中笔记
“佛于大众中,说我尝作佛,闻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耶。”——莲华经譬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静。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静是不静的;但山中的声响,不论是泥土里的蚯蚓叫或是桥夫们深夜里“唱宝”的异调,自有一种各别处:它来得纯粹,来得清亮,来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里洗濯过后觉得清白些,这些山籁,虽则一样是音响,也分明有洗净的功能。
夜间这些清籁摇着你入梦,清早上你也从这些清籁的怀抱中苏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楼住更是修得来的。我们的楼窗开处是一片蓊葱的林海,林海外更有云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接受自然的变幻;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散放你情感的变幻。自在;满足。
今早梦回时睁眼见满帐的霞光。鸟雀们在赞美;我也加入一份。它们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潜深一度的沉默。
钟楼中飞下一声宏钟,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荡。这一声钟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夸;说思流罢。耶教人说阿门,印度教人说“欧姆”(O——m),与这钟声的嗡嗡,同是从撮口外摄到阖口内包的一个无限的波动:分明是外扩,却又是内潜;一切在它的周缘,却又在它的中心:同时是皮又是核,是轴亦复是廓。“这伟大奥妙的”(Om)使人感到动,又感到静;从静中见动,又从动中见静。从安住到飞翔,又从飞翔回复安住;从实在境界超入妙空,又从妙空化生实在:“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
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刹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花开,花落,天外的流星与田畦间的飞黄,上绾云天的青松,下临绝海的巉岩,男女的爱,珠宝的光,火山的熔液:一婴儿在它的摇篮中安眠。
这山上的钟声是昼夜不间歇的,平均五分钟时一次。打钟的和尚独自在钟头上住着,据说他已经不间歇的打了十一年钟,他的愿心是打到他不能动弹的那天。钟楼上供着菩萨,打钟人在大钟的一边安着他的“座”,他每晚是坐着安神的,一只手挽着钟槌的一头,从长期的习惯,不叫睡眠耽误他的职司。“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没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窍蒙充六根,怎么算总多了一个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师的谈吐里不少某督军与某省长的点缀;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贪嗔的化身,无端摔破了两个无辜的茶碗。但这打钟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岁在五十开外,出家有二十几年,这钟楼,不错,是他管的,这钟是他打的(说着他就过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错,是坐着安神的,但此外,可怜,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么异样。他拂拭着神龛,神坐,拜垫,换上香烛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干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转身去撞一声钟。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却没有失眠的倦态,倒是满满的不时有笑容的展露;念什么经;不,就念阿弥陀佛,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那一带是什么山,叫什么,和尚?”
“这里是天目山,”他说,“我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带的,”我手点着问。“我不知道。”他回答。
山上另有一个和尚,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读书台的旧址,盖着几间屋,供着佛像,也归庙管的。叫作茅棚,但这不比得普陀山上的真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着或是偎着修行的和尚没一个不是鹄形鸠面,鬼似的东西。他们不开口的多,你爱布施什么就放在他跟前的篓子或是盘子里,他们怎么也不睁眼,不出声,随你给的是金条或是铁条。人说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没有吃过东西,不曾挪过窝,可还是没有死,就这冥冥的坐着。他们大约离成佛不远了,单看他们的脸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么,一样这黑刺刺,死僵僵的。“内中有几个,”香客们说,“已经成了活佛,我们的祖母早三十年来就看见他们这样坐着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里的和尚,却没有那样的浪漫出奇。茅棚是尽够蔽风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鲜鲜的人,虽则他并不因此减却他给我们的趣味。他是一个高身材、黑面目,行动迟缓的中年人;他出家将近十年,三年前坐过禅关,现在这山上茅棚里来修行;他在俗家时是个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许还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说他中年出家的缘由。他只说“俗业太重了,还是出家从佛的好。”但从他沉着的语音与持重的神态中可以觉出他不仅是曾经在人事上受过磨折,并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泄漏着他内里强自抑制,魔与佛交斗的痕迹;说他是放过火杀过人的忏悔者,可信;说他是个回头的浪子,也可言。他不比那钟楼上人的不着颜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里逃来的一个囚犯。三年的禅关,三年的草棚,还不曾压倒,不曾灭净,他肉身的烈火。“俗业太重了,不如出家从佛的好;”这话里岂不颤栗着一往忏悔的深心?我觉着好奇;我怎么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时意念的究竟?
“佛于大众中,说我尝作佛,闻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耶。”
但这也许看太奥了。我们承受西洋人生观洗礼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积极,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让,把住这热虎虎的一个身子一个心放进生活的轧床去,不叫他留存半点汁水回去;非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决不肯认输,退后,收下旗帜;并且即使承认了绝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体的取决,不来半不阑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后退:宁可自杀,干脆的生命的断绝,不来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认。不错,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 例如亚佩腊与爱洛绮丝但在他们是情感方面的转变, 原来对人的爱移作对上帝的爱,这知感的自体与它的活动依旧不含糊的在着;在东方人,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灭,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迹的解脱。再说,这出家或出世的观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国,是跟着佛教来的;印度可以会发生这类思想,学者们自有种种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释,也尽有趣味的。中国何以能容留这类思想,并且在实际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个朋友差一点做了小和尚)!这问题正值得研究,因为这分明不仅仅是个知识乃至意识的浅深问题,也许这情形尽有极有趣味的解释的可能,我见闻浅,不知道我们的学者怎样想法,我愿意领教。
十五年九月[1]
编辑本段
作品赏析
题为《天目山中笔记》。既说“笔记”,则不一定与山有关,也有可能只因是在山中所记而已。不过,山也并非和该文主旨完全无干。天目山是浙西名胜,山色秀雅,多奇峰竹林。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天目作为名山,与佛与禅息息相关。作为题记的那段偈语,已经揭示了该文的用意。
劈头一句“山中不定是清静”:有松声,有竹韵,有啸风,有鸣禽——“静是不静的”,因为有“声”。有“声”,却不是俗世的营营嗡嗡,而是天然的声音,显得纯粹、清亮、透澈,使人心宁意远,这种不静反而是静。“声”之后写“色”——作者目所能及的一切:林海,云海,日光,月光和星光,并非纷扰熙攘的尘世,故而人处其中就会自在而满足。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体现出一点点徐志摩的境界了,实际上却依然距离那段有“佛”和“法音”等字样的偈文太远。直到他在对山中钟音做了一番颂赞之后感叹:“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钟这种单纯的音响,是对人的灵智的一种启示,它包容了万世万物,无始,亦无终,无声,亦无色。
该文的重心其实是写了与佛有关的两个人物,也就是天目山中的两个和尚。
文章由宏大微妙的钟声联系到了打钟的人。钟是昼夜不歇、片刻一次的,打钟的和尚也已不间歇地打了十一年,连每晚打坐安神也挽着钟槌;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痕迹或失眠的倦态,倒有自在的笑意;他不刻意念什么经,甚至也不识字,只知身处天目而对其他细节无所关心(徐志摩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问答)——如同佛陀在《经集》中所说:“那些超越疑虑,背离苦恼,乐在涅槃,驱除贪嗔,导向诸天世界的人,乃是行道的胜者。”这种“胜者”,也是“圣者”,那是他的(也是读者的)“俗眼竟看不出什么异样”来的。
无忧无欢,无智无聪,圣者证道于平常,这是徐志摩设想的佛家的最高境界,却不是他所能企及的。徐志摩所能企及的(也就是他能以身处之的)是另一种和尚:他不是如前一位平常而悠远的那种,也不是冥坐苦修、鹄形鸠面的那种。他住在茅棚里,家中尚有亲人,可能还曾有过妻子,至于向佛的缘由,他只肯解释说“俗业太重”;他人事上受过磨折、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禅坐和草棚难以压倒他的肉身,是个修道者也是个活鲜鲜的人;他也有可能是个忏悔者,是个回头的浪子,出家仅为了情感的解脱或自我痕迹的消灭——这如同徐志摩本人某种心境的写照——这样的佛徒更能使徐志摩产生感触。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二六年秋,后人并不知道当时徐志摩的心态。徐志摩一向被视为一个情感充溢、踊跃入世的诗人,这篇文章也表现出诗人心灵的又一层面。这还有另外一个例证,那就是徐志摩在其名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对佛音梵呗的顶礼和咏赞。
————————————————
作品名称: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创作年代:民国时期
作者:徐志摩
作品体裁:散文
编辑本段
作品原文
一
“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道骞司德的乡下,你或许碰得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颏,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照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的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我们读过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圣人,在卫撒克士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光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拂拭乱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节会的欢欣;或在济茨或雪莱或史文庞的遗迹,悄悄的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蒂闲(Theuophile Gautier)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The Inward Eye)里,像在他最服膺的华茨华士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绩,就是眼前最琐小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窥测的。从他那六十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六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傲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
二
上文是我三年前慕而未见时半自想象半自他人传述写来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国时,承狄更生先生的介绍,我居然见到了这位老英雄,虽则会面不及一小时,在余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不能不记下一些踪迹。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力乏是意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危峰时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自此我益发坚持我英雄崇拜的势利,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我去年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为泰戈尔、顺便我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但我只见着了哈代。
有伦敦时对狄更生先生说起我的愿望,他说那容易,我给你写信介绍,老头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带了你到道骞斯德林子里去走路,他仿佛是没有力乏的时候似的!那天我从伦敦下去到道骞斯德,天气好极了,下午三点过到的。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Max Gate的方向,我就欣欣的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邈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的一边剪草,我问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我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发一阵狗叫声,在这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
“哈代先生在家,”她答我的问,“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
我想糟了。“慢着,”我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末请候一候,”她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
她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该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她又笑了。“我怕,”我说。“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她可不咬,这儿生客来得少。”
我就怕狗的袭来!战兢兢的进了门,进了官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不曾出现,我才放心。壁上挂着沙琴德(Jonh Sargent)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记得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是朴素的,屋子也低,暗沉沉的。
我正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两人的脾胃相差够多远,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下来,哈代推门进来了。我不知他身材实际多高,但我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见他,我的印像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儿。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热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我说话,仿佛我的“开篇”辞他早就有数,连着问我,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的苍老的口音,“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前面那几句问话是用不着答的(狄更生信上说起我翻他的诗),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话,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的跼蹐,似乎在这天神面前我们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分占先似的!(啊,你没见过萧伯纳,——这比下来你是个蚂蚁!)这时候他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低着,眼往下看,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鬃也不全花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形三角,两颧像是特别宽,从宽浓的眉尖直扫下来束住在一个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窈的,往下看的时候多,不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代的”,是他那口连着两旁松松往下坠的夹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忧郁的深沉,他的口脑的表情分明是厌倦与消极。不,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额,着发的头角,你看了觉得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你感觉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觉着难受,他那皱纹龟驳的脸皮正使你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侵陵,雨雷的剥蚀,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什么时间与空间的变幻都在这上面遗留着痕迹!你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看他那下颊,谁说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的厌倦,他的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你不易相信他与我们一样也有喜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伛偻,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伛偻。喔哈代!
详见百科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