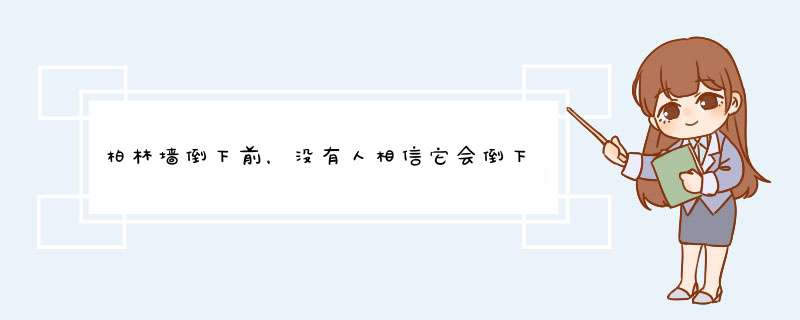
在德国的柏林有一道墙非常的出名,建于1961年的八月。
这是一道一开始以铁丝网为主要墙体后期又加固成混凝土为材料的墙壁,这道墙不仅仅将战败后的德国分裂为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更将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
这道墙更是成为了冷战时期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不仅仅标志着二战之后德国所经历的一段 历史 时期,更标志着两种意识形态在一个国家之中互相比较的最终结果。而在柏林墙倒下之前,所有人都不相信它有一天会倒下,而且是被建立的一方推倒。 它的倒下不光是标志着德国的统一,更标志着冷战的和平结束。
要说起柏林墙的建立,还得从二战之后德国战败开始说起。根据波斯坦协定,战败后的纳粹德国被美苏英法等四国分区占领。原本德国是四国共同管理,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社会 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冷战也开始爆发了。
美英法三国占领的地区与苏联占领的地区分裂成“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虽然属于同一个民族,存在于同一片土地,却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毕竟那个时代的美国国力确实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福利迅速让联邦德国人民的生活恢复了过来。
而眼高手低的苏联在当时虽然控制了大部分东欧地区,但是对于人民的生活并不关心,于是民主德国的人民过得穷困潦倒,水深火热。
这时很多民主德国的人就试图搬离“东德”,前往经济发达的“西德”去生活。 而这些搬离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有能力的手工业者。为了防止人才的外流和资本主义侵蚀,1961年8月13日的午夜,民主德国连夜修建了一个以铁丝网为墙基的隔离墙,彻底地切断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自由往来。
不仅如此,民主德国在四天之内将全长1695公里的柏林墙延伸到了整个东西德边界,封死了近两百条街道,同时又在50-100米外拆除了大量建筑,修筑了35米高的通电铁丝网,形成了一段以柏林墙为中心的“无人地带”。
为了能够彻底地控制住“东德”人民,在这段“无人地带”的周围更是修建了很多瞭望塔、碉堡、警戒桩。而在修建完柏林墙之后,东德最高***命令如果发现有人向联邦德国逃跑,就开枪射击逃跑者。
柏林墙伫立的这些年里,虽然客观上地减少了东德的人员流失。但是依然有非常多的东德人想尽各种办假证,挖地道,跳楼的办法穿过柏林墙,甚至有些波兰和捷克民众开车撞墙视死如归。
而在联邦德国的电视机中经常会报道在柏林墙的东面,有着一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德国人民,他们似乎被关进了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监狱之中。
由于柏林墙修建得非常紧急,很多家庭都来不及聚集在一起便被彻底分开无法相聚,爷爷奶奶需要隔着柏林墙眺望远处才可以看到自己的孙子孙女。想要翻越柏林墙的不仅只有东德百姓,更有很多在东德服役的士兵不满政府不顾民生的做法,转身翻过围墙进入西德。
一个叫舒曼的士兵穿越柏林墙之后回忆道: 很多父母即使近在咫尺都无法回到东柏林探望自己的子女,而那些想要团聚的家人往往就会被边境的士兵阻止。
很多东德士兵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地听从政府的指示,而是偷偷地将一些小孩和老人在上级军官不发现的情况下,放进了西德范围内。
而西德的士兵则在柏林墙的另外一面用床单接那些想要从墙东面跳过来的人,虽然有些人被接住了顺利地逃往西德,但是还有一些人因为身体原因和意外摔成重伤而去世。
被柏林墙隔绝开的并不只有东德和西德之间的人民,从长远的角度上看,柏林墙隔绝的是两种意识形态之下的人民生活。
联邦德国由于被美英法占领,迅速地形成了战后资本主义德国的发展模式。 虽然西德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通货膨胀,但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很多西德的年轻人开始接受反法西斯教育,一些有为的青年进入大学深造之后成为了医生、教师,曾经逃跑至西德的人们开始在这里安家落户过上稳定的生活。
他们可以住宽敞的房子,私有财产得到应有的保护,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稳定事业。但很多逃跑过来的人依然还惦记着那些被柏林墙隔绝开的亲人,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团聚。
而反观民主德国这一边,因为政府的管理无能,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人们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有些家庭只能所有人挤在破旧矮小的房屋里生活。有些有私产的百姓虽然有电视可看,但是电视节目里全是东德政府要求播放的洗脑节目。
政府利用控制精神的方法让东德百姓看联邦德国生活多么的窘迫,以防止有人再度逃跑到西德。 而这种赤裸裸的欺骗完全不能使东德百姓信服,更多东德百姓看到的是柏林墙那边的高级轿车,呢子大衣和建筑墙面上画着的可口可乐广告。
这其中也有一些东德政府的官员,虽然也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但是依然相信民主德国的政治正确。他们从内心中完全不愿承认自己羡慕西德那边优渥的生活,认为那样的生活是堕落的。
反而反复地鼓吹东德生活是规律的、严谨的。但事实上他们也知道柏林墙的那边普通人都过得比自己要自由得多。
而在柏林墙的两边的守备军队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西德这边虽然一段时间内也是有士兵站岗等安排,但是几个月之后,西德士兵则被换成了穿着制服的联邦警察。 而那些以前曾经巡逻在柏林墙外的士兵往往都扮演着给予逃跑者接应的角色。
而东德的士兵每天除了要被安排在柏林墙外的工事里站岗,还要加班加点地加固和修补被逃跑者破坏的墙体。而他们应有的劳动报酬往往都要受到上级军官的层层盘剥,他们甚至都不能养活自己的小孩和老人。
事实上在 历史 的角度上讲,德国的分裂根本不会有所长久。 因为纳粹德国时期,德国百姓也依然过着被管制和被洗脑的严苛生活,而他们认为东德政府在对他们做的正是法西斯的做法。他们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享受内心中真正的自由了,而这种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成为了推倒柏林墙的一股巨大力量。
1989年11月9日之前,东德为建国四十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在这个阅兵仪式进行时有非常多的东德人民进行自发的示威游行。
而这时的东德政府根本无力控制示威的民众,只能采取铁腕手段对示威者进行逮捕。而越是铁腕镇压,越是有更多的示威游行爆发。
到了九日当晚,众多的东德民众开始在柏林墙的检查站附近聚集,尤其是东柏林市民一次次的试探性地拿出身份证件向士兵询问出境的可能性。 而这时的东柏林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上千人了。 有些东柏林市民试探着跨入“无人地带”,看着对面也聚集着上万的西德民众。
东德百姓没有再惧怕士兵的枪口,勇敢地冲入了柏林墙。而这时柏林墙上的军官和士兵并没有开枪阻拦,反而是选择了沉默。有些边防军官甚至命令打开大门,让聚集在柏林墙两边的百姓见面团聚。 这是改变 历史 的时刻,柏林墙从这个时刻起在人们的心中彻底地倒塌了。
第二天的时候,东德政府新的***改变了以往完全铁腕的态度,允许东德居民有秩序地享有出国的自由。东德终于迎来了四十年以来赢得民心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一出台,几乎上万柏林年轻人便骑上了高墙。 用冲破牢笼的姿态彻底地推倒了无论是在城市中央还是人们心里的柏林墙。
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代表了冷战时代的来临和结束。冷战的源头来源于美苏之间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不可调和,一个强调民主自由,一个强调共产共和。
这两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孰对孰错,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之下的政府都不能不顾百姓民生。 用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为代价换取的政治正确,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更不是真正的共产共和。
二战之后的德国百姓其实早已对纳粹时期没有自由的生活麻木了。很多人认为柏林墙根本不会倒塌的原因在于,没人认为自由会真的属于自己。但是柏林墙的建立也彻底地激发了德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在人们的心中这道永远不会倒的束缚之墙其实早已经倒了。
闰年
《闰年》是安南德·图克尔执导,艾米·亚当斯、马修·古迪、 亚当·斯科特等主演的一部爱情**。影片讲述了女孩安娜为了嫁给完美男人,决定在2月29日这天向男朋友求婚,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邂逅了小旅馆帅老板德克兰,安娜的爱情究竟会走向哪里?
另名求爱吉日
德国旅游季节气候及穿衣指南
德国旅游季节气候及穿衣指南
最佳旅游时间
德国位于大西洋和东部大陆性气候之间的凉爽西风带,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到这里旅行,一般只要准备华北的适用服装就可以了。夏季的白天很热、晚上较凉,需要带上毛衣;冬季北部气候较暖湿,甚至比南部温暖。冬季(1月)平均温度在l.5—6度之间;夏季(7月)则在18—20度之间。一年四季均有降水。属于例外的是上莱茵河谷、上拜恩和哈尔茨山区。相比之下,上莱茵河谷更加温暖潮湿;上拜恩经常可以感受到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燥热风;哈尔茨山区山风刺骨、夏凉冬雪。
旅德穿衣指南
旅游衣物
夏 (6月7月8月)
夏季有时仍会像南方的炎热,但比较乾燥,早晚温差也满大的!
只趁暑假来德国游学或旅游的朋友:
七八月的天气虽然还算满暖的, 但有时也会出乎意料的突然变冷,
尤其是八月底的夏天,有时也会出现需要小毛衣的气温哦!
尤其像在山区的旅游地, 晚上多少都会有点冰凉冰凉的,
带件薄毛衣在身上,一路走回家才不会被冷到。
无论如何,请最好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薄毛衣或长袖衬衫,
至少绑在腰间或塞在背包不会很累赘的那种。
春秋(3月4月5月,9月10月11月)
春秋天的天气总是不稳定,请务必於出发前几天,查看天气才做最後的准备!
有时四月也会有20度的高温,像今年五月也从持续好几天的30度,
但通常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降到了15度的底温!
所以几件御寒的衣服还是不能少。
不过皮箱被一堆毛衣和厚重的大衣一塞,很容易就满了说~
所以呢,可以挑个二三件最暖的毛衣(不易透风的更好)。
若嫌外套太重麻烦,不妨换件可以挡风挡雨的风衣。
另外围巾也最好带著哦,爱漂漂的美眉可以带条丝巾,
这样行李也就不会太多太重ㄌ。
冬(12月1月2月)
德国的冬天,不骗你,真的很冷ㄋ。
不过好加在的是,几乎所有的室内场所都有暖气。
所以一进屋内,就会被烘得暖暖的。
因此在穿衣的方式和习惯,也要有适当的调整!
不然逛在室外被冻成雪人,跑到室内可能就被烤成黑人。
准备长期在德国的朋友:若来德国不是刚好冰天雪地的话,
这裏的建议是: 冬季衣服尽量都在德国购买!
若还是觉不放心,硬要带些 什麼,
那就先带件衣柜裏最暖的外套,再塞上二件最心爱的毛衣吧。
到了德国才买冬季衣物的优点是,除了种类和样式的选择性较高外,
价格方面也相对地便宜不少。 毕竟 有很多衣物在台湾仍是不容易找到,
因为气候差异大,穿戴的衣物也会有所不同。
而冬季来德国参展的朋友也别太担心!
若只是来参展,因为室内普遍都满暖的,
平时美美的套装还是可以派上用场哦!
简单来说,若一天在室外的时间不连续超过半个小时,
也就是只有搭车转车等(交通工具上也都有暖气),
那麼一堆不适合套装的毛袜雨毛衣都可以省下。
但若有室外的活动,像是还有二三天的观光行程,这种寒冬的装备还是不可少哦!
德国主要城平均气温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柏林 2 3 8 13 19 22 24 23 19 13 7 3
-3 -3 0 4 8 12 14 13 10 6 2 -1
汉堡 2 3 8 13 18 22 23 23 19 13 7 4
-3 -3 0 3 7 11 13 13 10 6 2 -1
法兰克富 3 5 11 16 20 23 25 24 21 14 8 4
-2 -1 2 6 9 13 15 14 11 7 3 0
慕尼黑 1 3 9 14 18 21 23 23 20 13 7 2
-6 -5 -2 3 7 10 12 11 8 4 0 -4
注:上格为日间平均气温,下格为夜间平均气温。 单位:摄氏度
以上四大城市均有一定代表性:柏林位于东部,汉堡位于北部,法兰克富位于中西部,慕尼黑位于南部。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我快速的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多少时间并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着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道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法和发音的精华。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去过一个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黑面包泡汤。
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朋友,当时,我的男友是位德国学生,他在苦写论文,一心将来要进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变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说了。
在德国,我的朋友自律很严,连睡眠时枕下都放着小录音机,播放白日念过的书籍。他说,虽然肉体是睡了,潜意识中听着书本去睡,也是会有帮助的。他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我们见面,也是一同念书。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
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外总也大雪纷飞,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继,经济拮据的压力。总是想到父亲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喝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总是什么物质的欲望都减到只是维持生存而已了。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休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不在我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
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微微的笑着。他,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
就那么走到外交部去,一面走一面问人,路上有围着白围巾的青年,一路跟着要换西柏林马克或美金,随便多少都可以。我不敢睬他,只是拒绝得难过。
都快下班了,才问到签证的柜台,也不存希望给或不给,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个离别时叫人落水的眼睛里。
是东德,在东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种梦境,很朦胧的倦和说不出的轻愁。那本护照——台湾的,就如此缴了上去。
看护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两下,就向身后的同事叫嚷,说:“喂!来看这本护照呀!蒋介石那边来的。”人都围上来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双眼睛里。随便人们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蒋——介——石——嗯。”那位中年人叹了口气。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当他说到这句话,我就自杀似的冲出了一句:“蒋介石,我还是他女儿呢!”“真的?!”对方大叫起来。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陈、陈、陈……。“你说老实话哦!”他说。我不说话,只是笑了笑。那双眼睛,今朝才见便离了的眼睛,他说我真美丽,他用英文说,说成了他和我的秘密还有终生的暗号。
“你姓陈,他姓蒋,怎么会?”又问。
我反问他:“请问给不给经过东德的签证嘛?”他说:“给、给、给……。”急着哗一下盖了章,就成了事。
隔着柜台,我竖起了脚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你真美,谢谢你。”然后,走了。
东柏林在展越南战争的照片,进去看了一下。那张,美军提着越共的头,踩在无头尸体上,有若非洲猎象猎兽的成就感,在那个大兵的脸上开着花。没有再看下去,觉得自己是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去饭店吃了一顿鱼排,付帐时,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种笑,使我付出了不是过境时换的当地钱。有二十块美金,给了十块,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没有等找钱,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经过一家书店,看见齐白石的画,我一急,进去了,要人窗内拿下来,发现是印制的,不是原墨,就谢了走开。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着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东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点时已经暗了。可是这边的城没有太多灯光。问到了出关回西柏林的地方,关口很严也牢,是九曲桥似的用曲折墙建出来的,我猜是怕东边的人用车子来闯关而设计的。
他们不给我回去,一直审问,问我那张白色的通行证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会身上又有一本台湾的护照藏着。又问来时身上报了二十美金,怎么换了五块美金的当地东德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块一张。我说吃饭时付错了。问是哪一家饭店,我答谁记得路。
他们不给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说:“你们自己发的通行证,去问放我过来的那个关卡。去问!打电话去问呀!好讨厌的,也不去解决。”
不知过了有多久,我弯弯曲曲的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关,门口站着来接的,是中午那个以为已经死别了的人。他在抽烟,看见我出来,烟一丢,跨了一步,才停。
“来!我带你,这边上车,坐到第五站,进入地下,再出来,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轻轻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经过的军人,都向我们敬礼——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车站了,不知什么时刻,我没有表,也不问他,站上没有挂钟,也许有,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一辆又一辆飞驰而过的车厢,我只看见那口井,那口深井的里面,闪烁的是天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没有,是呢绒草绿军装。我在拚命发抖,他也在抖,车站是空的了,风吹来,吹成一种调子,夹着一去不返的车声。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风吹过来,反面吹过来,吹翻了我的长发,他伸手轻拂了一下,将盖住的眼光再度与他交缠。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后一班,你上!”他说。我张口要说,要说什么并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着还想说,他又推我。这才狂叫了起来——“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请你请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么也没有,西柏林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怎么上车的不记得了。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的被带离,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直到火车转了弯,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来,被送进医院已是高烧三日之后才被发现的。烧的时间头痛,心里在喊,在喊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个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医生只有早晨巡视的时候带了一群实习医生来,探病的人一周可以进来一次。我的朋友念书忙,总是打电话给护理室,叫**来传话问好,但人不来。
医院的天井里有几棵大枯树,雪天里一群一群的乌鸦呱呱的在树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总是将头抵在窗口不说什么。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说话,走上来,指着窗外对我说:“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的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