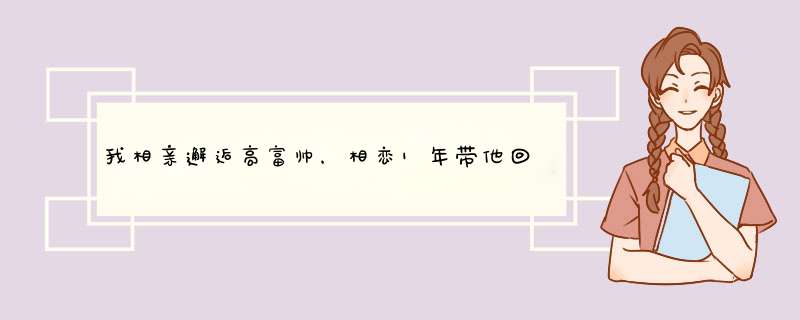
1
离过年还有两个月,母亲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虽然很想念父母,但家是不想回的,毕竟已经三十岁还没结婚的我,很清楚自己的下场:问不完的问题,相不完的亲。
我还知道,有人说我“读那么多书干什么,还不是也找不到老公。”这个世上就是有些怪人,他得不到的,偏偏你有,他就一定要把那东西贬得一文不值。
母亲又来了电话,说已经替我买好往返的机票,她劳心费神地盼女儿回家一趟,我要再以值班为借口搪塞,就太对不起老人了。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见到叔姨婶子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只回来一周,相亲的安排已经到九天以后。我说相亲实在是撞大运的事情,去一百次也不见得成功一次,还不如我自己慢慢找。
因为这句话,老父的血压都气得升了好几回,要是在旧社会,他一定要骂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亲拿着降压药告诉我,他血压高得厉害,让我千万不要再气他,不然要到医院过年了,我只得答应去见见那些人。
第一次相亲定在本地的五星酒店,母亲怕我偷偷不去赴约,非要陪着我。大冷的天,我一边心不在焉地答着对方的问题,一边担心母亲会不会冻坏。
好不容易应付完两个相亲对象,结了账准备回家。是了,两位男士都对我说:“齐**,不如AA吧?”八十一杯的咖啡,我喝了两杯,另外还单点了一碟糕点,都是自己付钱。我虽然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但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心里不大舒服。而且那声“齐**”叫得也有点不伦不类。
母亲在酒店门外等我,我一出门,她就裹着羽绒服迎了上来,屋里有暖气,外面却是很冷的,她呼出的气成了一片白雾。
“怎么样,都见了?”她用了讨好的语气。
我回想起把方糖撒了一桌子的A君,吃我糕点还吧唧嘴的B君,人生最大的痛苦也不过如此:你明明看不惯,却还要文质彬彬,陪他把这场戏演完。
她见我不说话,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闷声把它呼出来。我知道她的担心,她和父亲四十多岁才生的我,如今我三十了,他们也年逾古稀,像所有父母一样,他们不放心我,害怕自己先走之后,没人对我嘘寒问暖。我没做过母亲,但这种心理想必是大多人都能体会的。
她也正是抓住我的这种歉疚,刚要进家门时突然来了一句:“就见最后一个,明天,德顺酒楼,小伙子很不错的。”
我来不及答话,她就闪身进了满是暖气的房间,速度快得让我不相信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哎呀,冷死了,那几个对象,我一个也看不上。”她脱下厚厚的羽绒服,代我向父亲解释,却把相亲不成功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不是女儿的错,你不要总是骂她眼高手低,是我看不上的。
楼道里吹过一阵冷风,我鼻子酸得痛了一下。
2
第二次相亲,母亲嫌我素淡得像清汤挂面,一点荤腥也没有,“小姑娘去相亲,总要收拾得花枝招展,你看看你!”她不满地把我的黑白套装扔在床上,非要我穿一条大红色的连衣裙。
“妈妈,我又不是去拜年,再说了,难道相亲就非得红一块绿一块的?”我还是套上白衬衫,我当然算不上小姑娘了,不过就算是老姑娘,也不必去迎合别人的审美,自己舒服就好。母亲那天在酒店外等我,冻出了感冒,我不再让她跟着去,换好衣服就出了门。
这次的对象叫李牧,光看样貌可以打八十分:浓眉大眼,笑起眼角有皱纹,身高估摸在一七五,我偷偷看了他的肚子,没有啤酒肚,又是加分项。不过可惜,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
“李牧吧?我叫齐实。”我抻一抻外套,坐在他对面。他竟然还系了领带——藏青西装,和衣服一色的领带,“你来推销保险吗?”话一出口,我忍不住想自己掌嘴,母亲说我嘴太毒,得罪人了都不知道。
好在他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对,我是李牧,你二姨妈的表妹的侄子的表弟。”我被绕得晕乎乎,他又问,“你怎么会叫齐实?”
很少有人会对我的名字感兴趣。我告诉他,我生在春天,那时家后面有一株桃树,开了很多花。我父亲教语文,见了桃花,想起诗经《桃夭》里的“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描写草木结了很多果实,生机勃勃。我家姓齐,就取了这个名字,而且父亲也希望我做人实实在在,不要玩些空的虚的。
他认真听我讲,作出一副沉思的样子,过了好半天,我以为他会说“叔叔真博学”之类的,没想他说:“你爸爸脑洞真大,要是我看见桃花,估计只能想起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心里已经把他骂了千百遍,面上还是要客客气气地夸他幽默。顺便问他一句:“你条件这么好,可以找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啊,为什么来相亲呢?”来之前我了解过他的基本情况,三十三岁,在本地一家大型国企任项目部经理,在黎州大龄未婚青年圈应该很抢手。
他答:“巧了,我偏不喜欢年纪小的。对我来说,跟你一样年纪的更有味道,难道你喜欢年纪小的?”
损我一顿,又将我一军,这个李牧不是善茬,算是棋逢对手,不过他的毒舌更隐蔽,更有杀伤力,我不得不提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好在接下来我们只随便聊了聊各自的生活爱好、本地房价涨幅之类的话题,没有再短兵相接。
离开的时候,他礼貌地起身,留了我的电话,“有机会再见。”一句客气话,我才不会当真,毕竟我就要回C市上班了。
3
回C市那天,父母送我去机场。
在车上,母亲一直欲言又止,我问她什么事。她说相亲的B君看中了我,想和我再相处一下。我没有拐弯,直接告诉她,我和对方不太合适。她抿着嘴,像有话要说。
父亲开了口,“不合适就再找找,有中意的再说。我们希望你快点结婚,不过也不至于让你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到底是父母最亲,知道我的心事,也舍不得我吃苦。
母亲不死心,又问我:“那天那几个,就没一个看上的?”
我摇摇头,却想起了毒舌李牧,不过见面的可能性也不大了。飞机越升越高,我想象父母在视线中变成两个小黑点,再模糊不见。
春节前公司堆了一摊子事,潇洒过后面对整桌的文件,完全不知从哪里下手,脑子里像有几百张车子引擎轰轰作响,上演“速度与激情”。好不容易熬到快下班,手机上一个陌生号码来电。
归属地显示是黎州,我怕是相亲的B君打来的,犹犹豫豫不敢接,同部门的小张受不了一直响,替我接了电话。她嗯嗯啊啊地答着,笑嘻嘻的。末了把手机递给我,告诉我有人约我吃饭,男的,她已经替我答应了。我白她一眼,怎么没有问过我就答应。她说对方认识我,又说,“齐姐,不是我说你,成天两点一线的,多没劲,你也要丰富一下业余生活!”
我无奈地叹气,年纪不尴不尬的,真糟心。年纪大的说你心不定,年纪小的说你心态老。
没想到是李牧来的电话。我和小张刚走出公司大门,就见一个人朝我招手,又叫我的名字。小张眼尖, 轻轻捅捅我后背,“齐姐,蛮不错的,一定抓住机会。”
李牧说公司派他到黎州出差,他刚下飞机,举目无亲的,想起存了我的电话。他还是穿了藏青色的裤子,搭黑色羽绒服,总算没系领带。我因为小张刚才那句话,脸红了一路,好不容易镇定下来,带他去附近的咖啡厅。
“又喝咖啡?”他笑了一下,“我以为不用这么正式,再说了咖啡也喝不饱。”
其实过年相亲连喝了几天咖啡,喝到我反胃。本来选择咖啡,是觉得他这样所谓的青年才俊,应该喜欢那种地方。听他这样说,我放了心,七弯八拐地带了去了街边的小馆子,一口气要了三斤麻辣炒螃蟹。
李牧左手擦着鼻涕,右手拿着螃蟹钳子,吃得津津有味,“齐实,没想到你这么爱吃辣,不过真好吃。”他吃一口螃蟹,又咕嘟嘟灌下一口柠檬水。
酒足饭饱,他说正好他住的酒店离我家不远,可以陪我一路散步消食。大概是吃人嘴短,他语气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戳人短处,他问我:“听顾阿姨说,你挺不错啊,怎么现在还单着?”
这问题简直没法回答,无非是喜欢我的我没看上,我中意的却不爱我,但我还是好脾气地答了:“小时父母管得严,上了大学还不许我和男同学单独出去。念了研究生他们开始着急,希望我最好一毕业就能带对象回家,不过空缺了二十多年的恋爱经历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补好,”我是善于自嘲的,“研究生时候喜欢过一个高年级的,死去活来那种,拼了命对他好,他说我太幼稚,不是他爱的那一款。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有了结婚对象。”
他笑我:,“看不出你还是个痴情种子。”
我瞪了他一眼,一腔真话都喂了狗,掏心掏肺告诉他,他竟然又来打趣我。不过他也坦白,说被女朋友甩过,还不止一次,分手原因无他,都是说他不够浪漫。他朝我抱怨:“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谈恋爱不看人家是不是真心,总在乎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我不以为然,活该他至今单身。
4
一个月后,李牧所在的公司计划在C市设立分支机构,派他先来打头阵,我和他相处的机会逐渐多了。
开始他还会找理由约我吃饭,比如“碰巧到你们公司,吃个饭吧。”,或者“今天哪里又打折了,我有优惠券,晚饭约不约?”
同事丽姐碰到过他几次,明明一直傻头傻脑在楼下等着,等到我下了楼,却装作才到的样子,冒出一句“好巧啊这里都能遇到你”。
丽姐对我说,这样又呆又傻又贴心的男人不好找,要赶紧把握机会。我点头,觉得丽姐的“又呆又傻”用的实在恰到好处。
我在玻璃窗边往下望,他已经在楼下站了五分钟。丽姐催我赶快下去,“又降温了,外面气温这么低,当心他感冒。你先走吧,老板来了我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磨磨蹭蹭下了楼,朝他的方向走去。他一脸茫然地站在车边,我叫他,“李牧。”
他嘴变成“o”型,好像下一秒就要说“好巧”。我打断他,“楼上就看到你了。”他尴尬地笑了一声,从此之后约我吃饭再没有找过理由借口。
不过老实讲,和他吃饭还挺自在。比如他和我一样无辣不欢,也喜欢在吃烧烤时候配上一罐生啤,吃不惯孜然,偏爱咖喱。
李牧的话很多。他去过很多地方,会跟我讲茶卡盐湖亮得一面镜子,吴哥窟古老苍凉,飞天壁画的仙女看起来真的像要飞到天上……
但毒舌还是万年不变的——“少吃一点夜宵,三十多岁的人了,消化不好,胃要痛的。”“降温了要多穿衣服,穿这个牛仔裤,破破烂烂好像叫花鸡。”“你真白,不过好像除了白就没别的优点了。”
很多次都被他气得想掀桌子,但一想到我还要有求于人,不得不做小伏低:公司要接一个市政绿化项目,老板让我制作标书,美其名曰要让我多锻炼。可怜我虽在公司干了几年,做的都是行政工作,写年终总结什么的倒是在行,标书却从没有接触过。
一次向李牧抱怨,他满脸不在意地告诉我,做标书,他是行家。我半信半疑,直到他头头是道地讲出“投标邀请”“投标报价”之类的名词来,才相信他与我相比,确实是内行。
“要我帮你可以,”他狡黠地笑,眼角皱出几丝纹路,配了他略显沧桑的脸,还怪有一种男神驾到的感觉,“不过,得请我吃一个月的炒螃蟹。”
一斤炒螃蟹一百块,就算每天只一斤,一个月还是要三千块,这笔买卖太不划算。他告诉我,“不行你找外面的人做, 一万起价,还没有我这么专业。”我只得认怂。
于是每天下班之后,陪他吃一盘炒螃蟹,便到我家弄标书。平时看着他不大靠谱,做起事来倒很认真。他先找了几个标书的模本给我,由我根据公司基本状况写出初稿,他再来帮我修改,“资质最好写清楚吧。”“价格方面还要再跟老板汇报一下。”“你这个格式用的根本就不对!”
我耐心不够,有时针对他的修改意见,我只随便改动一两个字就再返给他,想着让他修改,却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也只得一概全收,点头哈腰说我再改,态度端正得像个挨东家训的狗腿子。不过好在他吃了五天的麻辣螃蟹之后总算说再不去吃了,让我省下一笔钱,还不至于身体、心灵和钱包一起受创。
5
临近投标,标书还在修改,我心里很是紧张。李牧说我偷懒,如果早弄好了现在就没必要如临大敌。无奈我在写标书这事上确实废柴,他只有亲自操刀。
熬夜是少不了的,而且李牧一到晚上就说肚子饿,点外卖他也不要,说自己胆固醇高,适合吃点清淡的,比如可以吃我煮的面。在那一阵子,我把我会的夜宵都做了个遍:番茄鸡蛋面、酒酿汤圆、皮蛋瘦肉粥,李牧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膨胀起来。
挑灯夜战之后,我早睡得昏天暗地,李牧就在客厅眯一会,再送我去上班,又被同事撞见,大家都是过来人,丽姐常打趣我,“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开始还会脸红,后来干脆不解释了,说多了倒像此地无银。
李牧对于这些误解好像也全然不觉,不知道是迟钝,还是不在乎。丽姐有一次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苦笑一下,说走着看。其实心里想的是:明明看起来已经“同居”,两人却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好不容易挨到开标那周,标书基本做好,成与不成,也不是我能说的算了。
大概是那两天熬夜太多,我身体不大舒服,右下腹时有疼痛,还伴有恶心、发热等症状。丽姐好心递来感冒药,又悄悄问我是不是有了,我脸一黑,我又不是圣母玛利亚。
李牧也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想本来也不是大病,挨过投标了再说。
投标前一晚,我吃了几颗感冒药睡下。大概凌晨三四点,右腹部传来一阵刺痛,本来感觉痛点在右边,过一会上下左右都疼了起来,疼得冷汗直往外冒,眼前灰蒙蒙一片,脑子也是混混沌沌,竟然想不起拨急救电话。
又挨了一会,疼痛稍微过去一些,这才拿起手机,电话里传来李牧带着瞌睡的声音,巨大的疼痛之下我已经完全忘了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李牧叫我不要挂电话,他这就赶来。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传来门铃声,我几乎是半走半爬给李牧开了门,他问我哪里不舒服,我答不上来,只一个劲说肚子疼。再醒来的时候,我人已经到了医院,李牧正捏着我的手给我按虎口。“疼。”我告诉他。
“还很疼吗?”他伸手来为我擦汗,很着急。
“你捏得我手疼。”
医生说我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又问家属来了吗,李牧松开捏着我的手,告诉医生他就是家属。手术之后,李牧又像个大妈一样每天给我送水果和鸡汤。直到医生说,“哎,那个家属,你不要给她吃了,快让她下地走动,不然伤口粘连了麻烦。”
住了几天院,李牧和我对医生把他默认为我的“家属”都心照不宣。出院之后,没有什么告白之类的环节,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但手术时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事后还是经常笑话我,“你知道那天电话里你跟我说什么吗?”——“不记得了。”
“你说李牧救命,我要死了。吓得我跑到你家,见你穿着一套灰不溜秋的睡衣靠在墙上,一头的汗,像一只刚被拔毛的乌骨鸡。”
6
多亏上次标书做得不错,临近中秋,老板开恩,准了我五天年假,我也得以回家陪父母过节。
我问李牧要不要一起回去,他说他父母四十周年结婚纪念,两人飞去了海南度假,丢下他这个拖油瓶,他在电话里幽幽道:“我不回去了,孤家寡人的没意思。”
我说可以去我家,正巧让他认认门,他眉开眼笑说马上订机票。我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
因为有李牧陪着,父母没有到机场接我。出租车刚进小区,李牧就拉着我直直往前冲,我问他,“你又不知道我家,瞎走什么?”
他这才顿悟般停下步子,提着大包东西跟在我身后。李牧买了些桂花糕、青团,还有C市特产的甘蔗酒,都是我父母爱吃的,想必来之前也做足了功课。
母亲见我和李牧,一脸的惊喜,见他提了许多东西,又嗔怪:“这孩子,提这么多东西来,多生分。”语气熟稔地像老早就认识,我疑惑了看了看李牧,他却换了拖鞋陪父亲下象棋去了,还真是自来熟。
母亲做事利索,饭菜很快上了桌。我到客厅叫父亲和李牧,两人早丢了象棋,看电视笑得前仰后合。我父亲一向待人冷淡,不知道李牧用了什么法子,能让老头子高兴成这样。
饭桌上,我本来还担心李牧第一次来我家有些拘谨。谁知他比我还像主人,一面逗我父母笑,一面给我夹菜盛饭,明明才第一次见面。
我问李牧,他说那叫缘分,第一次和我父母见面就能相谈甚欢。我肯定不信的,李牧走后,便问了父亲。
父亲翻箱倒柜地找出一张照片,“先说好,你别生气。”(小说名:《不浪漫情话》,作者:触茶。来自:每天读点故事,看更多精彩内容)
隋与初唐时期,描绘楼台宫观是当时的风尚。山石树木作为楼台宫观的配景,相应受到重视。当时擅长人物的画家,大多擅长此道。其中展子虔因有作品《游春图》传世尤值一提。
展子虔(550~604年),渤海(今山东阳信)人,历北齐、北周入隋。《游春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卷轴画,画贵族游春情景。先用墨线勾勒,然后重着青绿,山脚处饰以金粉,金碧辉煌。在构图上则予人以“远近山川,咫尺千里”之感。
较之《洛神赋图卷》中非自然排列的山川树石,《游春图》的进展似乎只是把人物放到作为背景的山水中去,这一步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南朝山水诗人走进自然、亲近自然的欲望,这一步的实现是难以想像的,而这一步的迈出几乎完成了中国山水画自然主义历程的一半,即完成了山水画在空间关系上的错觉处理。此后的三个世纪,自然主义的山水画才完成了它的另一半路程,即通过皴、擦、点、染的综合性程式技法使隋唐空钩无皴的山水视之有质地感。
有学者从画中人物幞头、斗拱和鸱尾不合隋制,推论《游春图》底稿应在中晚唐以后,而摹本则不早于北宋中期。
晚唐人张彦远曾评价魏晋以降至唐以前的山水画为“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又论初唐山水画为“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宛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可知直至初唐,山水画技法仍很稚拙,尚不足以真实地描摹出自然景观。因此《游春图》能否出现于隋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过,初唐人彦悰《后画录》(此书真伪仍有争议)称赞隋代山水画家江志为“模山拟水,得其真体”,似又揭示了隋代画家已从对自然对象的观照中,逐渐获得写实造型的能力。
如何缩小把握自然真实与技法稚拙之间的距离,是继展子虔之后的唐代山水画家的目标。唐代山水画家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其一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继承并完善自六朝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画风偏重于装饰性;其一是以吴道子、王维、张璪为代表,借用人物画中表现三维空间的线条技巧,把山水画从二维空间画面上理想化的楼台山石主题转换到创构有三维空间的真实自然上。
李思训(651~716年),唐代宗室,开元初年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故后世称为“大李将军”。善画青绿山水,虽从展子虔出而更显工谨细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李思训山水:“湍濑潺潺,云霞漂渺。时睹神仙之事,杳然有岩岭之幽。”元汤垕《画鉴》也说“展子虔画山水法,大抵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可见其画虽偏于山水方面,但画中人物仍多,尚不脱六朝古态。
另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天宝年间,李思训曾为唐玄宗画一掩障,使玄宗“夜闻水声”。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没有活到天宝年,因而无法据此而证实李思训是否已具备如此高超的写实技巧。不过,这则传说语虽玄虚,但也表明了唐代人对掌握自然真实的渴望。
传为李思训的作品有《江帆楼阁图轴》。画高岭长松,山路楼阁,数人乘马或步行游赏;山外江天寥廓,风帆飘缈。山石用细笔勾勒,青绿重彩设色,富于装饰趣味。有学者认为《江帆楼阁图》山水树石风格与敦煌壁画中晚唐画相似,画中人物戴中唐以后幞头,建筑也似晚唐作风,表明此画是晚唐作品。
其子李昭道,职虽未至将军,但世人因其父称亦谓之“小李将军”。李昭道的画法大约承其家学而更加精致。《历代名画记》称“变父之法,妙又过之”。《唐朝名画录》称“昭道虽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慧,笔力不及思训。”
传为李昭道的作品有《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入四川事,画中悬崖峭壁,石磴曲盘,树间苍滕萦绕,行人策骑登山,画法空勾无皴,青绿设色,极为稚拙,颇类唐人山水作风。此画虽难以肯定是否李昭道所作,但此画属于二李青绿山水画风,仍可作为二李山水画艺术的参考。
从与大小二李同期的墓室壁画中的山石画法来看,初唐时期的山水画表现方法多以中锋线条勾勒轮廓,然后填色,墨的运用尚未被重视。这一种勾线填色的青绿山水是依俯于人物技巧发展而成的一种高古风格的山水画形式,它在隋和初唐已逐渐成熟,而李思训、李昭道则使之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以释道人物著称的吴道子,在山水画方面也创造出以线为主的写意画风。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天宝年间,李思训与吴道子同在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李“累月方毕”,吴“一日而毕”,李没有活到天宝年,此事绝无可能,但朱景玄记录此则传说,正好也说明了李、吴二人画法上的不同。
张彦远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思训、昭道)”。吴晚于李,“始”、“成”之说,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张彦远的原意,可能说的是水墨淡彩创自吴道子,青绿技法至二李才臻完善。
吴道子的“山水之变”不同于二李重彩设色、富于装饰趣味的青绿形式,而是以线条为主要刻划手段,色彩只作为补充手段。吴道子神采飞扬、灵动多变的线条,复加之设色简淡等技巧,较之青绿技法,更为真实地表现出山石的结构与气势,从而为山水画获得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也为此后水墨山水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当然,吴道子虽突破了自六朝以来青绿重彩的体格,但他并没有彻底完成山水画的变革任务。五代山水画家荆浩说他“有笔而无墨”,可知他的山水画,只有线条,虽表现出了山水的气势,即所谓的“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但山水的质感刻划仍有欠缺。这有待中晚唐及五代山水画家完成。
王维(698~759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历官尚书右丞,故称“王右丞”。盛唐著名诗人,亦工书画。其作品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誉,惜无真迹传世。
王维的山水画可能同时受到吴道子与李思训的影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评之“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说他“笔力雄伟”,吴道子的笔法正以“雄壮”见称,这都可视作他承受吴道子画风的证据。画史上又载王维画“皆如刻画”,显然又有与李思训相近之处。
王维在画史上的重大影响是他的“破墨山水”。所谓“破墨”,即以墨加水调成浓淡不同的层次,用以渲染,代替青绿设色。而水墨渲染在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此后皴法的出现。就作品而言,王维的山水画在唐代的品评并不甚高,较吴道子、李思训为下。到了宋代,文人绘画兴起,因为王维的山水画笔意清润,诗画合一,与当时文人趣味若合符契,于是开始备受推崇。到了明末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说,更是把王维尊为“南宗”始祖。应该说,王维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艺术成就,而在于他的艺术思想。王维是唐代山水画家中诗名最大又通禅理的一个,且王维半官半隐的身份,后世文人画家大多类之,正是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了共同的审美情趣。
盛唐时期既是依靠人物画技巧发展起来的青绿山水的顶峰,同时也是山水画寻找自己独立的语汇的开始。前者应是沿续六朝山水画遗风的结果,后者则是吴道子等人在人物画技巧的变革中产生。中晚唐的山水画家正是在此起点上进一步探索山水画的独立技巧。
中晚唐山水画家有张璪、项容、王墨、朱审、王宰、刘商等。其中以张璪、项容、王墨最为著名,而张璪在唐人心目中甚至比王维更高。
张璪,字文通,吴郡(今苏州)人。张璪以画松最为著名,能双管齐下,且生枯各别。据《历代名画记》称,张璪作画“惟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这种画风显是承继了吴道子豪放奇诡的作风。但他较吴道子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善用水墨,五代荆浩《笔法记》称张璪的画“真思卓然,不贵五彩”,可见张璪能用墨法。
张璪的画法似受吴道子、王维等人的影响,但当同期另一画家毕宏问他师授时,他答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据说毕宏听了这话,竟为之搁笔。张璪著有《绘境》一篇,但已失佚。项容以善水墨山水著称,五代荆浩曾言“项容有墨而无笔”,可能指的是项容用墨太过放纵,虚化了线条,导致画作缺乏骨气。王墨是项容的学生。他与画史上言王默、王洽者实为同一人。据《唐朝名画录》称:“善泼墨山水,时人故谓之王墨”,又记其“凡欲画图幛,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
从文献记载看来,唐中叶后,山水画在构图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南北朝时期表现山水只有左右横向布置的远近之别,而无前后纵深区别远近的构图形式转向在有限的画幅内展示无限深邃的山水境界,即所谓的“咫尺重深”。
由于此期恰是水墨山水勃兴之时,过去常将“重深”理解为与水墨画有关的一个形容词。实则“重深”应是表现山水画深远景象之词,它与构图关系密切。“重深”一词屡见于中唐之后山水画作品的描述之中,可能说明此时山水画家已完全掌握在画面上表现深度的方法,有意识地向纵深方向开拓画境,开创了山水画发展史上的新局面,使山水画从“咫尺千里”跨入“咫尺重深”的阶段。
唐代石窟与墓室壁画中保存了唐代山水画的部分实物资料。如莫高窟332窟南壁《迎佛图》(武周时期)、217窟南壁法华经化城喻品(开元初期)、172窟东壁文殊像(天宝晚期)所画山水,陕西富平出土的墓葬六屏山水壁画(盛唐时期),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一件唐代琵琶上所绘两幅山水人物画,均可见出当时画家对表现画面深度已很娴熟。
唐代中晚期水墨山水画的发展历程,因实物资料欠缺,更多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进行推测,推测结果正确与否,实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大致可以认为,中国山水画技术与创作方法的两大问题“势”(即表现空间深度)与“质”(即表现山石质感肌理),“势”的问题在唐代已基本解决,唐代山水画已克服了早期图案式造型处理,更趋于写实。而“质”的问题,尽管青绿山水已取得极高成就,水墨山水也正逐渐兴起,但基本上还是线条勾勒的画法,这一问题仍需留待五代解决。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