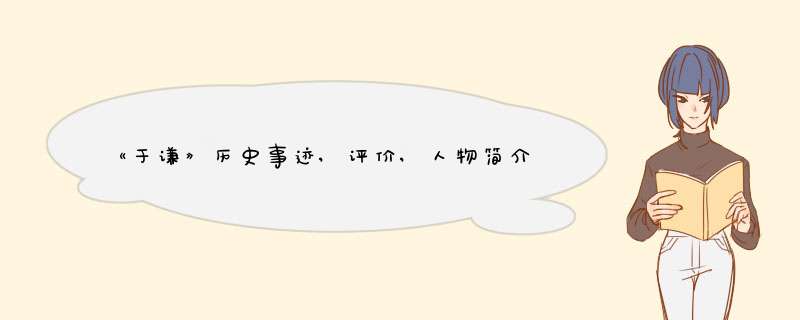
《于谦》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举进士。宣宗即位(公元1425年),授御史。谦才智超群,谈吐鸿畅,宣帝每倾听之。都御史顾佐,待僚属甚严,独特尊重谦,以为才能胜己。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成祖第二子,宣宗叔)谋反,宣宗亲征,至乐安(今山东惠民县),高煦惧而出降。宣宗命谦数其罪。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地战栗,口称万死,宣帝大悦。后,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又上书言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宣宗知谦可大任,时正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乃手书于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谦到任,即轻骑遍历所部,访问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上书言之。河南近黄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设长,责以专事修堤。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镇将私恳田,谦尽夺之为官屯,以资边用。在位九年,迁左侍郎。
初,三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掌政,素敬重谦,凡谦所奏,朝上夕批。至是,宣宗、三杨相继去世,太监王振用事。有御史姓名类似于谦者,曾忤振,振恨之。谦入朝,荐参政王来代己,通政使李锡根据振之旨意,劾谦以久不升迁而怀怨望,擅举人自代,奏请处死。已而振知其有误,释之,降为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吏民伏于皇宫前上书,请留谦者上千人,诸王亦为之请,复命为巡抚。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复为兵部左侍郎。
次年七月,蒙古瓦剌部也先入寇大同等地,兵势甚盛,塞外城堡,相继陷落。王振挟英宗,率师五十万出征。未至大同,军粮已乏,僵尸满路,又闻前方兵败。八月十四日,退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东);也先突至,明全军覆没,王振死,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至京,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之议。时京师疲卒羸马不满十万,人心惶惶。侍讲徐有贞建议:“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于谦斥之,曰:“欲迁者可斩。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力主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议是定。及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总理朝政,群情激愤,当场击毙王振死党马顺,朝班大乱,祁钰惧而欲逃去。谦排众直前,宣谕顺当死,众情乃定。祁钰首以谦为兵部尚书,负责筹画抗敌大计。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谦受命后,即采取如下紧急措施:诏外军入援;运通州粮至京;安抚军民;运南京军器至京;启用一批将领。又籍王振及其死党家,以平民愤。时天下无主,太子幼弱,谦请立祁钰。祁钰遂即位,是为景帝。
也先俘英宗后,待之甚厚,欲持之以骗取边城,勒索金帛,并迫明朝让步。及闻景帝即位,奸计不得行。不久,叛阉喜宁(与英宗同被俘)尽以明之虚实告之,也先决计引兵南犯。十月一日,拥英宗至大同,诡称送之还京,胁守将开关;总兵官郭登不纳。也先遂由阳原(属今河北省),南下逼紫荆关,破之,直趋京师。京师危急,景帝即以谦提督诸营军马,令诸将悉受谦节制,不听命者,先斩以徇。京营总兵官石亨主敛兵不战,坚壁以老敌师。于谦以为不可示弱,主坚决抗击,乃将全部兵力分列九门外,准备背城拒战。谦率主力阵于德胜门外,以当敌冲;令闭各城门以绝将士归路,令曰:“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后退必死,故皆用命。
十一日,也先抵京郊,使英宗作书,分送皇太后、景帝、文武大臣。朝廷遂有和谈之议,并遣人至军中问谦,谦曰:“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也先欲攻德胜门,谦令石亨设伏。及敌万骑至,伏兵尽起。也先败退,转攻西直门,亦受到顽强抗击,居民升屋呼号,争投砖石。也先初轻明朝,以为京城旦夕可破,相持五日,屡遭反击,而毫无进展,乃乘夜经良乡(在今北京房山县)逃去。谦分军追击,夺回被也先所掠之人畜甚多。
也先从京师败退后,仍不断犯边,但均被击退,于是决心送还英宗,以求与明和好。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大同参将许贵奏:“有敌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谦曰:“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胆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而也先益欲求和,屡遣使者送英宗。景宗为保帝位,不欲英宗还。谦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八月,英宗归,幽居南宫。
英宗既归,谦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并上安边之策,请令大同等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又,原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神机、三千诸营,各有总兵,不相统一,谦选精锐十五万,分为十营,设总兵,隶属于都督,称为团营(团营之制始于此),统一训练。以石亨为总兵官,谦提督军务。明军之编制,至此,为之一变。
当也先猖狂之际,内乱相继而起。浙江叶宗留(矿工起义领袖)、福建邓茂七(农民起义领袖)、广东黄萧养(农民起义领袖)率众起义,据地称王,广东、广西、贵州少数民族亦蜂起造反。前后征调,谦独当其任;战争瞬夕万变,谦临机处置,皆合时宜,群僚莫不惊服。谦号令严明,虽勋臣宿将,稍有违反,无不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因而深受景帝信任,所奏无不从。景帝欲用一人,必密访谦。谦皆实对,不避嫌怨,无所隐瞒。由是不任职者皆怨谦。谦性刚,对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怨者尤众。徐有贞因主南迁,为谦所斥,更是恨之切齿。石亨虽为谦所荐引,官至总兵,因畏谦而不得逞,京城之捷,又未得赏,亦不满,但为讨好谦,上书荐谦子于冕。谦责之曰:“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亨惭恨交加。
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与太监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扶英宗上台。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拟处极刑。王文极力辩之。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遂弃市。时年五十九。天下惜之。后归葬杭州,谥曰忠肃。
谦为人正直,少有壮志,敬慕文天祥。年十七,曾以石灰自喻,作诗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有军事政治才能,临危不乱,处事果断,是京城保卫战之英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全军覆没,人心惊恐,社会骚动,明皇朝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谦不避艰险,挺身而出,斥南迁之议,力主保卫京城,挽狂澜于既倒。其主要措施:拥立新君,拒绝和谈;征兵选将,加强守备。在保卫战斗中,他拒绝闭城以老敌军之意见,大胆采取背城战法,示以必死之决心。综观中国战史,多见背水之战,罕见背城之战。背城之战较背水之战更危险,非战即死。在保卫战中,他赤胆忠心,临阵督战,泣谕三军,身先士卒,故人人争奋。
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死后家无余资。每回京师议事,两手空空,从不携带馈赠物品。有人曾劝带点土特产,以送权贵。谦作诗曰:“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泛指民间)话短长。”诸权贵不满,但无可奈何。也从不言功。及谦之继任者陈汝言(石亨死党)事发,赃累巨万。英宗召大臣入视,曰:“于谦被遇景泰(景帝年号)时,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亨低头不语。
在上文「 ”驳于谦乃‘土木堡败’罪魁论:缘起,英宗被俘退位诏中判定的祸首”,我们看到了「 ”于谦竟然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充斥了无厘头、假设。本来对这种观点似乎没必要反驳。 但通过李鸿章在1896年巴黎奥运会上唱「 ”黄梅小调”竟然能获得许多人的宣传,有人竟然将其放入专业书刊的行为看,似乎又有些可以理解。什么神奇的谣言,你若不辩,就可能骗到许多小青年。其实,1896年首届奥运会是在1896年4月在雅典举行的。1896年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李鸿章才来到巴黎。 随便一搜谣言就能不攻自破,许多人竟然懒到举手之劳都懒得去做。脑袋都不去想想。 于谦作为汉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果可以这样被随便抹杀,那就太可怜了。 今天我们就谈谈,于谦到底有没有陷害明英宗的能力呢?答案是没有。于谦当时只是兵部侍郎,就连兵部尚书都不具备这样的权力,更何况副职。我们首先要了解兵部如何官兵。 (1)兵部与内阁谁的权力大?别轻易回答 甭说兵部侍郎,就算兵部尚书又能怎样?它能独自调兵、调粮吗?它的权力在明英宗时代能在老几?当然,兵部侍郎的地位已经不高了,只要再提高一层就是掌握天下兵马的兵部尚书了。 在六部当中户部比兵部地位要高,调兵的话户部管不着,但是军粮、武器装备等军事物资方面,户部可是完全可以插手的。这个问题还不是关键,在大明是六部权大还是六部权大?这个回答并不简单,必须要分阶段说才行。在明英宗时代的两个时期,内阁权力大于六部;在代宗时代,六部权力大于内阁。 洪武年间,朱元璋废相前后,大学士只是参谋人员。朱棣之后因为六部九卿许多都是建文帝的人,因此,利用内阁的权力制衡六部的权力。由此,杨荣、杨士奇等人进入内阁,内阁势力日渐增长,但请记住吏部作为六部之首其权力仍然要强于内阁。 因为杨士奇大力倡导「 ”保举法”,「 ”三杨”由此夺走了吏部对京官的任免权,权力开始大于六部。但请注意,吏部因为控制地方大员的任免仍然保持着制衡的能力。请注意,之后,「 ”土木堡之变”兵部尚书权力尚书为六部之首,六部权力开始提升。 (2)兵部、内阁、司礼监、御马监、都御史共同掌兵 兵部要想调兵、调粮首先要向内阁汇报,内阁要实行「 ”票拟”,票拟完成后要经过「 ”批红”。明英宗时期的「 ”批红”还并非司礼监的完整权利,明英宗时期是「 ”票拟”「 ”批红”向后世转变的关键时期。因为王振的擅权,「 ”批红”常常是司礼监的任务。 司礼监「 ”批红”完毕之后,以「 ”传奉圣旨”的名义,向印绶监、御马监发出调遣兵将的兵符、火牌。由此,兵部才能调兵、调粮。同时,还需要户部进行配合。 由此,对于调兵、调粮的权力,兵部尚书可没有独自决定权好不好。如果那样,兵部尚书造反怎么办?从来就没听说过,兵符由主帅掌管。 不要说全国兵力,就是京城的兵力,并不同样无法调遣。因为,在京营的控制上,并不虽然有一定权力,但为了防止兵部控制兵权,都察院的右都御史也负责京营的操练事宜,即「 ”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或(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或(都察院)右都御史。 掌京营操练之事。” 明景陵 (3)「 ”土木堡之变”那有什么文臣集团的阴谋 于谦要想完成自己的「 ”阴谋”,那就必须整合好内阁、司礼监、御马监、都察院四个系统的主管人员。当然有人会说,当时大官都被「 ”明英宗调走了”。但问题是,明英宗走是走,但留下了官场运行制度不能就此瘫痪呀。明英宗,特别是王振自然要留下自己的人看着,继续运行既定的官场运行制度。 内阁和司礼监、御马监这些皇帝的、王振的亲信们,要么要与于谦合谋、要么都是智力太有问题,缺少一样都不可能。这个「 ”阴谋集团”的人员数量也太多了。同时,「 ”文官集团”的阴谋也是属于妄想,这里没有「 ”文官集团”的阴谋,有的只是「 ”土木堡之败”后,「 ”文官集团”必然势力做大的结果。 试问,陪同明英宗前往的大臣们难道没有文臣们?三百多人的官僚集团,可以说「 ”京城”内的官僚精英们至少三分之一都去了。如果是「 ”文官集团”的阴谋,那么,难道这三分之一的官僚精英就没有一个是「 ”阴谋集团”的至交好友亲朋吗? 失败中死亡的三百多文武中有多少人都将与留在京城的这些官员有多少关系,那么,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结论: 张辅、张懋父子墓 为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文官集团要把另外一个文官集团全部消灭。那么,这是哪个文官集团? 同样,文武官员、勋贵集团等不是敌人,明朝也不是北宋仁宗以后的文武官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姻亲遍布、朋友关系都很多,特别是京官系统,你不能把明朝制度上的「 ”以文制武”看成北宋的那种「 ”文官欺辱无关”的状态。 同样,司礼监和御马监的权力在「 ”土木堡之变”后越来越大,具备了提督京营的权力,也就是说,「 ”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中的六部权力上升的同时,太监的权力也在上升。有些人口口声声「 ”勋贵集团彻底覆灭后,文官集团就上升了”,明英宗时期勋贵集团本身就没剩多人,朱家能打仗的没几个、张辅那样的也不多,这些人去不去是英宗、王振说了算还是所谓的那些留在京城「 ”文官集团”说了算? 论者都是以结果导出阴谋,而不是去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换句话说,这些人属于没事儿干了,坐在小黑屋里看着结果发呆,问自己「 ”这样的结果会出什么阴谋呢?”您是不是「 ”侦探剧”看多了呀。 下文我们主要从明英宗、王振的进军路线谈谈这一问题,看看诸如不给发粮以及泄密到底除了阴谋论外,还有什么可能! 驳于谦真的是「 ”土木堡之败”的元凶?先看看这个人的观点 李鸿章潘鼎新死咬王德榜,左宗棠张之洞力保之 张居正与海瑞的不同,改革与革命在晚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于谦作风廉洁,为人耿直。 谦生活的那个时代,朝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当时各地官僚进京朝见皇帝,都要从本地老百姓那里搜刮许多的土特产品,诸如绢帕、蘑菇、线香等献给皇上和朝中权贵。
明朝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
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以示对那些阿谀奉承之贪官的嘲弄。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
《入京》
明代: 于谦
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译文:
绢帕、蘑菇、线香这些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可是因为贪官污吏的搜刮,它们反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免除百姓的不满。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明英宗时,贪鄙成风,地方官进京,不带重金厚礼是办不成事的。时任地方巡抚的于谦,却每次进京都是两手空空,连绢帕麻菇之类的土特产也不带上一点。并口占《入京》此诗。
绢帕、蘑菇、线香都是他任职之地的特产。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反而成了百姓的祸殃了。他在诗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进京什么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朝见天了。诗中的闾阎是里弄、胡同的意思,引申为民间、老百姓。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县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
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瓦剌兵逼京师,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冤杀,谥曰忠肃。
-中华历史贤臣:两袖清风·于谦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