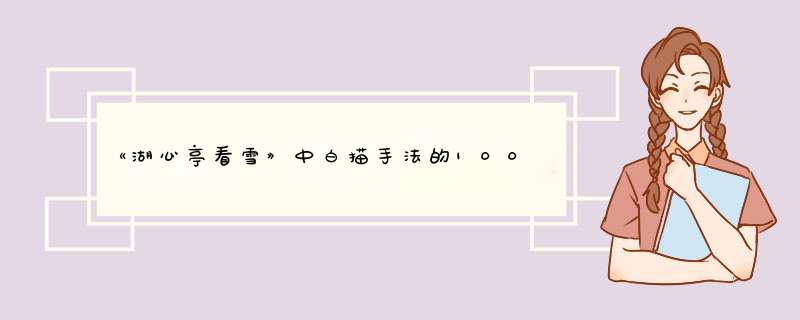
清朝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描写雪景的句子: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雾凇……上下一白”一句写出了造化的神奇,天地间举目皆白,“一”用得尤其巧妙,一下子把夜晚里天空、云雾、湖水之间浑然莫辨的壮阔、朦胧而又凝静之美景全景式的展现了出来。“湖上影子……两三粒而已。”一句更是抓住了夜色中雪景的特点:雪夜之中到处是白茫茫一片,除了雪所见到的湖上的影子只有像一抹印痕的湖堤,湖中的亭子也被映衬的只有墨点一般大了,而作者所乘的小舟以及舟中人更是小得如草芥和米粒一样。这种缩小式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既逼真地写出了凝静中似乎又有些灵动的湖上奇观,同时这种微雕般的小景又与前一句的阔大之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觉得在这样一个浩渺无穷的冰雪世界,人是何其渺小——真可谓“沧海一粟”啊!对于身处太平盛世的我们在读到此处尚且有如此感叹,那么对于身处明亡清兴朝代更替之时的作者来说不是更有一种人生渺茫的感叹吗?就这样短短两句不但让我们眼前有了一个空旷浩渺、凝静清绝犹如童话一般的冰雪世界。还让人深深地感触到作者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内心无处言说而只好寄情山水的无限情愫。这字里行间留给读者思索的巨大空间如同简练文字所呈现的“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空旷世界,读者可以任意想象和猜度。这就是白描,它不加修饰、不须陪村和烘托,看似俭省朴素实则造成了一片“艺术空白”让读者再去进行二度创造、深层联想,从而品味出画外之音,言外之意。
用白描手法,可使人物描写更富神韵。
1、在外貌描写中,运用白描手法,能洞穿人物骨髓,由貌触及本质、灵魂。
看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孔乙己》中的一句白描: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虽然就朴朴实实的一句,但其内涵却极其丰富。它把孔乙己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性格一针见血的展现了出来。站着喝酒,是短衣帮的人,他们的生活贫困,而生活穷愁潦倒的孔乙己只得和他们为伍,已经挤不进长衫客的房间了。然而,他又不肯脱掉长衫,仍要维持那读书人的架子,以显示他在精神上还是比短衣帮略高一筹,足见他的迂腐和虚荣心。孔乙己这种拮据的经济状况和迂腐的精神生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使他成了咸亨酒店唯一的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特殊人物。
2、在语言描写中,运用白描手法,能传神表达人物内心,展现情操品质。
王愿坚《七根火柴》中有两段文字,一段是无名战士把七根火柴交给卢进勇时:
“ 同志,你看着… …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
另一段是,卢进勇赶上部队,把火柴交给指导员时: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本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
两段中,通过简简单单的两个 “一、二、三、四… …”的白描,使我们展开丰富的联想,能真切的感受到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读第一个“一、二、三、四… …”我们仿佛看到无名战士要把自己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火柴交给卢进勇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心里在说,我有火柴呀,七根呢,你看!说出了一。在数二时伤口一疼,声音很低,很短。数三时他在跟疼痛做斗争,也在积聚所有的生命的力量,他尽可能的深吸了一口气,把三四由低到高的挤了出去,而且说四时他声音坚定,目光坚定。他仿佛看到了,围着火堆,战士们在养精蓄锐;枪林弹雨中,战士们在冲锋杀敌… …说完四后他嘴角有笑,面容安详。第二个“一、二、三、四… …”是卢进勇赶上部队,完成了无名战士的重托,把火柴交给了组织时说的。说一时他的心情是神圣的,庄重的。说二时,想起无名战士在草地牺牲的情景,他两眼噙满泪水,声音发颤。数三时,卢进勇语气中充满了完成任务的放松与欣慰。数四时,想到红军北上抗日的大业,这火柴将点燃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语气高昂奋进。相信,每个读过此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的“一、二、三、四… …”
3、在动作描写中,运用白描手法,可使人物内心情感的表露更准确、语言凝练。
看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中的描写:
“仅仅有一次,他的教鞭好象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
就在这平平实实的字里行间,蔡老师对学生们的关爱,如一股涓涓细流,从每名读者的心中涓涓流出,绵长深远。
张明(语文报——写作指导)
平日讲写作,提及白描这种“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手法,重点强调它在刻画人物肖像和描述自然景物方面的特殊作用,却忽视了这种手法在叙事上同样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现从读书笔记中摘录几个白描叙事(当然很难不涉及人和景)的例子矫正这个观点。孙犁先生散文《亡人逸事》中有这样的文字:
“有一天,母亲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母亲问她:“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她弯下腰,挎好筐条猛一立,因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她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拣起来,背到家里去了。”
孙犁先生对亡妻刚刚过门时的回忆,朴实无华的语言,纯真稚气的青年女性形象,情意绵绵的情感世界,都建构在立体感极强的白描叙事当中,富于生活的原汁原味,更渗透了孙犁先生对亡妻缠缠绵绵的思念。这样的写法让人过目难忘。散文大家朱自清先生的《看花》:
“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由城外而去。到了F寺,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我们称寺里的工人为道人),立即领我们到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桃花是正开着哩!”
这群缺乏起码生活常识的城市孩子,之所以要理直气壮地到城外寺庙里去“白吃桃子”,是因为当时中学生有打进戏园白看戏的先例。小学生善于模仿,天真稚嫩,淘气顽皮,初生牛犊不怕虎——丰满欲出的群体形像,完全潜伏于简洁平淡、毫无雕饰的叙事描写当中,真实而自然。散文之外,小说中更有大量白描叙事的例子,举老舍先生的《月牙儿》为证:
“临走的时候,妈妈挣扎着不哭,可是心底下的泪到底翻上来了。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去,她的亲女儿。我呢,我连哭都忘了怎么哭了,我只裂着嘴抽达,泪蒙住了我的脸。”
这位悲苦至极的母亲,为了能在乱世之中寻找活路,丢下唯一的亲生女儿。母亲“挣扎着不哭”,女儿“连哭都忘了怎么哭了”……如此洗尽铅华的叙事,比任何抱着痛哭、嚎啕大哭,甚至呼天抢地恸哭的场面描写都能产生感人的艺术力量。
苏东坡先生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可见作为写作手法,白描无论写人、绘景还是叙事,都属于炉火纯青的上乘功夫,我们不仅在阅读中应时时注意,仔细品味,写作中更要多加练习,以求得心应手。
整首词清新秀丽、朴素恬静,以白描的艺术手法,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语言浅显易懂。这首词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喜悦之情,客观上反映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生活的憎恶。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