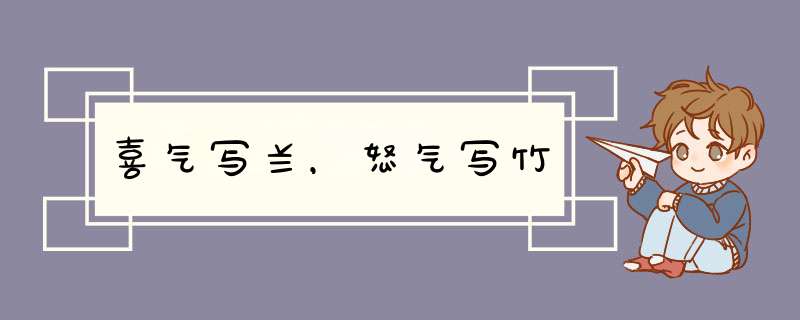
(《漫谈美学——在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上的演讲》,2002年)
在中国诗画中,水边垂柳常表示轻柔抒情,山上高松表现刚强正直。
中国画论说:“喜气写兰,怒气写竹。”
中国古人不知道刚才提及的西方心理学,但他们讲的道理却相同。
刚强、愤怒的情感,通常用直线表现,柔和、舒闲的情感则用曲线。
所以说喜气时画兰草,画竹则表现硬朗、愤怒,也是说感知同人的情感有一种同构的关系。
雕刻家用不同的颜色、质料、形状,书法家用线条的直、曲、停顿、流畅,以及空间结构,都不只是外在的感知而已,而是与内在的情感直接相关,给予人不同的感情感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部分就是中国古典艺术。中国古典艺术是以“意境”为核心,以“意象”为纽带,以艺术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生命体现。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诗歌和绘画,都不约而同地把“意境”作为最高审美范畴。“意象”是凝聚作家主观情思的,富于审美意味和文化内涵的客观外在物象。举例来说,元代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其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就是典型的意象,这些带有作家主观情感的外在物象共同烘托出苍凉悲凄的色调,把“断肠人”的羁旅之愁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境”又称“气韵”、“性灵”,是艺术家借助艺术符号,通过不同意象聚合而成的一种新质。意境的生成基于意象但又超越意象。中国的古典艺术有“写意”的传统,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它们都是以“意境”为轴心彼此交叉又互相渗透的实体,也正是因为有了“意境”,才把不同的艺术形态连结和沟通起来,中国的古典艺术也正是借助于“意境”这个生命范畴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按照一定方式组成具有民族特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具体到中国古典艺术的两个重要门类,诗歌和绘画,也正是以“诗境”和“画境”在“取境”或“造境”上的一致性,才得以实现沟通。
以中国古典艺术最为发达的唐宋来讲,王维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擅长绘画和演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王维的艺术作品别具一格。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诗具有优美的画境,王维的画又有独特的诗境。诗画都以“境”为旨归,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传达了相似的艺术感觉。王维本人也承认诗歌和绘画的相通,他说绘画“乃无声之箴颂(文学),亦何贱于丹青”。在讲授王维的诗歌时,我们重点解析王维诗歌中的画意,并且通过展示王维及其他山水画家的画作来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造境”。
宋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形态最为成熟的一个时代,宋尚文治,设翰林画院,选拔人材的标准除了诗文论策以外,兼试绘画。同时经常以敕令形式公布画题于天下,其画题大抵引用古人诗句,使应试画人于笔墨技巧之外,兼求思想揣摩的妙合,无形中使画人兼具文人思想。这种“重文”的风气养成以后,宋、元画家多能用形象的艺术抒发诗文的涵蕴,构思入微,神趣天成,形成了绘画史上“文人画”的空前发展。当时招考的画题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落日楼头一笛风”,“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等。这些诗句极富有形象色彩,十分适宜于表现画面。就看画作者如何表现主题,并以此评定高下。宋人的做法对我们教学的启发颇大,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摘取画面感较强的诗句,以命题作画的形式,让学生揣摩诗歌的意境,并用适当的艺术形式给予表现。
中国古典绘画,融诗、书、画、印于一体。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诗与画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诗的意境和画的形象互为表里,血脉相通,人们常说:“诗是画的内涵,画是诗的外溢”,“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正因为中国古典艺术中不同艺术形态的相通性、互补性,使得从一种艺术形态过渡到另一种艺术形态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转换也不是无条件的,教学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相互转换往往是限于同一题材或同一情节。
中国古代有许多咏梅的诗词,如王安石的《咏梅》,苏轼的《西江月・咏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等,也有不少颂梅的图画,如宋杨补之《四梅花图》,宋马麟的《层迭冰绡图》、元王冕的《墨梅图》等等,尽管这些艺术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抓住了梅花的洁白、芳香、耐寒等高贵品性以隐喻那些节操高尚的人。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一书中曾把同一题材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比较,最后他说:“诗的价值并不存在于表现抽象观念的诗行或散文诗中,而在于通过意象的美妙编织,能唤起情绪和沉思。然而,观念在这里是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在发生作用的,它帮助我们在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方式中去把握整个意义。”梅花因其物性上的耐寒早发,成为中国人心目中隐喻美好品质的一种固定意象,所以这么多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梅花作为表现对象。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就选取了“梅花”这个典型的意象作为切入口,布置学生阅读中国古代的梅花诗,并且从中总结出梅花物候上的特性和气质上的独特,并且结合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梅花画,以诗配画的形式创作一副以梅为表现题材的艺术作品。这种 教学设计 极大的启发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受到学生一致的好评。
第二、对同一内容的作品的深层次意蕴上的领悟要一致。
以中国古代山水画为例,中国古代山水画特别注重意境的创造。苏轼《题王维吴道子画》曰:“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又《题文与可墨竹》曰:“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北宋画家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将这种“得之于象外”、“荒怪轶象外”的画境提炼成一个“远”字,谓之高远、深远、平远。后北宋画家韩拙《山水纯全集》又补充了“阔远”、“迷远”和“幽远”,合称“六远”。这种“远”的画境,其实就是对有限个体、有限空间的一种超脱,让人突破山水有限的形态,将人的心灵牵向遥远,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冥合的境界。比如唐柳宗元的《渔翁》和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就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于表现意境的高远上。
第三、要充分考虑各种艺术形态在表达上的优劣,截长补短,臻于完善。
诗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为载体来表现外在事物,而绘画以具象性的纸笔来描摹外在事物。诗歌可以提供无限的想象,而绘画给人直观感觉。两种表现形式各有所长,亦有所短。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色调对比非常鲜明,给人以油画般的感觉。白居易《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不成眠。”构图十分巧妙,夕阳的光和萤火虫的光形成明暗的对比,宫殿和萤火虫形成大小的对比,唐明皇的“悄然”和萤火虫的飞动形成动静的对比。仿佛使人眼前出现一副垂暮老人大殿挑灯,萤虫飞动的画面。
然而,诗中的画,并不一定都能画出来。明张岱《琅缳文集・与包严介》:“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如李青莲《静夜思》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故乡’有何可画?王摩诘《山路》诗:‘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尚可入画,‘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则如何入画?又《香积寺》诗:‘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危石’、‘日色’、‘青松’,皆可描摩,而‘咽’字,‘冷’字,则决难画出。故诗以空灵才为妙诗,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屑也。”
这些都说明了在诗画相互转换的过程中,由于不同艺术形态所依附的符号系统不同,从而造成转换过程中的审美效果的变化。
参考书目:
(1)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1版。
(2)虞君质《艺术概论》大中图书公司 1964
(3)李泽厚《华夏美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邓海霞,大学教师,现居江苏苏州。
用画画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其实这个很简单。哪怕你不会画画。那么你就可以用笔在纸上印有自己的情绪,支配可以画出东西来。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是会画画的人,他在学习情感的时候是比较。有规律性的或者是那个画面会更好一些。更具观赏性而已。这个主要是心理学。心理学上他就有我心理医生会根据患者这个来绘画的内容线条所体现的东西。来看患者内心世界。那么还有一点也就是说。不要认为去看心理医生就是有病。我们现在社会这么。压力大,浮躁,所以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去看心理医生。心很正常,有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其实就是听一听,心理医生的疏导,然后。就是与他谈话之后不让你得到放松。
一 “画中有诗”是创作和审美的初级阶段
讲初级阶段意在阐明它是通向高层次绘画表现的起始点,并非是对“画中有诗”的否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诗画 艺术所自觉追求的一种境界。
这一命题是宋代苏轼提出的。他在论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原无语,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那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怎样的含义比苏轼稍前的邵雍在《诗画吟》中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伊川击壤集》卷十八),把诗与画区别为诗状物之情,画状物之形。清代美学家叶燮也言道:“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赤霞楼诗集序》),进一步指出了诗与画的相互渗透,就是情和形的相互渗透。所谓“诗中有画”,是诗的境界鲜明如画,即欧阳修说的“见诗如见画”。而“画中有诗”,《宣和画谱》称:“每下笔皆默合诗人句法,或铺张图绘间,景物虽少而意常多,使览者可以因之而遐想。”即画中有诗一般的情景交融的意境美。所以,从本质上讲,诗与画是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创造出共同的审美境界。
从物质形式上看,诗是以语言文学存在于延续着的时间,而画则是以线条与色彩等造型形式对空间的占有。从表现形式上看,诗是抒情言志,画则以形写神。因而,在创作过程中,诗人与画家必须对各自的物质形式和表现形式进行调节与选择,以寻求物质形式上的交叉与表现形式上的沟通。而这种交叉与沟通只能建立在表现境界的同一性上,绘画中所包含的“诗意”也只能在某些方面与“画意”相吻。所以有人随即指出了诗与画不完全能融合。如与苏轼同时的参寥即言:“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明末清初的张岱说的更明白:“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此外,陈著一、董其昌、程正揆等皆有论述。但对这一理论的异说,并未能阻止它的盛行。经苏轼点出后,风靡古今,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艺术目标,评画的一条准则。
其实,若论评画的准则,由“传神”到“画中有诗”的“传情”无疑是一次大降格,由宇宙自然对人的作用关系降到了人对宇宙自然的作用关系。实际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解释的最根本关系是绘画与文学的关系,“画中有诗”即绘画艺术中所包含的文学性。文学性的特征是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感受和叙述。绘画的文学性则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叙述、描绘及经,给予审美者以美感性表现,或者说更接以情感性表现。情感的主体是自我,自我对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在这种情感支配下的“诗画”境界包含两种认识:一是对自然美的认识,主要通过描绘自然景物,抒发自我对自然美的寄托(如王维);一是借描绘自然事物,抒发自我对社会的认识(如八大山人)。二者皆属于情感性认识而非认知性认识,故尔它只能作为认知性认识的基础。
如果从心理学上讲,情感是客观事物和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的一种关系的反映,包括感官的生理感受及主观意识、理想等。刘勰《文心雕龙》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物即是自我所选择的描绘对象,情即是自我审美感情。情感活动的状态和范围受“诗画”的境界即绘画向文学性倾向的影响,但基本为绘画内容所描述的景物和事物。同时,也可能在情感活动中,对绘画内容进行情感上的丰富、补充和改造。这就是“咸酸之外”、“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画外意境。
由于文学性强调了情感的价值,因此,主体情感被引申和激发到艺术创作意识中。对于以水墨为主的中国画,便有了“色不碍墨,墨不碍色,处处虚灵,非关涂泽”(《黄宾虹画语录》)的情感认识,所有的色彩都可以超越它自身的实际意义而为表达人所有的情感所利用。所以,春天并非皆绿,秋日也不都黄。“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荆浩《笔法记》)这样看来,“画中有诗”的境界只了限于情感的价值,而对于情感活动所得以凭借而升华的精神境界及其扩大与深化所得以成立的本质性认知则未能完全再这一境界中体现。但超越情感活动去真接获得宇宙自然信息的感应却又如镜中花、水中月。因此郭熙讲内外交相养,才能使画境向深广驶进。
二 “禅境”标志着对“诗画”的深入
不能否认,中国山水画“诗画”的境界,虽然包涵了历代画家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观照和各种形态的技法不断完善。但从“诗意”中寻求旨意遥远而高妙的“意境”(苏轼语)和“逸气”(倪云林语),其意义仅限于在实际上把绘画从魏晋以来重“形似”的美学准则转向到“神似”和个性化,使作品不流于庸俗、呆板和空洞,从而更富于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
对王维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肯定系苏轼所为,但是否王维的本意追求,尚难结论。王维虽是诗人,但却在禅宗兴起后,究于此学,精通禅理。其名字便以佛教人物维摩诘之名分而用之。他的诗和他的画同他的思想一样,具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追求“禅趣”和“玄思”的“禅境”。而“禅境”是怎样的境界
“祥”的原意为“静虑”、“沉思”,谓要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瑜珈师地论》曰:“言静虑者,于一所缘,学念寂静,正审思虑,故名静虑。”认为能使心绪宁静志注,便于深入思虑义理,故又称为“善性摄一境性。”它一方面要求“禅”的本体——主观自我,要澄静胸怀,排除杂念,以空灵澄澈的“本心”去体验万物;另一方面,作为“禅”的客体的外部世界要有一定的选择性,即能作用于“本心”,通过“正审思虑”获得刹那间心灵感受的“环境”。因此讲,“禅境”是“环境”对人的认识产生影响。它区别于文学性的“诗画”意境所为的情感特征和色彩特征。同时,它又超越文学性绘画对自然美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它通过’环境所提供的空间及空间作用于大脑产生的特殊思维,为人们暗示出超越这种空间的认知。宋代郭熙《林泉高致》中“深远”、“平远”、“高远”三远法的提出,便是这种特殊思维的启示。其后,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又于“三远”之外,立“阔远”、“迷远”及“幽远”之名。严格地讲,此“三远”已非真实的空间,而是一种“环境”空间与人的主观思维发生关系后幻化出的“烟雾暝漠”、“微茫缥缈”的新“环境”。正因为生成的新“环境”令人“阔”,令人“迷”,令人“幽”,所也能令人“审”,令人“思”,令人“静”。
以“禅”为宗形成佛教宗派于中晚唐在全国风靡后,深深地渗入到绘画领域。北宋熙宁、无丰之际,苏轼、黄庭坚等人倡导的“文人画”,即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暂借好诗销永夜,每到佳处辄参禅”(苏轼《跋李瑞叔诗卷》)。“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黄庭坚《题赵公佑画》)。于是,以参禅之心而入画的创作便自觉不自觉地对后世诗书画得兼的文人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如明董其昌为表示与“禅”的关系,直接将画室名为“画禅室”,并在理论和实践上皆有充分的认识。唐以后的大多数画家都有意无意地受到“禅”的影响。
“禅境”所呈现的空间感受也同修禅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一样,呈现出差异性。抛开笔墨技法不谈,“禅境”的差异性反映在作用于人的思维和心理的同向递增性。虽是差异,但有层次。层次的递增的过程,也是向宇宙自然的哲学认知性的归属过程。如果讲“诗画”的文学性境界是一种“美”的体验,有抒怀言志的情感价值,那么,“禅境”便能让人从美中入“静”,面对“自然”,然后由“静”生“虑”,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接着再由“虑”入“定”,进入到“本心”与“客观世界”混而为一的思维状态。最后由“定”生“知”,通过认知性的活动把握“具体而微”的生命的意义与宇宙自然的本质结构。事实上,“禅境”最后的层次即是我们所要论述的哲学归属。
相续而递进的画境,为异质而有别的画家划开了界限。有的只限抒胸中抑郁愤满不平之气,抒胸中逸气聊以自娱。有的则悟对通神,穷理尽性。只有在澄怀观道,通过静、虑、定、知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掌握自然的结构和规律,表现自然,才能从地加学养、积累素材、感受自然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讹解中挣脱出来,以“思接天地”、“神游八荒”的感应接受宇宙自然的信息。董其昌尝言:“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因此要在认识中提高认识,在境界中创造境界。借助“禅”的特性,加深“本心”的修炼,加深对自然的认知。
三 认知的表现层次与发展过程中的完善
绘画高级阶段所表现出的哲学归属,实际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如果讲“禅境”是在文学意境基础上通过描绘事物的“环境”性氛围来加强“环境”对人精神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哲学性的认知便是在“环境”对审美者作用下所对客观世界乃至宇宙深层的体悟。从本体论看,认知层次的递进与发展是由自我意识的外化同客观世界的对立到将自我意识提升作为“本体”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即艺术创作的思维过程中“自我意识”的主体与扩大了的“无限自我意识”的本体的相互冥合,最后归于取消一切认知的对象和取消一切关于对象的认知,使绘画成为一种横断时空的存在,达到“人境俱夺”的地步。
在中国文化中,对宇宙本体的哲学认知是通过“本体”人的“自我意识”的认知而实现的。作为中国文化意识的绘画艺术,其发韧之初就与探索宇宙自然的奥秘紧密相联,并从自觉到不自觉的认知过程中,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也培育和获得了大脑随机开放的艺术思维和表征认知观念的艺术形式。随机开放的思维,为自由地认知提供了前提,而且有可能将认知结果变成观念,转化为具体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
具有影响力的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体系,在直接衍化出中国艺术的思想体系。山水画由于其包含之广,气势之大,在它的艺术形式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思维特点和时空风貌,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独特认知关系的理解和表现。老子称为“万物之母”的“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的这种超感官存在的特性,也决定了人们在认知过程和创作过程中把握它的独特性。魏晋时人颜延之在写给王微的信中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强调指出了绘画的哲学本质。它不仅仅是表现客观世界的形式美,而是在认识宇宙自然的规律中,体现出这种规律。所以绘画理论家告诫画家们要“澄怀观象”、“悟对通神”、“度物象而以其真”,以虚静的胸怀领悟宇宙自然的无限,超越物象外在的形式,这样才能挖掘和表现出自然内在的真意,黄宾虹言作山水要得山水奥秘,写出自然之性,也即此意。自然是无限的,“无限”便不能有“界”,有“界”就是否定。对无限的实体——山水来说,在质上对认知它的每一种界定,便意味着对其无限性的否定。所以,这种无法靠感官而只有靠体悟把握的“无限”,可以凭借具体形式的技巧表现。但是,这种深层意识的把握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以隐匿性呈现的。感觉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付诸人类感官的客观对象都是有限的,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使比抽象概念更能提供内涵潜能的表现形象本身,一旦成为感官所获取的对象时,其潜能的释放也是有限的。因此,在中国画家看来,仅仅满足于视觉的具体是暂时性的愉悦,表面上的美化,流动着的情感,偶然性的再现,所以它缺乏可靠性和永恒性。
然而,经过对宇宙自然的本质“道”的体认,表现事物才能回归于永恒的本质的内美。所以,黄宾虹反复强调画家要深入到对象的内部,向内部深层追寻它的生命和运动,以“俯仰自得”的精神去观察宇宙万象,深入大自然的节奏,“游心太玄”,去表现无穷的空灵而又实在的生命本质。作画岂可一味画其表,如石受光,为外表之色泽,可画,但不是非画不可。至于石之质,此中内美必须画,其构成、性质及与自然的关系是非画不可。做到这一点,需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修身养性,净化人格,提升情怀,内省体验,真正获得高级认知后的审美观照。因此,“造化有神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须于“静中参”得。(《黄宾虹画语录》)如果画家心灵的提净没有完成,人格的自然化没有至达极静,是不能得到造化中的神韵,不能得到自然深入发出的美的信息。故此,绘画不仅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知,也是人的精神、人格走向完善的过程。这是人的精神和创作灵感被“自然”内在美的力量驱策前进所然,当然,这种自然内在美的力量转化为可视的形象,是以表现在绘画中的诸多哲学认知范畴为条件的。
中国哲学真正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宇宙本原问题的探讨。这一探讨从人生哲学出发,把人类的观察思考范围由人生、社会而扩展到整个宇宙,并形成“人法地、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人生论。主张“人之道”要服从于自然无为的“天之道”。并从宏观出发又经过微观的审视,指出了天之“道”中所包含的总体对立因素,即阴与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构成了宇宙生命的基础节奏,构成了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它是永恒的万物变化之纲,是支配物质世界或现实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画家从对宇宙的深察体悟中,把这种认识本体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深化为抽象的思维能力,使中国画艺术形式的背后建构起思维开阔、意境宏绰、观念众多及具有潜在理性思辨的艺术思想。在创作实践上,形成由阴阳关系而生成的黑白系统。
从中国画的基础本质材料便依据其自性对自然界的黑白关系,一分为二:黑色的墨和白色的纸;又以视觉造型为中心通过笔的运动形成黑色的可视形象和白色背景;然后,再以审美心理为要凭,产生感应性的黑白变化。这种变化中,具有可视形象的笔墨界线能发生转化,如黑到极处即是白(黄宾虹的“亮墨”);最后是沿着认知活动的递进,升华为观念,黑是实,白是虚。黑是密,白是疏。既是对立,又是统一。黑与白成为中国画家成功的圣光。
《老子》讲:“知其白,守其黑”。宋范应元注:“白,昭明也;黑,玄冥也。”白是显现光亮,黑是隐匿黑玄。绘画掌握了显现出的事物关系,才能潜匿住自己的本真,使表现如同宇宙中的事物一样,增加含蕴的层次与质量。如前哲评黄宾虹的山水为“浑厚华滋”。“浑厚”是指“黑密厚重”,即物质的质量性,为黑;而“华滋”则为物象表面所呈现的特征、是白。所以《老子》所言之“白”,并非虚空无物,它可以是纸地,是空间,是表象,而这一切都具有物质的质量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白”是“黑”的扩散,“黑”是“白”的凝聚。“首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我们不妨把传统中国画对山石树木的描绘看成是一种固定的黑白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笔墨是至高无上的。通过笔与墨的变化传递塑造物象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线条的抑扬顿挫、缓留疾徐和用墨的浓淡干湿焦宿破积,又形成了黑白关系中黑白层次的抽象化。它一方面实现物象实体面与面相交接的一种综合与抽象;另一方面,也是对宇宙自然充满生命力质的动感的一种概括。凭借笔墨表现,守住了集中体现物象质的“黑”,也即守住了物象质的具体特征。黄宾虹七十余岁时尝称自己的作品为“平实”,至晚年则称“虚实”,对事物的认知发生变化。他画夜山,“夜行山尽处”,开朗最高层。“顶天立地的庞然大山,到处是黑,到处是实,但却黑中透亮,实里藏虚,明唐志契所言之“藏”亦即此意。虽极其敏密,千笔万笔,布满一局,但密而不繁琐,重重叠叠,饱藏着无限的精蕴。“藏”于“黑”,也要“露”于“白”,通过对万千姿色的墨的应用和变化,减少或增加,使黑白的对立发生转变。这里有一因子——水的参与。水为白,水的介入,既可与墨的色彩关系发生变化,又可使与墨的自性关系呈现新征。墨本一色,同水混用,可千变万化。古人言“墨分五色”、“墨分六色”皆含此意。“一钵水,一砚墨,两者互用,是为墨法。然两者各具其特征,各尽其所用,各有其千秋。”(《黄宾虹画语录》)认识到水的作用,才能发挥其独到的艺术特性。从物质上讲,墨为“火”性,水与火的对立与融合,才能使艺术表现呈现自然性。这点,黄宾虹曾说:“墨是火烧的烟,画了墨,浇上了水,不是灭火吗”“我是用水灭水,不要火去再烧了。”所以,“水墨交融”也是黑白关系具体化的表现。以白当黑,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既要立足黑的实体的质量,更要立足于白的虚空变化,如此才能于“墨华飞动湿云生”中“求淡以浓”、“求白以黑”,作神奇的变化,显示出中国画中的理性精神和智慧,而且在精神的奥妙和智慧的玄哲中获得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
《约客》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情景交融、清新隽永、耐人寻味。
赏析:
1、“黄梅时节家家雨。”作品开篇首先点明了时令,“黄梅时节”,也就是梅子黄熟的江南雨季。接着用“家家雨”三个字写出了“黄梅时节”的特别之处,描绘了一幅烟雨蒙蒙的江南诗画,每一家每一户都笼罩在蒙蒙的细雨之中。
2、“青草池塘处处蛙。”在这句中,诗人以笼罩在蒙蒙烟雨中的青草池塘,震耳欲聋的蛙鸣,反衬出了一种江南夏夜特有的寂静的美。蛙声愈是此起彼伏,愈是震耳欲聋,就越突出了夏夜的寂静,这就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以动写静。
3、“有约不来过夜半”,这一句才点明了诗题,也使得上面两句景物、声响的描绘有了着落。用“有约”点出了诗人曾“约客”来访,“过夜半”说明了等待时间之久,主人耐心地而又有几分焦急地等着,本来期待的是约客的叩门声,但听到的却只是一阵阵的雨声和蛙声,比照之下更显示出作者焦躁的心情。
4、 “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使诗歌陡然生辉。诗人约客久候不到,灯芯渐渐快燃尽,诗人百无聊赖之际,下意识地将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打,而笃笃的敲棋声又将灯花都震落了。
诗人独自静静地敲着棋子,看着满桌的灯花,友人久等不至,虽然使他不耐烦,但诗人的心绪却于这一刹那脱离了等待,陶醉于窗外之景并融入其中,寻到了独得之乐。
全诗通过对撩人思绪的环境及“闲敲棋子”这一细节动作的渲染,既写了诗人雨夜候客来访的情景,也写出约客未至的一种怅惘的心情,可谓形神兼备。全诗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扩展资料:
1、原文
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释义
梅雨时节家家户户都被烟雨笼罩着,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传来阵阵蛙声。已经过了午夜约好的客人还没有来,我无聊地轻轻敲着棋子,看着灯花一朵一朵落下。
3、作者简介
赵师秀(1170-1219),字紫芝,号灵秀,又号天乐。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时人将其与翁卷(字灵舒)、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并称为“永嘉四灵”,开创了“江湖派”一代诗风。有《清苑斋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