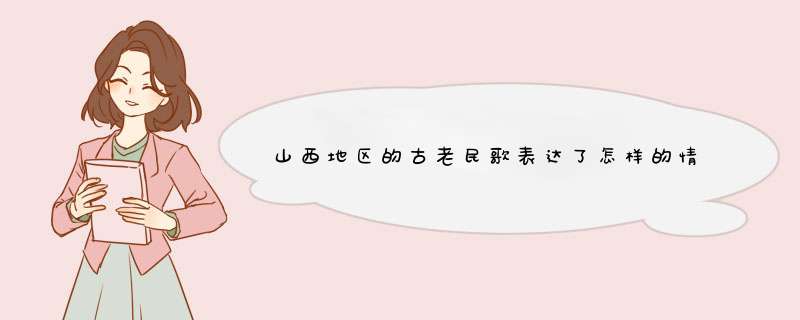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唐风》和《魏风》,大都是产生在山西地区的古老民歌。
这些民歌,如《唐风》中的《椒聊》、《葛生》、《绸缪》、《鸨羽》等;《魏风》中的《硕鼠》、《伐檀》、《十亩之间》、《汾沮》、《葛屦》等。
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或歌咏劳动生活,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无耻,或倾诉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有不少是反映婚姻或爱情生活的。
从这些民歌中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不仅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用民歌来歌咏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而且通过民歌,去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古代中国,人们心中都有一种愿景,那就是:求家族之长存,于是有了家族制度。祠堂,正是家族制度的外化表现形式。几千年来,中国的家族制度一直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这种生活理想,田园情怀,返璞归真的态度,以趋福避祸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清淡的幸福。
粉墙黛瓦的建筑,斑驳的墙面,搭配著青山绿水,碧天白云,刹那间如置身山水书中;向里走去,木制的长廊,精美的木雕,古老的窗栏又仿佛回到了那些旧旧的年代,让人沉浸不知自拔。
古老的祠堂处处散发着岁月的味道,残留着年代的印记。中国的民间祠堂,在20世纪饱经战火和政治的打压后,多已分崩离析……那些供桌上的牌位,和他们背后的农村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也早已坍塌,风光不再。
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
家族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祠堂在乡村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性,作为商讨和教育的“公共场所”。传统的中国乡村,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等,这种交流也既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维系。人们也在与先人互动之中,保持着自己的敬畏和乡村的“大义”。
不同家庭、宗族分支的不睦、矛盾乃至仇恨,有了一个缓冲和化解的场所,很多时候,这也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表演”,而是一种可替代法律诉讼的实质仲裁。其存在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据说,现在中国的村庄以每天七八十个的速度消失,或者说突变为面貌奇怪的城市。而与此同时,究竟何为城市?城市应该如何建设?人们却并没有搞清楚。历史就这样,在几笔糊涂账和机器轰鸣声中走向双重破坏。
现在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指出一条令人信服的道路,可能尚为困难。不过可能首先要做的是心存敬畏,平静反思。否则那些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们,迟早将会疲惫地发现,自己成了飘荡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听弹琴
刘长卿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1诗题一作“弹琴”。2泠泠:洋溢貌。3七弦:古琴有七条弦,故称七弦琴。4松风寒:松风,琴曲名,指《风入松》曲。寒:凄清的意思。
七弦琴上弹奏出清幽的琴声,静静地听就像寒风吹入松林那样凄清。虽然我十分喜爱古老的曲调,但现在的人弹奏的不多了。
刘长卿(709—780),字文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大历中,官至鄂岳转运留后,为观察使诬奏,系姑苏狱,后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
刘长卿“以诗驰名上元、宝应间”(《唐诗纪事》)。他的诗多写贬谪飘流的感慨和山水隐逸的闲情。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称为“五言长城”。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炼,接近王孟一派。
刘长卿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
长卿的五言排律今存53首,占总数的10%。五言排律在初盛唐可谓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在此背景下,长卿的五排能够独辟蹊径,虽不能与盛唐诸家阔大的气势、奔放的节奏和高亢的声调争胜,但在思想的深邃、语言的流畅等方面则又大胜往昔。
这是一首借咏古调的冷落,不为人所重视,来抒发怀才不遇,世少知音的小诗。前两句描摹音乐境界,后两句抒发情怀。全诗从对琴声的赞美,转而对时尚慨叹,流露了诗人孤高自赏,不同凡俗,稀有知音的情操。
诗题一作“弹琴”(《刘随州集》)。从诗中“静听”二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
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由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作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泠泠”形容琴声的清越,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情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换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穆如松风的琴声虽美,如今毕竟成了“古调”,又有几人能怀着高雅情致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字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进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者的稀少。有人以此二句谓今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清才冠世,一生两遭迁斥,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他的集中有《幽琴》(《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之一)诗曰:“月色满轩白,琴声宜夜阑。飗飗青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其中四句就是这首听琴绝句。“所贵知音难”也正是诗的题旨之所在。“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咏听琴,只不过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地位最崇高的乐器。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古代每个文人的必修之器,即便不擅也必悬一二张于书斋。历史上的著名琴家有孔子、司马相如、蔡文姬、李白、杜甫、宋徽宗……
古琴自一出世便中年已过,一派尘埃落定的沉稳,那是儒家的气质。别的乐器是声,而古琴是韵。它是一种主语状态的情绪,向内的,在最僻静处完成它的寂寞。“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琴道便是它的在野情怀。古琴的声形气韵清高纯古:泛音的轻灵清越,散音的沉着浑厚,按音的舒缓凝重,那指法,真正是蕴藉典雅、润匀透静,一如中国画的水墨烟云。
古人层层叠叠的指纹堆积如落叶,使我终于不敢落指。每一落指都是曾经,感觉不是弹在弦上,而是摸在前人的指尖上。不知它是否也想念着久别的手指,不知谁又是它梦中的手指?正是“挽断罗衣留不住”,人已去,而他或她生前用过的琴却坚持着。被岁月还回来,但终于还是又拿走了。从此便惦着它,再也放不下来
我不过是一个路过古代的人。
我只能把古琴的古归还古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李白有一首《山中与幽人对酌》,明白流畅,情致盎然: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由此看来,这诗中字句定是受了他癫狂饮酒与无弦瑶琴的启发。
放旷如李白,也要从《桃花源记》中寻找灵感慰藉,以觅知音。雅兴忽来诗下酒,来来来,子当为我弹琴,我当为子高歌。纵使弹断七弦无人听,也要借昔年之酒,消心中块垒。
醉时无烦无恼无牵无挂,又何必非要醒着。在这离乱的世间,醒时似醉,醉时方醒。或是如他半醉半醒,半癫半狂一般,方是入了化境,于心中自有大光明。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刘长卿《弹琴》
古调虽好,只是如今这世界尘嚣日上,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世间定是无人肯弹的了。然而琴依旧,酒依旧,菊花不曾坠北风,他却已翩然而去。
只留一柱清香,半卷残文,山水杳杳,待你来寻。
古体诗词,这种近乎死亡的艺术,在当今铺天盖地的风雅小品、官样文章面前,岂不同样尴尬?“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不过,这样也好。清静。现在,是我最需要清静的时候。知音不必多,有三五个,足够了;读者何求繁?有七八人,不少啦。
在一百年前,中国人但说琴,指的就是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最古老也最受推崇的乐器,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件瑰宝。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无不爱琴,隋朝甚至将能否操琴定为天下取士的一个标准。而如今,许多国人是从**《孔子》中才第一次见到古琴、听到琴音的。尽管唐刘长卿曾叹“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然近代以来古琴竟然式微到国人完全不识、有文化者都琴筝不分的程度,令人心惊!虽然2003年11月古琴艺术已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诗人刘长卿曾在《弹琴》一诗中哀叹: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1977年8月22日,美国宇宙飞船“旅行者”号发射的时候,随船有张代表地球的金碟唱片,收录的二十七首曲目中有一首便是管平湖弹奏的《流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著名古琴演奏家、广陵派传人陈雷激端坐于"画卷"之上,扬手抚琴,以纯熟的琴技、和雅的气质,让全世界第一次同时聆听中国最古老的古琴音乐!
吟诵着“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这样的句子,厌倦了城市的喧嚣,钟情于在大自然中心灵的释放。带着相机,用心去品尝人世间喜、怒、哀、乐、怨、恨、愁的百般姿态;用第三只眼睛记录普天下奇、雄、峻、险、真、善、美万种风情。踏上旅程,专注于旅途中历史、文化及思想的碰撞,从更深的层面去感悟世界。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感慨世事与人心的变化,人心不古。他以此来讽刺今人不如古人高尚,大有知音难觅的感觉,实际上也有“曲高和寡 ”的问题。
距离造成的美感往往在审美鉴赏上固执地表现出来。白居易《问杨琼》谓“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刘长卿《听弹琴》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便是因时间距离久远所造成的美感,并非他们所处的唐代缺少佳歌妙曲,碍于近视罢了;而我辈隔着千余年看唐代歌、曲,又觉得那般典雅高逸,不可多得了,盖距离使我们思维空间疏朗,触发想象,而想象的沉浮往往过滤实际的功用,显露新的感知和体验,并以此为媒介,使审美心灵自由而充实。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只有诗能经得起时间风雨的侵蚀,保持着永不消褪的绿色。中国的唐诗,一千多年来一直震撼着中华儿女的心灵,而且必将万古长青,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